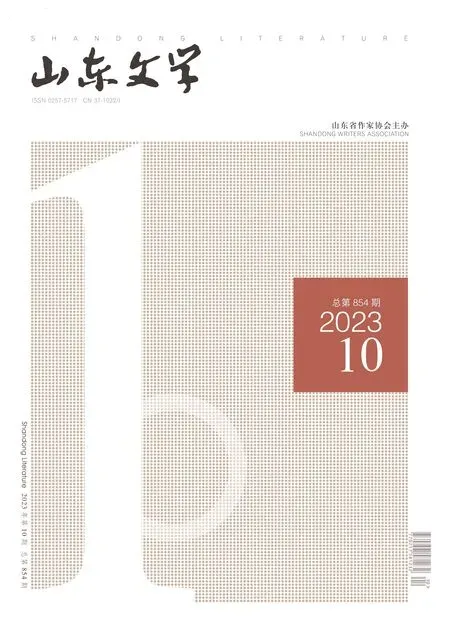祖母爱讲笑话
王海滨
1
订婚后不久的一天,有人说那个人要从村中经过,祖母急忙拽了最小的妹妹跑到街口去观瞧。等赶到的时候,那人已经穿街而过,只看见一个穿着白洋布长衫的颀长背影。这个背影让祖母从此心安:个头不低,不瘸不拐;穿洋布衣衫证明家底的确不虚,且一袭白,贩夫走卒是穿不出来的。
半年后,祖母坐上披红挂彩的八抬大轿,一路上吹吹打打,好不热闹。三姨祖母回忆说,当年她和祖母挤在轿内,可能因为空间狭小,祖母的脸一直红红的,喘着粗气。等到听到外面鞭炮齐鸣,传来一声高喊“落——轿——”不见轿帘掀起,却见伸进一双戴着绞丝银镯子的肥胖白嫩的手,摸索着攥住了祖母的小脚,前前后后摸了一个遍,才倏地缩回去,嘴里发出咯咯的笑声:
“好,好,缠得好……能生能养……”
我们家族是大家族,曾经很是殷实富足。据说,徒步穿越我们家的枣园,整整要走一顿饭的时间,迄今家中祖坟所在地还在邻村后面——也就是说,这个邻村是在我们家当年的地界上发展起来的;而且人丁兴旺。曾祖母一生养育五子,生五祖父的时候,父亲已经两岁,他从小就很照顾这个小叔叔。
母亲回忆说,她进门的时候一大家子还都住在一套占地面积大约有四五百平米的四合院里,曾祖父母携五祖父住三间北屋,祖母和父亲姑姑住两间南屋,其他几位祖父携家带口分住东西几间厢房。祖母住过的那个房子后来成了三奶奶家的柴房,在我的印象里头有一扇门一个窗户,矮小破败。
每到大年初一,晨光微露,堂屋里守岁的气死风灯还未熄灭,祖父就带着几个兄弟去北屋磕头,然后是祖母带着几个妯娌去磕头,父亲长大以后,开始带着他的几个叔伯兄弟次第去磕头,我隐隐约约记得自己也去磕过头,磕完头,曾祖母会从屁股后面的紫红色小坛子里取出几颗醉枣塞进我手心里。她晚年在我们家生活过,和祖母一个房间,一个里屋一个外屋,天天让祖母给她准备热水洗脚。到月底,她会站在院子中间,一见父亲下班回来,就颤颤巍巍地喊:
“清升,给我剪剪脚。”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们村开始设立市集,为了补贴家用,祖母带着几个妯娌们卖馍馍——在四合院中垒起锅灶,一起蒸一起用篮子提着赶集去叫卖。
有一年闹饥荒,祖母辛辛苦苦从娘家背回来一袋地瓜干,明明就放在南屋的粮柜里,可出门捡拾柴火的空当不翼而飞。祖母就站到了南屋房顶上“骂街”——农村的“骂街”大致分两种:一种是荤骂,满口脏字,一种是净骂,也就是哭诉,祖母属于后者,她迎风站在那里,扯开嗓子哭孤儿寡母的不容易,哭她去娘家讨来口粮的辛苦……
第二天早上,那袋地瓜干又出现在屋门口,只是瘪下去一半。
2
听说,祖父爱穿白色洋布长衫,步速很快,说话爱引经据典,语速也快。倘若没有得病,他大概一直会在村里教书。
有一天,和几个年轻乡邻说笑闲聊,其中一人开玩笑似的捶打了一下他的左胸,当时无碍,但不久后捶打之处开始胀痛,慢慢开始腐烂。祖母把白洋布长衫撕扯成条状,团成团填塞进腐烂处,一天一换。替换下来的洋布条先清洗,再用滚烫的热水消毒,然后一一展开晾晒在小院里,有风吹过,洋布条飘飘扬扬翻动,搅动着一股股恶臭弥漫,晚辈们都捂鼻掩面快速进出。
曾祖父母吩咐其他几个儿子赶着驴车载着祖父遍寻名医,但就是没治好。三年后,烂至胸口,32岁生日刚过的祖父闭上了眼睛。
那一年,父亲12 岁,大姑母9 岁,小姑母一岁半,还有一个孩子在祖母的肚子里,才几个月。
因为怕阴宅冲撞了肚子里的孩子,祖母没能去给祖父送葬。不过,这个孩子并没留住,那年年关,祖母去磨房磨面,推着推着磨杠,腹中的孩子流产在磨道里了。
也是个男孩。
……
转眼来年春天,曾祖母要过生日。这是一个很隆重的日子,来了很多亲戚,北房里摆放了三张八仙桌——有两张是特意借的。身为长房长媳的祖母里外张罗,脚不沾地。她还吩咐父亲去大门外照看亲戚们坐车来时使唤的牲口;转头发现还少两个海碗,就急忙差遣大姑姑再去邻居家借。就在这个空当,我那个叫小嫚的小姑母睡醒了爬下炕来,爬到院子中那口大铁锅前,锅里是宴席最后一道汤菜——白菜粉条炖豆腐,应该是那锅汤菜的味道吸引了她,她伸出小手想去抓锅沿,大概是想借力站起来看看锅里到底是什么,于是,铁锅反扣了过来。
小嫚姑母在炕上倒了三天。抱不得,一触碰就会掉皮。大面积的烫伤引发感染导致她全身器官衰竭而亡。
有一年除夕,家人们围炉闲聊说到旧事,我问父亲为什么祖母自己当年没有再嫁呢?八十岁的父亲一恍惚,继而好像很不好意思,喃喃地说了句:
“那个时候,嗨——”
他抖抖索索地站起身来,走到阳台上去抽烟,烟雾一时缭绕。
父亲的话一下子让我想到了二姨祖母,她28 岁守寡,也一直独居。
3
有一年,祖母突然双眼失明。
怎么会眼瞎呢?因为一口袋玉米。
父亲十九岁时到县师范读书,没钱交学费,就用粮食代替。那次从家带了一口袋玉米去学校,口袋捆绑得不结实,路上几乎全撒落了。消息传到家中,祖母急火攻心双眼就看不见了。两位舅祖父听说后赶来用三轮车推着她,步行六十里找到一位名医,才得以及时救治。
一直到我成年,才知道父亲为了上学还曾离过婚:他在18 岁那年迎娶了二祖母娘家村里一位姓郭的高个子姑娘,第二年他却要去读书,全家老少都不同意,郭姓母亲更是为此寻死觅活,最后干脆跑回了娘家。她在娘家没有等来父亲放弃学业在家老老实实过日子的允诺,等来的却是一张休书。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农村,离婚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何况像父亲这种情况,多亏了一大家子的多方帮衬,才能顺顺利利把婚结成,居然还敢提出离婚!
出乎所有人意料,也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曾祖父母、诸位兄弟妯娌轮番上阵,走马灯一样在南屋出出进进,叱责、质疑、命令、要挟……到了第四天,两个舅祖父也赶来劝阻。但是,最终父亲还是把婚离了,因为祖母支持。
父亲读书快毕业的时候,姑母也考上了这所师范院校,依然遭到了一大家子人的反对,最后是因为得到祖母坚定地支持而付诸实施。
当年祖母是怎么支撑儿女学费的呢?问过父亲和姑母,都只说太不容易了,再详细的内容就只有叹息……
祖父这一辈兄弟五人,各自开枝散叶生儿育女,呼呼啦啦好不热闹,到现在全族人口已不下六七十,但独有我们这一支脉彻底走出了那个小村庄。
师范里有位姓孟的老师特别赏识父亲。多年来和我们家走动频繁,每逢春节,都要来家里给祖母拜年,来了坐一坐 说些由衷问候的话,走时会再三叮嘱祖母:
“那么不容易都过来了,现在可得要好好享福啊……”
4
我曾经为外祖母写过一篇文章,一气呵成,并很快见诸一国内大刊。但是当我想为祖母也写篇文章的时候却历经五年之久,写成后几经修改,相熟的一位编辑还是委婉地告知离发表尚有差距。痛定思痛,才发现根本原因是祖母和外祖母在心里的分量不一样:不能说不爱祖母,只能说没有那么深,对她的爱可能仅仅是血缘维系,在我成年后对她的怀念仅仅停留在诸多的不解上。在整个少年时期,我其实是很厌恶祖母的。不仅仅是我,我的小姐姐也是如此,所谓哺育之恩,祖母没有给我们,自然也就缺少了某种深切的情感纽带。我一直想落笔写出一个普通中国农村女性的生命轨迹,却忽略了她还是我的祖母。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因为她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中是缺失的。
姑母比母亲长一岁,她在师范上学的时候,母亲曾无私地把微薄的工资拿出来予以资助,姑嫂婆媳也有过几年短暂的其乐融融。她们交恶是因为一辆自行车:姑母新婚,姑父送她一辆自行车,她却用不上,就想转售他人。父亲当时在异地上班,来回正需要一辆自行车,母亲就希望姑母折价卖给自己,不料却遭到拒绝。母亲想不通,于是两人当着祖母的面发生口角,祖母立场鲜明地偏袒姑母,甚至扬手打了母亲一个耳光;几年后,我的三姐和姑母家的大表姐相差几天出生,祖母毅然决然地抛下孙女不管去照顾大表姐,这让母亲愤怒到极点,婆媳关系彻底走向低谷。
祖母一手带大大表姐后,又义无反顾地一手带大了大表哥和表弟,三姐和我则由我的外祖母带大。所以,我小时候对祖母的印象并不是很深刻,只记得她偶尔会回来住几天,大部分时间,只有去姑母家才能见到祖母。
在我们家,有两个人和祖母的关系始终处于冰点,一个是母亲,她从不不主动和祖母说话,即便祖母主动搭讪,也是淡然处之;而且,婆媳大战频频爆发,愁得父亲借烟浇愁,家里整天乌烟瘴气;印象中有一次,祖母牵着我在大街上看一个小贩卖小金鱼,那个小贩笑嘻嘻逗弄说我长得瘦弱像个小姑娘,祖母开心地笑起来。回到家向众人转述小贩的话,引得姐姐们也笑,我则大哭,母亲在屋内听闻后摔门帘出来没好气地借题发挥说起了不好听的话,弄得祖母十分尴尬。
另一个就是我最小的姐姐,凡是祖母经手的事情,她总挑不是,例如,对祖母做的饭菜,不是说淡就是说咸,不咸不淡就说油少,三天两头和祖母找茬耍脾气。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祖母在我们家应该很不快乐。不过,一直到她生病之前,我都不知道她在姑母家其实也不快乐。
每次去姑母家,都看见祖母在厨房里灰头土脸地忙得不亦乐乎,要不就是歪躺在院子中一大摊棉花上,戴着一个用绳当腿套在头上的老花镜,穿针走线地做被子、褥子、棉袄棉裤——祖母去世多年后,我去参加大表姐儿子的婚事,看着新房里摆放的好几床新被子,大表姐说那都是祖母做的。
祖母对姑母家倾注了全部的爱,为那个家立下了汗马功劳,但随着孩子们的长大成人,她的发言权越来越少,地位也越来越微乎其微。是什么原因让她和姑父反目呢?我到现在也不知道——祖母从没有透露过。最为不解的是,每当战火燃起,姑母都会率领孩子们毅然决然地站到姑父的立场上。
记得有一次我奉命去看望祖母,恰好碰上他们闹矛盾,姑父一脸憋屈的样子,青筋暴露,拍打着胸脯喊:
“这是我家啊,有这样的吗?……”
祖母哪样了?不得而知。
祖母就哭哭啼啼地收拾好东西回到我们家来,但最多一个月,就又主动回去。
应该是在60 岁以后,祖母在我们家居住的时间才长起来。但每年春秋时节,她还是坚持要去姑母家住上十天半个月,缝缝补补拆拆洗洗,所以每次回来都累得疲惫不堪,父亲心疼地长吁短叹,生怕祖母累出好歹。母亲就私下里去质问祖母:
“能疼一下你儿子吗?能不去吗?”
祖母转头就对着父亲流泪,父亲的心情就更糟糕,晚上就训斥母亲,于是硝烟又起……
69 岁那年春天,祖母从姑母家回来就病了,卧床半月有余才渐渐康复。恰好姑母来看望,母亲直言不讳地说了几句抱怨的话,因为句句是实情,姑母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倒是祖母不高兴了,回怼起母亲,于是,陈谷子烂芝麻地三人又闹起来。最后,祖母收拾包袱跟姑母走了,谁知,第二天,不知何故却被姑父赶出了家门。
无处可去的祖母在中途一个杨树林里哭了整整一宿,第二天就中风了。
中风后的祖母马上被父亲接了回来。经过诊治和我们的精心照料,半年后康复,除去走路不再像以往那样利索,看不出其他什么异样。转眼到了第二年秋天,祖母死活要再去姑母家小住,父亲拗不过——母亲干脆不管不问,因为她知道阻拦是没有意义的,反而会落下抱怨。祖母去姑母家不到一周,再次中风,父亲心急火燎地赶过去,质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姑母抽抽搭搭遮遮掩掩地说,祖母夜里从床上掉了下来。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来,自从祖母去世后 我的表姐和两个表兄弟从没去给祖母扫过墓。
5
祖母兄妹五人,她排老大,下面两个弟弟两个妹妹。
父亲在祖母的娘家有个小名叫老虎。王老虎在那个小村子里人尽皆知,因为他为姥娘门上操碎了心,尤其是对两个娘舅,大小事宜,从买便宜化肥农药到盖房子娶媳妇,能帮必帮,尽心尽力——这诸多事情都是经过祖母转达给父亲,母亲为此很不悦,不止一次质问祖母知道求人办事多么难吗?祖母垂着眼皮不说话,待母亲转身离开,才嘟囔说:
“没有他俩舅,有现在吗?忘本了!”
父亲应该是牢牢记着这句话,每每帮忙都是义无反顾。
这让祖母在娘家很有威望,极有发言权。四个侄子六个侄女的婚姻大事一度都是祖母拍板定夺,他们新婚的喜被一定是祖母扎下第一针亲手缝制。
祖母在身体康健的时候,每到农忙时节,都一定回娘家帮忙。好在两个兄弟住前后院,她忙完前院再忙后院,一秋下来,虽然人会消瘦许多,但侄子侄女们一口一个“大姑”的叫着,让老太太的精神状态特别好。
在祖母卧床两年后的夏天,她乡下的一个侄子来看望,提出要接她回乡下去住几天,权当散散心。祖母也强烈要求同去,父亲也就同意,但总归是不放心,一星期后又采购了一些日用生活用品还有瓜果蔬菜,派我送回去。
夏天的午后,二舅祖父一家应该都在午睡,农家小院里很安静,我正琢磨祖母住在哪间房里,却听到西厢房有动静,走过去一看,一下子泪奔:房门口挡着门板,地面铺了一张炕席,听到动静,蜷缩在炕席上的祖母抖抖索索地竖起头来,瞪着目光浑浊的眼睛,努力向门外搜索,嘴里发出呻吟:
“我想喝口水啊……”
6
我姐弟四人中属大姐的性格最豁达和开朗,且富有幽默细胞,任何场合,只要她在,一定笑语不断。大姐说自己的性格影响于祖母——她一岁不到就被送回到祖母身边,一直长到五岁,是性格形成的最主要时期,从生理学角度来讲她所说不虚。
祖母中风在床后,父亲经常请一位叫齐凌元的大夫给她看病,她私下称呼齐大夫为“齐汤元”,每次人家来之前,她都要一本正经地嘟囔:
“又要吃汤圆了。”
她的表情、语调惹得我们大笑到齐大夫进门。
那时候,大姐已经结婚生子,有时会把她的孩子带到祖母床前,祖母会翻过来覆过去地含混不清地讲一个叫胡闹的笑话,逗的那个一岁多的小人笑个不停。我隐约记得这个笑话小时候也曾听祖母讲过,的确十分好笑,但总听也就乏味,而她自己却总是讲着讲着就笑得流出眼泪。
祖母一直爱干净,黑黑的头发很浓密,在脑后梳成一个发髻,永远纹丝不乱,身段身形保持得也很好,脚底的千层底布鞋,鞋面乌黑,鞋帮洁白——为了保持这种洁白,老太太都是用粉笔涂抹鞋帮,一双鞋永远面是面底是底。待中风以后,虽然已力不从心,她还是努力保持这种干净。
但是从乡下回来以后,祖母的病情就开始日渐加重,某天醒来后,右半边身子不能自如动弹,开始由我们喂食,尽管每次吃饭都戴上大围兜,衣服上还是溅满汤渍和油渍;头发不能再梳拢成髻,只好铰短,先是齐耳,再后来就成了寸头。
从那开始,祖母再也没嘟囔着回老家看看。
又过了一年多时间,祖母大小便开始失禁。最为头疼的是一不留神,她就把手伸向排便盆,搅和抓弄,弄得衣服被褥上到处都是,母亲一边收拾一边更是没好气地训斥……
有天大清早,父亲居然发现祖母正在往嘴里填一坨排泄物……
可喜的是,经过诊治,祖母能迈步行走了。只是她不再注意自己的形象,天气好的时候,我们把她搀出来晒太阳,明明给她系好了衣扣,转头不知怎么就被解开了,袒胸露腹,告诉她不能这样,她似乎听见又似乎听不见,脸上挂着神秘兮兮的笑,一回两回三回,再往后,只要不是冷天气,也就没有人再关注她的衣衫不整,听之任之。
祖母病重的最后两年我已经在异地工作,每逢我回家探望,有时祖母会瞪着昏花的双眼很淡漠地看我,仿佛不认识,有时则会露出一丝讨好的笑,还会抽抽嗒嗒地哭,像个小孩子,可怜巴巴的样子。
我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刚刚推门站到院子里,祖母好像有感应一样从她的房间挪出来了,花白的短发,像深秋的枯草肆意蓬松,两手提着裤子,敞着怀,周身散发着一股不好闻的味道,漠然地看看我的女朋友,又看看我,然后靠近一些,小心翼翼含混不清地问我:
“这是你媳妇儿吗?”
我点点头,祖母就转身慢慢地回房间去了。
7
确切地说,我是看了电视剧《大宅门》才动了给祖母写篇文章的念头,剧中有一个情节在我的生活中真实地上演。
曾祖母很长寿,在祖母被病痛折磨的时候,她还活得健健康康,每天拄着拐杖,迈着三寸金莲到村头看河水东流。她在九十六岁寿终正寝,守孝人员过百,送葬的队伍里有几个晚辈头戴红帽——五代同堂的人去世算“喜丧”,最小的子孙辈不戴孝帽而是戴红帽,这是我们鲁西北的风俗。
我恰好被派遣到北京出差,来不及回家奔丧,等到出差一结束,就急忙往家赶,到家那天曾祖母刚出完殡。我提着从北京特意买的稻香村点心推开院门,迎面看见母亲从祖母的房间里惊慌失措地奔出来,冲着站在院子里的父亲失声喊:
“咱妈不行了!”
母亲已经几十年没有这样称呼过祖母了,以至我一开始都没有反应过来,母亲嘴里的妈是谁。等到母亲瞥见了我,又补充了一句“你奶奶不行了”,我这才恍然,手里的点心盒子一下子扔在了地上,快步跑进屋,看见我的祖母闭着眼歪着头神色安详地倚靠在一垛被褥上,嘴角流淌着大米粥:
“第一口饭还吃得好好的,第二口就不进了……”
老家刚刚拆卸下来的灵棚又连夜搭了起来。
祖母叫什么?
王葛氏,王是夫家姓,葛是娘家姓,氏代表女性。
父亲和姑母都不记得祖母的名字。
知道祖母名字的那一辈人也都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