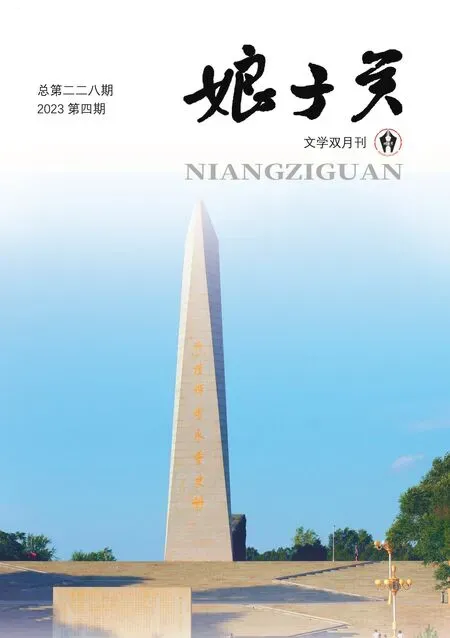“五四”后“狂飙”文学的沉浮与命运
——论高长虹的小说创作及其他
◇段崇轩
猛士“狂飙歌”
1924 年,26 岁的山西青年高长虹,揣着新出版的油印《狂飙》杂志,闯荡北京。此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然过去五年,一个更为复杂多变的“后五四”时代逐渐展开。高长虹是新文化、新文学“武装”起来的青年,他先到北京、后赴上海,就是要掀起一场如火如荼的“狂飙运动”,推行思想、艺术、科学的革命。在新的社会、时代面前,他的运动、文学难免艰难、受挫。此后在社会一系列的剧变中,他依然坚守着“五四”思想与精神,虽有变化但未能脱胎换骨,因此换来的就是挫折、悲剧了。“五四”文化就像自然界的月亮、太阳,作用于高长虹以及无数知识分子的精神,形成一波一波的潮汐。
几十年来,对高长虹的认识、评价,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翻转。从“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青年作者”[鲁迅:《奔月》注释,《鲁迅全集》(第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9页。],“一个自我膨胀的自命的尼采式英雄”[彭安定:《论鲁迅与高长虹》,《晋阳学刊》1986 年第6期。],到与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等可以比肩的“一位杰出的有才能的作家”[董大中:《狂飙社纪事》,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 年版,第1 页。],“一个赤诚爱国而又特立独行的人”[廖久明:《高长虹年谱·序》,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1 页。],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似乎还是绝无仅有的。学者董大中、廖久明、阎继经、陈漱渝等,在搜集资料、编选文集、考证历史、辨析史实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建树可观。但在深入、系统地解读、研究作家作品方面,还有许多课题有待去做。
高长虹短短56年的生命,可以划分成五个阶段。“叛逆时期”。他1898年生于山西省盂县清城镇西沟村一个书香之家。1914 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各科成绩俱佳,尤以国文、英语突出。同年遵父母之命,与邻村王巧弟结婚。1915 年袁世凯预谋称帝,阎锡山操纵学界政界开提灯会劝进。高长虹不仅不参加,还写了一首《提灯行》诗进行讽刺,因此遭到校方迫害,逃回村里。1916 年独身赴京,在一家亲戚的相助下,在北京图书馆读书,在北京大学旁听、自学,后又回家苦读。此时新文化运动兴起,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特别是西方的文学名著。1921年开始在《晨报》《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等报刊,发表诗歌、评论与翻译作品。在《国风日报》“学汇”副刊发表的《反诗》曰:“就像块无限大的岩石,政府压在我们的头上,压得我们气息恹恹,更没有一丝儿挣扎的力量!”“狂飙时期”。1924 年高长虹约集高沐鸿、段复生、荫雨、藉雨农以及二弟高歌共六人,在太原成立“平民艺术团”,创办《狂飙》月刊。不久后单身赴京。二个月后《狂飙》周刊附属在《国风日报》问世。同年与鲁迅相识,得到指导、扶助。1925 年周刊停办后,参加鲁迅发起组织的莽原社,成为《莽原》周刊的主要编辑,鲁迅给许广平信中称:长虹“是我今年新认识的。意见也有一部分和我相合……他很能做文章……”[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62 页。]又说:《莽原》周刊“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0页。]同时还与人创办《弦上》周刊。1926 年高长虹移师上海,恢复《狂飙》周刊,新办《长虹》周刊。开展狂飙演剧运动。在五年多时间中,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评论、小说作品,在北京、上海引发广泛影响。他与鲁迅的关系,则由师生、“战友”而变成论敌、“情敌”。“游历时期”。1930年春高长虹东渡日本,直到1938年回国,在漫长岁月里,他由日本到德国、法国、荷兰、瑞士、英国等许多国家。他过着几乎是饥寒交迫的流浪生活,但却关注着国内国际形势,创办报纸,参加“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研究行动科学、抗日问题,创作诗歌、杂文,还有两部长篇小说。“抗战时期”。1938年,抗战全面爆发,高长虹急切回到中国,经潘汉年介绍,奔赴武汉进入全国“文协”,又到重庆,参加“文协”组织的各种文学活动,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评论。1941 年徒步去延安,受到革命根据地高规格欢迎,成为“文协”驻会作家。有几件事显出他与根据地的格格不入。边区文协召开理事会,推举他为文协副主任,他却推辞不受。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他受到邀请,却成为惟一的缺席代表。1946 年,高长虹先到晋绥,后转哈尔滨,再赴沈阳,住在东北旅社,1954 年春突发脑溢血去世,结束了寂寞的残生。
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行为,什么样的文学创作。高长虹的思想构成是开放的、庞杂的、现代的;当然也是矛盾、不成熟的。作为青年知识分子,他几乎全盘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思想。什么是“五四”精神?王元化说:“‘五四’的个性解放精神、人道精神、独立精神、自由精神,都是极可贵的思想遗产,是我们应当坚守的文化信念。”[王元化:《再谈五四》,《思辨随笔》,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 年版,第13 页。]高长虹在这些方面,比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接受更为全面、激进。在这一思想谱系下,他汲取了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思想与精神。代表作家歌德、席勒的作品,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狂飙突进运动”主张“自由”“个性解放”,歌颂“天才”,提出“返回自然”的口号,都成为高长虹开展“狂飙运动”的思想圭臬。他在《狂飙周刊宣言》中称:“是啊,我们要起来了,我们呼唤着,使一切不安于期待的人们也起来罢。”“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的始流,一张树叶之飘动可以兆暴风之将来,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周刊,便叫作《狂飙》。”[高长虹:《〈狂飙〉周刊宣言》,《高长虹全集》(第三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超人哲学”,与德国“狂飙突进运动”都是一脉相承的,也受到高长虹的尊崇,同时成为他文学运动与文学创作的思想资源。因此董大中认为:“高长虹所提倡的‘狂飙运动’是歌德‘狂飙突进运动’的中国版。”[董大中:《狂飙社纪事》,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关于无政府主义,鲁迅曾称高长虹为“安那其主义者”,但有论者认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他并不绝对地反对政府,只是反对腐败的、无能的政府;他也没有同无政府主义者和团体有过关系。然而,无政府主义思潮中倡导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强烈的“乌托邦”理念,确实影响了高长虹的思想,他的文学理论文章《近代艺术与无政府主义》,就论述了现代文学艺术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密切关系,显示了无政府主义在他思想谱系中占有的位置。在文学思想观念方面,他厚今薄古、重西轻中。他有较好的古典文学素养,特别是诗歌、小说;他认为中国古典文学源远流长,有很多优秀作家作品;但对古典文学中脱离时代、吟风弄月的倾向,作了尖锐批评。他谙熟新文学,对鲁迅等一批作家作品作了充分肯定、评价,但也用严苛的态度与尺度,对新文学中他认为保守、落后的作家作品进行批评。他对世界文学有着广泛的涉猎、评判,认为西方文学特别是德国、俄罗斯文学,代表了文学发展的高度。他认为中国文学应该向西方文学借鉴、学习,特别是西方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文学,努力使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中的一部分。他的一系列思想观念,虽然粗糙庞杂、甚而自相矛盾,但它确实表现了“五四”新文学的无限生机、活力和壮大。
高长虹是一个创作潜力丰沛,写作才能多样,作品数量庞大的作家。他几乎是文学的全能选手,各种文体都能驾驭,均有代表性作品。诗歌集辑的有:《精神与爱的女神》《闪光》《给——》《献给自然的女儿》;散文随笔集辑的有:《心的探险》《光与热》《草书纪年》;政论时评集辑的有:《政治的新生》《延安集》;文学评论集辑的有:《时代的先驱》《走到出版界》《集外集》;戏剧集辑的有:《小剧场》;小说集辑的有:《曙》《实生活》《青白》《游离》《春天的人们》《神仙世界》。总共约20种。201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高长虹全集》,共四卷,总字数176 万,未能搜集、收入的作品一定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是,如上作品集,只是以某一种文体为主,有时会混入少量别的文体作品。而在高长虹的创作中,散文与小说,时评与评论等,常常是混淆难分的,并无分明界限,它体现了高长虹创作中的自由状态,也反映了“五四”时期文学文体上的模糊、宽松。
吴福辉在《我读高长虹的小说》中说:“最能表明他的文学价值和精神价值的作品,恐怕是散文诗、诗和杂感批评,然后才是小说。”[吴福辉:《我读高长虹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1期。]这一观点有道理,但不准确。小说在高长虹的创作中是极为重要的,作家本人格外看重的,其思想艺术上的创新,并不弱于他的诗歌、散文。美国作家弗兰克·诺里斯说:“我们的时代,是小说的时代。无论在哪一种艺术中,时代生活从来也没有得到如此充分的表现。”[[美]弗兰克·诺里斯:《小说家的责任》,崔道怡等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上册),工人出版社1987 年版,第35 页。]小说不仅能充分表现时代,也能充分表现作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解读、评价高长虹的小说就是十分必要的了。他一生创作有14 篇短篇小说、3 部中篇小说、1 部长篇小说,共25 部(篇)。1931 年曾有报道说:高长虹在日本创作一部长篇巨制,已完成70 余万字,但却毫无踪影。1934 年高长虹在巴黎创作一部名为《中国》的长篇小说,但现在看到的只是连载于法国报纸上的法文片段。读高长虹的小说,确实可以看到一幅更逼真、丰富的时代图画,看到一个更幽深、独特的作家精神世界,感到“五四”时代作家对现代小说“狂飙式”的追求,这是读他的诗歌、散文难以领略到的。
论述高长虹,回避不了他与鲁迅的矛盾冲突。二人交恶有三个诱因:一是莽原社对狂飙社的“退稿事件”,二是关于鲁迅“思想界之权威者”的评价分歧,三是围绕许广平的“月亮之争”风波。这些都是导致高长虹长期被“污名化”的历史事件和根源。新时期文学以来,董大中、廖久明等发掘资料、精心辨析,终于弄清了高鲁冲突的来龙去脉、症结所在,还高长虹和鲁迅以“清白”。我们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是高鲁二人过于敏感,发生误会。而高是一个桀骜不驯、无视权威的人。责任最先在作为晚辈的高长虹;其次是文学阵营中的人有门户之见,作为“安徽帮”的作家为了小团体的利益,在鲁迅那里进行了挑拨离间;最后是高长虹以及“狂飙社”成员,同鲁迅在文学思想与观念上的不同,加剧了他们与鲁迅以及周作人的矛盾冲突。明白这些,有助于我们更深切地理解高长虹的文学作品。
革命的“变奏曲”
20 世纪20 年代中后期,进入“后五四”时代。直到30年代,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国民革命、军阀混战、苏维埃壮大、抗战开始。在这样的历史大变局中,文化、文学也在艰难地探索、转向。新文学社团不断涌现,新文学阵营开始分化;“五四”新文学逐渐被“革命文学”乃至“无产阶级文学”所替代,30 年代之后则是“抗战文学”的勃起。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26 年高长虹与他的“狂飙社”由北京转移上海,复刊《狂飙》周刊,成立狂飙出版部,与人创办《世界》周刊。在《狂飙周刊的开始》发刊词中,称:“我们以为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有科学与艺术便生存,没有科学艺术便灭亡。……我们的重要的工作在建设科学艺术,在用科学批评思想。因为目前不得已的缘故,我们次要的工作在用新的思想批评旧的思想,在介绍欧洲较进步的科学艺术到中国来。”[高长虹:《〈狂飙〉周刊的开始》,《高长虹全集》(第三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页。]与一年半以前北京《狂飙》宣言相比,这份发刊词显然少了气势,但主旨是相同的,即进行科学、艺术、思想上的变革与建设,引进西方的现代科学与文化。秉承的依然是“五四”思想与精神,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和目标。高长虹的思想与实践并没有错,甚至可以说是美好而有意义的,但又分明与时代的主流“游离”了,是一种主观的、理想的产物。
高长虹的绝大部分小说写于1925—1929 年之间,即从北京到上海这一段时间。但他基本没有正面书写开展“狂飙运动”,创办一系列刊物,与各种势力斗争的重要事件,而是描述了他的日常生活、生平经历,以及情感、思想、精神历程,可谓革命的“变奏曲”。但从这“变奏曲”中,又可窥见风云变幻的时代面貌,洞见作家躁动幽深的灵魂世界。
“五四”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作家的小说往往是他的自叙传。高长虹同样如此。他说:“如果把我的小说看做我的自传,我宁愿他不看我的小说。在小说中找我,还不如在批评中找我较为方便。我的小说中,虽即是极像自传的描写,里边总有那最反自传的描写。”[高长虹:《小说不是自传》,《高长虹全集》(第三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年版,第352 页。]但他又在小说中通过人物之口说:“小说没有不是作者的自传的,或者说是一种广义的自传。”[高长虹:《那个人》,《高长虹全集》(第三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4 页。]其实这两段相互矛盾的话,暗含了几层意思,首先是“越盖弥彰”,不想让人们在他的小说中对号入座,引来不必要的非议。其次是认为小说确实是作家自传,但应该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广义的自传。可以说,高长虹的小说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以现代主义为追求的。在他那些自叙传小说中,表现了他对“五四”精神的继承与坚守。
《生的跃动》创作于1925年,是作家较早期的小说。此时他已身在北京,写的则是他中学毕业后在城市寻找出路的经历。其中有自传,也有虚构。作品中的主人公“他”,先在P 城谋得一份当家教的职业,一个官僚家庭、两位男女儿童,工作轻松、薪酬可观。但他厌倦这种没有活力、前途的工作,又跑到T城。在这里寄居公寓、无事可做,环境嘈杂、经济窘迫。只是偶尔到工厂里,找工人调查、聊天。在松散的情节链条中,穿插了“他”寂寞、烦躁、跃动的情感精神世界,对心中的“女神”、对爱情的渴望,辛苦写稿而稿酬太低的沮丧,在深入工厂、工人中对社会问题的发现……尽管如此,他依然鞭策自己,“固执地向着那在他面前铺开的路径上大踏步走去”。小说细腻而逼真地展现了一个“五四”时期青年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情状。《游离》以“我”为叙事人物和主人公,写1925年冬天与弟弟的故乡之行。弟弟先行回京,“我”因铁路中断困居太原,竟有二三个月。写了“我”与家庭以及亲人们的关系、感情,为不能尽儿子、丈夫、父亲的责任而有负罪感。写了“我”从事的文化文学工作的艰难,前景的黯淡;想象着怎样改换门庭去军队当兵,去科研行业搞科学研究,做一些务实的有成效的事业……此时高长虹已在北京打出一片天地,但他内心却忐忑不安,深刻地回顾、反省着自己的人生、事业。显示了高长虹心灵中最柔软的一面。中篇小说《曙》是作家1927 年下半年,在杭州养病、写作期间,给八岁的儿子高曙,写的45封信,是一部书简体小说。这是一本流水账,写自己的所经所见,自己的工作、心理,对儿子与家庭的思念、思考,完全是写实主义的。它涉及作家对革命、对中国,对新文化、新文学的思考与反省。对自己的思想观念、文学修养等资源、体系的梳理、检讨。对儿子的感情、教育、未来的深思、谋划。絮絮叨叨,情真意切,是高长虹小说中颇具自传性的一部作品。如上这些小说,近距离、多方位地展现了高长虹的奋斗历程,凸显了一个“五四”文青的独特形象。这些小说确实具有自叙传特征,因此有些高长虹研究专家,把小说中一些情节、细节,时间、地点等,当作史料使用,甚至写进年谱。事实上,正如高长虹说的“小说不是自传”、“是广义的自传”,“里面总有那最反自传的描写”,有些情节、细节,看似真实、确凿,但可能是虚构的、想象的,已经变成了艺术。这是需要慎重对待的。高长虹的自叙传小说,既坚持写实主义方法,又汲纳现代主义技巧,但有些作品中没有达到浑然一体的境界,出现了某些粗糙、生硬的现象。其中的部分主要人物“我”或“他”等,是一种纪实性、意象型人物,虽然逼真、感人,但缺乏完整感、立体感。这是需要指出的。
1926 年鲁迅说过一段话:“革命时代总要有许多文艺家萎黄,有许多文艺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乃仍被吞没,或者受伤。被吞没的消灭了;受伤的生活着,开拓着自己的生活,唱着苦痛和愉悦之歌。”[鲁迅:《马上日记之二》,《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3页。]这番话说的就像是高长虹。他有一部分小说,不是写的生平自传,而是精神自传。这部分小说情节奇特、意境神秘,形象超拔、意蕴复杂,有散文诗特征,并充分运用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等现代方法和手法。鲁迅所说“晦涩难解”,这部分作品就是典型。但只要弄清作家这一时期的情绪、心态,熟悉所运用的艺术方法的特征,还是可以破解的。笔者以为,这部分小说艺术地、深邃地体现了高长虹“五四”落潮期的孤独、悲哀、虚无的内在精神,比那些写实的自叙传小说,更富有思想和艺术价值。
《这只是一个梦》描绘了“我”走进梦中。这是一个充满平庸、愚昧、自私、内斗的世界。“我”在其中探索、劳动、建设,却受到了所有人的孤立、污蔑、驱逐。作家用梦来象征现实,表现了精英知识分子在现实和民众中的孤独感、无助感。《现实的现实》在一幅黯淡的图画中,勾勒了“我”与“他”两个剪影形象。“他”开创了一条发光的道路,踽踽独行。“我”勇敢、执着,追随“他”、学习“他”,成为“他”的影子。我们本是同道、同志,但却不能对话、不能走近,皆成为“独行者”。小说用象征主义方法,揭橥了革命者之间的隔膜、矛盾;用表现主义方法显示了独行者的寂寞、自闭。笔者以为,作家在其中蕴含了他与鲁迅的关系,他对鲁迅的尊重、愧疚之情。《震动的一环》中的意境更为奇特、阔大。“我”——一位战士,死而复生,变为鬼魂、灵魂,在浩渺宇宙、熙攘人间飘荡。“我”观察、思索着宇宙中的太阳、地球、行星、彗星,感受到宇宙的壮阔,人类的渺小。“我”搜寻、关注着人世间卧病在床的母亲,“我”所爱恋的女子,还有辛苦劳作的农民,对他们心怀感恩、怜悯。“我”愿化作一颗彗星,掠过地球,“火裂自歼”,用自己的毁灭照亮世间。作品用象征主义方法,借灵魂形象象征“五四”知识分子,用意识流手法,展现一个曾经的战士“心事浩茫连广宇”。《最后的著作》仍以“我”为主人公,告别朋友、事业、尘世,来到一座名山,静静地回顾历史、反省自己,用枪对着胸膛,用笔写下:“我们在一生的奔波之后,现在才走入一个绝地。”“让我们把绝望一同带到绝地去,而只贻我们的孩子们以希望吧!”然后开枪自杀。这是一种精神的绝望与自杀,小说充满了象征主义色彩。这四篇诗意小说,曲径通幽又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凉、孤寂、自省、绝望的心理和精神世界。与鲁迅的小说、散文有许多相通之处,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上极富创新,抵达了鲁迅所说的“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的境界。
在时代的洪流中,在文学的演进中,高长虹的小说也在变。1928 年创作的《一个兵和他自己的家里》,主人公虽然是“我”,但已变成一个受伤归乡的兵士。“我”在夜幕中感受到了到处是“荒废、寂寞、空虚”。当“我”在野外瓜田的茅屋中找到妻子、儿子时,他们却不回应“我”的呼唤,不打开自己的房门。一个为国为家赴死的兵士,却难以让亲人相认,革命者与民众之间横着深深的鸿沟。这依然是“五四”启蒙思想的体现,但作家把他的笔触转向了普通兵士、民众,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1934 年在法国创作的长篇小说《中国》,全书难以得见,学者刘志侠在巴黎的《世界周刊》上,找到了法文版小说节选章节《中国矿工》,连载两天。学者说:“读完之后,发现这不是一篇传统的短篇小说,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作者描绘中国一个煤矿村子和矿井的面貌,短小的篇幅,却出现十多个人物的名字,就像导演一面在舞台上搭建布景,一面让演员出来走过场,自报名字,预告大戏还在后头。”[刘志侠:《高长虹的欧洲岁月》,《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2期。]从这简短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高长虹的笔触,不仅转向了乡村、农民、士兵,也转向了煤矿、工人,转向了更广大的底层社会,与“革命文学”“左翼文学”靠拢了。
爱情“乌托邦”
读高长虹的人、小说,人们会感受到一个共同的、突出的主题:爱情。学者陈漱渝说:“‘我呼爱人,爱人不应’——这句话出自高长虹诗作《爱的憧憬》。跟上世纪的很多作家(如鲁迅、郭沫若)一样,高长虹也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因为婚姻生活的不幸,致使高长虹有‘爱的憧憬’,不过多为单相思,结果是‘我呼爱人,爱人不应’。”[陈漱渝:《“我呼爱人,爱人不应”:高长虹与三位女作家》,《上海鲁迅研究》2009 年第2 期。]学者在文章中列举了高长虹同三位知名女作家的微妙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高长虹的爱情生活与爱情情结,以及对他小说的解读。在三位女作家中,高长虹与石评梅关系最密切、最长久,但也只是高长虹的精神相恋,他把这种感情写进了多篇小说中。冰心是高长虹十分仰慕的,他曾经写评论赞赏她的《小读者》,是否暗恋过冰心?难下结论。他陆续发表的《情书》21则,当时在文坛上风传是写给冰心的,鲁迅也信以为真。但笔者认同陈漱渝的观点,可以把这一束情书视为“高长虹的文学创作和情感自慰”。高长虹与许广平的关系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迷案”,当时传言高长虹的组诗《给——》就是写给许广平的。新时期以来,董大中、阎继经等学者,经过大量、细致的考证、研究,认为抒情对象并非许广平,而是石评梅。
文学中的情节、人物,都是根植于现实生活以及作家经验的。源于哪些事件、人物,并不重要,也不能较真。重要的是作家能否写出艺术的、成功的情节和人物来。高长虹在他的一系列爱情小说中,不仅写出了旧式婚姻的陈腐、荒唐、不合理,也写出了现代婚爱的脆弱、艰难、不可靠。同时建构了一种美好、纯净、浪漫的爱情“乌托邦”。他对婚爱生活的描写,同样显示了一个“五四”知识分子,对社会人生的揭示与思考。
“五四”知识分子是夹击在新旧两种婚爱中的一代人,他们所受的痛苦、牺牲,具有深刻的社会人生内涵。《结婚以后》无疑是一篇自传小说,描述一位叫象山的17 岁中学生,按照家庭的安排,与邻村的“童养媳”成婚。作为一个品学兼优的青年学生,他渴望自由爱情,希望爱人“读过书”“懂事理”“有高远志愿”。而新妇门户相当,人长得漂亮,脑子聪明。只是没有文化,又缠了脚。这让他十分苦恼、沮丧,心里酝酿着“出妻”计划。但同床数天后,他同新妇相拥亲吻,“同她享受那秘密的幸福”。客观讲,这桩婚事虽是旧式婚姻,但却是“美满”的,被众人羡慕的。他对新妇没感觉,想着“出妻”,但又禁不住性的诱惑。廖久明评价说:“该篇小说粉碎了包办婚姻的最后一道防线,表面上‘美满’的包办婚姻也不美满。该篇小说尽管存在着缺点,但无疑是1920年代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在同类题材中,它更是别具一格,名列前茅。”[廖久明:《白猫也是猫——高长虹短篇小说〈结婚以后〉解读》,《名作欣赏》2007年第2期。]高长虹用更多的笔墨,写了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向往、追求。《红心》写海外归来的朱心,与到处闯荡的张红,热恋两年,决心离开北京,到上海等南方城市去漂泊。北京的“官僚气”、上海的“拜金狂”,都是他们厌恶的。他们奔波在命运的路上,但有温馨的爱情相伴。《青光》写大学生王辰匀,面临的前途、理想、爱情、经济等种种问题。他与美丽、活泼、聪明的杨海珊相爱,二人约好到日本留学。但杨海珊要他筹划留学经费,在选择专业上好高骛远,张口闭口谈钱,使他感受到女人的世俗、自己的窘迫,给美好的爱情蒙上阴影。两篇小说把青年人的爱情写得真实、鲜活,但在艺术表现上较为粗糙。
《革命的心》是高长虹小说中的一篇力作,具有更多的自传性,女主角就是以石评梅为模特的。小说书写革命诗人刘天章,在北京创办狂飙社,与张燕梅相爱。又赴上海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释放后重回北京,重拾狂飙旧梦,重温与女友的爱情。最后振奋精神,与女友再赴上海继续革命。董大中经过严谨的考证后说:“这篇《革命的心》,就是一篇‘自叙传’性极强的小说,除了‘现在时’的生活属于幻想以外,对‘过去时’的描写,是一点也没有虚构的,它也使我们知道了高长虹心灵上更多的秘密。”[董大中:《鲁迅与高长虹》,《董大中文集》(第4 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37页。]作家对男女主人公的出身、经历,两家的世交,两人的相见、交往等,都作了如实的描述。但对他们热烈的恋情、相约赴沪,却作了凭空虚构。石评梅爱的是高君宇,对高长虹虽然欣赏其才华,但并无真爱;而高长虹始终把石评梅当作“女神”,存有奢望,当现实的爱情彻底破灭之后,他在小说中建构了“爱情神话”。小说中,刘天章经历了上海被捕的劫难之后,他痛苦地思考了革命、文学、爱情的关系。意识到有些人“是为恋爱而去革命”,“他恋爱,只是为了一个梦”。主人公得到爱情之后,“有了未曾有的精神上的刚健”,“能够更努力地把自己完全献给那革命事业”。爱情是高长虹从事革命的精神支柱,他把爱情当作心中的“华严”。
对自由爱情的坚信、寻找,始终是高长虹爱情小说的主调。中篇小说《春天的人们》是作家1928 年春天,在上海写给情人的29 封情书。在平铺直叙中,梳理了自己在上海四年的奋斗史。“我”满怀理想与雄心,筹办大学、创办书店。但却突然想辞掉工作、事业,应朋友召唤从军上战场,或是到科研部门从事科学研究。但经济困顿,日常生活都难以维持。什么路都走不通,最终决定回到北京,与情人相随到国内、国外周游天下。在这一束信札中,情人的形象是模糊的,有石评梅以及父亲的影子,但往往一闪而过。作家虚拟一个情人,只管尽情倾诉。他反思了自己所处的时代:“这一二年来的中国已是狂飙的中国了。然而,那个最狂飙的中国啊,却还是远得很……”面对社会人生的渺茫前途,痛切地感受到:“寂寞啊,更大的寂寞啊!”所以“我”才放弃一切,与情人相伴而行,浪迹天涯。充分表现了一个“后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在困境中期望退隐的精神走向。中篇小说《神仙世界》,运用了很新潮的现代叙事方法,文本的主体部分,描述的是青年作家李健雄,他的爱情悲剧与两个女子之间的纠葛。他出身贫寒,没有职业,张淑女家境富有,才华出众,他们反叛旧式婚姻,自由自主结合。但这样的现代爱情,却最终走向了破裂。李健雄在百无聊赖中去神仙世界茶楼喝茶看戏,一下子就迷上了美貌羞涩的女茶役吴桂珍,一次次去喝茶会面,并期待着爱情发生。但女茶役深知不是一个阶层,用沉默拒绝了他。张淑女得知隐情,毅然出走。李健雄告别伤心地,去东京“寻求他新的生活”。这个故事有着丰富的社会人生内涵。她揭示了现代爱情隐藏的危机。两个单身匹马的青年,既无社会基础,又无经济积累,再加上种种现实障碍,美好的爱情是很可能破灭的。作为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很容易爱上那种单纯、美丽的底层女子,但这样的爱情更是难以实现。现代社会解放了青年的爱情、婚姻,而横在他们面前的路,依然山重水复。
高长虹故乡有家室,在外找“爱人”。但他不愿意再有一个家庭,再去做一个丈夫。而他渴望着一种情爱、性爱,一位知音。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不了,就只能在文学中构建一个爱情的“乌托邦”。
弗洛伊德认为文学是力比多的升华。高长虹推己及人,把目光转向广大社会普通民众的爱情婚姻,创作了《她,第三个丈夫的第三个妻子》。在单纯的情节、简短的篇幅中,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她”一生嫁了三个丈夫,而第三任丈夫娶过三个妻子,“她”是第三任。“她”不仅是后妻,而且没有子女,“她”为“缺乏一个光荣的名义”,“心上凝结成一个坚硬的核”。但“她”与丈夫有爱情,同表弟、长工有暧昧关系。作品的情节、人物都是粗线条的,但却显示了高长虹的一种洞察能力,他把底层女性在爱情、家庭、婚姻上的纠结、困扰、期盼,都呈现出来了。
走向现代派
高长虹在一首情诗中曰:“我爱你,是艺术的化身,唉,我啊,我啊,我正是艺术的情人!”作家把心中的“女神”、文学融为一体,称自己是二者的情人。可见他对文学的敬仰、虔诚,对走近文学、创新文学的渴望。正是这种情结的驱动,他执着探索小说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方法,创造了一种多姿多彩的现代小说“风景”,成为新文学发展中一位“先锋”作家。比之他的诗歌、散文,他在小说文体上的探索花样翻新,走得最远。但也正是这种激进的探索,使他的部分小说不够精粹、成熟,增加了阅读、理解的难度,削弱了作品的影响、传播。
高长虹有着较丰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他把《离骚》《水浒传》《红楼梦》称为“三大杰作”,在他的诗歌、散文中,可以读出《诗经》《楚辞》的韵味。但他认为中国古典文学是弱于西方文学的。他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取同一步调,广泛吸纳西方现代文学思想与作品营养,不仅大量阅读,而且努力翻译,同时及时评论。他涉略的西方作家有惠特曼、雪莱、歌德、席勒、莫泊桑、海明威、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数十位,对西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各流派,都有一定研究,从而建立了一种开放、多元、现代的文学理论与创作思想。“狂飙社”中的重要成员,如高沐鸿、高歌等,都深受他的影响,创作上选择了以现代主义为主的道路。
“五四”新文学,既有现实主义思潮,又有现代主义思潮,二者常常是相互缠绕的。高长虹的小说同样如此。他有两种类型的创作,一种是现实主义的,但也渗透了现代写法;一种是现代主义的,其中也积淀着现实元素。其实二者的结合要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有很大难度。
先看高长虹的写实类小说。或许有人认为,高长虹的小说属现代派,现实成分可以忽略不计。其实早在1922年,高长虹在致沈雁冰(茅盾)的信中就说:“我以为今后自然主义应该向理想方面发展了。……二十世纪的新人生观已经确定而且在各处实行起来了,自然主义也正应此时代之要求向理想的境地而前进。”[高长虹:《致沈雁冰》,《高长虹全集》(第三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 页。]这封信发表在《小说月报》1922 年第5 期。在这里,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可以画等号,高长虹强调了对理想的突出。后来高长虹在多篇文章中谈到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倡导文学的“时代性”。他认为现实主义是一个基础,很多杰作都是现实主义的,作家要在这一基础上提高、升华。譬如《结婚以后》写中学生象山结婚的一系列过程,《革命的心》写青年诗人刘天章从上海到北京去会女友张燕梅的故事情节,都是规范的现实主义叙事。但在事件的连接处,却插入了大量的心理描写乃至意识流,扩展了小说的时空和内涵,却没有改变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曙》《春天的人们》,前者是父亲写给儿子的信,后者是男子写给情人的信,都采用了书简体表现形式。这种形式容易写成拉拉杂杂的流水账,两部小说也确有这样的缺憾;但也容易写得细腻入微、深切感人,两部小说也真有这样的优点。现实主义小说注重故事情节的完整性、逻辑性,这就难免会形成故事的封闭性,而削弱了内涵的丰富、多义。高长虹在现实主义的前提下,运用表现主义方法,解决了这一艺术问题。譬如《一个兵和他自己的家里》,只有四千多字,“我”作为伤兵从失败的战场回到家里,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勾画。作家把大量的笔墨,用在了写“我”一路上对战争的反思,对个人命运的回顾;“我”在乡村旷野上寻找妻子儿子,“乡村变成了历史的甲壳,而深夜便是历史了”,“我”站在瓜田茅屋前,被拒之门外,妻儿与“我”的深深隔膜,一家人的痛心生分……在叙事中运用了议论、抒情、想象、体验等手段,都是表现主义方法。把一个兵的归家,突然放大了、强化了,既写出了一个平凡、质朴的乡村青年形象,又写出了战争对国家、乡村乃至个人的深刻影响。
再看现代类小说。高长虹的现代类小说无疑比他的写实类小说更为精彩、成熟。但这类小说并不多,且因“晦涩难解”而读者较少。在这类小说中,他熟练地运用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等现代方法。高长虹说:“艺术不只是反映现实,而且要象征时代和它的运动。”[高长虹:《抗战文艺和它的发展条件》,《高长虹全集》(第四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页。]象征主义是19 世纪末在英国等西方国家出现的一种文艺思潮。其原意后来演变成“用一种形式作为一种概念的代表”。此后引申为凡能表达某种观念及事物的符号或物品的就称为“象征”。这一思潮强调主观、个性,以想象创造某种带有暗示和象征性的神奇事物,用以表达作家的主观理念和内心世界。象征主义的观念是深受高长虹认同的。他说:“表现派文艺,也确是我最先倡导的。”[高长虹:《复济行》,《高长虹全集》(第三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年版,第354 页。]表现主义是20世纪30 年代在法国以及欧美国家兴起的文学艺术流派。在创作上主张表现事物的内在本质,提倡突破对人的现实行为的描写,而揭示人的灵魂。表现主义思想是深得高长虹赞赏的。高长虹说:“中国的文艺,当然还需要心理的描写。不但是古代的作品,就连新的作品都算在一起,最缺乏的是心理的描写。”[高长虹:《最新的文艺从生理出发》,《高长虹全集》(第三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年版,第413 页。]这里的心理描写,指的就是意识流方法。意识流文学是20 世纪20 年代从心理学引入文学领域的。这一思潮认为人的意识活动不是以整体的、理性的方式进行的,而是以碎片的、自由的方式进行的。认为人的意识是由自觉的和不自觉的意识乃至潜意识共同构成的。意识流理论同样也是高长虹喜欢的。这些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五四”新文学中及时地引进中国,受到了很多作家的欢迎、借鉴,高长虹成为最积极的作家,充分运用到了创作实践中。
《这只是一个梦》写了一个虚幻的、变幻的梦的世界,用来象征现实世界。而其中的“我”又象征着精英知识分子。“我”在梦中遭受到民众对“我”的怀疑、孤立、驱逐,运用了表现主义手法。《震动的一环》中那个死而复生的灵魂,不仅是“我”的象征,同时也是整个知识分子的象征。灵魂在宇宙、地球、故乡游荡,所经所见所想,既使用了表现主义,也使用了意识流手法。《现实的现实》描写“我”和“他”两个独行者的形象,两个人的孤绝、隔膜,象征着革命者之间一种独特而非正常的关系。《最后的著作》刻画“我”告别尘世、事业,隐居荒山,写下遗书后开枪自杀,象征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厌倦、绝望,展现了“我”千回百转的意识流活动。不采用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等现代方法与手法,是很难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这样强烈、复杂、幽深的精神世界的。
在小说创作中高长虹还运用了其他一些表现形式和方法。如诗意抒情手法,《小东西启启的故事》描绘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孩子启启,坐在小河边看河水、看鱼儿,沉浸在一种冥想中,被老仆人称为:“像一个希腊的哲人。”既有诗意,又有哲理。如西方现代叙事学中的元叙事和叙事圈套。元叙事说的是作为叙事人的作家,在文本展开的过程中,指出情节是怎样虚构的,作品所蕴含的意义、问题等;叙事圈套说的是作家在叙述中,在情节、人物设置上故意制造重复、空白、意外等,以增强小说的吸引力和可读性。譬如《神仙世界》里,整个文本有三个故事圈套:作家“我”与女茶役吴桂珍的相遇交往;“我”的朋友近真和王静和的自由爱情;近真在小说《神仙世界》中演绎的李健雄和女茶役吴桂珍的爱情故事。其中,核心人物是女茶役吴桂珍。“我”与小说中的李健雄是重叠的,近真与小说中的李健雄也是重叠的。“我”曾经追求过的真实的吴桂珍与小说中虚构的吴桂珍也合二为一了。真真假假,扑朔迷离,柳暗花明,演绎了一个“后五四”时代几位青年意味深长的爱情故事。譬如《那个人》的主体情节,是作家谢与同写不出“杀气腾腾”的革命文学来,只能写一些恋爱生活小说。但虚构的故事、人物,竟同他的现实生活叠合在了一起,他与两个女人的爱情、纠葛,既是小说中的,也是生活中的。怎样应对爱情问题?怎样处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让他苦恼不堪,只好下决心罢笔。作家自如地运用了元叙事方法。现代叙事学是西方20 世纪20 年代才出现的,此后逐渐生长、壮大。高长虹几乎是同步的地取法了现代叙事方法与方式,可见他对新方法的痴迷,对小说现代转型的执着。
高长虹的小说大抵写在北京、上海开展“狂飙运动”时期。1934 年他在法国创作长篇小说《中国》,表现广大的底层社会和普通农民、矿工。他一定感觉到了知识分子的那一套思想观念,现代小说的艺术形式与方法,不再能吻合社会的发展、变动,更难以见容于成为主流的“左翼”文学乃至“抗战文学”,因此绝然辍笔。但他的“五四”思想与精神,却在后来的随笔、散文、评论中,依然不时地显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