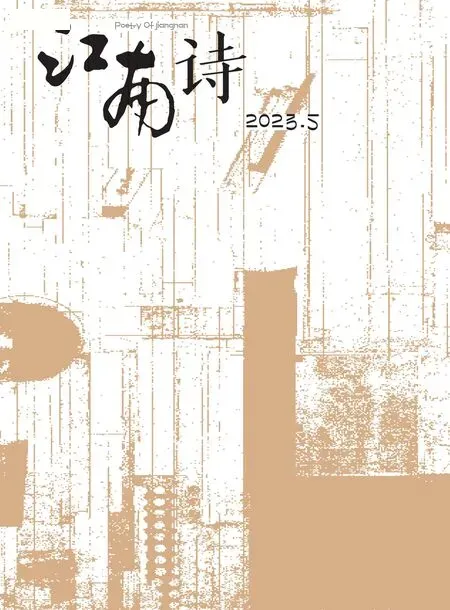清晨听到鸟鸣(七首)
崔子川
麦草垛
将金黄的麦子,献祭给粮仓
之后。他们衰老的身体
躺下来,挨挤在一起
相互取暖
等到雪花飘落,他们还会
被抽取出来。他们最终的命运
或是扔进马厩,或是焚身灶火
他们在大地上,一堆一堆
堆积成无言的墓碑
这多像我那些,失联多年的
大伯二婶
留守在我,年轻的故乡
呼唤着,跟我一样被风
吹散了的麦粒们
清晨听到鸟鸣
这些早晨的歌者,在富春江畔,争相向我
吐露东吴孙氏的秘密
他们的嗓音,像剥开箬叶的粽子
鲜亮,圆润,非遗的传人
他们世代居住在,黄公望的山居图里
那些早已上岸的九姓渔民
是他们的异姓兄妹
我努力想拨开云雾,仔细辨认
他们的模样。只看到满山翠绿
扑向我,沾满尘埃的旧风衣
水的骨头
百度:水中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是水的骨架。
没有骨头的水,缺乏微量元素
缺乏生命动力元素
是病态的水,是死亡的水
在小溪,在大河,在海洋
触摸每一具朝气蓬勃
水的骨骼。
柔软的水,可以生发出
无数个善良的替身
可以放低身段,直至地平线以下
如遇礁石,它愤怒的骨头
顷刻之间,堆砌千层的雪峰
专家们称,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有百分之二十,须从水中获得
我恍然悟道:水的骨头,支撑起
我们在尘埃中的身子
格桑花
念着她们的名字,我总有一种
高海拔的战栗
粗粝的太阳,风,苍鹰
是她们每天快乐的玩伴
在大昭寺,在茶马古道,在牧民卓玛家的牛粪堆旁
我都见过她们的笑,圣洁,鲜艳,羞赫。
她们盛开在,卓玛高原红的脸蛋中
盛开在峭壁,藏民赶马的歌声里
盛开在江南,我落雨的屋檐下
今夜听见雷声
今夜,听见天空压抑很久的
喘息。一些人皮面具
惊恐地躲进城堡
接着是密集的雨,鼓点般
敲打这忽明忽暗的人间
但我仍不敢开窗,不敢
和这些雨水相拥痛哭
我只能遵守黑屋里
挂钟的戒律
将世事循着规矩,一幕幕演出
就像听到这梦里的雷声
也只能,把被子捂紧
我的房子是纸做的
我在宣纸上,造了一座小房子
就像乡间我的那些亲戚们
在田垄上造的土地庙一样简朴
它不宽敞,但足以容纳我一个人
卸下尘衣。在里边打坐,参禅
它选用了最柔软的材质
却丝毫不逊色那些金碧辉煌
我的房子,临水而筑
有清风可品,有明月可鉴
孤 岛
它远远地站成一尊佛
惊涛骇浪,是它的底座莲花
孤寂的黑夜,它燃起航标灯
泅渡,南来北往的船只
它派遣忠厚的海风
点化,沾满尘埃的我
让我一层层脱掉
草帽,手表,身份证和鞋袜
就像一层层脱掉,三千烦恼
我将手举过头顶,面朝庄严的它
一层层浪花,微笑着
将我泅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