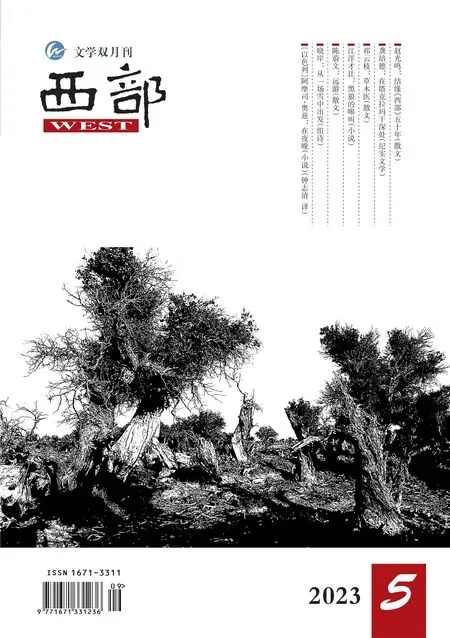占位
周齐林
1
在我脑海里,故乡的记忆始终停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而时光的这叶小舟在生命的河流里彻夜疾驰,不管不顾。我身在此岸,却心在彼岸,如一个笨拙的刻舟求剑者。
炽热的阳光透过窗格子照射在我脸上,一阵凉风由远及近地吹来,树叶发出哗哗的响声。教室里寂静无声,午休时间,同学们徘徊在梦境的边缘,十四岁的我忧心忡忡地望着窗外的那一片绿。这是1999 年的盛夏。
一个月前的月考,原本成绩名列全年级前十的我因为早恋一下子滑倒了五十名外。每次月考后,班主任都会按成绩调整座位。在班主任严厉的批评声里,我的座位被调整到窗户边,瞬时被边缘化了。
自那次月考后,每次数学课,我成了被点名上黑板做题的主要对象。
上课的铃声响起,不停撞击着我的耳膜。每一个响声还未完全释放开来,转瞬就被后面的声响吞噬。声音前仆后继,连成一片。刺耳密集的声音惊醒了还在睡梦中的同学们。远远地,我看见班主任夹着一本教案疾步朝教室走来,我的心跳不由加速起来。班主任一声不吭地走进教室,而后迅速拿起粉笔,在黑板上抄下四个题目。目光如利剑般射向整个教室。教室里此刻寂静无声,许多同学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班主任仿佛懂得心理学,谁低头最厉害就点谁上来做题目。已经点了三个同学的名字,起身时身体碰撞桌椅发出的咔嚓声在我耳畔响起,很快我隐约看见三个身影站在黑板前。四个题目,还要叫一个人。我心跳加速,低下头默默祈祷。抬头的刹那,班主任的眼神最终还是落在了我身上:“周齐林,你上来做最后一道题。”我起身,站在黑板前,看着眼前这道几何题,心跳加速,浑身禁不住颤抖起来。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黑板,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这题我不会。身旁响起粉笔的沙沙声,另外三个同学正奋笔疾书。我顿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班主任点完名就出去了,他倚靠在教室门口的栏杆上和隔壁的一个老师说话。我见班主任转身进教室,迅速紧握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个答。张鹤就站在教室门口的一角,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写完答,却不知该如何继续下笔。僵持了许久,班主任看出了我的尴尬,厉声呵斥道:“下去,怎么和猪一样。”我低着头,灰溜溜地回到座位上,直感到脸上火辣辣的。
暮色里,炊烟袅袅。一路奔跑至家,气喘吁吁。祖母正坐在院落的老板凳上吃饭,祖父则在躺椅上抽水烟,他吸一口,烟雾就在眼前缭绕开来。父亲坐在圆桌上座旁喝烧酒,母亲则紧挨着他坐在一旁。在家里,吃饭坐座位很讲究,必须遵循长幼老少的原则。祖父那张精致的藤椅一直放在上座,即使空着,我们也不敢坐上去。有一次我坐在上座的藤椅上吃饭,父亲用严厉的眼色看着我,我立刻坐回到一旁的板凳上。祖父的威望就是在日常的细节中建立起来的。他的一声咳嗽都充满威慑力。与祖父不一样,祖母不太喜欢坐在桌边吃饭,她最喜欢夹点菜,坐在院落的老板凳上吃。那条老板凳是祖母从娘家带过来的,缝缝补补敲敲打打许多次,祖母一直舍不得扔掉。她端着饭碗坐上去,老板凳嘎吱嘎吱地响,仿佛有什么东西破碎了。
匆匆吃完晚饭,在稀薄的夜色中回到学校,教室里早已灯火辉煌。踏进教室的那一刻,我的心跳不由加速起来。这个晚上的两节晚自习都是数学课,班主任正在黑板上抄题目。教室里鸦雀无声,气氛变得无比压抑起来。十分钟后,我又被点名上黑板前做题。
从此,数学课成为我的梦魇。梦是窘困现实的映射。直至许多年后的今天,许多个夜晚,梦中的我仍会被班主任叫上黑板前做题,最后在一阵惶恐不安中醒过来。窗外夜色深沉,如水的月光透过窗格子洒落在我身上,回顾梦境,一切恍若隔世。
2
那年中考失利,我最终以三分之差与省重点高中擦肩而过。我以总分排名第一的成绩进了距家几十公里外的一所普通高中。高一时我的成绩还保持在全年级前十。到了高二,我严重偏科,成绩迅速滑到四十名之外。每次月考完后,学校会张贴红榜。面对红榜,我总是绕道而走。我终日沉浸在文学作品里,蚂蚁搬家般从校外的旧书店把一本本砖头厚的小说搬到自己的课桌里。
午后,在班主任的一声号令下,全班同学按个子高低排序,男生站成一排,女生站成一排。一切准备就绪后,手持成绩单的开始按成绩高低念名字。“彭胜。”班主任叫了一声,紧接着我看见瘦小的彭胜常胜将军般在紧挨讲台中央的那个座位坐了下来。我如热锅上的蚂蚁,时间变得难熬起来。那次考试我位列全班倒数第五。原本拥挤的走廊变得空落落起来,只剩下我们五六个成绩垫底的。班主任扫了我们一眼,用不耐烦的语气说,你们都进去,随便找个位置坐。
教室里黑压压的。我们迅速走进教室。我低着头,抬头的刹那,眼神与红撞击在一起。红坐在教室中央的位置,我们那种朦朦胧胧的情愫回荡在彼此的心里。我最终在教室最后一排紧挨窗户的位置坐了下来。窗外是一片耀眼的深绿,一只麻雀在梧桐树上发出阵阵鸣叫。红是班里的尖子生,她活泼可爱,脸上终日挂着一抹少女独有的红晕。在学校的食堂、操场上,我们彼此擦肩而过时,我的心跳加速,脸发烫,而她则微低着头,脸上的红晕愈加鲜明了。
翻开课本,无意中翻到《鸿门宴》这篇课文。项王、项伯东向座,亚父南向座,沛公北向座,张良西向座。项王、项伯是首席,范增是第二位,再次是刘邦,张良则为侍坐。鸿门宴上的座位排序鲜活而生动地呈现了古人座位的尊卑。我从鸿门宴的座位排序上看到了自己处境的艰难。
我正在上课,忽闻有人喊我名字。循声望去,见母亲提着一个包裹四处寻觅我的身影。我疾步走出教室,从母亲手里接过米和菜。
“近视这么严重,怎么还坐在最后面?”母亲担心地问道。这一下问到了我的痛处,我随便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送至校门口,母亲执意让我赶紧回去上课。看着母亲在烈日下疾步行走的身影,一股淡淡的忧伤忽然把我攫住。母亲没有坐车,而是步行十几里路来给我送饭,她的衣服已被汗水湿透。辣椒炒肉、鱿鱼丝、苦瓜炒蛋,都是我爱吃的菜,母亲还特意买了几个苹果和香蕉。静静地看着这些菜和水果,母亲在烈日下行走的身影浮现在我眼前。眼前的食物迅疾变成了一把把锋利的刀,插在我的心尖。母亲的期待即将落空,她的辛苦是徒劳的。我辜负了她。
一个月后,非典来袭,不时有在广东打工的人回来。学校如临大敌,最终选择放假一周。还有一个半月即将高考,学校把高三年级的前四十名学生留下来补课。作为差生的我自然不在其列。薄暮里,我踮起脚跟,看见留下来的四十个同学坐在一间新教室里,正埋头苦读。我心底蓦然涌起一股深深的忧伤,感觉像被抛弃了般。不远处,一片枯黄的落叶在半空中左右摇晃着,缓缓落下,即将落地的那一刻,一阵清凉的晚风从不远处疾速吹来,叶子在风的吹拂下,迅速飘到了不远处的臭水沟里。如血的黄昏,静静地凝望着眼前的一幕,我感觉自己如这片叶子般被命运的风暴裹挟着,四处飘荡。命运的风肆意摆布着我,我却无力反抗。一股深深的无力与悲哀感在我内心深处涌荡开来。抬头的瞬间,我看见一片片翠绿的叶子挂在枝头,迎风起舞。绿叶的经络清晰可辨,仿佛能看到液体的流动。它们生机勃勃,紧紧地把自己固定在枝丫上,不停向外伸展,贪婪地吸吮着阳光和雨露。我像一片落单的叶子,被风吹落在孤寂冷清的小路上。
一辆浑身沾满污泥的中巴停靠在校门口的马路上。暮色渐深,中年售票员正使劲地朝我挥手。我如一条漏网之鱼迅速被一张大网打捞进去。
3
汽车在夜色中疾驰了一个小时后,哼哧一声戛然而止。我从车上跳了下来,夜的帷幕已完全落了下来,不知名的虫子在草丛深处发出阵阵鸣叫声,远处的屋舍影影绰绰。
推开院门,昏黄灯光的映射下,那张原本弥漫着烟火气息的餐桌此刻冷冷清清,六张凳子空落落的。祖母正手持三根香,虔诚地站在案上的佛龛前。她嘴里念念有词,仿佛在祈福什么,不远处的梧桐树上忽然传来乌鸦的阵阵悲鸣。祖父躺在院落的凉椅上,闷声抽着水烟。
见我归来,祖母疾步走进厨房,端着热气腾腾的饭菜出来。彼时祖母身体还很硬朗。我打开房间,却不见父母的身影。
“林林,你过来一下。”院落的祖父咳嗽着说道。“你好好高考,不要担心。”祖父边说边递给我一张纸条。一种不祥的预感迅速笼罩在我心上。昏暗的灯光下,我颤抖着摊开纸条,看见父亲熟悉的字体,“林林,爸爸带妈妈去南昌做手术了,你好好高考,勿念。”父亲的纸条让我恐慌。我想起一个月前返家时母亲那张异常苍白的脸,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中药渣子铺满了门前的小路。母亲显得异常虚弱,喝完中药,她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的那一抹抹深绿发呆。
我怔怔地在院落站了一会儿,转身跑进房间。翻箱倒柜寻觅一番,在大衣柜的抽屉里,一张折叠的病历出现在我眼前。病历上清晰地写着“子宫内膜癌中晚期”。我顿时陷入无边的忧伤里。
一连几日,家里静悄悄的。餐桌旁属于父亲和母亲的座位空落落的。餐桌旁的那张竹椅是母亲独有的。母亲喜欢坐竹椅,竹椅清凉,到了冬天,她就在竹椅上垫一块棉布。薄暮里,坐在饭桌旁的我盯着对面的那张竹椅陷入冥想中。
祖母见状,用力敲了敲桌子,响声把我拉回了现实。
“林林,不要多想,老天爷会保佑她的。”祖母看着我说。
多年后,母亲才跟我讲起那次去往南昌住院的经历。抵达医院的那天已是深夜,住院部床位紧张,寂静的夜晚,父母亲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过了一夜。次日下午,在一个远房亲戚的帮助下,母亲才顺利住院。
一个月后,在父亲的搀扶下,母亲走出了医院。天空灰蒙蒙的,阴云密布。父亲招手欲叫一辆出租车,抬手的那一刻,母亲拽了拽他的衣角。在母亲的一再坚持下,父亲搀扶着母亲坐上了通往火车站的公交车。公交车空荡荡的,车里开着空调,凉意逼人。
火车站人潮汹涌,汗味、烟味、香水味,各种气息混杂在空气里,令人窒息。父亲扶着母亲在一张长椅上坐下,自己疾步朝售票窗口跑去。回来时,父亲手里多了两张卧铺票。“再坚持一下,等下上火车就可以躺着睡一会儿了。”父亲言语里满是心疼。母亲原本叮嘱父亲买两张硬座票。
火车启动,喧闹的车厢里顿时安静下来,母亲蜷缩着躺在下铺。这是暂时属于她的位置。父亲坐在对面的铺位上,静静地看着母亲。车窗外是广阔的田野。
在火车上休息了两个小时,母亲恢复了些微体力。下火车后,火车站广场上有直通县城的中巴车。父亲搀扶着母亲,找了车中央一个紧挨窗户的位置坐了下来。中巴车开出市区不到半个小时,母亲就剧烈地呕吐起来。母亲晕车严重。呕吐完的母亲脸色愈发苍白。车厢里弥漫着一股霉味儿,父亲打开紧闭的车窗,一股风裹着丝丝凉意迎面扑来,吹乱了母亲的头发。几分钟后,父亲又小心翼翼地把窗玻璃关上了,只留下一道细小的缝隙。窗外的风使劲挣扎,透过细小的缝隙钻入车内。
薄暮里,父亲和母亲终于回到了熟悉的小镇。我站在门槛上,看着瘦弱的母亲,禁不住泪流满面。母亲一把抱着我,不停地抚摸着我的头,连说没事。临近九月开学,那个细雨弥漫的黄昏,在床上躺了近两个月的母亲终于回到了餐桌边,重新落座在那张久违的竹椅上。
寂静冷清的家又处处弥漫着烟火气息,缕缕炊烟缓缓朝天际飘去。
那年高考,学校只考取了七个人。我离二本线差了几十分。几经挣扎之下,原本读理科的我最终选择了文科复读。一整个暑假,我从堂哥那里借来高中三年的政治、历史和地理书籍,放在身边,厚厚的一叠。寂静的午后,凉风吹拂,我端坐在祖母的那张旧板凳上苦读着,耳边不时传来母亲咳嗽和翻身的声音。一切与母亲有关的声音时刻激励着我。八月下旬,收拾好衣物和书籍,我和几个一同落榜的朋友来到了隔壁莲花县的一所中学复读。我选了教室最后排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班主任是一个长相斯文的中年男子,教我们数学。恍惚中,我感觉一切又回到了初中时代。
红考上了省外的一所大学。那年寒假,学校补课,午后,寂静的校园里忽然传来一阵清脆的笑声,如此熟悉。我犹豫着朝走廊走去,倚靠在栏杆上,循声望去,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夹杂在人群中。正是红。红穿着一袭红衣,红扑扑的脸蛋看起来愈加动人。除了我之外,还有七八个同学也在这所学校复读。大部分同学去了县城的中学复读。我久久地看着红,她的笑声落在我的心坎上,我却感到一丝疼。转身欲走的刹那,红忽然抬头看着我,我们的眼神交汇在一起。我怔怔地站在原地,仿佛触了电般,浑身禁不住颤抖起来。我还是疾速转身走进了教室。她红扑扑的脸蛋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红给我写过两三封信,我认真写好了回信,却始终没有塞进附近的邮箱。红家境优越,她不属于我。次年,我顺利考取省城一所大学。见我志愿未填报她所在的大学,亦从未回信,红从此再无来信。
多年后,我与红在一次聚会上相遇,我们没有紧挨着坐在一起。再次相遇,我们隔桌而坐,彼此相看一眼,仅此而已。临走时,我们握手告别。
4
母亲病重做手术欠下诸多外债,大学期间,每逢暑假来临,我总会用学生证买上一张半价火车票前往广州打暑期工。适逢暑假,火车上拥挤不堪。我买的虽是坐票,却无座可坐。汗味、烟味、各种体味、发馊的方便面味,车厢里各种气味混杂在一起,令人窒息。站到后半夜,我腿脚发麻,酸痛不堪,转身的刹那,见车厢连接处空出巴掌大的地方,便迅速从背包里抽出两张旧报纸垫在地上。一屁股坐下,疲惫的身体紧挨着车厢的铁皮,一股清凉透过衣服钻入体内。昏昏沉沉地睡去,醒来天已大亮。
站票、坐票、卧铺、一等座、二等座,经济舱、头等舱,不同的座位映射出一个人的生存境遇。
出火车站,远远地看见哥哥在朝我招手。哥递给我一瓶冰冻饮料,又给了我一个大拥抱。哥依旧那么瘦,他瘦长的手臂揽着我。
休整几日,我进了哥哥所在的鞋厂做普工。我的工位职责是贴底,在鞋掌底与地面接触的部分贴一层橡胶底。每天的工作时间从早上八点持续到晚上十点,除去午休时间,近十二个小时。月薪一千二百元。
流水线上,一只只半成品的鞋子以均匀的速度朝我走来。我必须在半分钟内把底贴好。台面的鞋子一旦堆积,就会遭来车间主管的一顿骂。去厕所必须请假。一次憋了许久,膀胱几乎要炸裂开来,我来不及请假,匆匆往厕所跑去。再次回来时,台面上的鞋子堆成了小山。车间主管怒目圆睁地看着我。“罚款一百。下次再这样直接滚蛋。”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工厂是一台巨大的机器,机器上的每个螺丝钉在巨大的推力下随之飞速运转着。在工厂,最基层的工位,人如机器般被牢牢固定在一个位置上。晚上十点,下班铃声响起,工友们飞快跑出厂门,往溜冰场或者大排档走去。我沉默着走向宿舍,一整天的工作下来,我早已疲惫不堪。
几天后的上午十点,工厂突然停电。原本井然有序的车间变得混乱喧嚣起来,工友们在车间里四处跑动。我在自己的工位上坐了许久,起身疾步走到车间门口。正欲出去,厂门口的车间主管见状瞪了我一眼。我顺势退回车间,在附近一个空着的工位坐了下来。
“你坐在我工位上干吗?”忽然,一个女工气势汹汹地出现在我眼前。
“坐一下怎么了?你这么凶干吗?”我生气地说道。
“你坐别人的座位还有理了?”女工说道。
我骂了句神经病,转身走开。
“你才是神经病。”女工回道。
我以为一切结束了。不料晚上加完班,我正往宿舍走,暗影里一个瘦弱矮小的男人朝我扑来。昏黄灯光的映射下,他手中的水果刀寒光闪闪。刀是无声的。我心底禁不住一颤。眼前的一幕让我措手不及。
“丢你老母,竟敢欺负我女朋友。”
我来不及辩解,刀朝我腹部的方向刺来。情急之下,一个转身,我把他扑倒在地,双手牢牢攥着他手中的刀。哥闻声赶来,欲把他手中的刀夺掉,不料刀一个转弯,扎在哥的大腿上,鲜血顿时流了出来。我一脸担心地看着他,大声疾呼着,几个保安赶来迅速把持刀者制服。
两个月后,我拿着两千四百元工资,回到了熟悉的大学校园。
当我大学毕业,怀揣简历在异乡漂泊时,故乡那些与座位有关的记忆慢慢变得残酷,如刮去鱼鳞的草鱼,浑身布满血丝。
5
座位是身份的象征,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座位,有的人坐得很舒服,有的人却如坐针毡。
在单位,我每日坐立不安。办公室三张办公桌,我资历最浅年龄最小,靠近房门的那张桌子就是我办公的地方。我身后是工作多年却迟迟没有得到提升的凯,凯后面是部门的科长。科长年过五十,在副科的位置徘徊多年,前年刚扶正。我不敢有丝毫偷懒,背后有两双眼睛盯着我。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眼皮底下。
一个房间,三个办公位置,最好的当然是最里面紧靠窗户的位置,身后的窗户和身前竖起的电脑屏幕架起天然的屏障。最差的自然是我所在的位置,前面大门敞开,后有两双眼睛,毫无隐私可言。
犹记得初到单位报到第一天,下班的铃声响起,我拿着新办的饭卡去一楼食堂吃饭。食堂的电视里正播放着国际新闻。打好饭菜,我选了中间一个好位置坐下来,一边吃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电视。这个位置视野开阔,离电视不远不近。慢慢地,我发现许多吃饭的同事纷纷转身或者走到我面前,用诡异的眼神看着我。我顿觉不妙,心底发毛,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心底萌生。饭堂打菜的阿姨忽然疾步走过来对我说道,“阿林,这个位置是领导坐的。”我听了立马端起饭碗换到紧靠墙壁的座位。刚坐下吃了一口饭,耳边响起脚步声,回头看见一个打扮颇为讲究的中年妇女走进食堂,在我适才的座位上坐了下来,很快,食堂的阿姨满脸笑容地把饭菜端到她桌上,我观察到她的每个动作都小心翼翼,生怕有什么闪失。
熟悉工作后,单位经常有活动,我所在座位的职责就是端茶倒水。漫长的饭局从晚上六点迟到晚上十点,看着饭桌上一桌桌熟悉又陌生的面孔,我时常陷入虚无中。
2018 年,我终于有了一辆代步车。一大早,我刚把车稳稳当当地停进车库,锁车准备走的那一刻,门口的保安却把我拦住了,“地下车库车位有限,只停在编人员的车,你赶紧开出去。”保安气势汹汹,一点也不给我留情面。他的话让我立刻明白了自己的身份。无奈之下,我只好重新发动车,准备停到二楼的露天停车场。因刚拿到驾照,加之心情略显紧张,倒车的刹那,我一脚油门踩重了,车屁股撞到了一辆奥迪车上。“你死定了,撞到了领导的车。”保安见状,疾速跑过来,大喊大叫道。我顿时僵住,浑身直冒冷汗。保安迅速掏出手机拨通了领导的电话,他点头哈腰的样子让我印象深刻。所幸车主宽宏大量,不与我计较。“领导人好啊,说刮花一点没事,叫你下次注意。”保安笑着朝我说道。
我总以为这事到此结束,却没料到这成了我办事不稳重的标签。
在单位,我时常感觉自己是一台设计精密的时钟,挂在墙壁正中央的位置。我噤若寒蝉,不敢多说一句话,每天我按照固有的节奏滴答滴答地响着,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只有回到家,我疲惫紧绷的神经才会舒展开来,仿佛一条搁浅在岸的鱼回到了熟悉的河流里。
6
在异乡漂泊多年,薄暮里,炊烟袅袅,一家人围桌吃饭时那种热闹而温馨的场景时常浮现在我脑海里。这个弥漫着乡土气息的场景早已烙印在我脑海深处,那种热气腾腾的生活气息时刻从记忆深处涌上来。
多年后,漂泊多年的我回到故乡,正是薄暮时分,晚霞红透了半边天。微凉的风在寂静的村庄肆意游荡着。
推开院门,厅堂昏黄的灯光下,年迈的父母亲正在吃饭。年过八旬的祖母端着一碗饭依旧坐在院落的老板凳上,老板凳已修修补补许多次,就像祖母的身体,在医院修修补补多次,摇摇欲坠。
饭桌旁,属于祖父的那个座位已空缺多年。祖父的位置移到了案上,母亲用祖父生前常用的那个碗倒满家酿放在他遗像前。“喝吧,在那边吃好点。”母亲轻声说道。从饭桌旁的座位移到案上的位置,如此短的距离,却是祖父的一生。
祖父去世后,他睡了多年的床板迅速被搬空,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床架子摆在房间里。我扛着四块祖父睡了一辈子的床板,疾步行走在通往禾水河的路上。床板满是灰尘,在我肩上留下一个巨大的印痕。气喘吁吁地走至河边,我用力一甩,床板迅速落入河中,浪花四溅。站在岸边,我看着床板随着流水渐行渐远,直至消失在远方。
清晨,父亲把祖父睡了大半辈子的草席搬到村里池塘边的岔路口。父亲拿出火柴,咔嚓一声,草席迅速点燃,转瞬被大火吞噬,变成黑色的灰烬。
祖父的衣服被一件件扔入熊熊大火中。老屋里与祖父有关的旧物都扔进了火里,最后变成了灰烬。
祖父的床位、座位随着他的离去都空了。那些与祖父有关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变得面目模糊起来。
当我深陷于祖父有关的回忆中时,门外的一声巨响把我拉回了现实。转身望去,我看见祖母一屁股跌在地上,那条跟随了她一辈子的老板凳散了一地。四条凳腿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凳面摔成了两半。
我迅速上前把祖母搀扶起来。祖母看着散了一地的老板凳,面露哀伤。这条她出嫁时作为嫁妆的老板凳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次日中午,母亲在厨房里炒菜,祖母把散架的老板凳缓缓塞入灶台中。火舌舔舐着黑漆漆的锅底。干柴烈火,火瞬间把老板凳吞噬了。
五年后,身患老年痴呆症的祖母在一个寒冷的冬夜跑出家门,一脚踩空,坠入冰冷的河中,溺水而亡。
几天后,在县殡仪馆,祖母如老板凳般被缓缓推入火化炉里,一个小时后,祖母变成了三斤重的灰烬。
当我再次从异乡归来,走进院落时,祖母端着饭碗坐在老板凳上吃饭的熟悉场景成为遥远的记忆。厅堂里,只剩下父母亲端坐在餐桌旁。祖母的位置也被移到了案上。祖父祖母的遗像并排立着。我从房间里拿来祖父祖母生前用过的碗筷,倒满白酒,放在案上。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你们在那里好好过。”我手持三根香火,默默三叩首。
时间是最无情的侵占者,它默默地把每个人在尘世的位置吞噬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