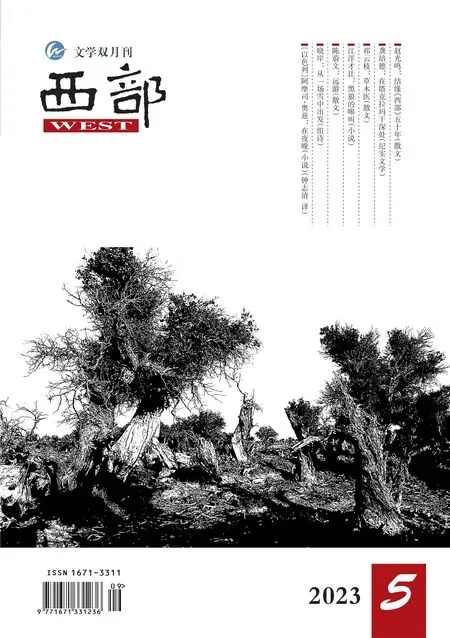六星街的主人与过客
张惜妍
那是个初夏,周末的黄昏,我约了依琳娜到六星街散步,我俩说好在黎光街六巷的青骊民宿门口会合。我走到中心转盘,确定了一下方向,顺着路牌寻找,我这个路盲,走着走着就迷路了。
鸽子飞过上空,哨音清亮,巷道里有老人坐在大门口的木凳上聊天,有主妇举着胶皮管子浇花,潮湿的地面散发出泥土的清新,孩子们三三两两嬉闹,猫咪跑过墙角,太阳的余光照在蓝色的墙面上。
这个六角形的街区,街道曲折,小巷密布,漫步其中,如同卡尔维诺的书名《蛛巢小径》。路牌设置得很迷惑,黎光街、赛里木街、工人街交错并行,每个路牌都是从一巷开始按照数字排序到十巷。明明你正对着工人街的指向牌,转个身又面对的是赛里木街,特别容易混淆。当我和别人说,“我在黎光街十巷的手风琴馆等你”的时候,和我约见的人很有可能一边应答一边向着赛里木街的巷道走去。
有时打车,出租车师傅会问,哪个六星街?上海城的六星广场还是师范后面那个?然后谨慎地调动大脑里的路线,试图迅速定位到乘客指定的位置。
——“差不多能找到。”
——“那个地方岔路太多了。”
唉,都是不确定的短语,听得我不放心,一路提醒他,那附近有个学校,还有个餐厅,有个气派的大院子。其实,说了一路,我自己也没说清楚,目的地到底在几巷。不过下车时司机会好心建议,去六星街,要是想准点到达,最好提前十分钟打车。我们都没好意思说破——至少八分钟是给迷路转圈圈预留的。
六星街街区的规划布局与十九世纪末现代城市规划先驱埃比尼泽·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1898 年)有着极其相似之处。街区整体上呈六边星状,中心是公众建筑,外围为居住区,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居住模式。对于很多本地人来说,六星街就像一个环环相连的迷宫,外地人更是走进去出不来,出来进不去。
六星街的中心是一个六角圆盘,黎光街、工人街、赛里木街从中心点向四周辐射的六条街道。据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俄罗斯族人居多,转盘这儿有一个水井,是整个街区唯一的生活水源,就成为活动聚集地,人们在水井边乘凉,在树荫下拉手风琴,唱歌跳舞、聚会、举办婚礼。
如果给这个叫六星街的地方写说明书,有几个关键时间节点是必要的。2009年,六星街列为旧城保护性改造的重点项目,保留了原始风貌;2010 年被命名为新疆历史文化街区;从2019 年开始,市政府对六星街区建筑风貌、生态环境、经营业态实施全方位保护,那是对六星街更新改造提升成景区的起点。流光溢彩的城市史就此掀开一角。
从那时起,巷道的一侧,各种施工材料堆放挤压,路况变得狭窄而复杂。这个位于城市北侧,占地四十七公顷的街区,倘若就年轮来算,历史并不算长。据史料记载,1934 年,伊犁屯垦使公署由霍城惠远迁至宁远(今伊宁市),伊犁屯垦使邱宗浚聘请德国工程师瓦斯里在1934 年规划设计之初,将源自欧洲规划理论的放射形路网,与中国各民族传统院落组合而成。从路牌可以得知,六星街由纵横交错的三条主要街道形成,分别是黎光街、工人街和赛里木街。而在1964 年之前,这些街道并无自己的专属名字,它们被人们统称为六星街。
经过近百年的变迁,多民族聚居的六星街在纵横之间交织出奇特的文化共生现象,这是它最显著的价值所在。来自首都的城市规划师李昊,走过世界很多城市,心中有着理想之城的标杆,对于现实中的城市评价,有时难免苛刻。然而,站在六星街上,他说:“对于六星街,我实在是无法不赞美它。在这样中西合璧的街坊中漫步,很容易感受到城市独特的文化个性。在某条路上,我似乎依稀能看到英国莱奇沃思那样的田园小镇风貌,历史的变迁又仿佛重现眼前。城市幸福感,也就来源于这种生活气息。”
在六星街,那些刷着蓝色围墙、屋顶或门柱的庭院,传统与现代融合并存,以马赛克般的形式展现出了城市文化的多样性。蓝墙之外,一架花篱,摇曳着田园诗意。在游客眼中,走进迷宫一样的巷道,仿佛走进一处公共艺术展示中心,演绎着绚丽的民居和鲜活的民俗生活。
新建的中心小广场不大,长椅供人歇脚,老人推着婴儿车走累了,坐在那里休息。天气晴好的时候,常有一个俄罗斯族白发老人戴着墨镜,坐在那里即兴演奏手风琴,当他展开右臂,徐徐拉开琴,微眯着眼,能感受到神情的舒展和自我的存在。他或许在琴声中回忆:某年的某个夜晚,那时候族人众多,时常有家庭聚会。面包香甜,热茶温暖,姑娘们的歌声笑声像解冻后的冰河,哗哗啦啦奔涌,起舞助兴。他还是英俊小伙,拉着手风琴伴奏,深情的眼眸随着紫色的裙子旋转翩飞。如此生动的景象,属于年轻时代,只有爱情才能展开眼神对视之后细节纷繁的剧情。
周末或者节假日,小广场常有群众自发的演艺活动,以老年人居多。巷道里也有年轻人自组的乐队聚集,歌声充满真诚和梦想的力量。玩乐器的小伙子卡尔帕提穿着牛仔裤和蓝色的圆领衫,他擅长把都塔尔弹奏与现代电子曲风结合编曲,配上他的烟嗓,即使最熟悉的流行歌曲,也会在星星闪烁的夜晚,给听者带来另一种惊喜和感动。
一年夏天,在六星街音乐庭院里,一场民间艺人的专场音乐会正在进行。我再次见到卡尔帕提,还是一样的牛仔裤、蓝色短袖衫。灯光迷蒙,烟嗓婉转,唱着感伤的情歌,仿佛时光真的停滞在了某一刻,定格在了某场回忆之中。幸好,他所处的场景说明了这个酷爱音乐的男孩在时间的激流中保持自己的节奏,平稳一点,闲适一点,每一天、每一年都没有与音符分离。
民间艺人赛努拜尔的都塔尔弹唱响起。
请你将茶杯倒满
如若能再次相遇
我的心会无穷地开心
总是会倾诉彼此的感情
能和最亲的人一起哭泣
也想和最亲的人开心
……
即便是跨越语言、地域和民族,这种质朴深情的歌唱总会让不同的人获取共鸣。朴素、浓烈、坚韧、温暖、纯净、深沉,这些可以无限堆砌的形容词,皆不足以描述她的歌唱,她的都塔尔早已与家乡、土地、亲人和生命融为一体。每一种乐器都有各自的灵魂,借由一双双弹拨的手,将生活的褶皱填满美妙的音符。
作家罗伯特·瓦尔泽曾写道:“在夏天,我们吃绿豆,桃,樱桃和甜瓜。在各种意义上都漫长且愉快,日子发出声响。”夏夜在六星街,歌声萦绕、器乐悠扬、笑意欢畅,有相亲相爱的人,有远方来客,灯火阑珊,人间值得。哦,就是那个难以忘却的夜晚。演出结束后,我和友人却找不见车停在了哪里。我们从巷头找到巷尾,找了相邻的两条巷道,终于找见,七转八拐,驶向回家的路。
人流在街角汇合又离散,街边的树,庭院的花,承载的记忆和情感更广大复杂。街区的魅力藏于树荫之中,光晕的斑点打在墙上、路上和人们的身上,随风晃动,梦境一般记录着四时的更替以及岁月的年轮。我有时路过看见老人坐在树下发呆,他身体欠安?不,也可能往事正在回忆里卷土重来。还有一次,我在树下等人,无意瞥见身边白杨树上有一行刀刻的小字——我在这里等过你。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就用一句话概括终结,简单又复杂。这棵树就像一个亲历过重大事件的证人,身上携带着证据,无声无息老去。
白杨、槐树、梧桐、白蜡、橡树……在无法扩建的路边,向有限扩展的空间表达沉默。庭院里的人,从老人到孩童,都爱着街边的树,就像爱家人,从根部爱到树梢。院门内的人,来来去去,生生死死。路边的树,则一言不发,供那些回味往事的人坐在树下缓解孤单,获得一些旁白和物证。
古丽努尔嫁到赛里木街有三十年了,我去她家的时候,她白衣花裙候在门前,身材高大、热情温暖。房屋是本地典型的蓝色小院,走廊摆着红色的海棠,盆栽无花果树,还有那种宽叶的橡皮树。古丽努尔生在兵团,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高中毕业后分配在一家国营宾馆工作。她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出生半年后被诊断为脑瘫,她为了照顾儿子辞职。曾经多少个黑夜,她在丈夫的怀里泣不成声,在亲友们面前强撑欢颜。好在一家人相亲相爱,抵御着儿子残疾带来的悲伤。在家人的精心呵护下,原本被医生论断活不过二十岁的儿子,已经度过了二十六岁的生日。她还有一个女儿在特殊教育学校当教师。“女儿就是为了照顾哥哥学了这个专业,她可尽心了,教她哥哥认字写字。你看,这是哥哥给妹妹写的字。”小学生的方格本上歪歪扭扭写着“吃了,饱了。”四个字,热乎、踏实,看得我眼窝潮潮的。
老刘是锡伯族,娶了一个汉族媳妇,家住在黎光街二巷与江苏路的交叉处。下岗后,夫妻俩在街角开了一家小商店。他出生在六星街,熟人熟地。“我对这一片太熟了,活了六十年没有离开过。我年轻那会儿,巷道里只要出现个陌生人,我瞅一眼就知道他要干啥。”他说的没错,骑自行车的少年,来到一扇后窗下,车铃有节奏地叮当数次。屋里女孩听明白了,找借口出门,坐上自行车迅疾而去。母亲找不见女儿身影,赶紧关窗户,好像窗外的树叶在风中窃窃私语说闲话一样。更远处的一棵树,看见一对青年男女进了通用机械厂的大门,牵手游荡到月亮升起。“是我老了吗?过去的事情忘不掉,现在的事情记不住。”当年的通用机械厂早已荡然无存,一片住宅区覆盖了曾经红火的厂房,可在老刘心里,青春的回忆清晰如昨。谁说不是呢?我感觉,人到中年以后,眼前的事物越模糊,从前的事物却越清晰。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说:“在梦中的城市里,他正值青春,而到达依西多拉城时,他已年老,广场上有一堵墙,老人们倚坐在那里看着过往的年轻人,他和这些老人并坐在一起。当初的欲望已是记忆。”
依琳娜带我去过她的长辈阿拉娜的家,我承认自己带着很大的好奇心,这一点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有着怎样的故事和传奇?他们是中国公民,身份证上的民族一栏填写的是俄罗斯族。简陋的屋子里,最显眼的是墙上挂着的家人们的黑白照片。“这个,我妈妈,这个,我妹妹,她们都躺在六星街的墓地里。”
这所房子和里面旧式的物件告诉来者,这座城市里曾经生活过什么样的人,以及这些人在这座城市里曾经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阿拉娜的丈夫阿那托力久病卧床,卷曲的白发堆在头顶,面容清瘦。床下竟有四五只猫咪在玩耍,时不时有一只调皮地跳上床,从老人身上踩过去,像在鼓励床上的老人:要活下去,要生机勃勃。依琳娜用手指一指猫食盆,“看,日子不宽裕,啥时候来,盆里都盛着满满的猫粮,没亏着小家伙。”
我经常看见七十多岁、身体肥胖、走路喘气的阿拉娜,双手提着艳丽的裙裾在俄罗斯风情园跳舞,没想到家里是这样的境况。“我喜欢跳舞,管它呢,活一天跳一天,高兴就行了嘛。”
去年阿那托力去世了,阿拉娜还是照样去跳舞,碰上了就聊几句,她也不诉苦,只是淡淡地说:“一起生活六十年了,剩我一个人在家里不好受,出来跟大家跳跳舞,什么都不想了。”对于悲伤,人的天性中并无对症的良方。以往的岁月里,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在手风琴的伴奏下高歌跳舞,这是一种苦乐,一种达观。
皮特罗是东正教堂主事的人,白色的教堂沉默低调,礼拜日到此做礼拜的族人并没几个,这里是他们最后的精神家园。倘若要找寻俄罗斯族曾给予这片地域的影响,旧教堂、墓地、手风琴馆和那座经历了百年的俄式破旧大门……岁月沧桑都在六星街上得到印证。连多数本地人也不知道在闹市区竟然有这么一片古老的墓地。一个世纪以来,那些去世了的俄罗斯族人,就长眠在这块墓地里。从黎光街二巷进入,透过榆树的浓荫,当年的教堂只留下了门楼和角楼的一部分,破旧的大门上钉着一个黄色木条的标志。门外是繁华世界,而门里属于往昔,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寂静。
皮特罗的老父亲年逾八十,衣装洁净,络腮胡子浓密花白,坐在夕阳里,身影有一种失落的优雅。皮特罗说教堂祈祷用的小蜡烛都是他做的,老人时而有些糊涂。他一本正经地把我叫过来,在我耳边说,“我有一个秘密,我奶奶说了,不让我告诉别人。”
我们已听不到曾经回荡在城市上空起伏蔓延的钟声,却依旧有鸽子绕着教堂飞翔。那个在年轮里消失的人们聚集的六星街,偶尔会在皮特罗的老父亲口中“复活”。
这都是与六星街有着深厚过往与情缘的主人。我的成长时光与这片街区无关,反而能因此获得某种异质的、个人化的表达角度和感觉。我追溯着六星街的前世今生,我写过它,并不意味着我就了解它,我对它依旧陌生,依旧会迷路。
有一回我又迷路了,误入工人街五巷,巷口一户庭院外立着一株高大的蔷薇,根茎粗壮、枝条修长,一树娇艳的黄色花朵密密匝匝,特别壮观。我在花树前拍照、流连,冒冒失失走进院子和主人攀谈,忘了自己要去干吗,不过因此牢牢记住了那一树蔷薇。第二年夏天再经过那里,门口那一树黄灿灿的绚烂消失了,从邻居那里打听到这家人出租了院落搬走了。我站在那里,就像做了一场梦,怀疑那棵花树是我的幻觉。可明明好几个人都告诉我,那里真的有两棵招眼的树,院门外是蔷薇,院门内是樱桃树。改造后的庭院成了演艺餐吧,我进去过,在树上摘过甜美的大樱桃,而那一树蔷薇,竟然真的消失了。那么大一棵花树,怎么能移走呢?在另一个地方活着吗?
在新媒体视频里高调亮相的六星街,以个性鲜明的风貌和魅力成为这座城市旅游的新地标。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要到六星街走一走,否则就好似没有到此一游。
漫步在街区,民宿客栈、手工艺品店、餐厅、特产店鳞次栉比。咖啡馆、酒吧、饮品店越来越多。夜间灯火闪烁、劲歌热舞,往来穿梭的年轻人俊颜鲜衣、咄咄逼人的青春,让夜晚的六星街完全不同于白昼的小巷幽深。他们似乎在宣示:这街道,这座城,这时代,完全属于又一辈新人。
全新面目出现的景区让原本就找不到方向的路痴,更找不到路了。
王炜炜的民宿开在黎光街九巷,她和无数预定的游客一起经历着六星街的迷失时刻。因为找不到路,就在附近打转而放弃住宿的事时有发生。
——“导航那么精准,为什么你还找不见呢?”
——“你到了啊?不好意思,我出去接你,自己给迷路了。”为此,她亲自设计了手绘地图,拍成照片,发给每一位咨询的客人。
依琳娜在广场中心的俄罗斯风情园经营着一家面包店,建筑物明黄色的外墙加上墨绿色的木窗很是显眼。更明显的标识是,路边树荫下立着一个俄罗斯姑娘举着面包的彩塑。就算站在马路面对面的方位,顾客还是常常找不见。
——“看见广场上的三套马车铜塑像了吗?往马头正对的方向过马路就到了。”
——“三匹马?你指的是哪个马头对着的对面?”
这是依琳娜经常接到的询问对话,搞得她啼笑皆非。因为她自己也是路痴。“朋友听说六星街有好几家咖啡馆,让我推荐一下哪家的好喝,我大脑里迅速展开了地图搜索并确定了方位,表述时却无法说清楚到底在哪条路上。只好对朋友说,说了你也找不到,自己去转转吧,转到哪家进去就是了。”
看来,没有一个路痴能顺利进出六星街。
六星街成为“潮街”,三条主街上,大部分宅院被购置或者租赁,开设为时尚门店,新潮涌动、生机焕发,周围的餐饮被带动运转起来,所有业态共同依附在这个被称为“旅游景区”的生态圈链条上,像毛细血管一样相互连接,又相互供养。
六星街的好光景到来了,咨询招商政策的、打听房源的、装修开张的……很多客商没能等到来年春天,那条彼此供养的毛细血管,被疫情剪开一条细微的口子。谁也没想到,这条细长的口子,愈合的时间竟然长达三年。这三年,太难以描述了,感觉时间在瓦解,日子既飞逝而过,又好像永远过不完。
无论因何而阻隔,时间的脚步总是坚定不移朝前走的,年轻的人和事永远像浪潮一样滚滚而来,那是发展的力量,在每一个时代成为不羁的风尚。即使游客稀落,新店铺依然登场,明丽的色彩刺激着斗志,经营者对未来充满信心。就像草原上的火灾,土地完全被烧黑烧焦,所有绿色都消失了,可烧焦的土壤养分更丰富,新的植被长得更茂盛。人也是这样,他们总能找到办法,怀揣着希望重新开始。
许多人在崭新又永恒的当下面临选择,“韧性”再度成为一个具有神奇魔力的字眼。所有的问题似乎都来自一种信念,失败也好,痛苦也罢,各种人生障碍不过是一个终会过去的糟糕时刻。新的造梦逻辑,带来新的希望和新的迷茫。痛苦正在过去,遗忘还没来得及发生。但无论如何,六星街正慢慢从寒冬的阴沉走进阳光明媚的春天。
春节前,我带女儿去拜访一位暂居六星街的电影导演,聊得开心,不觉忘了夜已深。告辞以后,母女两人又转向了,索性顺着路随便走。除了行驶而过的车灯,几乎没有行人。走着走着,见一家院门口亮着灯,两个巴郎在卖烤肉串,孜然的香味绊住了女儿的脚步,她站在烤炉前吃得那么享受。
那个夜晚,空气寒凉,圆月高悬,天空明净。月亮下面什么都显得美,忧愁也可以转化成诗意,要是月亮旁边闪着星星更是感觉美妙极了。我和女儿继续沿街步行,像把一本旧书一页页翻过去,读出新意味。长大的孩子,蒲公英一样随风四散,即将大学毕业的她将飘落何方?这个冬夜,一盏小灯照亮的院门、烤肉的香气,不知道会不会让离家的孩子长久挂念。
这样的夜晚,以前没有出现过,像电影镜头般美好,转瞬就消失了。我记着,写下来,这美好就获得了永恒。
冬天过去了,春天过去了。五月,初夏来临,晚霞渐出,浅浅的金色余晖照耀下,六星街的玫瑰在空气里晕开,自然而热烈。这样的一个夜晚,皮特罗的老父亲溘然长逝,带着他奶奶的交代,那不能告诉别人的秘密,再也见不到天亮。送别老人那天,我走在黎光街四巷,路边的树干斑驳得就像生活的裂痕,树还是那些树,在太阳最炽烈的日子也能感受郁郁葱葱的凉。生离死别终将来临,我们在怀念一个人的时候,到底在怀念什么?有些告别是无法说再见的,那就叫做永别。但是你想起那个人,汹涌的思念无法停止。那些树叶缝隙里投下的光影,就是生命里最珍贵的记忆。
想想前些年也走过这里的小巷,日子静谧漫长,街角的小店放着陈奕迅的《十年》,听歌的人心想,十年后的岁月遥遥无期。后来在小巷里又听到《十年》,不禁轻叹浮生也不过转瞬。如今走在这里,反倒是会被不经意间撞见的某一个场景打动——同行的人,吹过的风,琴弦里流淌的诗,来不及告别的名字,树皮上刻着的誓言……一切的一切,自然、平实,又自带温度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