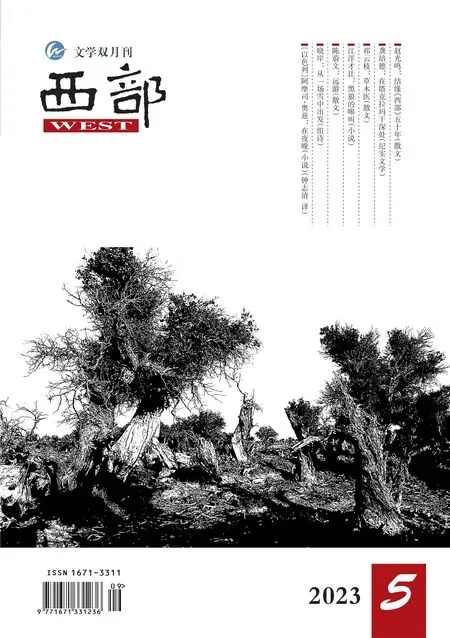远游
陈蔚文
1
当名字变成一个床号,十四床,我又一次进入到一段白色时间中。那天是周日,还有一周过小年。趁中午阳光晴好,洗头洗澡,午睡了会儿。下午阿姨来打扫,我正往大锅里注入开水,准备用来泡父亲送来的一大袋子菜,江南老家的“落汤青”,用盐开水泡几天就变成了别有风味的腌菜。
突然身体右侧一阵疼痛袭来,熟悉的,在近年内已发作过几次的痛。尚不能完全确定,这是阳过后的半个多月,也没准是久咳后导致的痛。
我在桌前坐下,喝了口茶,在网上看了些轻松内容,期待痛的缓解与消失。
然而没有。它延续到夜晚,十点半发微信给曾给我治疗过的二附院主任,描述了症状,问他是否需要拍片。
他回了,根据他的判断,我十之八九是旧疾复发。但科室已改成“新冠重症病房”,没有床位。为此他打电话给同事又确认了一次,一张床也没有,他说,“你赶紧去一附院挂急诊。”
没有他的催促,或许我会拖到次日。他的催促让我从床上爬起,穿衣,只拿了手机和先生出门——这一走,直到七天后我才回家。
2
因为是呼吸类疾病,医院按重急症处理,安排了加急CT。结果即刻出来,确是复发了,第四次复发。许是因为阳后体虚,许是因为久咳,或其他不可知的原因——与疾病打交道多年,你越来越知道“不可知”在病中的比重。没有为什么,没有显因,就是摊上了。
看片医生打了电话给科室住院部,幸运的是,刚好有一张空床,下午才空出的。
赶紧办入院。
深夜,在医生办公室,我提出有无保守治疗的可能。当即遭到否定。年轻的医生说,明天下午主任来查房时,会比他更坚决地建议手术。保守治疗容易复发。
“但是,我之前已做过一次手术,还是复发了。”我知道这个说法不会得到医生认同,去年我特地去上海看了位专家,他的意思,即使复发过,但手术仍然是目前治疗的第一选择。
次日下午主任来,果然建议手术。安排在次日第二台。
当别无选择时,平静下来回想周日中午起意洗澡——通常我会在睡前洗,那天为何中午洗好呢?难道预感下午会旧疾复发,即将入院?
晚上九点后不能喝水进食,因为疼痛,躺下都费力,只能侧身睡。半夜护士来查房,邻床老太呻吟:“我好难受。”她不停叨念着。她的儿子,一个面目温暾的中年男人从病房外的椅上起身进来,给她倒水,大声问询。这个男人和他从深圳回来的老姐姐轮流夜值。
白天老太太精神不错,问医护:“我好些了吧?”
“你自己觉得呢?”
“我不知道。”八十岁的老太太的样子有些像懵懂女孩。
肯定好多了啊。医护人员说。
老太太是因为基础糖尿病的状况入院的,已住一周。从病情考虑,她的饮食被限制,她一直要求吃这吃那,女儿不答应,只少少地喂她一些食物。从老人的胃口看,她显然好多了。病友们说,她已是相当幸运的一位老人。
为何到半夜她就叫唤呢?
“她就这样,白天睡足了。”从深圳回来的女儿说。
3
近中午十一点,手术室来接。手术床在地面移动,发出咯隆隆的金属摩擦地面的单调声。熟悉的声音,一如熟悉的疼痛。声音传导到侧卧的背部,经历这些年的折腾,我已无惧。或更准确地说,想缓解病痛的愿望战胜了手术的恐惧。
当医生说,只有一种方案可以解除疼痛时,你甚至希望手术早点进行。
痛不欲生、痛之入骨、切肤之痛、痛楚彻骨……这些词语像泛着寒光的刀刃,又像一条毒蛇嘶嘶作响的蛇信子,在人体内游走,或驻于某处,释放毒液。
我对痛的最初印象是患胃癌的外公,他在生命最后阶段,消瘦异常的面庞显示病痛残酷的折磨,那还是八十年代中期,疼痛医学远没今天发达。
手术床在候诊区等待,在我的左右还有两位病人等待,她们要进行的是乳腺手术、结石手术。第四位病人又推了进来。
结束上午的第一台手术,主刀大夫们可能正用午餐。手术床排在一起,没人说话,安静地等,等着推向不同的手术间。
某间手术间的门滑动启开,终于到我。
“上手术床。”
我从推床爬上手术床,头顶是圆形无影灯。面部被罩上一个罩子,医生开始询问姓名年龄,核对信息。还有身高体重,以确定麻醉用量。主刀的主任还没出现,也许他只有等病人麻醉后才会现身。
麻醉通过之前预置的手背输液管流入,冰凉清晰地滑动,当滑动到脑部,意识瞬间有点模糊。
醒来时,听见有人唤我的名字:“醒醒,睁开眼!”我像从某条幽深的海底隧道潜回。
后来知道,推回病房是下午三点半。
4
手术当晚,已是十二点多吧,突然一个女人匆匆推开半掩房门,进病房,她径直奔向洗手间,关门。
是谁?深夜这般突兀地进来,老太太的女儿也发现了,她从椅子上起身,敲洗手间的门。门没开,老太太的女儿在门外质问:“你谁啊?谁让你进来的?”
冲水声,女人出来,嗫嚅着,说是医生让她来借用一下的。
“哪个医生?你是病人家属吗?是家属怎么不到自己房里用洗手间?”
女人低头匆匆走了,不知如何辩驳的仓皇。
老太太半夜又开始叫唤:“我好难受。”她女儿问她哪里难受,老太太说不出,只不停哼。绵长,一哼两钟头。
护士进来查房,记录术后体征;有家属在走廊打电话;呼叫护士的摁铃声……术后第一晚,伴随着这些声响,几乎未眠。
第二天上午,医生通知有个单间空出,下午可搬。病房靠近走廊顶头,双床,方便家属陪护。安静不少。能睡得好些了吧,但当天深夜,突然又匆匆闯进来一女人,虽看不清脸,可肯定不是前晚的那个,她同样直奔洗手间,才迷糊要入睡的我醒了。怎么回事?
我们向护士反应,问是否有可能进贼?结果护士说,应是楼下ICU 的家属,四楼无公用洗手间,家属经常上到五楼,随机找间病房解决内急。
“也不容易,”先生说了句。我想到头天深夜,十二点多匆匆进来的女人,即使在不明亮的灯下,也能看出她疲惫的面色。ICU 内是她什么人呢?必是至亲才会深夜守候吧。ICU内,至亲是否又能脱离险急,重返日常?
没有人再匆匆推门而入,直奔洗手间了。
5
术后四十八小时,镇痛泵卸去。引流管还在体内连着引流瓶。外物的侵入势必造成身体的不适与疼痛,加上不时地咳嗽震动伤口也会造成疼痛。
世界卫生组织对疼痛等级的划分为五种程度,末两种Ⅲ度(重度疼痛,疼痛持续,难以忍受,无法正常生活及休息,必须用药物才能缓解)和V 度(严重疼痛,疼痛持续,且伴随血压、脉搏等变化),应当就是人难以耐受的程度了。
1979 年,国际疼痛学会在世界范围对疼痛进行了定义。《中国疼痛医学杂志》的翻译为,疼痛是一种与实际或潜在的组织损伤相关的不愉快感觉和情绪情感体验,或与此相似的经历。
岂止是不愉快?是痛苦,是折磨。但同时有资料说,痛是人类进化的结果,它可以使我们免受更大的伤害;痛会提醒我们正处在或大或小的身体危机之中,同时也引导医生用最恰当的方式去解除这种危险。无痛病人之所以危险,是因为无痛不但会使病人自己失去警觉,而且会使医生丧失正常的审断。
但,显然不是所有的痛都能得到解除。晚期病人的痛就是无解的,只有痛在消耗已虚弱不堪的肉身,将其榨干。痛是身体燃起的信号,同时也是可以反噬的火焰。
凡耐受过疼痛折磨的人,都能理解“安乐死”的必要吧。比起死的恐惧,对痛的恐惧更甚。
因此,疼痛治疗不只是身体医学,还应当是伦理学、人类学,疼痛事关人的基本尊严与权利。据说,早年,人们认为痛是神灵对人类的处罚,它对德行出现污点的人类起到警告与惩罚作用。不,痛和道德无关,痛只是人类肉体机制先天存在的缺陷,它理应被现代文明与技术的进步逐渐克服。
2007 年,疼痛在我国第一次作为一级诊疗科而确认存在,代码“27”。这意味着,疼痛本身被作为一种疾病对待。它不再只用来考验肉体的意志力和忍耐度。
“世界以痛吻我,我报之以歌。”这个“痛”一定不是身体的,当痛把一个人折磨得奄奄一息,是没有气力“报之以歌”的……
我躺在病床,胡思乱想。插引流管的右胸部位在痛,手背在痛,静脉留置针已几日,许因为血管细,护士进针较深,导致痛感加剧。
比起重症病人的痛,我知道我的痛已算轻量级,可这并不能因此取消痛感的真切存在。就像即便想到忍受酷刑的英雄,也不能使我的痛化为乌有。它细密地存在于我的感知中,每咳一声,伤口震动一次。夜晚睡前,我服用了两颗止痛药。
在前些天,阳了的当晚,发烧导致腰椎和膝盖痛得躺平都困难,服用了一粒布洛芬后,痛才缓解。之后又开始了剧烈的咽痛。世界杯卫冕当晚,全世界的球迷都在疯狂为梅西欢庆时,我在卧室一圈圈走,如困兽。布洛芬止不住咽喉的剧痛,梅西的夺冠也止不住。
人,只能独自面对痛苦。
曾有记者问史铁生:“当你失眠,或者身体疼痛的时候会做什么?”
史铁生回答:“写作。只有写作是我身体疼痛时唯一的精神寄托。”
史铁生是我敬重的作家,这个回答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话,如是原话,他的境界是我企及不了的。当身体疼痛时,我什么也做不了,最经典的阅读也不能稀释这痛。我只能在房内转圈,或靠着床头,等待痛的放过。
痛,是人类原初的恐惧,癌症的疼痛发作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四,“有时候给患者带来希望的是每天九十毫克的吗啡,而不是靶向药”。
6
镇痛泵卸去后,身体疼痛明显。深夜,两粒止痛药大概提供了四小时的镇定。听见雨声,天已灰蒙,雨声透过小半扇开窗传进。不知几点了,时间在医院消遁,护士掌管时间,打针、测体温、服药。
会好起来的,当然,尽管复发四次,这疾患仍不至要命。可有些好不起来的人呢?譬如ICU 病房内的患者,此刻他们能听见窗外雨声吗?若能听见,会不会有些留恋?还是他们已不想囿于这具痛苦肉身中,被各种抢救设施缚牢,想早些解脱而去,融入天地间的雨声中呢?
听说那个半夜哼叫的老太太明天出院,虽然她自己不情愿,为此和女儿发生不快。女儿怪她在医生面前一直说自己“好难过”,影响出院,她觉得母亲矫情。“你知道多少老人在这一波中走了吗?我们这么些人围着你,没有自己的生活吗?”女儿穿红色运动衫,六十多岁看去麻利能干,她急着回深圳带外孙。她每天和外孙视频,在医院的耐心已到极限。
次日上午,病床靠门的老太太独靠床背,儿女去办出院手续了。路过她的病房,她一脸茫然地注视虚空。这个瘦小的老太太,丈夫早逝,她一直独居,近些年住进养老院。她不想出院,是否因为不想结束儿女在身边陪护的时光?这应是她感受的最后一点温情。在八十岁的衰弱中,兴许她恍惚自己还是可以撒娇的女孩,亲人一叫即到,送汤喂药。儿女各自散去后,留给她的只有孤独。她夜半哼叫的“我好难过”可能是真的,不一定全是肉体,是走向终点的途中感到的惶恐。
7
手术前一天,女友发来微信,告诉我她父亲去世了。此前,在ICU 几日,病情似有稳定,却又急转直下。
“妈妈看到了从爸爸身体里拔出的长长的胃管,不寒而栗。对我说:‘如果我病危,一定不要给我插各种管子,哦,不,是千万别送我进ICU,进了那儿就由不得自己了。’”
女友的妈妈是《秋园》的作者杨阿姨,八十岁时她写下自己母亲的故事,又写下自己的故事,连续出版了好几本书,获得许多奖项。
女友和妈妈说到预嘱,告诉她可以先立下身后心意,并说自己再过一些年头,也准备这么做。杨阿姨第二天就写了,告诉女友放在哪个抽屉。那晚,她又说起愿望,生命的最后时光别让她受罪,让她平静地死在自己家中,让儿女一定要照她的心愿办。
我想我也会和杨阿姨、女友一样选择。事实上不少“病危”是器官老化带来的衰竭反应,是最基本的生物学过程,非要人为干预,让人成为仪器的配角而延缓几天“活着”,实无必要。
人活着应当坚强,但不能只为坚强而活着。“生命不息,抗争不止”成为关于人类忍受能力的一个极高赞美,这赞美有时成为隐形绑架,带来过度治疗和病患的巨大痛苦——人的血肉之躯,注定存在抗争的局限性。
“我更主张理智的悲观主义,而不是虚假的乐观主义。”《从容的告别:如何面对终将到来的衰老与死亡》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在ICU 工作多年的重症专家希尔曼说:“我们要讨论治疗带来的负担是否会超过收益,临床医生经常会过高地估计治疗措施的意义,而低估其伤害。”这位有人文精神的医生呼吁以患者为中心,纠正对医学的误解——并不是不惜一切代价延长患者生命就是“医学”。
绝大多数人对如何走向终点没有真正的选择权,因为对死亡的禁忌,在他们尚清醒时,这个话题也不会付诸讨论。
2022 年,深圳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生前预嘱立法的地区,规定如果患者立了预嘱,“不要做无谓抢救。”医院要尊重其意愿,让病人平静走完最后时光。
有学者提议,生前预嘱应纳入医院病历和公民健康档案管理系统中,通过全国性立法一以贯之,让每位患者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临终抢救方式。
其实我很想和年迈的父母聊一聊这个话题,始终没有机会,难以说出口。长期以来,对死亡的禁忌使有关死亡的话题变得凝重,乃至丧气,但这的确又是无数家庭,也是后现代医学要面对的问题。
对新生,人们做好了迎接的各种细致准备。面对死亡,人们却常惶遽上阵,当我们想和即将离去的亲人讨论些什么,听听他们的心意时,他们往往已无法再说出……
8
一朵在海洋里漂流了无数个春秋的小海浪,它享受着海风和空气带给它的欢乐——这时,它发现前面的海浪正在撞向海岸。
“我的天,这太可怕了,”小海浪说,“我也要遭此厄运了!”
这时又涌来另一朵海浪,它看见小海浪神情黯然,便问:“你为何这般惆怅?”
小海浪回答:“你不明白!我们都要撞上海岸了。我们所有的海浪都将不复存在!这不可怕吗?”
那朵海浪说:“不,是你不明白。你不是海浪,你是大海的一部分。”
——在病床读到这段话和在其他地点读到是不同的。术后第五天,布满注射瘀痕的右手输液时突然手掌濡湿。血管堵塞,漏液了。护士拔针,在左手重新找血管,用最细的针进针。
输液缓慢坠落,我在手机小程序上随意找了本《相约星期二》,多年前的一本畅销书。美国作家米奇·阿尔博姆创作的自传体小说。故事真实讲述了作者的恩师莫里教授在辞世前的十四个星期,每个星期二给米奇所讲授的最后一门人生哲理课。
年逾七旬的社会心理学教授莫里在1994年罹患肌萎缩性侧索硬化,这种病是肌肉神经方面的绝症,肌肉会逐渐萎缩,导致死亡。莫里教授时日无多。米奇每周二都上门与教授相伴,聆听老人最后的教诲,并在他死后将这些教诲整理出版。
两朵海浪的对话便是书中一段。这段轻巧似寓言般的对话,是对死亡的最好安抚。人恐惧病与死,不就是怕撞向海岸后,成为泡影吗?如果换个角度想,撞向海岸后,就此融入大海,成为一朵新的浪花,也是生命的循环。
树叶化作腐殖,蒸气变成雨水,万物是循环的。人会以某种方式回归万物。
非常喜欢布莱森在《万物简史》中的一段话:
在构成我们身体的数以亿计的原子中,每个人都肯定穿越过很多恒星,并且曾经是数以百万计的有机体中的一部分,这其中包括其他人类成员,然后按照它们的方式,变成了你这个人。
死亡无疑是大自然基于现实做出的合理安排,不然,人类会如萨拉马戈的小说《死亡间歇》中写的荒诞场景——死亡被取消后,一代又一代人汇入耳目昏沉的浩浩大军,即使他们衰老病变,仍不准离开。哲学和宗教也失掉意义,蒙田说过,探讨哲学就是学习如何去死。现在全都不死,宗教和哲学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
之前人们认为死亡是种灾难,现在发现“不死”是新的灾难,就像太阳没完没了照射,永无夜晚和月光一样。萨拉马戈用貌似黑色的荒诞击碎了“不死”的人类神话。
9
南方的小年,拔了引流管,出院。两周后的年初八拆线。整整七天没出过医院楼层,街道上的景和人几分陌生,也几分可亲。又过了一关。在一次又一次过关中,感到疾病无所谓“战胜”,是的,疾病的强蛮不测,与人力间的悬殊,用“战胜”这个词也许有些逞强。但人的韧性同样不可小觑,生的本能使之一次次闯关。
过了小年是大年,群里各种祝福,有人贴出一副对联,左:辛弃疾,右:霍去病,横批:康有为——无疾多吉从来是根植于人类内心的祈福,正因难以长久实现,所以才成为美好祝福。
当然要做好某天闯不过去的准备,那必然会到来的一天。
日本作家小川糸的《狮子之家的点心日》中,主人公雫小姐查出自己罹患不治之症,并已发展至晚期,“我以自己的方式努力与它抗衡过,面对它的强势,终究败下阵来。于是,此刻的我坐在这艘客船上,离开了长期居住的公寓,解除了租赁合同,并决定在狮子之家聊度余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生与死是一体两面般的存在,”带雫小姐参观的护理师停下脚步,对她说,“区别只在于从哪一侧推开那扇门。”
在“狮子之家”度过最后时光的客人,如果去世,正门入口处的蜡烛会被点亮二十四小时。“客人的遗体从正门运出,送去火化。这与在医院去世不同。在医院,病故者的遗体总是从后门被悄悄运走,尽量不引人注意。”
在这个叫“狮子之家”的海岛安养院,有耐心的医护,有美景、美食,还有一只亲昵大狗的陪伴,雫小姐面对流沙般迅速溃散的时间,逐渐接受了与亲人的和解,还有告别。
译者说:“年初和夏天时,两位对我来说格外重要的亲人相继离世。记得译写的日日夜夜,我的内心清晰地分裂为几个自我。一个同自身的悲痛抗衡,一个同女主角交谈,一个同作者交谈,还有一个仿佛提着灯笼,与读者站在萤火明灭的水面之上,遥望尘世。”
“萤火明灭的水面之上”,这多像一幕告别的场景啊:死是生的倒影,水面之下是另一个世界,当人走到尽头,自然地滑向水下世界。水面上的人,倘深夜举起灯笼,会见到水下想见到的身影。
生与死是互为映照的镜像。
雫小姐最终走得安详。在以治愈为目的的医疗体系中,这样的离去像个童话,同时也让我们思考,一个人可以有更体面、温煦的告别方式吗?临终能否得到更多关怀?“狮子之家”描绘了一种可能,离开理应有更多选择。在山间,在湖畔,在海边,又或是家中,死亡伴随静谧、理解,而不是冰冷、恐惧,就像迎接新生命的鲜花与欢笑,在通向终点的路上,也应当有温柔的芳草,微风吹过,像送别一位即将远行的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