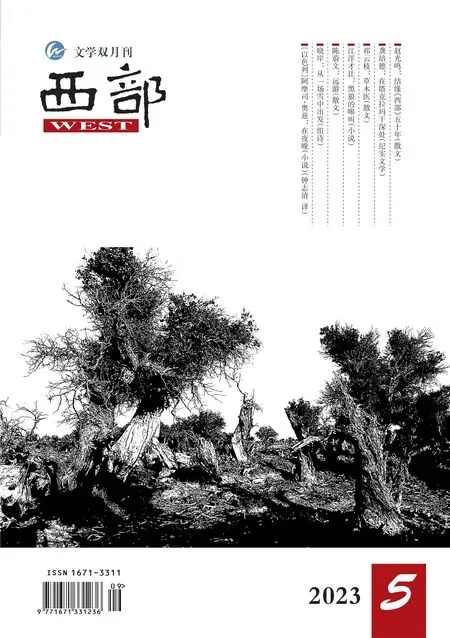来自星空的碰撞
杨遆峰
一
张紫曼忽然有些恍惚。
这事,成了她的死穴。被它一戳,她的身体立马七零八落了。
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床单,白色的被褥,头顶雪亮的灯管,还有永远都是一身雪白的医生护士。这巨大的白,铺天盖地袭来,连点缝隙都不给她留下。这一方雪白的天地,像河蚌一样,把她死死嵌在里面,想逃出来都困难。她不得不在这片巨大的白里凿个洞,蜷缩进去。时间长了,她都成河蚌里的软体动物,全然没了骨架和精神,仅剩一点残存的血肉,够她苟延残喘就行了。
又进医院了,不同的是,这次来的是邻省省会的医院。
母亲、她和这个庞大的孩子,三个人,像个行动小分队。只要一听说哪里的医院能治这种病,她们就火急火燎赶来,赶考似的,仿佛一考就能中,要是错过机会就太可惜了。她们领上他,去县城医院,去太原,再去北京,天南海北奔波,就连穷乡僻壤的赤脚医生也不放过。但都没效果。
张紫曼想不通,好好的孩子,一岁就会走路,慢慢会叫爸爸妈妈。到三岁后,心理却渐渐停止发育,仿佛时间绕过了他,让他的心智不再前进。医生说他得了一种叫孤独症的病。于是,开始给他看病。各种药剂、药片,各种液体,轰隆隆灌进他体内,把他的身体浇灌得异常庞大。八岁的孩子,看上去竟像十二岁。只是眼神还稚嫩,像婴儿的眼睛。如今孩子又不会叫爸妈了,他把原来的语言毫无保留地收回腹内,亲手埋葬了它们,连点残骸都没剩下。
病房比较宽敞,旁边那个床铺一直空着,她和母亲可以躺上面休息。其他病人受不了这庞大男孩叽里呱啦乱叫,还咬自己胳膊,所以不敢住进来,担心一不小心被咬了。一时间,她感觉这病房就是她家的。
第三天,病房里住进来一个男孩,脑袋因为打篮球受伤,男孩父亲陪护。很快,这个男人发现,临床的这个庞大男孩不正常。男人就像家犬护崽子似的,生怕庞大男孩冲上来咬他孩子一口。他瞪大眼睛,时刻盯着庞大男孩的一举一动。
她看着对面这个男人,三十来岁的样子,还算文质彬彬,满脸都挂着紧张,连换气都顾不上,似乎稍一放松,他的孩子就会被咬得满胳膊流血。她嘴角一撇,心想,一个大男人竟然担心一个小孩会伤害他们,真是可笑。同时,她又感到悲哀。很显然,在男人眼里,她家这个庞大男孩是不正常的。她把眉间的肌肉松开,让眼角努力挤出一点笑意,说,放心,我家孩子从不伤害别人。母亲此时也跟上,笑着说,就是,他只是喜欢咬自己,还有,还有就是……
她轻轻碰了几下母亲的脚,心想,够了,难不成还要把孩子的缺点和盘托出吗?因为她敏锐地察觉到,男人笑了,一种轻蔑和放松的笑在他眼底晃荡。那意思好似在说,好,不攻击人就好。紧接着,男人的眼里又泛出得意,似乎为没生下这种孩子而庆幸。
她问男人,你家孩子多大了?
八岁,阿姨。孩子自己说出来的,还甜甜地叫了一声阿姨。这让张紫曼实在不舒服。那孩子低头看书了,她看见封面上写着《弟子规》。
男人顺着张紫曼的目光看了一下,得意地说,我家孩子还会背好多唐诗宋词呢。
她慌忙从孩子那里收回目光,瞥了一眼男人那张得意的脸,心里满是醋意。
她有些心烦意乱,让母亲照看一下孩子,她太累了。母亲领上庞大男孩出去了,她则靠在枕头上使劲睡,睡眠对她来说,是件奢侈品。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被脸上湿漉漉的水惊醒。忙起身看枕头,原来是嘴边的涎水肆无忌惮地流到枕头上,洇湿了枕头。她不好意思地赶紧用余光扫扫周围,看有没有人看见。她的眼角一扫,就发现的确有个男人在偷偷看她,她能感觉到那偷窥的目光像小动物的皮毛一样,轻轻蹭着她的皮肤。蹭着她哪里的皮肤呢?她快速想了一下,不对,是胸脯。她忙低头看,果然,她衬衫上面的第一个扣子开了,足够那人的目光收割一阵子了。她能感到男人目光的贪婪,那是来自一个雄性想要攻击的目光。她忽然有些惊喜。她太久没让男人碰了,久到竟然忽视了自己还是个女人。
她才三十一岁,却像保姆似的,伺候弟弟一家。因为弟弟有些轻度智障,所以当初她照顾弟弟结婚,为他娶下媳妇。没曾想,却给她怀里强塞了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这些年来,她都不知道女儿和丈夫是怎么活过来的。只知道丈夫到处给大小商店送货,整天钻胡同。父女俩的一日三餐衣服鞋子之类的,她都顾不上过问。女儿看她就像看一个陌生人,连热情的表情都省了。丈夫把满腹的不满和愤怒化作凶狠的目光,使劲剜她,那架势非从她身上剜下一块肉不可。那眼神告诉她:你虽然嫁过来了,但却像个倾家荡产做慈善的人,毫不顾忌我的感受。
她能不知道丈夫偷偷找女人的事情吗?她不过是装聋作哑而已,她只是觉得太亏欠他和孩子了,她连责骂他的资格都没有。她能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已经不当她是一个女人了,对她身体的渴望也戒了。她能怎么办呢?她清楚自己无能为力。
二
如今,这个同一病房的陌生男人竟然偷窥她,男人眼角的那丝贪婪让她感动,让她忍不住想哭。
她假装没看见他,还索性弯身子,让身体线条更加凹凸些。她很享受他的目光,她怕惊动这目光,就像怕惊动小鸟觅食一样。
可是,母亲带着她庞大的孙子回来了。她知道,那从不远处偷偷爬来的目光就要收回去,她有些失望地抬头看男人。目光很快接上,她的眼里没有对他的埋怨,反而有种温柔的水波。这水波刹那间抵达男人的眼睛,他似乎明白点什么。他慷慨地向她笑,太困了吧?见你睡得很香,好羡慕。
她不好意思地坐起来,擦擦嘴,整理一下衣衫,又抬头朝男人笑了笑,脸上的皮肤没以前那么紧绷了。
他说,你还很年轻吧?
这句话让她感动半天,尤其那个“很”字,这是给她的最大肯定。她忍不住娇嗔地反问,你以为呢?话音刚落,她都为自己的矫揉造作感到脸红。
为了避免母亲看到她的窘态,她借口有些口渴,出门到热水房接水。忽然,她感到屁股被人轻轻拍了一下,那感觉像一只手在试探一盆水的温度似的。她猛然回头,马上触碰到他的眼睛。一看是他,她的目光马上软下来,体内的那点恼怒立刻烟消云散。她挪开身子问,你也渴了?
他的目光绑住她,眼里满是笑意,是那种喜欢的笑。他指指自己的胸膛,说,是这里渴了。
她抿嘴笑了。
她一时头晕目眩,她跋涉了八年,心早就提前老了二十岁,仿佛早已过了和男人打情骂俏的年龄。而这个男人,却一把将她重新拉回那个年龄。
她竟然身不由己地冒出一句,你老婆呢?这句话本身就有点暧昧。
他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没有张口。他的表情让她感到,似乎他家是个秘密,应该永远封进密封瓶里,是万万不能向外人道的。
虽然他没说,但她隐隐感到他身上蛰伏着一种不幸。他越平静,就越能证明这一点,就像平静的湖面下不知暗藏什么危险一样。她好想让他掏出更多的痛苦,最好是一部苦难史才过瘾。长期以来,她浸泡在烦躁与伤心的溶液里,她希望有更大的痛苦撞到别人身上,好把她比下去,能借此把她内心的伤痛好好稀释一下,好让她觉得她的磨难其实不算啥。她极力掩饰自己的表情,她得把她内心蠢蠢欲动的窃喜强压下去,装出同情他的样子来,免得人家责怪。
三
夜很静,已经深了,医院的走廊静悄悄的。张紫曼被那个男人牵着手,像只乖顺的羔羊。她看见连护士都把脸埋进臂弯里,沉沉睡去。值班医生的门紧闭着,估计早进入梦乡了。
他们的病房在七层,两人乘电梯下去,偷偷溜出一楼走廊,进入幽暗的草坪,藏到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下。他急不可耐地抱住她,她也回应上去。同时她的嘴里又急着吐出几个字,会被人看见的。
没事,我早就侦查好了,这里没有摄像头,也不会有人来。
她放心了。她感觉,这来自另一个男人的拥抱和自己的男人不一样,这陌生的拥抱、陌生的气息,给她一种强烈的新奇感。一时间,她好激动,同时又觉得愧对自己的男人。再转念一想,自己的男人不把她当女人,有人把她当女人,倒也坦然了。
她听到他喉结翻滚的声响,那潮湿的气息已经喷到她皮肤上。这偷偷摸摸的滋味,让她感到既兴奋又自责,还有些羞愧,她干脆闭上眼。
事后男人没忘记她的付出,说看你需要钱,把这点钱拿上吧,一点心意。她看着男人从钱夹里抽出五张票子,突然有些愤怒。但她又意识到人穷志短,不容她摆高姿态。男人见她把钱乖乖塞进口袋,长舒一口气,似乎眼前的女人不收钱的话,有可能会纠缠着他。她猜出他的想法,说,你放心,今天这一切就当没发生过。在这里分别后,咱俩谁也不认识谁。
他抓住她的胳膊打算往回走,有点强迫的意味。她一时有些恍惚,这个男人简直是进行了一次快餐消费。
不聊会儿天吗?她低声问。
会被人发现的。男人左顾右盼。她一听就想笑,刚才还一副肆无忌惮的样子,这么快就畏首畏尾了,比六月的天气变化还快。她知道这无非是个借口罢了,她的身体没动。
男人问,咱们聊点啥?
难道你不打算说说你的情况?她的声音里隐隐有些不快。虽然不打算交往下去,但最起码给人留个念想吧,也让人觉得这是个有温度的男人。
他觉察到她的情绪,沉思片刻,便开始说话了,一下排出好几句,仿佛为了满足她的好奇心。他说他叫刘志刚,在一家国有企业上班,老婆整天跑得不回家,就知道打麻将,和那些麻友们吃吃喝喝。家里一切全靠他收拾,里里外外全是他。儿子受伤了,可她不闻不问,依旧我行我素,还是整天和那些男人鬼混。
你老婆和你关系咋样?她最关心的是这句。他迟疑一下,似乎在揣度她的心思。接着他说,别提了,我都怀疑她和多少男人发生关系了,吓得我都不敢深挖,一旦挖出来,让我怎么面对?到时候连退路都没有。这个男人把自己说得很委屈,仿佛全天下的委屈都砸到他身上了。
听到这里,她身体一颤,他俩的遭遇好相似呀。她有种与他同病相怜的悲哀,同时还有种莫名的快意。有这些话来麻醉,她满足了。她忽然发现她要的就是这些,只有这样才能与她的经历相匹配。
四
男人不在时,她装作很随意的样子,问他儿子,你爸爸叫啥?
赵强,孩子说。
你妈妈呢?平时干啥?
做生意,很忙的,我去过她的公司,好漂亮的一个大公司,有很多人。我长大后也要像我妈妈那样,管好多人。
听到孩子的话,她心里直冷笑,连个真实的名字都舍不得告诉她,生怕她以后像追债似的去找他,真是猫偷腥还不愿留下痕迹,还编了一个动听的故事讲给她听,把自己说得受了天大的折磨似的。她明白了,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走得干脆利索,连根拔掉,从此永远遁去更好。哼!真是想多了,我只是贪恋这点男人对女人温情的余热罢了,你就是告诉我你家在哪儿,我也不会找你的。
她心里忽然满是醋意。她反应过来,原来她在嫉妒这个小孩,就像看到比自己强的女人,情不自禁地嫉妒,挡都挡不住。这小孩啥都知道,而且最要命的是,这么小竟然就有那么大的抱负。她真想把他小脑袋里的细胞一个个捏死,让他变成另一个庞大男孩。
她彻底绝望是在两天后的那个下午。隔着花圃,她看到那小孩站在她曾经去过的那棵树下,推了一把庞大男孩,意思是你不听我的话是不是?她见庞大男孩无动于衷地站在原地,使劲盯着树干,想必在看树皮褶皱里的蚂蚁。小孩见推不动他,就使劲踢他的腿,一边踢还一边笑,像捡便宜似的。可他照旧没反应,不愠不恼。那小孩飞扬跋扈的架势和庞大男孩不争气的样子,让她脑子里满是怒火。这简直太欺负人了,这不是在欺负我吗?
她越想越气,恨不得冲上去掐住那小孩的脖子。反应过来后,她又为庞大男孩感到悲哀,也为自己感到悲哀。他已经无可救药,还要把她拽上,让她也无可救药,让一大家子都无可救药。她注定是栽在他手里了,永无出头之日。
够了,别再给我丢人现眼了。与其让他不断受凌辱,还不如趁早做个了断,省得他再受罪,还拉上我们遭殃。她听见一个声音说。这声音把她吓了一跳。她知道这声音是自己体内发出来的,每个字都是被她嚼碎才吐出来的,她都能听到那些字在她嘴里发出骨头断裂的声响。
她惊讶于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想法。要知道,她为这个家一向都是心甘情愿地付出,为什么这次却变了?她自己也说不明白。现在她总觉得,有个人在暗地里操控她的身体和想法,她不得不跟这个人走。这个幕后黑手是谁?她想了半天,忽然,豁然开朗,那个躲在暗地里的人就是她,另一个被那个男人打捞出来的她。
五
她留意了一下医院周围的地形,发现医院北边正在进行棚户区改造,那块地界已经被折腾得惨不忍睹,平时很少有人去那儿,看来是个解决问题的好地方。晚上跑去不太好,医院处处都是摄像头,看见自己深更半夜领孩子出去,一定会怀疑到自己头上。白天午饭后比较好,这个时段是午休时间,人比较少。
中午吃完午饭,她让母亲先躺床上休息,她说带庞大男孩出去逛逛,他想出去玩。从北门出来是一条有些坑洼的水泥小路,小路对面是一排彩钢板隔离墙,她带着庞大男孩从豁口处钻进去。里面很宽阔,满眼是堆积成山的砖块瓦砾,还剩几处残破不堪的房屋遗世独立地硬撑在原地,像大海上的孤帆。
她把庞大男孩领到一处墙壁后,让他坐在地上。他果然安静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个认真听课的小学生。就要行动了,她忽然觉得时间慢下来,心开始剧烈地跳,手有些抖。她犹豫起来,有些不舍,她问自己还要不要动手。她听到自己心里在吼:他不知要活多久,你一定会被他拖垮的。
她的手开始掐他肥厚的脖子,她以为他会挣扎,会喊叫,会死命掰开她的双手。没有,他只是乖乖坐着,喉咙里连发出怪叫声都没有。尽管呼吸有些困难,他却不知该怎么办。她知道,只要他稍加反抗,她就难以得逞。但他始终没有,身体仿佛早已死去,只剩两只眼睛静静看着她忙碌。
忽然她觉得哪里不对劲儿,似乎有一双眼睛在看她。猛一扭头,便看见不远处有个拾荒老汉正好奇地瞅着她。老汉一手拽几个空纸箱子,一手攥个塑料袋,里面塞了些变形的塑料瓶。她赶紧拍拍手上的土,弯下腰,假装捡拾地上的书本报纸。老汉又盯了她几眼,转身走了,兴许拾荒更吸引他吧。看到老汉消失在垃圾堆后,张紫曼靠着墙大口喘气,老汉应该看到她怪异的行为了,这让她感到恐惧。不行,白天太显眼,还是晚上八九点出来合适。
一下午她都是通过看手机上的时间熬下来的,为了这个计划能实现,她有种如履薄冰之感,可是不这么做还能怎样呢?她心里乱成一团麻。天色一点点暗下来,屋内的日光渐渐萎缩。每萎缩一寸,张紫曼的心就紧张一寸。旁边床铺的男人正和他的儿子就着灯光吃饭,父子俩埋下头,像两只一大一小报团取暖的动物。她忽然想起来,自从父子俩住院后,从没人看望过他们,也没人打电话问候。男孩的妈妈像个传说似的,只活在父子俩口中。他们家到底是怎样一种状况呢?好奇心像螺丝似的,一圈圈拧着她。
这时,她听见男人的电话响了,她看见男人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瞥了一眼屏幕,眉心便拧起疙瘩。他走出病房,意思很明显,他不想让别人听到他们的对话。
他出去了,她的耳朵也出去了。出病房走上一截就是楼梯口,她听见他躲在楼梯处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你太过分了……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我会让你后悔的。
声音渐渐远去,他的脚步声吞噬了说话声。她知道他往走廊深处走了。她再也坐不住了,她发现自己不争气地站起来,走了出去。
她看见了,走廊尽头,他背对着她,正出神地看着窗外。
赵强,怕惊扰到他,她在他后面不远处自觉站定,轻轻叫了一声。那声音有点暧昧,像呼唤情侣的名字。她有点脸红,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喉咙里能发出那么柔软的声音。男人猛一回头,显然他没发现身后竟然站着个人。他的眼睛有些潮湿,她看到走廊顶部的白炽灯管闪烁着。
看到是她,他马上明白是儿子把他家的情况简单告诉她了,他再次把头扭向窗外。她走到他旁边,两人一起望向窗外。她看到两张模糊的脸悬在空中,远远近近的楼房灯光在他俩的脸上明灭,下面的城市灯火璀璨,路上车辆行驶正酣,夜晚的城市仿佛被打了兴奋剂。
我俩,被她抛弃了。张紫曼听到这几个字从他嘴里疲惫地爬出来,像是跋涉了很远的路。
他的嘴在玻璃上一张一翕,继续缓慢地说,她生意做得越大,越不在乎我的感受,越不在乎我这个人,仿佛我不存在。我很孤独,很痛苦,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
六
她偷偷侧头瞄了他一眼,看到他脸上有种浮生若梦的朦胧。她知道,此时把再多安慰的话送给他也是多余,道理谁都懂。
突然,他说,我要带孩子换个地方住,我要让她知道,我们是多重要,失去我们她会有多痛苦。语气很决绝,像是下一道打硬仗的命令。
她被他突然冒出的话吓了一跳,她没有响应他的话,他也没继续说。两人便不再说话,就这样默默站着,仿佛窗外耸立着一座墓碑,他们是来凭吊逝者的。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对着窗户上的他说,该回了吧?
两人转身的一刹那,她才猛然想起今晚还有重要事情要做。她看一下时间,已经十点多了,明晚再出去吧。
两人一前一后进到病房,母亲正在哄她的宝贝孙子,她用手轻抚庞大男孩肥沃的脊背,像在抚摸一个大宠物。她把病房的隔帘布撑开,紧挨着庞大男孩躺下。庞大男孩的肥肉流得到处都是,只能容她侧身躺。三个人共睡一张床,把床上的角角落落都塞满身体。她早就习惯了,早就练出给个缝隙就能出神入化地钻进去的本领。
她一时半会儿睡不着,隔着一层布,她听到那个男人在床上辗转反侧的声响,似乎有满腹心事要从身体里孵化出来。不知他在想什么。她脑子里塞满好奇,他每天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家庭?又是如何度过每一天?她对他隐隐有些担心。
不知何时,她迷迷糊糊睡着了。她似乎看到那个男人到处张贴寻人启事,见人就问有没有见过一个男孩。一觉醒来才明白这只是个梦,不过梦里那个男人的遭遇也够让她暗暗高兴了。但她窃喜了没几秒,就隐隐感到哪里出了问题。
清晨的风从窗口灌进来,吹得隔帘如波浪般起伏。借着隔帘翻飞的间隙,她猛然发现旁边那个床铺空了。她一下坐起来,掀开隔帘快步走过去。床上只有凌乱的被子和人压过床铺的痕迹,其他什么东西也没留下。她一下瘫坐在男人床上,身体坍塌成一堆沙。这个男人走了,连同他的儿子他的气味统统消失了。她盯着那空荡荡的床铺,心里空落落的,半天缓不过劲儿来。此时的他去哪儿了?在干什么?有没有想她?想到这儿,她暗笑一下,他应该巴不得早点蒸发得干干净净,免得她像警犬似的跟上吧。
凉风吹过她的脸颊,像蛇爬过身体。张紫曼这才发现,窗户是洞开的。她生自己的气,看你没出息的样儿,这么大的风没意识到,反而先注意到这个空床铺。此时她依稀听见楼下冒出嘈杂声,似乎有人在叫喊。她好奇地走向窗户,朝楼下张望,便看见一个男人和一个小孩躺在血泊中。只一眼,她便看出他们是谁了。
在那个人倒下去的地方,有个不锈钢保温饭桶和几双筷子从塑料袋里滚落出来,还有几本孩子的儿童图书。还来不及让身体慢慢变老,他就这样提前消逝了,并且残忍地掐断孩子的生命,况且那个孩子那么优秀,曾让她嫉妒得近乎发疯。
站在高空中,她俯视那个无辜的孩子,弱小的身板静静摆在男人旁,她忽然明白他昨夜说的话。她内心升起一股俯瞰众生的超凡之气,这一刻,她有种顿悟的感觉。这个男人太自私了,自己痛苦,却拉上无辜的孩子陪葬。其实,这世上,哪个人没有或多或少的痛苦?
世界上最极致的痛苦是什么?她问自己。她没急着回答,而是又看了一眼下面。下面的人群越聚越多,医生护士手忙脚乱地摆弄两人的身体,试图拽回他们的生命。或许,是那种深入骨髓的负罪感吧。她听到自己说。她进一步想,再没有比一个鲜活的生命葬送在自己手里能带来负罪感了,这让人痛不欲生。也许,在事情没发生前,反而是最幸福的时光,只是没察觉到而已。现在的痛苦或许是一种幸福。
她关了窗户,转过身,看见母亲和庞大男孩依然睡得很沉。她知道,母亲总是半夜起来睡到走廊的椅子上,给她腾出更多空间,以便让她睡得舒坦些,直到天快亮时才返回床上睡觉。庞大男孩的一只脚吊到床沿下,那只肥脚像发酵的馒头一样,直晃她的眼。
她走过去,把那只肥脚轻轻放到床上,然后看着他流涎水的脸庞,看来,这家医院的医疗水平不行。咱们该出院了,给你换下一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