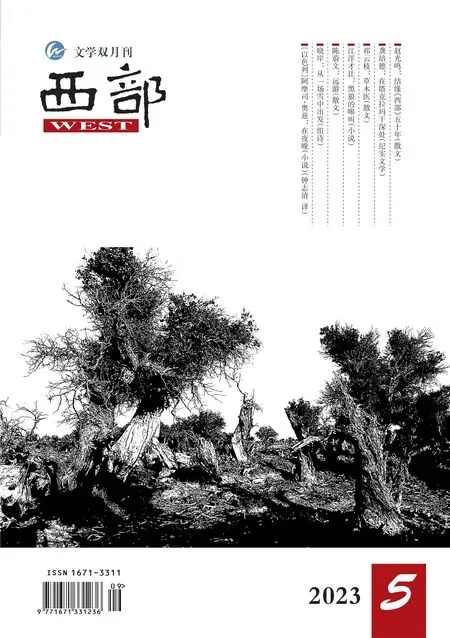布谷来时
蔚蓝
1
东南信风开始不息地从河湾深处吹来,谷雨季的滩涂,又一次泼墨着属于它这个时节的斑斓。大地在四月短暂的苍碧之后,渐次绚烂。大自然用一枝看不见却巨大,无处不在的画笔描绘着只属于这里的画图。这支画笔由温暖湿润的南风、一轮又一轮的雨水、明亮的阳光与越来越高的气温所制成,一层又一层涂抹到每一片草尖上与角落里。
以蓝为底色,天宇间涌起铅灰或白色的云块,随着风的河流飘向更北的北方。重重叠叠的青杨、白杨的绿更加阴郁,幽深的绿海之下隐匿着更多的秘密。遍野的芦苇从昔年枯萎的母体旁用几乎看得见的速度,生长成一枝枝纤长秀美的姿态,一片片地连成不见尽头的整体,在风中摇曳着一层层起伏的苍茫绿波。滩涂上农人种植的麦子、油菜的果实开始由青绿转为金黄,它们如一汪汪黄绿相间的湖泊在荒原上的绿树与芦苇间漫漶,勾勒出滩涂五月最动人的版图。
再把镜头拉近,那些隐匿在树木、芦苇与庄稼深处的草木又是一个微缩多姿的世界,季节变幻的河流,不会放开任何一个细小隐蔽的角落,从一片天空至一枚草叶,都流淌着只属于这个节令的脉络。披碱草一串串成熟的麦黄色谷穗悬挂纤长的枝头,水芹、益母草、苜蓿、泥胡菜正开完最后一茬花朵,一枚枚褐色果实正在成熟。它们构成着这片荒原的细节。
雨水明显增多并浩大起来,一朵积云飘来,不经意间就有一场阵雨不期而至,“沙沙”落在无数的叶片上,如涌起的潮水,渐渐淋湿了滩涂。当阵雨还来不及从它浓密的叶隙间滴落下来,雨却渐渐地停了。不同于早春时节雨水的缠绵,针尖一样下着茫茫不见尽头,此季的雨水开始密集并急促了许多,开始有了夏日雨水滂沱的气韵。阳光从云缝里穿射出来,一束束金色的光柱投射在滩涂的草野深处。空气湿漉漉的,弥漫着各种草木混合着的清甜气息。在雨水的濯洗之下,树林里每一片木叶与草尖都荡漾着洁净的绿,一颗颗水珠闪烁。树林里的青杨与白杨,开始迎来了它们一年中树叶最为丰腴碧绿的时期,又在阳光映照之下,显现出厚实秀美的轮廓,无数的光影在数不清的叶片间跳跃。
一场又一场雨水,河水几乎以肉眼看得见的速度上涨,开始淹没岸旁的草野,河流的版图正在扩张。但现在还不是它浩荡的时候,水流只是淹到了草木的根部。水流漫漶的地方,在风的摇曳下青蛙的歌唱比往日更为明亮。在河流生长之前,这些小小的精灵,早已被温润的春风唤醒,隐藏在潮湿的洞穴或清浅的河湾里浅吟低唱。同那些一样渴望雨水的草木们一样,千百万年独特的生命经验已刻进它们的基因,它们等待着河流又漫过这片河滩。几乎在一夜的雷雨声里,它们开始了集体的合唱。从清晓至黄昏,由暮晚到天明,在滩涂每一片河水漫过来的地方,都能听见它们不息的歌唱。这是它们一年中最为快乐富足的时光,无涯的河水与丰富的食物,得以让它们尽情享受着爱情的欢愉,繁衍着子孙。很快,在接下来漫长的时光,这样欢乐的盛景不再有。越来越丰盈的大地,同时让越来越多的天敌来到这片滩涂,弱肉强食的世界让它们生存受到巨大的威胁。河水日甚一日的上涨,会淹没整个滩涂,除去枝干纤长的芦苇与高大的杨树,一切会在流水的汪洋之下,它们不得不开始迁徙。
群鸟的合唱,在奏响春天华尔兹最后的音符,这些林中二月或三月加入进来的精灵,在整整三月或四月清凉渐渐泛绿的林中,不停息地展示它们曼妙各异的歌喉,只为受到意中人的青睐。而在这春将尽的时光,它们的歌声更加急迫,一年中最为黄金的产卵季将要过去,它们不愿孤单地度过余下漫长的光阴。
此时,最为活跃的是鹧鸪,林中四处可以见到它们的身影,相比其他羞涩的鸟儿,它对人类有着天然的亲近,在滩涂之外的村庄,常见到它们的身影,它们毫不胆怯地将巢筑在农舍旁的树木间,甚至窗户上。它们这样的心性可以让我清楚地看见它们求偶的表情。有一只立在我不远的一枝杨树枝上,灰白相间的羽衣与林中的绿叶很好地区分开来,它的脖子长着一圈点点灰白的羽毛,仿佛绅士一样围了一圈围脖,它全然浸润在爱情的渴望中,全然忘记我的偷窥,也许是不屑,这只树下直立的不能飞不能跑的怪兽,并不能对它构成什么威胁。它伸长脖子并发出“咕咕——,咕咕——”的歌声,悠长如袅袅的云烟久久不会散去,接着又重复着一样的动作,它正在呼唤寻找着属于它的伴侣。
在密密的林中,乌鸫的歌唱最为美妙。真让人惊讶,这种其貌不扬与乌鸦一样丑陋的鸟儿,竟有一副天籁一样的歌喉,在这风清日丽的林中,它不停变幻着曼妙曲调,一会发出“啾啾,啾啾”如大珠小珠落下盘地急促音调,一会以“啾——,啾——”把人带到缠绵的梦里去,转即又用“啾啾、啾啾——啾啾”回环反复歌声让人摇曳在晚春的南风里。这是种羞涩胆小的鸟,总是远离着人类,在它们歌唱时,很难近距离地观看,只能听见它们的歌声在林中如流水潺潺,唯有它们飞过天空的时候,才能窥见它们一闪而过纤小的黑色身影。
2
在春天的深处,我总是莫名地惆怅。一些事物开始在我心里沉寂,一些事物开始在我心里苏醒。江风浩荡,在盈耳的蛙唱与鸟鸣里,我清晰地听见布谷几声悠长的歌声响在树丛的上空。在大多数鸟儿齐集这片土地的时候,它们才匆匆乘着歌声的翅膀翩然而至。让人惊讶,当村庄四月紫蓝色的楝花,一簇簇开满村野枝头的时候,不早也不晚,这种神秘的鸟儿会在一个黄昏或是清晓,随着温润的南风,从更南的南方飞来,越过无数高山与平原,也越过浩瀚的海洋,把它明亮的歌声摇曳在村野的各个角落,仿佛是夏季的使者,它的到来宣告着这个季节的开始。
在这片滩涂上,布谷是一种奇异的所在,同人类中不事稼穑的诗人们一样,布谷只把一生献给爱情与诗歌。与其他同样擅长歌唱的林鸟相比,它总喜欢将身影隐于云端,而不是驻足枝头歌唱,一会飘摇在我的头顶,一会就流淌到树林的尽头,一会又在滩涂的深处,仿佛一个隐藏天空的精灵,只能聆听到它们的歌唱,却难觅它们轻盈的身影。在头顶是浩瀚的天空,足下是无垠的旷野,自由的灵魂与身体融入宽广的天地之间。它如水禽一样边展翅飞翔边纵情歌唱,却明显地迥异于水鸟们尖锐沙哑的歌声,它们巨大胸腔、强劲的肌肉,让它们发出辽远明亮的声符,天宇间摇曳的轻风,让它们的音色飘忽如梦境。每听到这种精灵的歌唱,一颗心总是变得惆怅,仿佛跟着它们飘渺悠长的歌声,流离到遥远的不可知的地方,却又抑制不住向往与喜悦,又一年春天悄然过去了,人间又少了一个光阴。
这种孤独的雀鸟,是天空的流浪者,除去求偶的季节,总是随着暖流在云朵间飞翔歌唱,仿佛是属于仙境里的事物,不食人间的烟火,而对其他的事情无心过问,滩涂上只闻其歌声,难睹其真容,也从未见它们的巢。事实上,它们从未筑巢。接下来的时光,在它们摇曳的歌声里,爱情终成正果,它们却将卵产于其他鸟类现成的巢中,有时为避免母鸟发现多出的鸟卵,而将母鸟亲自下的鸟卵推出巢外,便完成了一个父母的责任,转头又消失在云端之中,让歌声流淌。而那些不知情的不幸母亲们,精心饲养着别人的后代,殊不知这些雏鸟在出壳之后,已将它们真正的后代扼杀在摇篮之中。但我们不能以人类的眼光来评价布谷的作为,自然有它自己的选择,它用这种方式维护着自然的平衡与丰饶。
谷雨的四月,江南的春色未尽,气温反反复复,西西伯利亚的寒流与西太平洋的暖流做着你死我活的斗争,离初夏绵绵不尽的温暖还有一段时日。这些天性敏感的布谷,总被暮春反常的温暖所迷惑,从更南的南方飞来,开始在大地上鸣唱初夏的乐曲。但其间不期而至的寒流,会一连多日不能听见它们的歌唱,而当气温升高时,它们的歌声又飘忽在田野的上空。待到气温稳定的立夏时节,它们的歌声才在滩涂与田野的深处停息。
3
如一条流动的河流,也如一轮永不停息的旋转轮盘,时光在不停流逝,这里的一切事物在悄然用肉眼看不到的速度在变幻,生长着、成熟着或衰老着。只需用一日或几日的时间坐标为对比,大地又是一片山河。
离我上次来这片滩涂还不到十天的时间,雨水、雷声、阳光与南风轮番光临这片土地,远远地我听见布谷鸟的歌声几乎摇曳在整个荒原的上空,不是早先时候的一声或是两声的零落,而是无数声的布谷的歌唱,在它们曼妙歌声的浸润之下,一切事物都熠熠生辉,生动而迷人。它们明亮、辽远的歌唱,仿佛无尽的夏日时光,漫长得没有尽头,而一个人却悄然老去。从谷雨至芒种,整整一个多月春末夏初的时光,布谷是这片天空最美妙的所在,是这个时节最不可或缺的组成。它们发出的四声错落有致的声韵,被这片土地上的农人意会成上天派它来催促农时的号角:“做事不做嗨得欢,肚子饿了怪哪个?”在这样被翻译的歌声里,连村野里最懒惰的懒汉都心存愧疚,不得不扛着锄头去他荒草没过庄稼的地里。
事实上,并不是农人们想当然地催促着农事,它们正在用歌声寻觅着属于它们的伴侣,雌鸟用温柔的歌声回应,一起消失在密密的林中。爱情使它们亢奋,爱,是这样自然而然的事情。不仅仅布谷,这片土地上的生灵,对待爱毫不避讳,小小的身体泛滥着爱的柔情。它们用歌声或气息寻觅着生命中的另一半,辽远的大地变得温暖。
滩涂开始温暖,草木与庄稼迎来一年中最为繁盛的时代,它们饱满的种籽与果实将要成熟,那些以此为生的草蜢、金龟子、蝗虫们也开始了它们的盛宴。大地彼此相连,一切生灵互为依存,这些美味肥硕的昆虫,是这些远道而来的布谷最为美味的口粮。布谷以这些昆虫为食,那些丰美的木叶与种籽又成为昆虫的口粮,草木则吸收着泥土的营养,而一切万物终化为尘土,大自然的循环生生不息。
4
雨后的天宇,一大朵、一大朵云彩漂流四方。滩涂的天空,开始了一年中最为绚烂与变幻的季节。这是由雨水、阳光与风打造的辽阔庄园,在无垠蓝色天宇的映衬下,云朵用色彩把天空涂抹。并不均匀的雨水让云朵呈现出深灰、浅灰或灰白的色泽。而不经意的阳光从云朵里穿透出来,让每一朵云彩镶上了闪烁的金边,那些淡薄的层云,阳光把整片云朵映照得熠熠生辉,又因角度与云层厚度大小的不同,而显现出丰富有层次的斑斓色彩。阵风吹拂,一排排云朵在山冈上流浪,翻滚起云的浪涛,或有几朵立于滩涂的上空,几朵随流水飘向河流的深处,或冠于树林与村落的上空,盛开成一朵朵巨大的花朵,空气里弥漫着归意。
濯洗后的荒原,绿色的森林与芦苇丛闪闪发光,如朵朵绿云堆积。滩涂上最多的杂草,披碱草、水芹、益母草、苜蓿、泥胡菜的果实已经成熟,隐藏在深褐色的枯萎枝茎中,在这个暮春的时节,它们已度完这一生,枯萎的面庞与老去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些大地上的生灵懂得大自然隐藏其间的奥秘,在季节的转换里,一切恰到好处,不早也不晚,在一切做完之后,接下来河水将淹没这里的一切。
麦子、油菜,在阳光、雨水与南风交替着浸润之下已经成熟,漫漶在眼帘里的是纯粹彻底的金黄,把滩涂静寂的天空映亮。我的心间涌起无限悲伤,大地呈现着辽远的静寂,却不同于秋冬时万物凋零的萧然,而是丰盈充实后的沉静。这些成熟的麦子、油菜,都是一个个母亲,都有乡间怀孕的妇人一样温暖平静的面容,身体里孕育着日日长大的小生命,让这些母亲莫名地惊喜与安静,隐藏在它们身体里的神秘昭示悄然复活。它们谦卑地低下头,一切事情都不重要,只等着它们的孩子降临人间。群鸟的歌唱暂告一段落,它们在这个晚春的季节,收获了爱情,不再为寻觅爱情而不息歌唱。此时,这些忙碌的母亲与父亲,正不停穿梭在荒野与树林之间,无暇顾及滩涂的风景。几乎每一张小巧的嘴中都衔着一撮毛发、一片叶子或一根草茎,它们正在筑巢。滩涂流淌着莫名的温柔,万物美好。
它们都是这片大地的孩子,但它们的生命历程与人类又如此不同,从一株披碱草至天空的飞禽,这里的每一个生灵都有属于它们独特的生命道路。飞鸟把巢安在高高的树丛,从此它的孩子们的一生只属于天空与自由。当麦子、油菜成熟的时候,将是母亲们化为泥土的时候,这些伟大沉默的母亲,把生命的一个个密码隐藏在孩子们小小的果实中,在漫长的光阴里,这些孤独的孩子将面对着生命中的一切波折。
5
河流开始悄无声息地收复着属于它的夏日城池。前几日我立在水泥桥上,河水还可以哗哗地从桥下离桥面不到一米处流过,规矩地漫漶在河床里,只淹没了河畔低矮的披碱草与庄稼,远远看着,河流蜿蜒的姿态仍清晰可见。这次再来,汤汤的河水早已把水泥桥淹没,要不是我熟悉这里的地貌,根本就没人知道在这条浩荡河流的水底,它已成了飞鸟与鱼儿游弋的乐园。我现在只能站在河畔远远望着被水隔断的滩涂。雨水与上游的洪水,让曲折蜿蜒的河流变成没有规则的椭圆形,漫漶的流水侵占着滩涂的任何一个低于水面的角落,并仍在上涨。
如光阴里枯荣的草木一样,河流也在节令里繁茂又凋零。就是这同一条河流,经秋至冬,又及早春时,我感受到它从枯瘦至丰盈的历程。那时它纤弱如一丝白练,穿行在秋冬凄清的旷野里,四野是茫茫的沙滩与枯草,“呜呜”地北风呼啸。如草木生长,在几度春风细雨的滋润里,滩涂上的树木与荒草渐渐青碧,斑驳着野花点点,河流也丰腴起来,接着鸟儿与昆虫的歌声飘忽河面与天空,河流开始迎来一年里生命力最为旺盛的时期。
这才是河流本来的样子。我见过无数条河流,它们规矩地在被水泥石头控制的河床里流淌,岸旁生长的草木也被人为地规定。从一个春天至另一个春天,河流永远是死寂的,没有蛙唱与鸟鸣,只有无数的行人。树木之外,是城市高大的建筑与流动着车流的道路。这些都是死去的河流。
不知为什么,我越来越喜欢丰沛的河流,它蓬勃的生命力让我迷醉。我在人间已虚度四十多年的光阴,我开始老了,开始迷恋身体与灵魂里欠缺的东西。大河汤汤,木叶森森,鸟鸣于野,我感觉到身体里颓废沉睡的活力又被点燃。与之相反,少年时,我却痴迷秋冬的河流,多少个四野寂寥的冬日,我一个人沿着细瘦的河流行走,空旷的天地间只有我孤单瘦弱的身影,多少梦想与希冀燃烧于心中,而寂静的流水如忧思过度的瘦弱哲人一样,给一个少年的向往以神秘地昭示,让他火热的心安静下来,倾听心灵深处的声响。
青蛙的歌唱告一段落,只有零落的几声蛙唱偶尔响在河畔清浅的水间,然后就是辽阔的静寂。它们三月或四月的爱情终修成正果,它们的蛙卵开始一一在浅水间孵化成一个个新的小生命。更多的不幸者,成为天敌们的佳肴。就在我立在河畔时,一只白鹭衔着一只青蛙,从水草丛中惊起,消失在树林深处,这只卑微的以水为生的生灵,生命在天空结束。大自然是这样残酷又美丽,一个生命的代价,成就另一个生命的繁盛。越来越宽广的河流,已不是蛙群适宜的栖息地,它们只眷恋着清浅的流水。从某一个夜晚开始,它们中的幸存者开始迁徙,那是一个离滩涂几百米远的不被水患侵扰的田野与湿地。几百米对于飞鸟甚至人类来说,只是转瞬即达的距离,而于这些行动迟缓的幸存者,是一场漫长艰辛的旅途。河水淹没着它们春日欢歌的家园,借着夜晚月亮与星星指引,它们躲避着夜行人巨大的脚步,人类无意间的举动,于它们就是灭顶之灾,也躲避着好奇猫狗的追捕,加快着行进的脚步。在天色微明时,在无数个同伴倒下去之后,这些幸存者终于清晰地听见同类在清晓里的歌唱,也不禁用歌声回应着。终于,在一片水草丰美的溪流边,它们又有了自己的新家园,在接下来漫长的夏日,它们将与蝉歌分享这片池塘与河流。
野蜜蜂早已离开被水淹没的田地,去寻觅另一处花海。在这片土地上,没有哪一种生灵比它们更懂得花朵的所在,它们熟悉这片土地上每一种花的花期。花期已过的滩涂之外,是高高的堤坝,那后面是农人的村舍与田野,一大片一大片一年蓬开得正旺,几乎占领着每一块被农人遗忘的土地,一簇簇金色太阳一样的花朵漫漶天涯,那是属于野蜜蜂收获的田野。自然隐藏着我们太多不知晓的秘密,我曾询问过一个老农布谷与杜鹃的不同,这个在乡间务农一生的农人,眼中只有无尽的茫然与不解。一个生命就是一个世界。
斑嘴鸭成群结伴地飞走了,没有人知道这些精灵飞往哪里。一双自由的翅膀与灵魂可以带它们去往任何想去的地方,它们的故乡只属于流水与天空,那水草丰美,让它们自由飞翔的地方。它们眼中的世界与我们眼中的天地明显不同。这水中的精灵,从滩涂上扇动起轻盈的翅膀,向着广袤的天宇,滩涂上的一切在它的脚下渐渐变小,世界在它的眼中渐渐变得广阔,无数条河流、无数个村庄与田野在它飞过的身下闪现,它们从容地选择着属于它们的生活。这是它们筑巢的季节,而这上涨的河水并不适合它们将巢筑在岸旁的草丛里,它们敏锐的眼睛可以让它们在河流深处寻觅到一处安全之地。待秋天来临时,它们带着新生的生命,将再一次光临这片滩涂。
6
在明亮的阳光与雨水交织之下,滩涂上成熟的麦子、油菜被农人收割,只留下麦茬与菜杆,同时成熟的还有泥胡菜、水芹、披碱草与益母草,它们褐色的种籽被风带到远方或落在身下的泥土。
随着庄稼的收割,大地上的草木变得稀少,蝗虫等昆虫们开始向着更北的北方迁徙,草木繁茂,它们隐匿的却连绵不绝的轻吟也如潮水退去,祖先遗留在它们体内的基因,利用神秘的耳朵与嗅觉,可以通过风的信息与星辰的位置,让它们追随着远方田野庄稼散发的气息。这些小小的生灵成群地飞过一条条河流、一片片森林与田野,寻找食物丰美之地。它们这样壮观的迁徙,一点也不逊色那些候鸟成群地南北飞翔。
布谷的歌声也渐渐停息,无垠的天空寂寥无言。在接下来至深秋到来的时光,滩涂与田野有无尽的昆虫,将滋养这些被爱与歌唱劳损身体的精灵。它们甚至不再歌唱一声,隐匿在密林与田野间。滩涂与田野属于劳作的农夫,天色微明间,他们从鸟鸣声里醒来,在这里耕种、除草、施肥,一日日面容苍茫着老去。在深秋的某个黄昏,晚霞染红西天的云彩,布谷又沿着千万年来祖先的路途,孤独地飞往遥远不知尽头的茫茫非洲之南。
7
河水一日日地悄然上涨,它渐渐淹没着低洼的土地,又把它的版图扩张到收割后的旷野,很快又向着高处的树林进发。在又一场豪雨之后,河水终于漫过了全部的滩涂,在接下来的漫长夏日,滩涂又将交给河流,这片广袤的土地,都将被河水淹没。
树林深处,从二月开始的喧嚣终于渐渐沉寂,即使在密密的杨树林中,那些整日歌唱的鸟儿,也渐渐停止了盛大的音乐会。它们收获了爱情,树枝上一个个巢中,孕育着新的生命。悠长明亮的歌声变得温柔纤秀,喁喁低语着只有它们听得懂的话语。
宽阔的水面上,白鹭唱着嘶哑的歌,展着古诗一样的翅膀款款飞来。这些逐水而生的精灵,把一年余下的漫长光阴交给这里。这里有它们自由展翅的天空,有取之不尽的食物。它们着一身洁白羽衣,一双纤细修长的腿足,是这个季节滩涂上一首首天成的抒情诗。它们是鸟中的隐士,远离着人间的喧嚣,此时,夏日宽阔的河流悠悠从天上来,又缓缓地飘向云朵里去。一行白鹭飘飞于上,白色轻盈的身影倒映在清澈的河面上,让人讶然间沉醉不知归途,待恍惚间匆匆回过神来,它们已消失在流水深处不知所踪。接着又有三五只白鹭成群飞过,树林恍若一扇巨大的绿色屏风,它们是绿屏上的白色精灵。
一年中接下来的时光,河流把这辽阔的自由王国交给白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