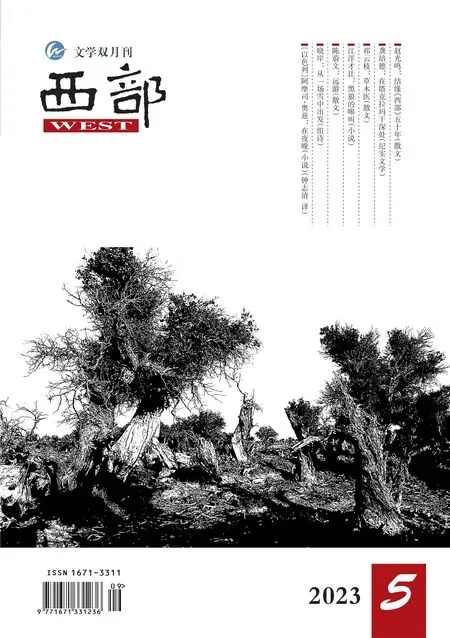原野物语
刘梅花
回到叶子和花朵中去
羊群路过村庄,路过枯萎的树篱,慌慌张张朝着山顶爬。如果它们的眼睛能看见天,就知道山顶上是白雪。雪域高原,最好的牧草就在山下。然而羊群不管那么多,一个劲儿上山。头羊真是蠢透顶。
牧羊人也不管羊群乱窜。他连牧羊犬都懒得养,孤独地在山野里走一会儿,吃烟,发呆,看天。如果被土狼拖走一只羊,大概他也不会生气。山野无尽的空旷寂静,会让人迟钝,产生幻觉,以为土狼也是羊。
实际上土狼是认识牧羊人的。它躲在暗处观察好久,如果不是狼崽子嗷嗷待哺,也不会冲动地猎羊而食。在牧羊人看来,土狼这种野蛮而彪悍的小恶魔终日藏在隐蔽处,令人畏惧又不齿——山野里土狼无处不在,终日游荡,然而躲躲闪闪,你见不到它的身影。如果有牧羊犬,倒是可以和土狼干架。可是他没有。
事实上牧羊人并不想和土狼照面,连野黄羊都不想看见。虽然野黄羊不可能拐走哪一只羊。他找到一大丛褐绿色树叶的灌木丛,蜷缩在叶影下歇凉。这样的灌木没啥用处,刺多,叶子硬,彼此缠绕交错,羊群不食。然而灌木并不这么想,它不觉得自己无用,它只为自己而生,只为自己而活,管你羊群吃不吃。植物完全没有必要讨好动物,苍茫大地又不是动物的。动物以为是自己的。
比起土狼,羊群当然要笨一些,没那么多阴谋诡计。不过它们的嘴巴能识别杂草,至少不吃有毒的植物。然而饥饿会使得羊脑袋发昏,管不住嘴,不留心吃到“断肠草”“羊闹草”什么的,回到羊圈口吐白沫,角弓反张,倒在地上抽搐。牧羊人掰开羊嘴,灌下醋,或者别的解毒药救活它。
老天打发有毒的草下界,不是故意的,是为了物种优化。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如果世界上全是好吃的草,那么食草动物们会陷入倦怠,身体里没有预警系统,不产生抵抗因子,最后消失在时间里。
牧羊人眼里的羊群,每一只羊都独一无二,黑头子,黄眼圈,大尾巴,白胡子。每只羊的羊生和人生并无区别。是的,宇宙里没有重叠的生命,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天地万物的信息里,每个生命都是唯一,得天地气运而生,留下物种遗传信息而去。
青草被羊群吃掉,羊群被人类吃掉,人类被大地吃掉,如此,万物相迭,相生相克,彼此消长。老天给万物设置好生命密码,谁也别想破译或者越界。土狼不想吃土豆,羊群不吃兔子,蚯蚓只吃泥土。
除了人类。人类最爱越界,见啥吃啥,连蝙蝠和穿山甲都不放过。最能破坏自然的,还是人类。可能老天原本打发人类来保护大自然,结果人类才不管那些,自己开心放飞自我,飞得太快,老天也撵不上。有人的地方,就会腾起江湖尘烟,老天管不过来。张三打猎,李四砍树,王五挖洞。
牧羊人啥都不折腾,就是赶着羊群吃草。他在山野里晃荡了一辈子,知道空荡荡的山野绝不是寂静无声——土狼的嗥叫,蛇在青草里游走的嘶嘶声,热衷于干架的公牛,彼此啄咬的灰雀子,各种不安分的声音飘荡在空谷里,是滚滚红尘的袅袅余音。既然在同一个世界,那么山谷空不到哪里去。
一座城,无论人群稠密或者稀疏,城市都得想办法养活。而山野空谷,看上去空荡荡的,然而它也得哺育无数张嘴——飞禽,四脚兽,鼹鼠,蚯蚓,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甚至虫子蝇子那些无数细微的小生命。大自然逃不过哺育生命的命运,那么多的嘴等着吃吃喝喝。就像一座山林,落满鸟啼,树木无处可逃。
大自然简直操碎了心——春天让百草生发,冬天让万物敛藏。为每一只羊的嘴底下,备下一把青草。为每一只雀儿的爪子底下,备下栖息的树枝。极寒天气,没有皮毛取暖的蛇,食量太大的瞎熊,大自然为它们备下冬眠绝技。
可是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想法,并不替大自然着想。土狼说,请为每一匹土狼,备下无数只羊,最好是野羊。土狼深谙人类的本性,最好各自安好,互不干扰。
土狼极其贪婪,明明只能吃一只羊,却一下子咬死一群。人类恨死它了。
偷猎者说,请备下一山又一山的野兽,最好是皮子值钱的野兽。银狐啦,梅花鹿啦啥的。野驴不要,叫声太难听。黑熊不要,打不过。
木材商说,请备下一大片原始森林,我的伐木工马上抵达,我的钱要多得子子孙孙都花不完。
苍天气得说不出话,还得刮风下雨,因为大自然需要。某个偏僻的小镇,人们天天骂天骂地。他们把自己贫穷的原因迁怒于天地,理直气壮。
可是,人类从不反思自己对大自然的敷衍。其实对大自然的优雅和虔诚,人类算是所有动物里最差的。鸟儿搭窝,找枯树枝,不伐新鲜的枝子。土狼的老巢,就是天然的石洞,不会自己再凿一个。黑熊路过开满鸢尾花的山谷,只是闻一闻,不会撅一大捆,拿回自己的窝里插着。马鹿遇见一大片虫草,也不会刨出来卖掉。
这些事,牧羊人当然都懂,只是不说。他见过一群一群的人,怎么样糟蹋山谷。挖开草皮搭灶,砍下树枝子烧火,煮羊肉,烧烤。然后在开满野花的草地上蹦跶,群魔乱舞,踏坏无数花草。这些人走后,丢下一地垃圾,啤酒瓶,塑料袋,瓜子皮,把一地狼藉扔给大自然。
牧羊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待他们如山野里的动物。人也算是一种动物。但是他更愿意看野生动物。山野里独自生活久了,不愿意和人打交道——人比土狼还要诡计多端。
马鹿腿长,跑得太快,只能瞧见一道黄白相间的虚影,一闪而过。蛐蛐拼命叫,灰雀子一伸脖子啄走它。鸡毛鹰翻越山头,雪鸡一头扎进草窠,尾巴高高翘着。鸡毛鹰俯冲,呼啦一下抓走雪鸡。野兔子躲避天敌耳目,贴着地皮撤退。
比起野生动物,羊群并没有经历太多的危险,所以没有战斗力。野羊是另一回事。不过羊群很少被袭击,不仅仅是有牧羊人跑前跑后,而是这种生物过于善良,大自然暗中相助,不让它们受到过多伤害。
每个动物的基因里,都有历代积攒的保命或捕食经验。这种东西人类认为是本能。野生动物尽量让自己身上的颜色融入自然,融入草木,尽量伪装得和寂静荒凉的大野为一体。如果仔细观察山野里的熊道,鹿道,狼道,踪迹依稀,极为浅淡,不会把厚重的大脚印拓在土地上。即便是大雪天,它们的脚踪也很诡异,显示一段,隐匿一段,连断断续续都算不上。隐去踪迹,是野生动物的一种本能——是对大自然保护的本能。
羊群没有这个想法,它们是人类饲养的,和人类气息相通。它们走到哪里都咩咩乱叫,羊蹄子深深嵌在地上,连碎石路上都能留下密集的蹄印。它们穿着白的黑的羊毛衫,屁股上被牧羊人打了碗口大的红色记号,极为显眼,一点也不想混入大野的枯黄或者黄绿灰褐。反正,羊群在这件事上绝无妥协,用它们骄傲的颜色,聒噪的声音,为山野布道,一丁点都不伪装。
羊和人类的关系很复杂,它信任人类,依靠人类保护,最后被人类吃掉。羊的一生,认为狼熊这些野兽才是天敌。它觉得人类是朋友。实际上,人类越来越不可能成为动物的朋友。因为人类太复杂,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类重叠,不可能有共同的和动物成为朋友的意愿。
老天怜悯羊,所以让它快乐做自己,不必提心吊胆,不必虚头巴脑伪装。羊群吃草就是吃草,不像别的野兽,一边吃一边聆听周围的动静。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如同怪兽可怕的脚步声逼过来一样,逃之夭夭。
土狼会把自己伪装成牧羊犬的样子,狗里狗气,夹着尾巴靠近想捕获的动物。然而它忽略了自己身上的气味,哪怕隔着一座山,小动物们都能嗅到,逃的比谁都快。
牧羊人大概不会思考这些,放羊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日子就是推着磨盘下山,过一日是一日。山野过于空寂,让人容易恍惚。远离人群的好处是心静,坏处是迟钝。人在人群中才能成长历练,适应各种算计。独自在山野里啥也干不成,能大把时间睡觉是另外一回事。
牧羊人觉得自己越来越笨拙,卖羊的时候,被贩子混入假币。小商小贩看他放羊放得傻呆呆,肆无忌惮欺骗他,买的东西都比别人贵。而他的亲戚朋友,借他的钱又迟迟不还。小偷也会偷走他的羯羊,狐狸又叼走羊羔子。没有人体谅他放牧的艰辛。
大雨来临时,牧羊人披着老旧的毡衣,那毡衣是个白色的口袋,套在身上。越高的山越没有树木,可能连灌木都没有。牧羊人独自立在山顶,雨水泼下来,他像荒野的遗产,孤独而厚重。荒野用一场接一场的大雨布道,牧羊人是唯一的听众。
雨那么大,甚至冰雹砸下来,把成熟的植物果球砸裂,把蓼莪草扑倒在地。山野里小动物们躲起来,甲壳虫躲闪不及,飘在水里,惊骇地呼叫。鸟儿收拢翅膀趴在窝里一动不动。牧羊人吆喝羊群,转移到高处,避开山洪。大自然脾气呛人,说干啥就干啥,一场山洪瞬间就会冲决而来。
雨来得快,停得也不慢。雨水把荒野熏得明艳动人,所有的草都愈加绿,所有的石头都愈加好看。雨过,天未晴,雾蒙蒙的,荒野里的事物洁净而俭朴,小野花们开成毯子一般。高海拔的山野里,野花大都匍匐在地——再也无法更矮更低了,几乎贴着地皮盛开。一切真实自然,连羊群都能感受到大自然清醒洁净。
这种生活粗疏简陋,一言难尽——时而落魄,时而满目仙境。前一刻风清日朗,下一刻狂风暴雨。时而与世隔绝,时而百花喧嚣。时而在深坳里扑腾,时而在花荫瀑布下闲逛。山中万物此消彼长,相互依附,整个山野向着苍天敞开,喷发出惊人的美和力量。只有牧羊人是旁观者,在风雨和晴空里沉沉浮浮,在阴天雪天里畏手畏脚。大自然把他打磨得皮实无奈,只能适应这种漫长时光。
有人说山中一日世上千年。但是他朝出暮归,往返于红尘和深山,不能体味世外之幽深。
他是农区的牧羊人,没有牧场,除了牧羊,还种庄稼。农区的牧人时常想着去另谋营生,对放羊不大上心,有一搭没一搭。羊群规模很小,三五十只而已。农民喜欢热闹,就爱混迹在邻居家人中间,不想独自在荒野里游荡。然而他放了一辈子羊,实在没有别的活路适合另谋。
他的放牧很随意,有时候在收割过庄稼的田地里,有时候在矮树林里,有时候在荒野山谷里。他和他的羊群到处流浪,除了羊价高低,其余对他毫无兴趣。
农区的牧羊人不大喜欢这样的日子,一边放牧,一边抱怨。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离群索居,乏味透顶。除了吃烟,喝温吞吞的茶水,实在无所事事。羊群不会成为大群,还得天天跟着小羊群晃荡。羊少,每只羊他都熟悉,羊群也听得懂他发出的指令。清早急急忙忙出圈,喝几口茶,啃个饼子。午饭还是干粮,潦草对付几口。只有傍晚羊群归圈,才可以认真吃一顿热乎饭。然而羊群东逛西逛,又要饮水又要胡跑,磨磨叽叽的,回家总是很迟,那顿热乎饭也差不多凉透了。
真正的牧羊人在牧区,骨子里有放牧基因,祖祖辈辈都和羊群牛群生活,因而热爱牧羊。当然,他们也有牧羊的经验,或者是资质。天地万籁,他们熟悉每一种牧草的名字和习性,熟悉自己的牧场和草原山谷。牧区的羊群是真正的羊群,几百只,上千只,云朵一样漫过草地。牧人有走马,有摩托车,有望远镜,不必天天跟着羊群晃荡,只要在自家的围栏里就妥当。
牧区的牧羊人大多养了牧羊犬,助自己一臂之力。牧羊犬最大程度上摆脱对人的依赖——它有一身厚毛,不需要再穿御寒衣物。饿了随便逮住耗子压饥,不必刻意等待喂食。管理羊群很在行,即便是很小的一只牧羊犬,走路都不稳当,也会对羊群有掌控欲望。
牧羊是修炼。有的人放牧一辈子,见惯了花开花落,草死草活,活得通透清醒,世事看淡。无论日子过得怎么样,内心富有平静。有些人看护羊群一辈子,看不见云朵山石,不关心苔藓和重叠的叶片,和原野毫无关系。孤独的日子,让牧羊人变得少言寡语,百无聊赖。等老了,就靠在墙根晒太阳,吃烟,勾头纳梦。
老牧人如果回想往事,能想到什么呢?往事都蒙了一层灰尘,像梦幻一样,他的眼前必定是一群羊,他跟在羊群后面晃荡。一群羊跟一群羊不一样,这一群不是那一群。一辈子经历了多少群羊?那些羊都去了哪儿?牧羊人当然会想起美味的羊肉,油脂滴在炭火上,嗞嗞响。那么,枯了的牧草会记起吗?飞虫蚂蚁会想起吗?土狼马鹿野兔子会想起吗?灌木岩石暴雨会想起吗?
不知道。如果和牧人攀谈,也许他会谈起这些,琐碎的,厚重的,听说的,见过的。也会谈起纯净的泉水和被花熏得清香的空气。实际上他还是喜欢回到叶子和花朵中间去。一个山谷就是一个微观世界。一片草原就能收藏万物。一个牧人就是一个自然学家。
也许牧人不会想这么多。放牧就是放牧,草木就是草木,羊群就是羊群。放牧不是消遣,是真实的生活。真正属于大自然的物种,必须单纯沉默。放牧自然也不是为了得到智慧或者纠正偏见,那些树木的暗影和潦草的旱獭洞穴,都不能给牧人启迪。如果想多了,就会吞噬放牧的风味。问题就在这里——放牧永远是放牧,然而又不是放牧。
对于务实者来说,思想的奔涌最好不要超过脚下的速度,也就是说,灵魂不要总跑在前头。也许牧羊人一辈子不在乎思考什么,只在乎羊群怎么样。无论他思考的多么精妙,都不会多得一只羊。不如正经放羊,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羊是羊。不尝试改变羊群,也不尝试改变自己,放羊而已。
至于放牧的副作用,或者说是放牧的必然趋势,那就是能看懂少数的自然物象,而后顺其自然。那一山草木,秋天一到,忽如远行人,说走就走。那一亩大雪,落在羊的世界,遮蔽掉草莽贫寒。那一场寒流,窝藏小溪,未老先衰。人生天地间,全都是过客。人如是,羊群如是,山野如是。
醒来的花朵和草叶
麻雀时不时发生争执,藏在浓稠的柳树叶子间破口大骂。这么小的家伙,却火气大疑心重。乌鸦披着黑袍子,披着人类的偏见,穿风而去。喜鹊在枝头挑挑拣拣,衔着一段枯树枝。它的巢就在树上,栖息于此。树下一团黑雾般的蚊子,极细小,却极多。
每次路过这片树林,总觉得很吵闹。无数鸟儿在林子里认真过日子——低声啼叫的,彼此挖苦的,怒气冲冲的,笑哈哈的,有气无力的,嘲弄的,无所事事的。没一只省事的主儿。
人类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鸟类的世界也是什么样子。至少有的鸟儿就很肤浅,竟然把巢筑在小溪边浮着的枯枝败叶上。那是我见过最潦草的鸟巢——草秆,细枯枝,水草叶子,凑合穿插在一起,勉强算个窝。虽然母鸡抱窝也很敷衍,但人家知道选择在高处干燥处——草垛上或者乱草堆里一阵乱刨,扒拉出一个窝,左啄右啄,尽量舒适一点,绝不会这么湿答答地泡在水里。
鸟儿胡逛去了,那天我等了好久,没见到它回窝。也许这是它扔掉的一个废巢,它早就别处攀高枝另筑了新窝也不一定。
喜鹊窝很高,白杨树上随处可见。喜鹊喜欢居家生活,把破旧的窝修修补补,每个鹊巢都硕壮结实。而且,它们喜欢在旷野大树上筑三层,旧巢上面筑一个新巢,略微比旧巢小。最上面还有一个,不圆,有点像葫芦。凤非梧桐不栖息。而普通鸟儿们,有棵大树搭个粗陋的窝就很欢喜了。
喜鹊巢耐风吹,河西走廊多大的沙尘暴喜鹊窝都安然无恙。至于别的鸟巢,那就不好说了。至少一场大风过后,我常去散步的那条道上,有摔碎的鸟卵。我怀疑是麻雀蛋掉落的最多,麻雀小,筑不了大巢,顶不住风乱摇。
依照我的想法,小雀儿在灌木丛里筑窝是最可靠的。就算瞎老鼠啦,黄鼠狼啦,狐狸啦这些家伙,也不可能钻到枝叶密集的灌木里去偷鸟蛋。大多数灌木都带刺,密不透风。
然而小雀儿不可能和我有相同的考虑,它们的巢就在稍微茂盛一点的草窠里,有时候一群羊跑过去,它们的巢穴翻个底朝天,鸟卵破碎。反而在灌木丛里的鸟巢不多。大概鸟儿喜欢展翅就能飞的环境,如果在密不透风的灌木丛里,它得钻进去,植物的尖刺会刺伤它,而且逃命也笨拙,不能随时起飞。比起平地轻易地飞翔,在灌木丛里逃跑鸟儿有太多的劣势——遇见危险它只能丢蛋弃窝,呼啦一下飞走。
鸟儿各有脾气。有些鸟儿喜欢藏在密林深处隐秘的地方,巢穴筑在树枝稠密处。有些鸟儿选择山野岩石缝隙里,远离人烟。有些鸟儿藏在植被茂盛的草甸。有些则喜欢峡谷里幽暗的,被草木遮蔽的石坎下。深山里但凡草木茂盛的隐秘地带,都会有鸟儿筑巢。隐蔽,混入自然,是鸟儿的基因里携带的生存密码。
我常去散步的河边,林子边缘没看见鸟巢,不过鸟叫声可以听见,有时候稀疏,有时候密集。尤其清晨,鸟鸣层层叠叠,一波未熄,一波又起。鸟儿们刚刚睡醒,花朵盛开,草叶带露,它们大呼小叫,听上去高兴极了。对大自然的美,鸟儿有深层次的认知,它们能体味出一花一世界的喜悦之情。
鸟类的分布确实是个迷。我不知道在哪儿可以遇见什么样的鸟,在哪儿有稀缺的鸟。鸟类的分布可能跟它们的食物有关系,爱吃坚果的,可能就会生活在有坚果的坡上。爱吃草籽的,就会徘徊在杂草稠密的山岭。
人迹罕至的林子里,有大量的虫子,苔藓,蕨类植物,这样的生态应该会吸引稀罕漂亮鸟儿。不过,有一回我在雪山下一个原始林子里拾蘑菇,很少听见鸟叫。也可能时间不对,正午的鸟儿都睡了。离开的时候,遇见一只啄木鸟,乱蓬蓬的毛,刚干过一架似的。
有翅膀就太自由,可以到处飞一飞。尤其野草疯长的废墟,半荒芜,大路小路渐渐被野草攻陷,没有人迹,鸟群会聚集到那儿,飞到残垣断壁,飞到草窠里,飞到树梢,自在又快乐。
河边有一群白鹭,时隐时现,细长腿子,显得优雅高贵。我不知道白鹭的巢穴在哪儿,大概不很远。白鹭在浅水中溜达,不知道是不是捉鱼吃。河边只有水草,没有浆果野谷这些东西。白鹭到底吃什么呢?那可不清楚。
我对鸟儿毫无兴趣,因为鸟类古怪难猜。能认识的鸟儿也不多,只能粗糙地以貌取鸟,把它们分为好看的鸟儿和朴素的鸟儿,当然也有难看的鸟儿。白鹭就是好看的鸟儿。蓝马鸡也是好看的鸟儿。难看的是乌鸦,鹞子,还有那种脑门上顶着一撮毛咕咕叫的麻色鸟儿。朴素的鸟儿就是鸽子麻雀喜鹊布谷鸟这些。
鸟儿们才不管我怎么区分,它们飞来飞去,乱七八糟叫着,天知道说些什么。有时候活泼聒噪,有时候低沉浑厚。尤其春天,鸟鸣多得能把风挤走。大概大自然对它们有点疏忽,它们自己把自己叫醒,在花朵和草叶中唱歌,兀自欢喜。至少鸟儿对自己的啼叫心满意足,不然也不会那么狂热。
有没有不啼叫的鸟儿呢?它们害羞,孤僻,独来独往,只喜欢幽暗荒僻的深山老林,或者没有人烟的荒野。想来肯定有——林子大了啥鸟都有。
在荒野里走了很久,如果听不到鸟鸣,心里就有些不踏实。那种空旷死寂,让人觉得走在月球上。自然界中少了这一声,就少了生命的气息。那些稀疏的草木,石头,羊道,残断水沟,亮烈日光,群山之间的阴影,都让人昏昏欲睡,那样寂静无聊。
翻过一个山头,猛地听见几声鸟鸣,无论婉转还是生硬,都让人心里一动。那些尖嘴巴里吐出的音符,还有噗噜噜翅膀扇动的声音,是活泼的生命,是大自然吐纳的气息。
我们对大自然的美,感知迟钝。人类的渴念很多,精力不在发现美这块儿。大多数的时候,对鸟儿是一种肤浅的感知,虽然它们的确很美。谁会痴痴盯着一只鸟看呢?除了鸟类学家。
鸟儿的眼神对人类有足够的警惕,滴溜溜转着,稍有风吹草动立刻振翅飞走。说真的,鸟翼掠过树枝子的样子很美。如果我突然出现在树下,拿两块石子叩击,四周顿时寂然。鸟儿躲在叶影里悄悄观察,又惊又疑。许久,扑啦啦飞出一只,看不清样子,虚影一闪而过,钻进不远处的浓荫里。
鸟儿不得不怀疑人类。没事干的捣蛋小孩,偷猎者,还有鸟类研究者,都时不时劫掠鸟儿。很少,但毕竟是有的。比起天敌的追杀,有些掳掠纯属意外。比如土狗,闲得心慌就去抓鸟。老鼠啦,蛇啦,也会把顺道遇见的鸟卵幼鸟偷走。别看鸟儿有翅膀,其实也丢盔弃甲够狼狈的。
自然界所有的生物都一样,没有哪个一辈子衣食无忧。每个生物都有天敌,同时又是别人的天敌。这是大自然设置的一个循环,飞禽走兽都得遵循。鸟儿吃虫子,鹞子吃鸟儿,更大的猛禽吃鹞子。越凶的动物,狮子老虎,大雕黑鹰,越稀少——多了就会有大麻烦。最弱的,兔子小鸟虫子蚂蚁雀儿,反而遍地都是。
老天让每一个生命都有生存的智慧,或者是赋予了它活命的本能。如果哪种动物过于霸道无敌,所向披靡,老天就让它灭绝。
有时候想坐在树下结识一些鸟儿,然而蚂蚁很糟糕,跑来爬上脚,抖掉一些又来一些,只好走开。寂静的山林里,鸟儿的影子看不见,只有各种各样的鸟鸣,从枝头抛撒。有些柔和,有些粗糙,有些古怪。也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像从地缝里挤出来。也有些叫得支离破碎,让人疑心鸟儿的嗓子里埋伏着古埙,或者含着果核。有些叫声并不是一声,很短促,只有半截。剩下的半截被咽下去了。
我常去的无非就是这几个地方,河边的树林,山野里,路过的几个村庄。村庄里只有喜鹊和麻雀鸽子,叫声温和,其余的鸟儿见不到。河边的树林里鸟儿多,叫声婉转,带着水的颤音,很可人。而山野里,鸟儿不多,都是不常见的,啼叫野里野气,古怪,高亢,还能随意切换——一开始嘈嘈切切,叫着叫着尾声拐来拐去,令人捉摸不透,到底是什么意思?
山野里的事物,比别处更加强劲生硬,连鸟鸣都不例外。也许是山野经历了太多的风吹雨打。实际上深山老林里,遁世隐居的鸟儿多了去了,并不是每一种鸟儿都被人类熟知。至少那些百丈悬崖峭壁上,到处都是鸟巢,然而谁也搞不清是啥鸟儿。蝙蝠最喜欢隐居世外,当然不是长得丑,而是一些神秘的无法破译的谜团。
我去过一个叫布尔智的地方,据说这地方很久很久之前住着匈奴人。一个深谷里,两边都是万仞悬崖。一种鸟儿直直从草窠里往上飞,耸肩,一窜一窜,一节一节升到天空去了,翅膀一下都没扑扇,令人惊讶。而且叫声婉转洒脱,简直是世外高人般的脱俗不羁。可能是云雀的一种,太远了,无法确定。
峡谷里各种鸟鸣不绝,路边的芨芨草里藏着白腹蓝背的一种鸟儿,长舌妇似的,反复叫,呱呱啁,呱呱啁。还有一种小鸟儿叫起来像吹口哨,急促,清越嘹亮,太好听。
据说古代有人能听得懂鸟语。多好,可以和鸟儿聊天吹牛,琢磨鸟儿的生命线索,窥视深沉而神秘的鸟类世界。一般人不解其意,只能听听鸟叫,判断一下鸟儿高兴还是失意。
每次到深山,都觉得自己像个傻瓜——草木的名字叫不出,鸟儿的名字不清楚,单单听鸟啼就特别满足。那些留守的鸟儿,叫声可能就是本地方言。至于迁徙的鸟儿,肯定叫的是普通话。不然飞来飞去怎么交谈呀。
有一回,在青龙山半山腰,一个茶摊上喝茶打盹。那天走了很多路,累得精疲力倦。迷迷糊糊中,头顶的树枝上鸟儿叫,鸣啭不绝,音调拖得老长,像来自很远的地方。抬头看,几只灰色粗脖子的鸟儿,在树枝之间跳跃,歌唱,左顾右盼,并不怕人。迷迷瞪瞪刚睡着,它们炫耀似的大声鸣叫,把人吵醒。醒了,它们却不那么狂烈地叫,鸟鸣声又遥远模糊起来。
鸟儿的叫声里肯定在传达某些信息,或者是它们的心情。如果静下心聆听鸟鸣,可能会获得一些人和自然界相处的隐秘意味。什么意味呢?说不清,但确实存在。
鸟儿通过啼叫,与世界对话,与同类建立情谊和共鸣。然而有时候,它也和人类一样烦恼,辛苦觅食,又不知道把巢筑在哪儿才安稳。
总的来说,深山老林的鸟儿认真,枯枝干草羽毛搭窝,每只鸟巢都结实好看,一点都不敷衍。有的鸟儿甚至飞到牦牛背上薅牛毛,铺在窝里软和温暖。啼叫声也比较纯粹,像唱歌。
我常常去散步的河边林子里,鸟儿搭窝就潦草多了,胡乱凑合个窝,也不挑地方。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这河边的鸟儿叫声焦躁不安,音质粗哑,似乎心神不定。
后来,那片林子被砍伐了一大片,一地残枝败叶。黄昏时分,倦鸟归巢,巢不见了。那是一种极其惊慌的鸟鸣,一层一层重叠,那么激烈又哀伤。暮色笼罩,河边的鸟鸣反常地稠密,它们拼命叫啊叫,又一次丢盔弃甲。我觉得鸟儿们瞬间苍老了很多,声音沧桑凄凉——这些涉世未深,而提前衰老的小家伙们。
鸟儿和林子,彼此之间要交换一些东西,鸟儿交出鸣叫和巢穴,林子给出荒芜的符号。大自然给每个生命都准备了坎坷,即便是鸟儿,也得学会沉浮打磨,度过艰难。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必须得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