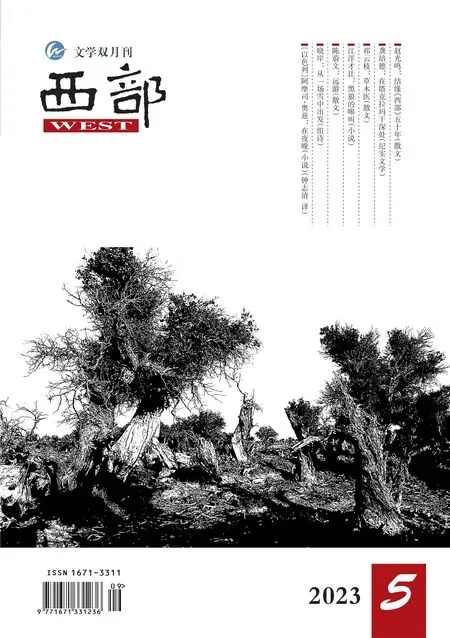前辈风范
中原
引子
退休后,除了开启个人新的生活圈子之外,当年工作时的种种人和事,也时不时在脑海中回旋。有对自己年少轻狂的反思,有对编辑生涯中诸多失误的惭愧。反思、惭愧之余,有几个人一直令我念念不忘。他们是长者,是前辈,也是领导,按理,我等后生小子应该和他们没有太多的交集,只有崇仰的份,但他们对我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前辈言传身教的影响和教育,师友们有形无形的感染和熏陶,让我懂得,要安于编辑职业,努力学习,兢兢业业地工作,娴熟地“煮字烹文”,把“为人作嫁衣”做好。正是如此,我这个编辑小白,也才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编辑,甚至还评上了正高(编审)职称。近读宋代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内中几句话,我觉得对应他们是再恰当不过了:“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王谷林
文艺圈里有点年岁的人,很少有人不知道王谷林的大名。
1976 年8 月中旬,我和杨晓芬、董为清同一天分配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当时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艺创作研究室)所属《新疆文艺》(汉文)编辑部当编辑。据编辑部负责人韩文辉介绍说,编辑部主要负责人是王谷林,他现在正在党校基本路线学习班学习,过几天才能结束。一周后他回来了,和我们见了面。他胖胖的,高高的,颜面红润,说话不多,慢声细语,和我们一一握手,并说了些“欢迎新鲜血液、多向老同志学习”等套话,但很亲切,很有领导风度。又过了几天,毛主席逝世,我们既忙于写怀念的文章,又要到社会的各方面去组稿,我向他请假外出时说了一句“王主编”,他当即正色说道:“在咱们文联不要称呼官衔和职务,一律称同志。这是当年刘萧无同志规定的。你可以叫我老王,也可以叫我王谷林同志。”听罢此言,我顿时肃然起敬。
后来听其他同志介绍,王谷林毕业于中央文学研究所,又在中国作协所属的《文艺报》任记者、办公室副主任,属于中层干部。刘萧无任新疆文联党组书记后,鉴于新疆文艺界缺乏人才,便让其弟刘白羽推荐一些可用之才,于是就有了王谷林1961 年的举家西迁新疆,任职新疆作协副秘书长、《新疆文学》副主编。现在看来,这个职务似乎不如在《文艺报》,但他却不在乎,由此我对他的敬意又增加了几分。
作为一个刊物的负责人,王谷林的表率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按时上班,伏案看稿,和编辑商量稿子的取舍,编前会和下一期的编辑计划等都做得举重若轻。他曾对我们几个年轻编辑说,现在稿件很多,质量参差不齐,大多数不退稿,但有些有特色的、有修改价值的稿件,有必要退稿,回信要反复斟酌,意见要具体,要说到点上。而几个老同志谈得最多的则是,王谷林很反对编辑搞创作,认为编辑写小说,写诗,势必分散精力,搞不好编辑工作,且有将业余作者的稿件窃为己有之嫌。据说,有几个编辑就是因为坚持搞创作而被他调出了编辑部。也许有人认为,王谷林自己写不了什么,所以才不让编辑搞创作。其实不然,把《新疆文学》1962 年第一期的《迎新曲》读一下,跃然纸上的是文采斐然、满怀深情,那就是王谷林执笔写就的。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就是王谷林的编辑观。当然,也不是绝对的,编辑写的评论作品,陈柏中、郑兴富等介绍新疆风物、点评年轻诗人的作品,他还是很赞成发表的。
我们几个年轻人有时和其他编辑讨论稿子,议论作者时,嗓门较大,他一般是不管的,偶尔让我们小声一些,他有时手持烟卷,也参与进来。但有两个编辑,仗着资格较老,经常八卦一些文联的人和事,他在里间屋听到了,当即严厉地训斥,一点也不留情面。我们也都惴惴不安:训斥他们告诫我们?不像呀!听同事们说,王谷林对编辑们非常关心爱护,不遗余力地奖掖扶持,他今天咋这么严厉?直至1990 年初,我到北京出差,那时他已从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机关党委书记任上离休。我在作家出版社遇见他的小女儿,请他转告我的问候。谁知没过几分钟,他女儿就告诉我说,她父亲请我后天到家中做客。他和夫人非常热情,饭菜丰盛,且有好烟好酒,我也就不客气了。酒酣耳热之际,我问他,当年你为什么那么不留面子地训斥某某编辑?他说,他们几个派性十足,一贯传闲话,破坏团结,非常讨嫌。编辑部怎能容忍这种风气!
大概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吧,编辑部某领导交给我一沓厚厚的稿件,说这是王谷林的电视剧本《饮马长江》,让我处理一下,在咱们刊物上发表。还说,稿子太长,近七万多字,刊物发不下,要删掉三分之一。于是我就按照领导的意见,用了近十天,删除,合并,改写,剩下不足五万字。发表后,据说王谷林很不满意,没有把他的意图表现出来。我也很惭愧,只是没有机会向他解释,或者说没法解释。一部完整的作品,你砍掉三分之一,怎能不伤筋动骨!不过这还算好的,盛名如刘萧无,创作了一部描写抗战时期女文工团团员成长历程的电影文学剧本《乔娥》,对当年那烽火岁月深情倾注,到头来也始终没有一个刊物发表。
2003 年,王谷林因病去世,我写了一篇短文,主要是检讨在《饮马长江》处理上的失误,以对这位我的编辑生涯的师长表达怀念和歉疚之心,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发表,不免遗憾。
韩文辉
他是我们分配到编辑部后第一个和我们谈话的领导,地位大概仅次于王谷林。高个,显得腰有些弯,头发有些花,五十多岁的样子。他说,我叫韩文辉,陕西人,你们以后叫我老韩就行。简单几句话就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老韩还说了几句话:“当编辑很难,政治的,业务的,组织联络方面的要求很多。要多向老同志学习,多读一些书。咱们资料室各类图书资料很多,有两万多册,你们要充分利用。”从读书的意义上说,老韩的这番话是形而下的,带有强烈的功利心。但对我们这些读书很少又初当编辑的青年人来说,却是十分必要的。以后很多年,我在这个资料室借阅了各方面的资料书籍数百本,历史的、宗教的、民族的、民间文化的……极大地提高了我的编辑素养。
老韩是1962 年从新华分社调到文联来的,从分社采编部主任到新疆作协无职务,当然是贬官。二十年后落实政策又调回了新华分社,从此联系就少了。在老韩年近九旬时,我去新华分社住宅区看望他,家中挂着他书写的一句诗:“腹有诗书气自华。”他送我两本书:《回眸记者生涯》《新疆纪行》,都是他退休后所作,质朴无华,感情真挚,处处显示他对新疆、对事业的热爱。我想,他这些年可能读了很多看似无用的书,所以字里行间无不显示出“气自华”。
癌症是否是绝症?是也不是,老韩所患的癌症就不是。老韩1990 年代初发现自己患了癌症,但经过化疗,肿瘤奇迹般地消失了。为什么?我想,是他心胸开阔、为人厚道。这里讲两件小事,第一件,我刚分配到编辑部没多久,一天,有两个同事把我叫到一边,说你要特别警惕某某人,他们都不安分,你别上他们的当。我没见过这两人,不好说什么。经过几十年的共事,我觉得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们都是很优秀的编辑,都比较长寿,而诋毁他们的那两个人,早已去世。十几年前我在陈柏中家说起这事,脑海中突然电光石火:包括王谷林训斥的两个捣是非的编辑,也都病榻多年而去世,可见搞鬼的人都不会长寿。第二件,1978 年,中国作协新疆分会恢复后,王谷林任副主席兼秘书长,老韩正式接任《新疆文学》主编。一次主持编前会,在讨论采用稿子时,决定用某编辑处理的稿子,杨晓芬已经处理完的小说缓用。杨晓芬的脾气上来,大吵一顿不说,改稿的红墨水瓶也随之扔了过去,搞得老韩衬衣上红花点点,而她自己,也是委屈得泪水涟涟。第二天,杨晓芬意识到自己过分了,早早上班打扫卫生,打开水,等老韩来了又是一番检讨,乖得不得了。老韩久经沧海,怎会和这个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的妮子计较呢,反倒是对她良言相劝。我很难想象,如果今天发生这样的事,会是怎样的情景。后来落实政策,老韩调回新华分社任副社长,大家设宴相送,晓芬还和他合照留念呢。你说这样的人怎不长寿!当然,天命不可违,老韩终于在2016 年10 月驾鹤西去,享年九十三岁。回想四十年的交往,怎不令人怀想!
王玉胡
关于王玉胡,二十余岁即以电影《哈森与加米拉》享誉全国,以前无缘相识,只有钦佩的份,到自治区文艺创作研究室后,在众多大腕中才见到了他,当时他任创作研究组组长。我与办公室主任李文去吐鲁番调研。行前王玉胡叮嘱道:“调研要实事求是。”外调回来后,我把调研情况整理成报告交给李文,李主任这时正被一些杂务纠缠,就让我先送到王玉胡那儿。第一次进他个人的办公室,我发现有一个大书柜,里面有不少好书,其中他的电影剧本选集《绿洲集》因为是绿色硬精装,很显眼。他发现了我的关注,就问:“你看过?”我说:“之前买了一本。”他说:“提提意见。”我在高中阶段非常喜爱电影剧本、电影理论,面对前辈此时也不知何为谦虚,就把我读他剧本的感想直接倒了出来:“《绿洲凯歌》对新疆农村妇女斗争经历的描写令我感慨良多;《黄沙绿浪》的对话太多。根据夏衍、张骏祥所说,电影应该以动作、表情为主。”他问:“他们的电影理论书你都读过?”我说:“读过。有些段落还能背呢。”他说:“这些书我也读过,也参加过几个学习班。只是……”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他没有就这个话题继续说下去,转而说:“文联是个好地方,有很多老同志,你多努力吧!”
1985 年7 月,中国西部文艺研讨会召开前,他沿着奇台、北塔山、青河、可可托海一带访问熟识的朋友,然后赶赴伊犁主持研讨会。据同行的作家吴连增讲,他这是为他创作《冬不拉之歌》体验生活,搜集素材。这部电影剧本在《中国西部文学》发表后,我认为是一部很不错的剧本,但没拍摄。1992 年,适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我奉命采写抗战老战士刘萧无,有些事需要听听王玉胡的意见,我就电话预约去他在幸福路的居所拜访。事后谈到《冬不拉之歌》,他十分无奈地说,现在是市场经济,电影厂也要自负盈亏,什么能吸引观众、能挣大钱,就拍什么,想通就行了。此时他的身体很不好,脸上那种疲惫的表情让人看着心酸。
2008 年,王玉胡因病去世。去世前,根据他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边陲纪事》充实而成的《新疆平叛纪事》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他给原《新疆文学》编辑部的同志每人赠送一本,可见他是一个很念旧的人。
俗话说:“三年学说话,一生学闭嘴。”我这个人却做不到,在很多场合不会转弯,发表意见很直接,难免得罪人。听说,王玉胡任党组书记时,编辑部某人大概是被我争辩得气急了,跑到他的办公室,不顾另外有人,直接告了我的状,说我多么狂妄,多么目中无人。王玉胡听后当即拉下脸来,冷冷地说,等你有了他那样的知识水平再来找我。听了此事,我的心灵深受震撼,不为他为我护短,为的是他的一身正气。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心情不顺畅都难。
刘萧无
刘萧无,我知道得很早,那时他五十出头,但却已显得步履蹒跚。再见到他,已是十年后,他分配到文联不久。文化单位嘛,许多人的诗和文章都写得不错,刘萧无的几首七律,大家公认水平最高。
他写的那几首诗,后来在某学会编辑的《刘萧无诗词选》却没有入选。我还专门问过他,他轻描淡写地说:“底稿丢了。”其实,通过1992 年和他的接触,我知道他丢掉的东西多了去了。抗战时期写的十余部鼓舞人心的剧本,进疆后写的话剧《伊吾四十天》由六军文工团演出数月,剧本却遗失了,根据民间长诗创作的歌剧《渭干河》则没有编入任何集子。他给的说法是,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就达到目的了。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的文艺观,抑或说,在他心中,除了文艺为人民,再无什么名利萦怀了。
进疆时刘萧无是一兵团六军的文化部部长,本来要随军部调到西北军区任职,据说是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但临行前同王玉胡一起被王震留下,他任分局宣传部文艺处长,王玉胡任王震秘书。他在战争年代落下的失眠症却长期困扰着他,于是找了个合适的机会到北京治疗。他是晋察冀出身,北京多有战友,大家劝他在北京工作也挺好呀!但他终究没有留在北京。克拉玛依矿区出油后,他立即返回新疆,奔赴克拉玛依,住帐篷,喝碱水,迎风沙,写出了轰动全国的《克拉玛依散记》。晚年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不留在北京,他说,我还是迷恋写作。一个人的成功,与外部环境密不可分。在不对的地方,你再有能力也难以发挥作用。从王震同志把我留在新疆起,我就知道我今生是离不开新疆了。
刘萧无晚年另有两件事很值得说说,一是创作旧体诗词,二是钻研书法。他有深厚的旧学基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调到文联后开始创作,有几首很有名,如《八声甘州·沙枣》《贺新郎·红柳》等。离休后他又系统地研究了诗词格律,诗更隽永,曲更流畅。他自己说,他的书法很一般,从八十年代开始加快了钻研的步伐,以《爨宝子碑》为中心,参照《龙门二十品》,果然自成一家。他的书法作品,写的都是他自己创作的诗词,这样的作品可称“二美并”。但他也为我破了一次例:我一位克拉玛依的朋友,指明要他写一幅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他答应了,过了一周,就让他女儿玲华给我带来了用爨宝子体写的书法作品。另外,他的书法作品从来不卖,通通送人,朋友、战友、熟人等。他送我的,几达二十幅之多,有的署上名送我,大多只署他的名,说,拿去送人不会太丢人吧!事实上我大都送朋友了,而且还倒贴了裱糊费用。
我曾跟郑兴富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用在刘老身上是否很恰当?老郑说,小鬼是谁?我调侃道,你很合适。他气得抬脚就要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