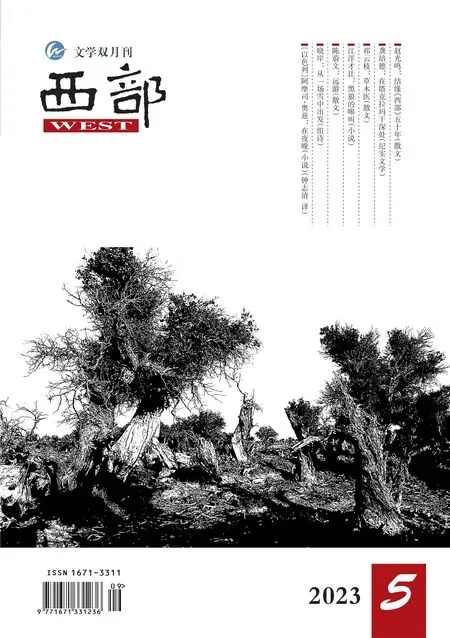写在文联七十岁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应该是1983 年9 月中旬,我走进了新疆文联,那是我在文联踏出的第一步。离开文联的最后脚印是在2017 年4 月中旬。算起来差不多三十四年。
第一次走进文联的那天,是走进民主路靠近和平剧院的那座三层楼。那座楼是1950 年代的建筑。土黄色的墙,绿色的铁皮屋顶,门窗天花板是绿漆,棕色的木地板,木质的楼梯。楼道里有人说话,会有回音。墙体很厚,宽宽的窗台,放很大的花盆和文件筐还是绰绰有余。整座楼冬暖夏凉。
记得我是带着敬畏的心情走进那座大楼的。因为那座楼是我走出大学校门,开始职业生涯的第一座楼。用那个时候的话讲,走进这座楼就是“走上社会了”。
进门的第一天。我一个人站在二楼一间挂着“组联处”字样的办公室门前,脚下是有点松动的木地板,年久失修,走在上面会有木板摩擦的声音。搞卫生的大姐告诉我,楼里的人正在开大会,就在楼道西头有两扇门的会议室里。我便走向那两扇门,尽量不让脚下发出声响。还好,我那时的体重四十七公斤,下脚轻,不会惊动里面开会的人。
透过虚掩着的门,果然见一屋子人在开会,烟雾缭绕的,大概五六十个人,衣服颜色差不多都是军绿、灰、深蓝,偶有颜色鲜亮的头巾和时髦的卷发,桌椅有点像中学教室的,一排一排。正说话的人显然看见我了,因为他的位置正好对着门。他看见了我,但并没受干扰,而是自顾自讲话,在座的人也都听得认真。印象里,说话的人一看就是领导,戴着一顶黄色的帽子,白色的衬衫挽着袖子,肩上还披着一件深蓝的中山装。那座楼到了九月,室内便有些凉意。毕竟,它是一座兴建于1950 年代的老楼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说话的人是王玉胡老先生,而那天是他最后一次主持文联工作会议,因为他要退休了。那天,跟他在一起的文联领导还有铁依甫江、库尔班阿里,如果没记错,应该还有刘肖芜老先生。他们当时在新疆文艺界赫赫有名。
我很感恩自己在文联三十多年的经历,文联在自己成长的同时,也让我们成长。
在文联当文学编辑的那些时光,尤其使我受益。
我们《新疆民族文学》编辑部对面是当年的《新疆文学》编辑部。那间办公室有张黄色的桌子,木质的,上有三个抽屉,下有两个门,桌面宽宽大大,黄色的油漆斑斑驳驳,显示它曾经的沧桑和荣耀。而《新疆文学》的老师们对它也总是津津乐道,说当年茅盾在新疆曾用过那张桌子,1960 年代王蒙在新疆也曾用过那张桌子,后来的几任主编也都是那张桌子的主人。有老编辑调侃说,谁有幸成为那张桌的主人,谁就能沾上那张桌子的灵气。于是,很多日子里,我们几个年轻人便会有意去触摸它,礼敬它。灵气不知沾没沾上,但内心的成长因为有了那样的“古董”,总是有所积累的。
我们《新疆民族文学》杂志两任老主编郭基南老先生和郝关中老先生,毫无疑问也是影响我、使我难忘的两位长者。
郭基南是锡伯族作家、诗人,精通汉文、满文、锡伯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被特别邀请到北京,参加故宫满文文献的整理。而我参加工作的那几年,他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龄。他有得是资历和经历,却一点架子都没有,活脱脱一个邻家老头儿。一个普通的邻家老头儿,做事儿却那么兢兢业业。早晨上班,他甚至比我们年轻人还早到办公室。他家住南门,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冬天夏天皆是如此。他并不知道他的早到,给我们几个年轻人带来的困扰——毕竟,年轻的我们需要懒床,割舍不下的晨梦对郭老早已无所谓了。害得我们为了不让他感到我们“没眼色”“不懂事”,也得赶早去办公室,然后假装提一暖瓶开水,或擦擦桌子,帮他整理一下他编辑过的文稿。时间长了,我们发现,其实他并没有在意我们。郭老编辑稿件时从不用钢笔,而是用毛笔。红色的和蓝色的墨水瓶,在他的桌子上至少有四五瓶。毛笔用墨水多费啊,蘸几下,墨就剩半瓶了。他用毛笔编辑,方格稿纸上一圈红一圈红,又一圈蓝一圈蓝。与这些红圈蓝圈一同印在稿纸上的,还有他桌子旁的窗台上一盆大叶子海棠花的落花。海棠花开无尽,郭老师划的圈圈也会无尽。就在他那些无数个无尽的圈圈中,我学会把来稿中疙疙瘩瘩的文字语句,变得有序,读起来流畅。然后,把学到的功夫再用到自己的写作中,让自己的文字更具有文学的语感。
郭老退休了以后,郝关中老师接任杂志主编,成为我的另一位人生导师。郝关中老师是新疆著名的维汉翻译家,曾翻译作品《离骚》《聊斋志异选》《鲁提菲抒情诗选》《纳瓦依抒情诗选》等,也是王蒙在新疆时的老朋友。1985年,我的第一篇小说《额尔齐斯河小调》在《民族文学》发表。那天,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看他正在读那篇小说,便有些忐忑,下意识往后退,准备撒腿开溜。根本不知道他会说什么,万一被数落了咋办?只见他面无表情地说:“回来,回来!”我便又走回去,等待发落。却听他说:“你这个娃儿起点挺高!好好写。”然后他抽了一口烟,发黄的手指弹了弹烟灰,他抽烟很厉害,是多年搞文字养成的。烟灰弹到桌子上,他熟练地吹了一下,又说:“当然,我可提醒你,以后想写东西,千万不能沾上官僚气,更不能沾上铜臭气。”这是郝老师的原话,我一个字没动。只是,到今天我也没有真正搞明白,他为什么看了我的小说后,把“官僚气”和“铜臭气”两个词联系起来说,因为那篇小说写的只是一个小盲童和奶奶的故事,这两个词与小说内容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随着时光推移,随着我的成长,我已然明白那其实是一个长者对晚辈的人生教诲。
文联的七十年,我有一半的时间在它的怀抱里。1990 年,文联搬离了民主路的那座三层老楼,去了位于红山商场旁的新大楼。这是应了那个年月自治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的需要,确实解决了文学艺术界艺术家们工作和活动的困难,文艺家奔走相告。记得当年新大楼里,大家议论最多的是大楼的设计理念。了得啊!一座楼的设计灵感竟然来源于一支钢笔?!没看见吗?这座楼的楼顶就是笔尖啊?它直冲蓝天,楼体的中缝就是笔尖缝的延续,是墨水通过的切口,墨水途经中缝,流向笔尖。十五楼的大会议室,其实就是钢笔笔尖的气孔,它位于笔尖的中间位置,钢笔不会漏墨正是因为有它。由此,我们搬进新大楼时的心情可想而知,况且对面还是《新疆日报》的大楼。这座大楼与红山比邻,矗立于河滩公路旁,旁边有老邮局大楼,有红山商场,还有揽秀园,西大桥,西公园,这座城市的文化制高点非我们楼莫属!那种感觉确实令人骄傲。再别说1990 年代初,整个乌鲁木齐没有几座大楼像文联大楼那么气派。关键是,我们还有电梯!足见上级部门对文化事业文艺事业的重视。
1990 年代中期,因为整个经济形势的影响,维修经费不足,大楼电梯停了,大家每天爬楼,最高的要爬十五层,有调侃说,上班从一楼爬起,到了楼顶,也该下班了。那几年,大家心里虽然少不了几句牢骚和怨言,但当那段断电的日子成为往事,电梯复行,大楼重新装修,却蓦然间为那段日子里大家的坚守而感动——整个大楼没有哪个杂志、哪家协会和办公室,因为没有电梯停止办公。
就在这座楼,老一代的编辑一批一批退休。有人回内地了,有人因身体等原因离开了我们。他们都曾为自治区文艺事业的发展做出过力所能及的贡献。我也从一名普通编辑成长为编辑部副主编,《西部》副主编,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到县里挂职驻村,进入文联党组并做作协的工作。一路走来,收获总是沉甸甸的。
近几年,走进文联大楼,看到的皆是年轻的面孔。他们大多是大学生研究生,有知识有学历,真正是起点高的一批人。我和很多与我同龄的人一样,既羡慕他们拥有的青春,又对他们寄予厚望。毕竟,他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未来与希望在他们身上。只是,他们看我们的目光,会不会也像当年我们看老一代文艺家那样,抑或,在他们眼里,我们像当年那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