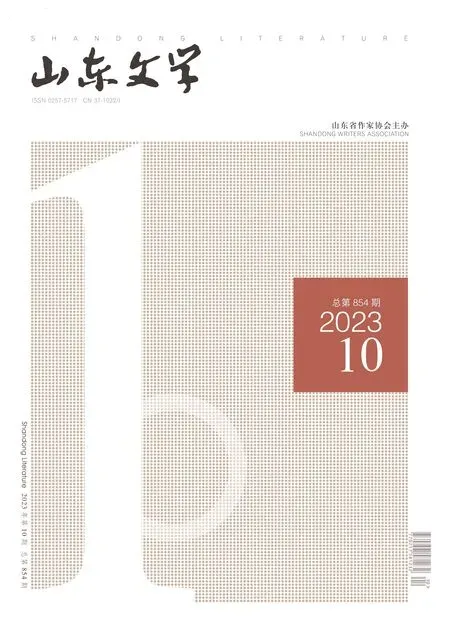樱桃花开
徐全启
一
那年代小孩子格外多,在村里,每个年龄段总有十几个小孩,于是小学在村里上,初中就统一到片里去。所谓的片,就是五六个村形成一个中心。一般找一个大村作为片区的中心,有五六个村统一置换一块土地,合伙盖上几排瓦房就成学校。
我们的片区在邻村大庄,与我们村间隔三里多地。大庄民风淳朴,多数人姓张,环境好风水也不孬,地下水清凉甘甜。夏天天热时,我们每到下课,就寻找开门的人家,看着院子有压井,直接进去找水去。
她是我们上一届的女孩。虽然跟我同岁,但因高一级,她让我叫姐。记得当我们徘徊着到处找压井的时候,她淡淡的一句:“跟我来吧,我家离学校稍远,可每天敞着门方便呢。”她剪着短发,皮肤白白,不胖不瘦的身材恰到好处,不高不矮的身高绝对入眼。圆脸蛋姿色融融,弯眉毛情意自然,说话时浅浅的酒窝淡淡地透着善良与温柔,自然红的嘴唇让人想起开放着的杏花红。
她家的院墙是用手抓石砌筑的,一块块鹅蛋般大小的石头,一块摞着一块,远看像张图画。门口的木大门是用几块板子简单拼在一起的,庄户人家没钱刷漆,幸亏有门对子盖在上面。记得她家的大门对子都是贴的板板正正,而寓意也特别,要么“国家政策好,人民大丰收”,要么“福临门第,祖国富强”。
“俺爹是当过兵的,他讲究!”她指着门对子有点炫耀着。那时候在农村,谁家有当兵的,是受人尊敬的。她的父亲当过兵,立马让人感觉不一般。
学姐姓张,听说学习特别好,长得又很漂亮。于是,她的家就成了我们课间休息的向往。“没事的,你们尽管到我家里来,正好下课时间我要回家照看一下奶奶,”她指着屋里说,“奶奶眼睛看不见。”她说着顺手提起猪食桶,用塑料瓢舀起来,两头黑猪嗷叫着趴在猪食槽子上,吧嗒着嘴吃起来。她笑了,笑得真是阳光灿烂。
她家从大门通往正屋的路也是用碎石铺的,大小不一,颜色统一,用砖镶着边,仿佛是地图,简单而古朴。四间瓦房,玻璃窗已不明亮,入户的风门子还是用山草编扎而成的。她进屋抱出了被子,随手挂在庭院南北连着的铁条上。她对奶奶很孝顺,几乎晴天就晒被子。压井的位置在院子的东面,井的南侧是大门口,门口东边是一棵十几公分树茎的樱桃树。
我第一次到她家的时候樱桃花正浓,满院飘香,蜜蜂嗡嗡。花瓣偶尔随风飘飘,地上白花花的一片像碎银子一样。
“哦,真美!”我看着往铁条上晒被的学姐情不自禁。学姐微笑着也如花一样,她走起路来是弹跳着的,随着她的脚步,粉色的花瓣四散开来,当时在我的心中学姐就是女神,最美的风采。
此后,或许是心照不宣,或许是习以为常,反正课间操的时间,我总是要溜达着到学姐家,拿着瓢喝着水,喝到肚子里的水甜甜的,眼睛也不闲。或许是青春期冲动,朦朦胧胧的,我游离的目光总在欣赏学姐的黑辫子,她白胖的圆脸以及她的体香。学姐的老爸是一个魁梧的汉子,经常扛着锄拿着镰,风风火火的勤劳样子。不知为什么,见了他喊了一声叔,我的脸通红通红。
“姐,你长大了想干什么?”我们私下里进行了交流。学姐在学校里学习好是有名的。
“干什么都行,只要离开农村就可,吃不上喝不好的日子不好过。”学姐因为有目标,平常格外努力,几乎从学校到回家的路上都背着英语单词及数学公式,且干活的时候,手里从来都是拿着单词或公式的小抄,不时地看着念着。
本来我学习也很好,可不知为什么,喝着凉水欣赏美丽的过程中,我的英语一落千丈。数理化都强,可120 分的英语成了我考学的路障。
樱桃花开花落又结果,小时候的夏天,印象里太阳特别的毒辣,晒的头皮都火烧火燎。“来,你压会水,天太热了,我泡泡脚!”学姐的脚又胖又白,让人心猿意马。“看什么看,快压水呀!”学姐喊着傻乎乎的我,“洗洗脚,再用洗脚水浇浇樱桃树,这样子不浪费,知道吗?这棵树是俺爹从战友家移来的小苗,果子可甜了!”于是,我呱嗒呱嗒地使劲上下启动着压井把子,学姐一桶一桶地将水浇到叶子卷曲的樱桃树底下。
“樱桃树好拨弄,生命力强,只要有土的地方都可以生长,开花好看,结果甜甜!”学姐说话时嘴唇红红,牙齿白白,鼻子随着脸一翘一翘的煞是可爱。
“你看下面长了这么多的枝杈,应该会拔出去,这样有利于树的成长,这樱桃树真有趣,根长。”浇过水的土松散着,树底下的幼苗经她小手一拔就出。
“能栽活吗?”我问学姐。
“应该能吧,栽多了占地方,”学姐边拽边说,“树根茂密影响种菜园!”在我们农村,屋前屋后只要有闲地方,一般舍不得干别的,都是会刨起来种点菜或者粮的,这样既方便又增加口粮。
“给我棵栽到俺的家门前吧!”我帮着学姐拽出了一棵稍大的,“我把它栽活,到结果时到俺家里吃果子,好吗?”“好啊好啊,来,我给它系上一点红,俺爹说用红毛线绳系,吉利还好活!”她边说边从头上扯了一块红毛线头绳系在小樱桃树的枝杈上,她粉丹丹的脸上是开心的笑容。
“咦,你的胳膊怎么了?怎么一大块青?”学姐看着我接过树苗的手惊讶地问。
“没事,上课时胳膊过界了?”我淡淡地回答。
“你同桌不是个营房的女生吗?怎么不像个女人?”学姐边说边拽了我的衣角一下,“痛不?你不好意思说,用不用我找找她?机关人又怎么了?都是同学,农村人就应该受欺负?”很明显学姐生气并心痛,我看着很感动。不知为什么从此以后的一段时间,我把学姐当成了自己的未来。
学姐学习认真,终于考上了中专,成了手捧国家铁饭碗、一辈子可无忧无虑的正式工。接到红色通知书的时候,我们都很高兴。当时樱桃熟了,一簇簇的樱桃闪着光,发着亮,红彤彤的在太阳下微笑,麻雀叽叽喳喳欢呼起来,瓜熟蒂落。随着温度的升高,地面掉了一层红樱桃,像红地毯似的。
“你吃树上的吧,”学姐客气地对我说,“我从小爱吃掉在地上的樱桃,熟透了掉下来的甜。”她边说边捡,随后就到压井旁的水桶里去洗,白白的小手捧着红红的樱桃伸到水中,真的是一红二白。
我伸手摘了一簇樱桃,边往嘴里塞,边看正用水洗樱桃的学姐。红袜白裤像芙蓉似玫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正值青春期的我有点热血沸腾。不承想,她也抬起了头,就在这红红的樱桃树下四目相对的时候,我像个小偷一样的心扑通扑通乱跳。
“别摘成簇的,那样的爹好拿到市场上去卖钱,要摘就摘单个的。”一起喝了几年井水的原因,学姐没把我当外人,手捧着洗好的樱桃走过来,“你尝尝,是不是掉在地上的甜?”
我没有再去摘,而是接过她手中的樱桃。她的手暖暖的,特别温柔,女人是水做的,两手接触的瞬间立马过电一样。樱桃在手中,感觉神秘而亲切。
“你拿回去的樱桃栽活了吗?”学姐也是脸红红地问我。
“嗯,我栽到门前已经活了,等结了果一定到我家去吃。”我随口回答。
“好好上学,上好了学才能离开庄户地,才能有前程。”学姐没有正面回答我,而是语重心长地叮嘱着我。
八十年代刚有黑白电视,武打片是《射雕英雄传》,小龙女与牧羊曲让人神魂颠倒,而台湾的琼瑶阿姨又来了个《在水一方》。学姐上学走了,她去了远方,井水也喝不到了。于是,稍有点激动的是我幻想着当个作家,靠写作一样也能成为正式工有出息。
梦里有许多的故事,几年时间,我成了作家,学姐笑嘻嘻地牵着我的手漫步在田间街头。可现实是梦想没有成为未来时候的故事,初中毕业成了我的最高学历,现实很残酷,我成了建筑工地推小车的壮工,而学姐当了医生。
时光如水,静默不语,仿佛就在花开花落的一瞬间,时光便化为了春色里的一缕香魂,渐行渐远,但樱桃树下雪白的小手,白里有红的红樱桃,像梦永刻心中。
二
医院的路上真是人山人海,春季乱穿衣,穿单衣的看不见冷,披棉袄的不见得热,反正凑在一起挺热闹。急诊与门诊一串串一排排,猛然一看就像有什么利好等着似的,急切并认真地排着队。
过去体检没有肠胃镜的检查,随着医改增加了该项内容。人过五十确实应该进行肠胃的检查。肠子无神经不知疯不疯,或许不疼不痒的时候就有可能因生活习惯及遗传基因的问题而发病。
白白的床单软软的床,躺下来心里有点发慌。“脱下裤子,露出屁股!”一个女医生的声音,有温柔中的不容商量。瞒过爹娘瞒不了大夫,我不得不脱裤子,顺手摘掉口罩。
“是你?”温柔的女医生带着惊奇,中等身材的女医生戴着口罩,我只能看到她圆圆的脸,炯炯闪亮的眼睛,看样子是熟人,我立马满眼通红,因为肠胃镜就必须得光着腚。
“张嘴,一点麻药马上睡觉,别心慌,一会就好昂!”声音是亲人般的温柔。她是谁?亲戚还是村里人?似曾相识,不常相见,但感觉温柔漂亮。我陷入了沉思中。似乎昨日还在踏着寂寞的跫音,还在迈着寻觅春色的怅然脚步。怎知一个回眸,一个转身或偶遇,与她便相逢在这令人心醉的春天。
“醒了吧?提上裤子吧,慢慢提!”女人的声音就是春天阳光的温柔,“幸亏检查得早,估计没事的”,随后,她与另一个女大夫扶了我一把,看我提好裤子,她摘下了口罩。
“是你?”我惊奇着张大了嘴巴,“姐!”虽然这么大岁数了,可依旧脸通红,又有点小偷做贼的感觉。多少年没见的学姐,我少时的伙伴,曾经的偶像,人生的迷茫中想象的方向。
“先到病房打个葡萄糖,补补营养!”她的眼睛里有闪亮且晶莹的光,“你先休息,待会去看你,我们还要忙!”
躺在病房的床上,我不断地揉着眼睛心中激动,是真的吗?真的难以置信,曾经夜思梦想的学姐竟然出现在我光着屁股查体的病床。她依旧年轻,仍然美丽,还是那种楚楚动人的感觉。同在一个城市,学姐考上学后三十多年没见,就像隔着千山万水般遥远。
我看着窗外盛开着的樱花,怒放着的迎春花,缭绕的情缱绻的念都融合在春的枝头摇摆绽放。窗外静怡的光阴,陌上花正艳,那一朵一朵的花骨朵紧凑着,拥抱着,依偎着,含苞待放。此刻,多想借助这撩人的魅惑写尽四月花开的婀娜,旖旎一段情感的传说。奈何学识浅薄,只能蘸着曾经的相思,屡屡描摹过去的轮廓。
上学时,曾经咯咯笑着按着压井把子使劲压水的美丽、翘着腿够樱桃的楚楚动人、手捧樱桃一白一红的清纯可爱。
我正在沉思她推门进来,“人到了五十就应该体检,你肠壁上有四块息肉,肉眼鉴别应该没问题,但末端已有血渍,这样下去极有可能出现问题,幸亏来检查得及时,以后一定要注意,千好万好身体健康比什么都好!”她边说边走近前来。
岁月是个无情的恶魔,她虽然仍存风韵,但是眼角遍布皱纹。苍天也不公平,相见年轻,再见如影随形,可只能说往事如风。
“劳模是免费体检,你好棒呀!”学姐说话的时候露出雪白的牙齿,很明显,其中有闪着银光的两颗镶饰物。
“农村人除了干活什么也不懂,这是第一次体检,没想到与您撞见,看样子真是有缘!”不知为什么,看着学姐眼角的皱纹与她灰白色的金牙,我的内心有酸楚的感觉。
“我们已经村改了,你们村改了没有?”学姐看了一眼我挂着的吊瓶,边坐在我的床边问我。
姐姐的样子亲人的感觉,“我们村没改,原来兴大拆大建,现在的政府很仔细,不具备条件不拆,不过看看你们老家村里一排排的新房子,说拆就拆也挺可惜的。”我发着内心的感慨。
“我们村拆了好久捞不着回,为什么要先拆后建?而不可先建后拆?娘不在了,俺爹无处可去就一直跟着我,可他的心一直在农村,想他的家,念他的樱桃树!哦,对了,你从我家拿的小樱桃活了吗?”
“活了,长得高高壮壮,刚拿回家时,我爹把它栽在家的门前,翻盖新房时,你已成家了,说内心话我很失望,当时我已不想要了,刨出来放在路边,爹说扔了可惜就栽到了屋东墙外,随后邻居盖房要接山墙,爹说邻里邻居帮帮又何妨,于是我妻子把它剪枝后移栽到峄山上,经常施肥浇水,现在更加茁壮,住几天你可以到我们山上去吃樱桃的!”我看着学姐发出内心的邀请。
“可以,真好,方便时我与俺爹一起去吃樱桃,村改时,俺家的樱桃树没挪活,俺爹哭了一场又一场,记得当时在老家,每逢樱桃熟了时,俺爹总是用黄色的军帽盛着樱桃,边摘边念叨,喃喃自语只有他自己知道,摘好后用井水洗干净放在桌子上贡养一下,不知为什么,我感觉老爹越老越神道,不守着人时,他把自己保留多年的小红旗铺在桌子上,举着拳头喃喃自语,时间久了,我与哥哥看见就装作看不见,你知道吗?我经常帮着奶奶晒被,但她不是我的亲奶奶,她去世后爹才告诉我们,我们原是一个村的邻居,爹与他的儿子是干兄弟,后来他的儿子死了,爹就把奶奶接回来了,你想没想着,我们院子里的樱桃树就是从奶奶家移过来的,樱桃树耐活放在哪里都能长。”
或许是多年未见,抑或是年龄大了的缘故,学姐的话比以前多,“噢,对了,你妻子对你好吗?她不错吧?”
我苦笑了一下,“一般般吧,好在人挺孝顺的,对老人比我强,我们是同学还是同桌。”
“啊!不会是上学桌子上划界线把你手砸出青的女孩吧?”学姐的话里有好奇。
“是的,就是她,刚开始挺厉害的!”我笑着说。
“她不是个营房里的机关子女吗?”学姐不相信机关子女嫁给农民,看我点头她笑了,“看样子有钱能使鬼推磨,你当包工头发迹她看上你了,是吧?”
我听着她的话不由皱了下眉头,爱情是缘分的恰合与情感的升华。从农村走出去的人为何依旧瞧不起农村,在她的潜意识里农村只能配农民吗?社会是个大学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很明显学姐落伍了。见我不接她的话,她看了看我床头的劳模体检单,脸上有些失望。
此时我的眼前晃动着的是记忆中那靓丽的身影,还有压井的水汩汩流淌着的欢快声,麻雀唧唧叫、樱桃“叭叭”摔在黄土地上的音符。
三
峄山海拔六十多米,从北看是山,从南看是丘陵。相传这里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上学约会的地方,山东侧的石头上,曾留下他们深深的脚印,可惜随着修路建设而悄然消失。远望峄山就是个花的海洋,山前是绿油油的树叶衬着红彤彤的樱桃,放眼看去满眼是甜。
接学姐电话,她家老爹想老家了,要出来透透风。可老家已拆迁,村庄已消失,好在峄山挪不走,搬不动,屹立不倒,于是他们想到峄山来看看。
山上的路虽然窄,但铺设沥青后非常好走。走在路上,樱桃的枝头随风悠悠,伸出手随便拽一把放在嘴里,立马甜滋滋的。我站在承包地里端详着一棵棵的樱桃树,因品种不一,树叶有深有浅,而结的果子有红有黄,各有千秋,红的甜,黄的酸,各有各的味道。从学姐家移栽的小树苗,先是种在屋前,又在屋东,最终栽到了峄山上。常言说,人挪活,树挪死。虽历经搬迁,但最终樱桃树生命力顽强,它不屈不挠,已长成枝叶茂盛的碗口大树。
学姐是开车上山的,红色的轿车在绿色的山林里格外显眼,门开处是学姐灿烂的笑容,“真美,爹,快出来看看!”她边说边打开车门子,一个满脸胡须的老人慢慢从车内移出了身子。学姐从另一边拿出了一副拐杖,老人手扶拐杖站了起来,他给人的感觉依然是个高大魁梧的老人。
“大叔您好!”我走上前来,“多年没见,看见您老真好!”不知为什么,看见大叔,我立马联想到我勤劳善良的老父亲。这山上的樱桃树好多就是他亲手摘下的,可只能先人栽树,后人乘凉,触景生情,心里不免一阵悲伤。
“哪棵樱桃树是从我家挖来的?”学姐站在樱桃树下问我,红红的樱桃嫩绿绿的叶子衬着她白净的脸庞,少时压井旁摘樱桃的女孩又重现眼前。随着时光流转,记忆生香,我只能把她深深地烙在心底,所有的记忆一如这微风中的樱桃树不言不语。
我指了指山坡前的一棵樱桃树,“就是这棵,挪了好几次,越挪越壮实!”
“爹,这棵就是从咱家挖出来长大的,您尝尝,还是那么甜!”学姐边说边随手摘了几颗递给老人。
“啊,终于又见到樱桃树了!”老人接过樱桃放在手中仔细地端详着,他的眼角泛起了泪花,“是真的吗?这个就是从我们家的那棵树底下挖来的?”
随着我们点头称是,只见老人缓缓地摘下帽子,两手扶着拐杖,郑重而仔细地朝着樱桃树鞠了一个躬。他的样子是那样的认真与虔诚,好像把樱桃树当成了人的生命,连鞠三躬,随后两行热泪流了下来,“贫穷的时候,我家的樱桃树甜了好多人,村子拆迁,我本来不乐意,可我不能影响了大伙,树大了挪不活,眼不见心不想,我没办法让别人去收拾的,樱桃树几十年的生命说没有就没有了,这样好歹有延续,也有了下一代!”大叔边说边往嘴里塞了一颗樱桃,说道:“甜,还是这么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