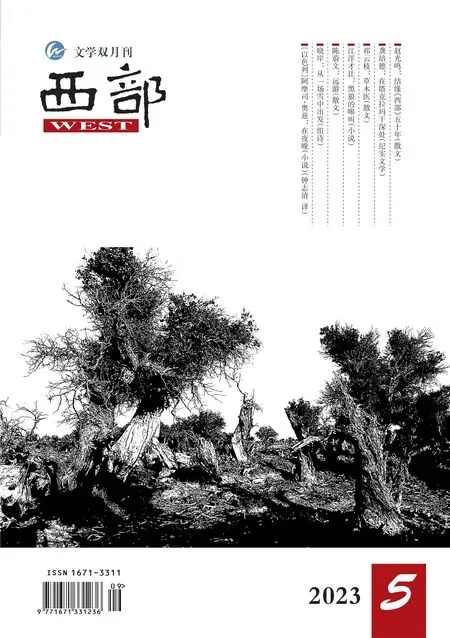无须翻译的微笑和眼神
刘亮程
我在文联八楼办公室的窗户朝北,能望见乌鲁木齐红山塔,但采光不太好,半下午时才能照进一缕夕阳。这缕夕阳我很少能享受到。我从《西部》杂志调到作协后,有了专业作家待遇,可以经常请创作假,不用上班了。有时半个月不来办公室,邮件便堆满桌子。那时作协办公室是我在乌鲁木齐唯一的收件地址。我和哈萨克族女同事哈娜提古丽一个办公室,我不在时,她每天把我的办公桌椅擦得干干净净,邮件整齐地码在办公桌上。她从来不让别人坐我的椅子。有来访的客人,都让坐在沙发上。见有人坐我的办公椅,她就会说,这是我们的著名作家刘亮程的办公桌,你不能随便坐。哈萨克族尊重诗人作家,哈娜提古丽是很好的诗歌翻译者,她对我的尊重方式是不让人随便坐我的办公椅,这是我在文联得到的从来没有过的尊重。
我们作协的维吾尔族同事热依汗古丽,每次见我都特别热情,像见了亲人一样。她是库车人,我写过散文集《库车》,和以龟兹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凿空》。可能我写她家乡的那些文字,使她对我有了不一样的亲近感。
我还认识一位维吾尔族女士,在文联哪个部门工作我不太清楚。一次她给我发微信说,她父亲以前在文联工作,父亲生前对她说,我是汉族作家中写得最好的。因为她父亲对我的欣赏,她也对我有好感,每次电梯里遇见,都会微笑着打招呼。有一年她好像生病了,身体憔悴,我远远地听她咳嗽。其实,我和她从来没有在一起好好说过话,没有吃过一次饭。只是在文联楼道或电梯里匆忙遇见,相互微笑,问候。这样的微笑和问候发生在我在文联工作的二十多年里。我经常不来,好多人我不知道名字,但她们知道我。我的一些文字翻译成维文、哈文、蒙文等,他们可能读过我的书,见面了问声刘老师好。我记住了许许多多的美好微笑,和问候。
我调到文联后,很早在伊犁文学活动中认识的阿拉提也到了文联,并当了新疆作协主席,他用维吾尔族思维写的汉语小说,活泼幽默,动感十足。他的小说语言就像维吾尔族姑娘会说话的眉毛一样,每个字每个词都在跳动,充满魅力。我和阿拉提是文友酒友,我们能把几块钱一瓶的酒,喝出大半夜的欢笑快乐。
我经常去民间文艺家协会马雄福主席的办公室,和他聊着天,眼睛盯着他负责主编完成的汉译本史诗《玛纳斯》《江格尔》,还有《新疆民间文艺集成》。我家里的这些大部头书籍,都是马主席送的。我还从蒙古族作家巴音巴图办公室借了一套最初汉文版本的《江格尔》,他见我喜欢,就说你拿去读吧,不用还了。我写长篇小说《本巴》时,在《江格尔》研究室学者尼玛那里,采访到他家族的一段故事,他的祖先是土尔扈特东归队伍中的一支,部族三千多人,在东归途中负责打头阵,几乎全牺牲了,留下几个孤儿。他就是其中一个孤儿的后代。这段故事我写到了以《江格尔》和东归为背景创作的小说《本巴》中。
调文联之前,我就认识了哈萨克族作家叶尔克西,她在《民族文汇》做编辑,我和编辑部的杨子、尹俭都很熟,他俩去沙湾找过我。我来乌市也住尹俭家。一次我去《民族文汇》编辑部,尹俭给叶尔克西介绍我是诗人刘亮程,叶尔克西笑着说:“你就是那个站在院子里举一把铁锨挖天空的人呀。”原来她读过我写的一首叫《天空》的诗。在那首诗里,我整天举一把铁锨站在院子,仰头看天上哪块云朵边可以挖地种麦子。
我1993 年辞去沙湾县乡农机站的工作,到了乌鲁木齐。先在正筹办的《乌鲁木齐晨报》打工,干了两个月,报纸没筹办成功,员工解散。我又经蒙古族学者孟驰北推荐,到《工人时报》打工,做副刊编辑。1997 年,正式调动到自治区文联《中国西部文学》(《西部》前身)编辑部。我在杂志社工作期间,得到郑兴富老师的特别关心照顾,郑老师是新疆西部诗运动的热心推动者之一,我在乡下时他从自然来稿中发现并发表了我的诗歌,还给我写了信。一次我来乌鲁木齐,他带我到家里吃火锅。郑老师是四川人,会做地道的麻辣火锅,郑夫人也热情好客。我还带我妹妹到郑老师家学做四川火锅,回去后在沙湾县开了麻辣火锅店,生意红火一时。
我在文联工作两年后,《一个人的村庄》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引起轰动的散文集的重要部分,是我在文联工作期间写的。文联宽松自由的环境给了我充足的写作时间,它成为我这样的地方文人所向往的归宿。
我在文联遇到好几位以前在乡下认识的人,其中最传奇的一位,是在1991 年我去伊犁时认识的。那时我在沙湾大泉乡农机站做农机管理员,写诗,在伊犁出版过一本薄薄的诗集《另一只眼睛》,得到《伊犁河》副主编顾丁坤和诗人杨牧的赞赏。那次我跟一个驾驶员朋友到伊犁去买俄罗斯倒过来的宠物狗。朋友带了五万块钱,全是五块的票子,一百沓子,鼓鼓囊囊装了一帆布包。到伊犁后我找到《伊犁河》编辑部的陈予,把帆布包扔到陈予宿舍的床底下,跟着陈予出去喝酒。第二天一早,陈予带我们认识了他的一位同事,说同事亲戚家有狗。我们到了伊犁河边一个大院子,几十条各种宠物狗在院子里叫。陈予的这位同事口齿伶俐,很会谈生意,一会儿功夫,就把三条狗卖给我们,收了两万多块钱。
很多年后,我在文联电梯上竟然看见这个人,我看着他,他没反应,好像不认识我。到办公室打问才知道,他是伊犁州文联的佟吉生,调到自治区文联音乐家协会当秘书长了。
有一次文联办公室主任马旭国招呼刘宾书记还有佟吉生我们一起吃饭,我给刘宾书记讲了我认识佟吉生的经过,大家都哈哈大笑。我对佟吉生开玩笑说,没想到一个伊犁的狗贩子都到文联当音协秘书长了。佟吉生立马说,你不也是买狗的吗,也到作协了。那时佟吉生的女儿后来的影星佟丽娅还在上中学吧,不知道她是否听说过父亲的这段故事。
那时候,新疆各地有才华的各民族作家艺术家,大多到了文联。文联成了各门类艺术家栖身创作的温暖怀抱。尤其那些底层的艺术家,也有机会调到文联来工作。他们在基层被土地和民间智慧滋养,在文联宽松的环境中创作,结出硕果。《伊犁河》杂志的陈予几年前也调到文联《新疆艺术(汉文)》。还有我的同乡李东海,以前在沙湾一中当老师,写诗,一天文联开大会,有人在背后拍我肩膀,一扭头,发现是李东海,他调到《西部》当编辑了。
文联是新疆各民族文艺工作者共同工作、创作、生活的一个大家庭,应该也是新疆民族成分最齐全的单位。我在这座略显拥挤的大楼里,听着不同语言的说话声,这让我对世界多了许多种认识。我会自觉地体味不同语言里文学的美妙,知道同一个地方的生活,在不同的语言文字里,呈现出那么丰富多彩的表达。在乌鲁木齐下雪的早晨,至少有五六种语言,在说这场大雪。而在阳光明媚的上午,“太阳”这个词也会出现在所有的语言里。尽管“太阳”在各种语言中发音不同,但我们对阳光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是一样的。不同的语言说着我们共同关心的事情。不同语调的汉语把大家聚拢在一起。无须翻译的微笑、眼神,无须翻译的绘画、音乐,和需要翻译的诗歌、小说,汇聚在一起。各种语言的互译间,不会丢失的诗意、美好、真诚,汇聚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