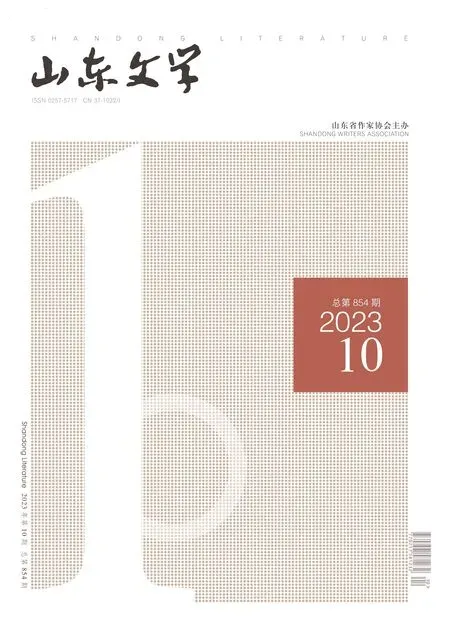恭 候
齐建水
连喜鹊都知道安仁家今日有喜事,天刚泛亮,就在房前的柿子树上叽叽喳喳地叫开了。
被喜事鼓动着,安仁和翠珍一夜都睡得很浅,一听到喜鹊叫就起了床。昨天,儿子打电话回来,说今天“西宫娘娘”要大驾光临。
这可是他们望眼欲穿的事!儿子三十三了,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不对,儿子念高中时,曾以女同学的名义带娇娇来过,还不止一次。不过那是十多年前的老黄历了。自从昨天中午接到电话,两口子便开始了家里家外大扫除。安仁和翠珍都是勤快人,平时就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他们要精益求精。
空气中有些薄雾,刚露脸的太阳被雾洇得又大又红。
安仁操起扫帚扫院子。院子是个三合院,东南门,西南圈,五间北房,三间为正房,两间辟为“耕稼馆”,东西各三间配房,天井不大。昨天,天井已经扫过几遍,只是挂满红柿子的树上夜里又落下了几片红黄的树叶。扫完了天井,又去整理厕所,整理完厕所又去整理鸡窝。家里喂了几只鸡,只为下蛋自己吃。原来是散养,怕它们到处拉便便,昨天安仁买来丝网,把它们罩了起来。只是一只红毛大公鸡侥幸逃脱了,此时正站在墙头上挺胸腆肚,对着太阳显摆自己的嗓子。
安仁回到正房,把抹布在水里投几把,开始擦桌子。桌子是栗红色的八仙桌,几样水果和洗净的茶杯放在一块。每只天青色的茶杯上,都映出清晨的光泽。抹完桌子,开始抹阁几,阁几上放着一台电子座钟,两边摆两个花瓶,花瓶里插着四季不败的塑料花,昨天刚洗过,开得正艳。右边花瓶的右边,整齐地叠放着几张报纸和几本杂志。安仁拿起一本杂志,仔细瞧着封面。封面上是一张照片,一张合影照片。几个年轻人跟一位长者站在一起,笑逐颜开。长者是儿子的领导,其他几位是儿子的同事。领导自然站C 位,儿子是领导的左膀,两人合举一块金色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农业科技一等奖。照片上所有人的肤色都黑不溜秋,跟常年遭风刮日晒的农民差不多。
安仁用右手食指摸摸照片上咧着嘴笑的儿子的脸,嗔骂一句“臭小子!”语气中带着说不出的舒爽和得意。骂完,嘴角上提,眼睛微眯,太阳穴浮起了深深的鱼尾样的褶皱。
翠珍正在收拾床铺。叠被子,扫床,把床单子弄得一点褶皱也没有。她先是笑着自语:“嘁,西宫娘娘!”接着看一眼安仁,说:“儿子也不知领回个啥样的娘娘?昨天让他发个照片过来,他说要保密,要给咱们一个惊喜。这臭小子!”她和安仁都叫儿子“臭小子”。儿子从小做事认真谨慎,说话却挺调皮,甚至有些油嘴滑舌。
安仁一龇牙,说:“要相信儿子的眼光。再说,不管啥娘娘,你都要尽心伺候,伺候好了娘娘才是好皇太后。”
翠珍一怔,撇撇嘴,笑着反问:“那我到底是皇太后还是丫鬟?”
安仁又一龇牙,说:“身兼多职嘛。要能屈能伸,该当皇太后时就当皇太后,该当丫鬟时就当丫鬟。”
“你倒会说!”翠珍一耸鼻子,剜他一眼。过了一会儿又问:“你说这娘娘会不会比娇娇更好看?更有能耐?”
“我哪知道?”安仁操起拖把拖地,弯着腰说:“你一直忘不了娇娇。”
翠珍若有所思,又说,“要不是你把他们拆散了,咱们的孙子都会满地跑了。”
安仁直起腰,眼眉一挑,不服气地说:“要不是我阻止儿子早恋,他怕连个大学也考不上,早在家种地了,那样人家娇娇会跟他?再说,他们上大学后,还好过一阵子呢,分手与我啥关系?”
“反正有关系!”翠珍不讲道理地说。越不讲道理的话越有分量,安仁不言语了,心里似乎也生出了一丝的懊悔。
娇娇是儿子的高中同班同学。儿子上高二的时候,安仁去学校开家长会,见儿子的班级排名下降了一截,就跟班主任老师进行了私下交流,回家后把儿子骂了个狗血喷头:“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呢,早恋会毁掉你的一生!”一向贫嘴的儿子第一次见他这般凶神恶煞,心里有话没敢说,从此再没带娇娇来过家里。
儿子读完四年本科,又读了三年研究生,参加工作也五年了,回家来还是形单影只。安仁和翠珍反倒不淡定了,见了儿子的面就唠叨:“老大不小了,咋还不谈个对象?”开始儿子说:“太忙了,哪有空谈恋爱?”安仁和翠珍理解儿子,儿子所在省农业科研所在海南有育种基地,他济南海南两头跑,有时在那里一呆就是半年多。可再忙也不能不恋爱不结婚啊!絮叨得多了,儿子的回答跟当年安仁的话如出一辙:“我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工作,早恋会毁掉我的事业!”
在儿子上高中时,安仁反对儿子和娇娇谈恋爱,可儿子考上大学后,又盼着儿子和娇娇谈恋爱。尤其这两年,娇娇开了娇娇农产品线上商城,当上了娇娇农产品电商公司的总经理,开办了“娇娇”品牌直播间,事业越做越大,靠直播就能把本地的农产品卖出去,甚至卖到了国外。疫情期间,物流不畅,安仁合作社生产的香米就是她利用电商平台给推销出去的。对儿子和娇娇的分手,他从内心感到惋惜
“儿子领回的娘娘能比得上娇娇就好了。”安仁在心里说。
翠珍提着同样的一颗心到厨房准备早饭去了。
安仁拖完了地,又朝屋里环视一圈,忽然发现墙上镜框的玻璃上有一个不起眼的污点,走过去摘下来,用抹布一擦,擦不掉,就放在嘴上哈热气,再擦,就擦掉了。镜框里是一家三口二十多年前的合影,照片里的安仁很年轻,三十多岁,黑发茂盛,三七分头,发沟齐整。翠珍也很年轻,刚烫过的时兴的蓬蓬头,把脸衬得又白又圆。儿子坐在两人中间,七八岁,虎头虎脑,顽皮地手打眼罩,出着猴相。一家三口都笑得很甜,每人的腮上都陷下挺深的酒窝。
安仁记得这张照片是在向阳照相馆拍的,后面的青山绿水是人工画布。那时,家里还没有照相机,更没有现在可随手拍照的手机。那时,生活虽然不是太富裕,却也衣食无忧,日子过得很舒坦。关键是没有压力,不用买房,不用买车,不用担心失业,不用担心明天发不出工资。何况安仁还是在让人羡慕的粮食直属库工作。直属库分管县城居民的粮食供应——关键是平价、按计划供应,不仅工作轻松,还能买八毛钱一斤的花生油,能把粗粮转个圈调换成细粮,换粮票时可换全国通用粮票而不是山东省地方粮票。翠珍的工作也不差,县副食品公司的营业员,也有购买紧俏商品的近水楼台。纵向比较生活越来越好,横向比较也有优越感,自然心情没法不甜。
思绪还沉浸在过去的美好时光中,翠珍喊他吃饭了。
今天的早饭很简单,花卷、鸡蛋、两碟小菜、几片火腿,还有一锅大米粥。粥是用自产的香米煮的,浓浓的香味飘得满屋子都是。安仁端着粥碗,忽然想起了儿子小时候跟自己的一次争论。那天吃早饭,儿子在粥里挑出一个小虫子,就想把粥倒掉,他制止说:“要珍惜粮食呢,粒粒皆辛苦。有个小虫子没啥,虫子是蛋白质呢,比粮食有营养。”儿子想了想,向左歪着头问:“那人为什么要吃粮食而不是吃虫子?”他信口说:“虫子太少了,不够吃。”儿子向右歪着头问:“那多养呀。你当防化员,可是专门消灭虫子的,你的工作不是做反了吗?”他不想让儿子看低自己的工作,就解释说:“我们消灭虫子,是为了保护粮食。民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人要活着就要吃粮食……”儿子打断他:“不吃粮食可以吃虫子啊,你不是说虫子更有营养吗?”他说:“这……虫子太少了,不够吃。”儿子说:“多养呀,你们防化员改成养虫员不就行了?”问题轱轱辘辘转了一个圈,又回来了……
安仁越想越觉得有趣,脸上的笑意又荡开了。
翠珍看看他,打趣地问:“吃欢喜丸子啦,怎么光笑?”
安仁说:“你还记得儿子小时候问人为什么要吃粮食而不吃虫子吗?”
翠珍说:“咋不记得?那次你让儿子问住了。”
“这臭小子从小就爱打破砂锅问(璺)到底,”安仁想起了什么,嘱咐说,“中午做菜,菜择洗得可要干净点,别有虫子。”
“伺候娘娘还敢粗心?”翠珍俏皮地说,“不过,有虫子才证明是无公害呢。现在不怕有虫子,就怕农药超标。等儿子回来了,告诉他多研究些不施农药的菜种子。”
安仁赞同地点点头。深思片刻,又感慨地说:“看来儿子当初上农大真上对了。”
翠珍看他一眼,说:“转过筋来了?当初儿子一接到通知书,你像别人剁了你的尾巴似的,急得那个样!后来整天耷拉个眼皮,好几年对儿子都没有个欢喜模样!”
安仁脸一下红了,辩白说:“我那不是担心儿子的前程嘛!”
那年儿子高考成绩出来后,不是特争气,却也不是太差,重点本科还是有把握。为了能跟娇娇在一起,两人填报了几乎同样的志愿,结果娇娇被省外的一所商学院录取了,而儿子被调剂到了本省的一所农业大学的农学专业。学农学还不是学着种庄稼?到头来不还是个种地的泥腿子?这给心气颇高的安仁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有不少人也持同样的看法,对安仁说:“你咋给儿子选个这样的专业?没尝够种地的辛苦?”
安仁郁闷得无话可说。尽管自己曾经离开过土地近二十年,可何尝没尝够种地的辛苦?
安仁的父亲,父亲的父亲,祖宗的祖宗都是清一色农民,他在高中毕业之前,也一直帮父母种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好在自己赶上了好形势,高考改变了命运。当时,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农民吃不饱肚子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三提五统”等摊派项目繁多,累死累活种一年地,剩不下仨核桃俩枣,能“农转非”逃离农村、摆脱土地仍是农村孩子的共同目标。不过那时高校的胃口很小,只能吃下很少的考生。他是幸运的,挤进了那个胃,考取了省内的一处粮食中专学校,学习仓储工程。毕业后,被分配到粮食直属库作防化员,舒舒服服过了好多年迎风招展的日子。可风水轮流转,二〇〇〇年前后,随着一次次粮食体制改革,国家储备粮都集中到大粮库去了,基层粮食部门生存状况急转直下,企业纷纷破产倒闭,他也成了一名下岗职工。由于学的是粮食化验,除了粮库,社会上不需要这种技能,另找几份工作也没干长久,无奈之下,只好跟先他两年下岗的翠珍一起“非转农”,回到老家种地。由原来风刮不着、雨淋不着的正式工转变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让他更深切地体会到了种田的苦。头顶烈日,膀子被晒得脱了皮;抢收抢种,累得直不起腰……这些且不说,单说老天爷一发脾气,一夜之间就可让你颗粒无收,任你哭天嚎地都没有用。
正因为知道种地的辛苦,安仁才发誓要让儿子脱离农业,从农村彻底拔根儿。他劝儿子复读,明年再考,可儿子坚持上农大。其实,儿子对读农学也不情愿,可他知道父母都下岗了,家里日子不好过,多上一年学就多给家里增添一年的负担。他说,大学有规定,到大二可以转专业,我去了一定好好学,到时转个理想的专业就行了。
老子拧不过儿子,只好妥协。别人家有孩子考上了大学,都要大摆升学宴,庆贺一番,可安仁宁可亏了份子钱,也坚持不办。一个农民变成另一个农民,有什么值得庆贺的?
这样郁闷的心情,一直伴随他近十年。儿子大二并没有转专业,因为他喜欢上农学了。他没想到农学对国计民生这么重要,而我国的农业科技水平竟落后先进国家那么多!没想到要种好庄稼还有这么多道道!没想到这种子的世界里竟是这么精彩!他沉浸其中不能自拔,把全部热情都投入到图书馆、实验室,对娇娇的感情松懈了,冷淡了,最后爱情之弦就崩断了。本科毕业后,他又报考了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受聘到省农业科研所,研究制种。他下地的时间比农民还要多,很少回家,发回的照片也多是劳动场景——催芽、播种、育苗、插秧、整穗、去雄、装袋、授粉、收割……
每次回家,翠珍都看着儿子心疼地说:“晒得更黑了。”
可儿子笑嘻嘻地说:“您儿子从小就不是‘肤浅’之人啊!”
安仁除了心疼,就是后悔自己当年没有痛下狠心逼儿子复读,让儿子换一条另外的人生之路。
直到前年春节,他的这种心态才得到了改变。儿子回家过年,捎回了几本杂志和几张报纸,并欣喜地告诉他,他们攻克了水稻“优质不高产,高产不优质”的育种难题,培育出了省水、省工、抗倒伏、抗病虫害的优质香稻,获得了农业科技一等奖。杂志和报纸以《把青春画卷描绘在丰收大地上》为题,详细介绍了他们科研团队不怕失败、刻苦攻关的事迹,还把这一良种的培育成功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联系起来。安仁曾长期在粮食部门工作,自然懂得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意义,脑子渐渐转过弯来。
安仁想着心事,饭吃得慢,翠珍催促他:“快点吃呀,吃完了要洗刷,还要准备中午的饭菜呢。”
“这才几点?还早着呢!”安仁嘴上这么说,却也加快了咀嚼的频率。这时,手机突然响起来。放下碗筷接听,是远房表哥,要托儿子买些优质稻种。他痛快地答应道:“行,儿子今天正好回来,我跟他说,没问题!”
前年春天,儿子带回些稻种让安仁在自家地里试种,所产香米口感好,价格高出市场价三倍多。去年,村里成立了香米种植合作社,进行了大面积推广,又获成功。消息传开,很多人慕名而来,通过他跟儿子联系,买种子,问技术,找货源,求合作。儿子就是父母的脸,每当有人相求,他都像美过一次容,感到很是荣光。安仁开始还担心儿子怕麻烦,没想到儿子有求必应,说优质种子种得越广、打粮食越多他越高兴呢。
太阳升高了,薄雾退去,天变得又高又蓝。
翠珍开始择洗青菜,一样样摆在案板上。
安仁系好围裙,正要切肉杀鱼,忽然听到院子里有人喊他,出来一看,是一位街坊叔,手里拿着一个前些年切地瓜干用的擦床子和一个拔棉花柴用的铁夹子,说要送给他。安仁非常高兴,连声道谢,接过来去放到“耕稼馆”。
“耕稼馆”是按儿子的建议办起一个家庭农具收藏馆。屋里的东西满满当当,四周贴墙摆满了杈、耙、锄、镰、锨、镢、耧、犁、粮囤、碌碡、牛鞭、簸箕、筛子、胶轮、扫帚、条筐等各种旧农具,中间还盘着一盘石碾。安仁和翠珍“非转农”后,为了种地,购置了一些必须的农具,后来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很多农具下岗退役了,本想扔掉,可儿子说,这是你们一段人生经历的见证呢,留着吧,以后我们有了后代,也好利用它教育孩子,了解农耕历史,珍惜粮食。安仁就把它留下来,整齐地摆在屋里。街坊们知道了,也把家里一些用不着的旧农具送过来,“耕稼馆”成了藏品丰富的家庭农具博物馆。没事的时候,安仁爱去摆弄这些老物件,看着它,眼前就浮现出春种秋收,浮现出饮食烟火。
送走街坊叔,安仁回到厨房切肉杀鱼。
翠珍说:“这两间房原本是为儿子结婚准备的,摆了那些东西,娶了媳妇住哪里?”
安仁说:“儿子要住西屋,说简单装修一下就行。”
翠珍又说:“西屋面积那么小,媳妇能愿意?”
安仁说:“我也这么问过他,你猜臭小子怎么说?他说西宫娘娘通常是最得皇上恩宠的,让她住这西宫她应该感到荣幸才是。”
“臭小子!正宫娘娘还没有,还想立西宫娘娘!”翠珍“噗嗤”笑了,接着又向往地说,“两个人定下来就催他们尽快结婚,现在三胎政策放开了,还有奖励呢!要是两年生一个,三胎还需要六七年,女人过了四十就是大龄孕妇,生孩子会有危险的。再说,趁咱们身体还好,能帮他们带带孩子,年纪一大就带不动了。”
安仁赞赏地点点头,说:“你想得还挺长远呢!”
这时,大门口忽然传来汽车喇叭声,翠珍惊喜地喊道:“来了,来了!”
安仁急忙停下手里的活儿,洗洗手,解下围裙,跟翠珍一起来到大门口迎接。
只见儿子拉开车门,躬腰摆臂,冲着车里的姑娘嬉皮笑脸地说:“西宫娘娘,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