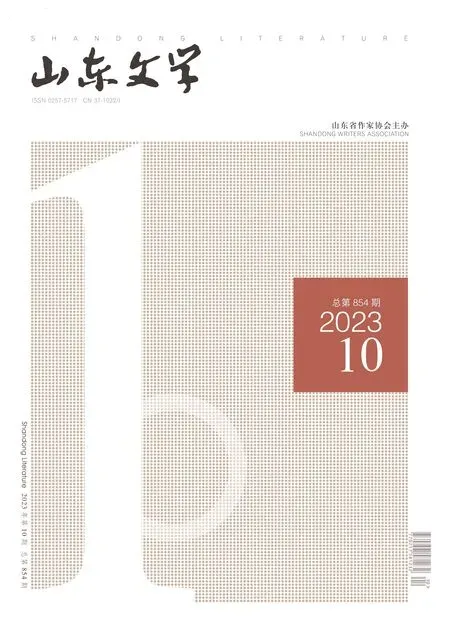屯土山与华容道
吴 苹
小街的早晨是从把子肉的香味里开始的。那香味先是丝丝缕缕、时断时续的,渐渐地越聚越多,层层叠叠地在小街的上空飘来荡去。到了后来,小街的每一个角落都被香味填满,以至于行人刚一走进来,浓郁的肉香味便迫不及待地往人身上扑。
“自从下邳降了汉,蒙丞相待我情义厚,上马赠金下马把银献,又赠我美女锦袍绣团圞,似这等恩情诚非浅,怎奈这财色二字不挂我心间……”九点来钟,“黄家把子肉”老店的大门打开,戏曲声也被肉香味送了出来。隔壁开水果店的杨翠云听到动静,一边吸着气说“香”,一边往屋里探了探头:“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卢天元说:“‘曹营十二年’里的一段,唱的是关公的故事。”“噢——”杨翠云走到卢天元近前,向四下望了望后才小声说,“卢叔,你知道吗?素香那个男的死了。”“有这事?”见小南摇着轮椅从旁边胡同拐了出来,杨翠云又将后面的话咽了回去。卢天元准备去推小南的轮椅,没想到杨翠云抢在了前头,她堆出一脸笑低头看着小南,说:“小南,好孩子,养伤期间还帮你爷爷打理生意,这么懂事的孩子现在到哪儿找去?”卢天元感觉杨翠云今天有点异样,一开口就抛出那么一句话,紧接着又出现这般殷勤的动作,后面不定跟着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呢。卢天元说:“一会儿我去打泉水,要不要给你家捎一桶?”“还真得捎一桶呢,那就辛苦你了,卢叔。我回去拿桶啊。”
那个男的死了。如果没记错的话素香今年应该五十岁了,那个男的比素香大十几岁,快七十了,这个年龄的人去那边报到也是常有的。不过,和七十四岁的卢天元比起来他还是年轻的。钱这个玩意儿,几乎能操纵这世间的一切,到底还是操纵不了寿命。杨翠云一大早说这个事是什么意思呢?杨翠云的娘家和素香的娘家离得不远,又是她将素香介绍给卢峰的,当初素香搞出那一桩子事,杨翠云之前肯定知道一些,她却一句话也没给这边透露过。为此,这些年卢天元对杨翠云也是颇有微词。
“怎么会有花儿?”小南从地上的竹篮里拿起一枝红玫瑰。卢天元说:“在早市上买的。”“早市上怎么还有这个?”“早市上除了大活人没得卖,啥没有啊?”今天,卢天元照例是五点半去的老东门早市,才转了半圈儿,两个竹篮就满了。正准备往回走,一转身瞟见了玫瑰花,摆在地上的一个蓝花包袱上,玫瑰叶子青翠欲滴,花儿娇艳馥郁,还挂着一身露水,一看就是刚采下来的。卢天元问过价格后感觉不贵,当即掏钱买了两束。玫瑰新增为济南的市花后,街头巷尾倒是常见它的踪影。卢天元将花枝修剪了一下,找了几个干净的玻璃瓶,把花分开,插好,而后在每个桌子上放了一瓶。此时,厨房里的几个大坛子正小口小口地吐着白汽,大厅里玫瑰绽放,给家常的烟火味中增添了几丝清雅。
卢天元走到灶前,打开锅盖查看米饭和肉的火候。大米是用泉水蒸的,粒粒晶莹剔透,闪着白玉一般的光泽。肉是八点钟炖上的,选的最新鲜的五花肉。先将肉焯水后备用,再将葱姜铺在炖肉的坛子底部,而后放上焯水后的五花肉,加酱油、水、花椒、八角等,大火烧开后转文火慢炖即可。卢天元每天只炖八十斤肉,绝不多做,通常这些肉到下午五六点钟就卖光了。倒是常有朋友劝他,说餐饮业的高峰期在晚上八九点钟,干这一行的人都唯恐不够卖,哪家不是准备了足够的食材,像他这种做法简直是跟钱过不去。卢天元就笑说,不够卖没关系,多做了剩下就不好了。朋友说,可以放冰箱啊,放一晚上明天再卖。卢天元仍是笑着摇头。人家见他油盐不进的样子,也就不再多说了。
人生在世,总得守点什么。卢天元父亲生前常说这句话。卢天元的爷爷是习武之人,当年比武时用兵器伤到了人,为此郁郁而终。因了这个,卢天元的父亲专门定了规矩:比武时不带兵器,不伤人。
卢天元推着电动三轮车出了院子,准备去杨翠云店里拿水桶。离着大老远,杨翠云就跟他打上了招呼:“卢叔,快,快,里面坐。”卢天元说:“你刚才想说啥?”“就是素香嘛,自那个男的死后,她的日子不大好过啊。”卢天元说:“不是有钱吗,咋还不好过呢?”杨翠云说:“卢叔你是不知道啊,这些年那个男人可没少挥霍。他一死,人家儿媳妇立马将一切大权攥进了自己手里,这还不算,儿媳妇还整天对素香摔摔打打的,素香跟人家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天天都得看那两口子的冷脸,躲都躲不过去。”卢天元说:“这种日子可是她自己选的,当初也是奔着享福去的。”“她走这一步可是天大的错误,唉,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得瞎折腾。人家的孩子跟她隔心隔肺的,哪能跟她亲昵?当初我就知道是这个结局,果然没走了我的眼。”杨翠云又说,“素香现在可怜着呢,受儿媳妇的气不说,还天天想小南,一说起来就掉眼泪。她话里话外都透出要回来的意思,又怕你们不肯接受他。”卢天元说:“现在想回来了,当初干吗呢?跟那个男人走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孩子?”杨翠云说:“说到底,素香也是小南的亲妈,到底母子连心呢。”“这个我可做不了主。”卢天元一甩手走出了杨家店门。
打水的泉眼在长盛南区的护城河边,距卢天元住的长盛北区很近,紧走几步穿过东关大街就是了。卢天元过马路时只顾低头蹬车,直到一辆汽车在他身边骤然刹车才猛地惊醒。司机摇下玻璃说:“哎,我说大叔,你骑那么快前面有金子吗?”他连连道歉,那人又小声嘀咕了一句:“也不看点道,这么大年纪的人了,还那么急火火地往前冲。”素香当初走的时候想没想过有这一天呢?之前的日子多好啊!儿子卢峰开公交,小南上学,老婆子还活着,开肉店挣的钱可着他们一家三口花。自她跟了那个男人之后,卢峰郁结在心不久便得了重病,家里的钱都花空了也没能救活他。老太婆思念儿子,常常流眼泪,没两年也跟着去了。这些年来,卢天元对素香的怨恨并没有消减多少,只是不像之前的老太婆一提起来就咬牙切齿的。
去年小南出了一次车祸,导致了大腿骨折。养伤期间,小南便以写稿来充实自己。为了激发小南的灵感,卢天元在空闲时常给他讲点旧事。此时,小南正在电脑前码字,兴许是思路受阻,眉头拧成了疙瘩。卢天元说:“写累了就休息一会儿,两三点钟时人最容易疲惫。”小南张开双臂,打了个哈欠,“等一会儿你还得给我讲讲,又卡住了。”小南从墙角处取了双拐,左腿下了地,试探着将右腿缓缓落在地上。卢天元忙跑过去扶他。小南说:“不用,我自己来。”小南拄着拐一步一挪地出了门,才走了五六步,额头上就见了汗。卢天元拿毛巾给他擦了擦,笑着说:“今天已经很好了,医生不是说了嘛,每天进行康复训练,过上几个月就能健步如飞了。”
回到房间后,卢天元把小南扶到轮椅上坐好,又递给他一杯热水。小南喝水时,卢天元就静静地看着他。那是一张具有卢家人典型特征的脸:宽宽的额头,挺直的鼻梁,下颌骨到下巴的线条如斧凿刀削般清晰、明朗。随着吞咽的动作,脖颈上的喉结快速蠕动着。怎么一眨眼这孩子就长大了呢?他妈走的时候他才八岁,晚上睡觉时还经常哭,卢天元和老伴就得轮流抱着他,轻拍他的背。待他响起均匀的呼吸声时,卢天元才敢将酸麻的手臂从他脖颈下抽出。
“爷爷,您今天怎么啦?”
卢天元忙将自己的思绪拉回来:“你还喝水吗?我再给你倒一杯。”他转身走进厨房,晃了晃那几个暖瓶,有两只已经空了。他将桶里的泉水灌进不锈钢烧水壶里,拧开天然气灶,蓝色的火焰舔着烧水壶,他却听见沸腾声从自己内心深处传来。
那应该是素香走后的事情。某次,他在小南的书包里发现了一双新鞋子。他问小南从哪儿来的,小南不说话。他担心小南学坏,声音里就有了火气:“不会是偷来的吧?”小南高喊:“不是!”“那是从哪儿来的?”小南还是沉默不语。老太婆似乎猜出了什么:“是那个女人给你的吧?”小南看了老太婆一眼,低下了头。老太婆抓起鞋子一把扔了出去:“孩子,你怎么能要她的东西呢?你别忘了,是她不要你的!是她气死你爸的!”小南抹起了眼泪。“你干啥呀?别吓着孩子。”尽管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是认同老太婆的说法的。
“爷爷,水开了。”卢天元猛地惊醒,烧水壶嘟嘟地吹着口哨,水溢到了灶台上一大片。“爷爷,您说要给我讲讲老辈人的事情,您看,您又忘了。”“好的好的。”卢天元搬了把椅子,坐到小南的跟前,“早些年间,老家那一带尚武。年轻小伙子们到了一处,便相互打听哪里有武艺超群的人,好去拜师学艺。那时候没有自行车,徒弟们去师父家学艺全靠步行——”
卢家庄的卢振邦就是教武术的师父。周围的人都知道卢家人会“金钟罩铁布衫”,卢振邦从小得家人真传,加上刻苦勤奋,十几岁上就将一把大刀舞得水泼不进。每次传授武艺时,卢振邦总会在干净的庭院里放置一张桌子,桌上铺着红布,将大刀端放于桌子正中后,才正式开始一招一式。
后来,卢振邦的名气越来越大,周围的孩子纷纷前来拜师学艺,行武之人也常来找他比试切磋。卢振邦给自己和徒弟们立下两条规矩:一是比试时不用兵器,二是只切磋不伤人。多年来卢振邦严守规矩,从无例外,败在卢振邦手下的人无不心服口服。
仿佛一夜间,日本鬼子如蝗虫般扑了过来。桃园镇的街头冒出一窝一窝的鬼子兵,仿佛雨后粪堆上一簇簇的狗尿苔。桃园镇家家关门闭户,街巷上除了蹿来蹿去的风声,就是鬼子们叽里咕噜的怪叫和咔嚓咔嚓的马靴声。
这日午后,卢振邦正在房里歇息,无意中一抬头看到左边墙上的大字——守,与之相对的右墙上是另一个字——放,字是专门找人写的,字体为行楷,写得龙飞凤舞、力透纸背,仿佛从墙上长出来的两株墨梅。午后的阳光从窗户里挤进来,给两个大字镀上了一层金。一个苍蝇不知什么时候钻进房内,在头顶嗡嗡地盘旋着。卢振邦用蒲扇赶了一阵子,终将苍蝇赶到了门外。桌上的瓶子里插着一支鸡毛掸子,卢振邦拿起它在两个字上细细拂了一遍。平日里倒是隔三岔五地拂一拂,灰尘自是没有的,这么做已成了一种习惯。
他正盯着字出神时,徒弟大壮跑了进来:“师父,听人说后村的老李在集上挨鬼子的打啦。”卢振邦忙问:“怎么回事?”大壮抹着头上的汗说:“老李在集上卖西瓜,几个鬼子上来就抢,老李上前阻止,鬼子们围起来一阵拳打脚踢,听说肋骨给打断了两根。为首的那个小队长叫龟田一郎,会些拳脚,数他最猖獗。”卢振邦说:“去把你师弟他们几个叫过来,商量一下怎么对付那帮畜生。”
大壮刚走出门,见大道上尘土飞扬,一群鬼子驾着三轮摩托车正朝这边驶来。车辆在卢家门口停下,为首的是个满脸横肉的家伙,指着卢振邦说:“你,卢振邦?”卢振邦说:“是我。”那人指着自己说:“我,龟田一郎。” 龟田身边的一个瘦子说:“卢振邦,太君要和你比武,识相点,麻溜地走啦。”卢振邦拿眼角扫了瘦子一眼,迈步向前走。大壮跑回院捧出了卢振邦的大刀,卢振邦摆摆手说:“不用。”
到了村中的旧戏台前,卢振邦站住脚:“就在这儿吧。”大壮捧着大刀立在他身边,村里的乡亲们看到此情景,立即噤了声。龟田一上台就挥着日本军刀嗷嗷直叫:“大日本武道必胜!”卢振邦纵身一跃上了戏台:“哼,没有灵魂的东西就像没有根的野草,岂能长久得了?”
话音未落,两人便打在一处。龟田出手阴狠险恶招招致命,卢振邦闪转腾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台下一片寂静,乡亲们全都屏住了呼吸,生怕错过一招一式。卢振邦虚晃一招,闪身到了龟田身后,抬腿就给了他一脚。这一脚有些力度,随着一声哎哟,再看时,龟田已经脸朝下趴在了台上。
卢振邦的脚踩在龟田背上时,台下一片哗然。卢振邦双目圆睁,腮帮子一鼓一鼓的。
周围的鬼子见此情景,端着枪围了过来。
卢振邦吁了一口气,收了回脚。龟田爬起来后,回头看了卢振邦两眼,才领着鬼子兵,钻进车子,撂下一股黑烟跑了。
大壮气得一甩手:“没想到师父这么胆小怕事,眼看着自己人受欺负还不能报仇,练武有个屁用?”周围也是一片沉默。
卢振邦怀抱着大刀,一脸平静,始终一言不发。
晚饭后,龟田正欲脱衣,灯却呼的一下灭了。一个黑衣蒙面人自窗外飞身而入,接着,一道白光带着强劲的凉风直逼龟田的咽喉。
龟田顿觉不妙,随手操起身后的椅子迎战。只听咔嚓一声,椅子被劈为两半。龟田大惊,退到桌边摸起一把茶壶向黑衣人掷去。黑衣人一偏头,茶壶摔碎在地。龟田趁机抓起桌上的军刀,黑衣人的大刀劈来,龟田举刀相迎,两刀相撞,火星四溅。当啷——龟田的军刀脱了手。
龟田脱口而出:“是你?”黑衣人也不答话,抬手将大刀横在了龟田的脖子上。龟田说:“为什么?”黑衣人说:“不杀你有不杀你的原因,杀你更有杀你的道理!”
黑衣人手起刀落,龟田的脑袋如西瓜般滚落在地。等到鬼子们闻声赶来,黑衣人早就蹿房越脊,没了踪影。
晚上的大明湖灯火通明、流光溢彩。卢天元推着小南顺着小东湖往北走,走到“竹港清风”前停了下来。每天的七八点钟,都有人在竹林旁边的亭子下唱歌,此时,一个老太太正唱阎维文的歌曲《母亲》。以往,小南都等演唱结束了再往回走,今天,没等一首曲子听完,小南就说:“回去吧。”卢天元推着小南往回走,一路上他都在沉默不语。卢天元知道他的心思,尽量把话题往别的地方引,他也只是嗯、嗯地应付着。
到家后,卢天元在床边坐下来,一时间不知道将目光落向何处。桌上有一盆绿萝,参差不齐的藤蔓越过花盆的边沿,杂乱无章地生长着,像在对他张牙舞爪。他的目光从花盆移到了墙壁上,那是一幅镶在相框中的十字绣,背景是一片森林,森林前伸出两条小路,一条伸向左边,一条伸向右边。一只山羊正站在小路的交叉口。山羊背对着他,他看不到它的表情。莫名其妙的,他的心里起了一个疙瘩。那疙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越长越大,大得让他呼吸不畅。终于忍不住,走到墙壁跟前,伸手去摘那幅十字绣。十字绣挂得有些高,摘了几次没有摘下来。他转身环视了一下,床上有只床刷,他抓起来就去捅,床刷碰到十字绣的边框,啪嗒一声相框掉了下来,一地玻璃碎得七零八落。
“爷爷,牙膏用完了。”“噢,我去买。”他一边扫着碎玻璃,一边答应着。忙乱中手被玻璃扎了一下,也顾不得找创可贴,放在嘴里吮了吮就算止血了。
卢天元走到水果店门口时,杨翠云还在店里整理水果。看到卢天元进门,杨翠云立时将笑容堆满了整张脸。那笑来得有些急,有些突兀,笑时不仅露出了牙齿,连牙床都慷慨地露了出来。“哎呀,是卢叔来了呀,快进来坐。”杨翠云抓起旁边箱子里的小红果,硬往卢天元手里塞,“卢叔你尝尝,这新来的小红果,又酸又甜,可口得很。”卢天元推辞不过,只得接在手里。卢天元说:“你说她想回来,是真的吗?”“那还能假?上次她说起这事时哭得稀里哗啦的。不信,我让你们爷俩通个话。”杨翠云拨通了电话,对那边说,“素香,卢叔在我店里呢,你快把你想说的话跟他说说啊。”卢天元将手里的小红果重又放回箱子里,接过杨翠云递来的手机,听到那头先是一阵沉默,过了片刻,有人带着哭腔叫了他一声“爸”,接下来是啜泣声,哭声越来越大,还夹杂着吸鼻子的声音,似乎一时半会停不下来的样子。卢天元只得将手机还给了杨翠云,杨翠云接过手机,小心地说:“卢叔,我知道素香有对不起卢家的地方,伤过您老的心,您别的不看,看在过世的大壮伯的面子,您原谅素香这一次,毕竟大壮伯和素香妈曾经是夫妻。”听到大壮的名字时卢天元沉默了片刻,叹了一口气,走了出去。
卢天元到了自己家后,将手里的东西递给了小南。小南疑惑地说:“怎么是这个?爷爷,我让你买的是牙膏啊。”“这不是……噢,香皂。”卢天元抓了抓头,“看这脑子。”“爷爷,你今天怎么啦,一直魂不守舍的?”“老了嘛。”
卢天元只得再次出门为小南买牙膏。回来后,一头钻到自己房间,关好门,将老太婆的遗像从柜子里翻了出来。照片上的老太婆不算太老,眼角还没有下垂。卢天元抚摸着她的照片说:“你倒好啊,一撒手什么都不管了,把这个摊子扔给了我,你说我该怎么办啊?”素香离开卢家后,卢家人才知道素香在结婚前就和那个男人有瓜葛,当时素香的爹妈嫌那个人有家庭,为了拆散他俩,四处找人给素香介绍对象,这才跟卢峰认识了。过了八九年,那个男人和老婆离婚后,他两人就又到一起了。“素香妈要是活着,我得狠狠骂她一顿,可让她娘俩把我们家给坑苦了。”老太婆又开始了埋怨,“当初杨翠云将她介绍给卢峰时,自知道了她妈是谁后我就不同意。就她妈那种作风,大壮哥死了不到一年,就和村里几个有老婆的男人搞到了一起,在咱村里待不下去了,又改嫁到了外地。看看,看看,什么根什么梢,什么葫芦什么瓢,到底还是随她妈啊。”“当初同意卢峰娶素香,也是为了大壮哥。”“她妈改嫁多年后生的素香,跟大壮哥有半毛钱的关系吗?可怜的大壮哥,一直念着自己死去的原配媳妇,四十多岁时才娶了素香妈,本想生几个自己的亲骨肉,不想,一场暴病撒了手,一个孩儿也没留下。”
“爷爷,您过来一下啊。”小南说话时,眼睛却没有离开电脑屏幕。“今天您给我讲的,我都写了下来,马上快完工了,一会儿我给您读读啊。”“好。”卢天元思忖了一下,说,“小南,我跟你说……说个事情。”“什么事?”小南的手仍在键盘上忙活。“小南,你妈……”小南敲击键盘的手停了下来,卢天元斟酌着措辞,“你妈现在过得不是太好……那个男人死了……”话从嘴里吐出来后,他感觉心里稍稍轻松了些。小南听后,没有抬头,也没有说话,放在键盘上的双手轻轻抖了几下,这个动作尽管很细微,却没有逃过卢天元的眼睛。过了片刻,小南才说:“爷爷,您还是接着讲吧。”
年轻的女人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头朝南躺在堂屋正中的门板上,脸上盖上了黄纸。女人的肚子原来鼓起了一个小山丘,现在被践踏成了平地。女人死了,肚里的孩子也死了,死在黎明之前。院子里,年轻的男人正在挣扎,他的身体被四五个弟兄按着,嘴里的骂声却没有停止:“日本鬼子,我要把你们剁成肉泥!”旁边一个老男人拿着毛巾要堵他的嘴,年轻人挣扎时又将自己的鼻子给碰破了。老男人一屁股坐在地上,咧着嘴大哭起来:“大壮,我的儿啊,你非要去送命,爹也不活啦。”
卢振邦走过去拍着大壮的肩说:“大壮,好孩子,师父知道你心里痛,师父心里更难受,这仇一定得报!鬼子一定得杀!但不是现在。你没了媳妇孩子心里难过,你不想想,你爹要是再没了儿子,他可怎么活?”旁边的二牛来了一句:“师父,怕什么,弟兄们拿着大刀冲进鬼子窝,拼他个你死我活。”卢振邦瞪了二牛一眼:“你要不怕鬼子血洗镇子,就去蛮干!”大壮停止了挣扎,用拳头砸着地面,砸得手上渗出血来。
卢振邦怕大壮爹撑不住,又担心大壮找鬼子拼命,一直没敢走。
点灯时分,卢振邦正在劝大壮父子吃东西,二牛扛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从外面走了进来。屋里的人正诧异着,二牛将麻袋扔在了地上,说:“逮了个鬼子娘们儿,找个僻静的地方浇上油点天灯。”二牛打开麻袋,一个日本女人从麻袋里滚了出来。女人很年轻,二十岁左右,穿着和服,盘着发髻,脸上薄施脂粉。卢振邦试了试她的鼻息,担心她醒来,点了她一个穴位。有人问:“二牛哥,怎么逮住的?”二牛说:“天黑之后,我摸到鬼子据点附近,准备收拾几个鬼子出出心中的恶气。我刚在那棵歪脖大槐树上藏好,就看到一辆人力车停了下来,这个鬼子娘们儿正从车上下来,我看着四下没人,一拳就把她揍晕了。大伙说怎么处置她吧?”大壮将手中的大刀扬起,拿手指拭着雪亮的刀刃:“我要一刀一刀地将她活剐了。”大壮爹喊了一声:“慢着,听卢师父的。”
一个年轻人凑过来说:“师父,我看不如趁天黑将这娘们儿拉到刘三刀的土匪窝子,把她往那儿一扔,那帮土匪见了她,准像饿了三天的狼见到肉一样。让小鬼子也尝尝他们的女人被祸害的滋味。”卢振邦低声喝道,“还不闭嘴!鬼子是畜生你也是畜生?”
“把她放了。”
卢振邦一句话,在场的人全都惊得张大了嘴巴。二牛高声说:“为什么?”卢振邦说:“冤有头,债有主。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屋里一片寂静。
卢振邦再次试了试那女人的鼻息,伸手拽了块黑布蒙住了她的眼睛,而后将她塞进了麻袋。
卢振邦这次没有让徒弟去,亲自扛着麻袋出了门。到了二牛说的那棵歪脖大槐树下,他打开麻袋,将昏迷中的女人放在了地上。
没几日,县城里的老鬼子庆生,桃园镇的大小鬼子几乎倾巢出动。一直喝到半夜,那帮鬼子才抚着肚皮上了返程的大卡车。一路上,鬼子在车里高声吆喝着,大笑着,肆意地打着酒嗝。等到鬼子发现前方路上的障碍物时,汽车已不受控制地撞了上去。
车里的鬼子一阵吱哇乱叫。此时,不知道从哪儿射来的一支支飞镖,鬼子们惨叫着倒下一大片。接着,路边的深沟里跃起一帮黑衣人,个个手持大刀,向着晕头转向的鬼子狠狠砍去。片刻工夫,鬼子们全都没了动静。黑衣人将鬼子的尸体抛进沟里,清理完路上的石头,将地上的枪支挎上肩,手提大刀风一样地消失在夜幕中。
已经九点半了,卢天元却一点睡意也没有,他只好打开手机,调出收藏的几段戏曲:《屯土山》《赠袍赐马》《灞桥挑袍》《单刀会》《华容道》等,他点开《华容道》刚听了几句,小南摇着轮椅走到门口:“爷爷,该休息了你怎么又听上戏了?”他说:“《屯土山》《赠袍赐马》和《华容道》是我最喜欢听的几出戏,关公这一生就活在这几出戏里了。”小南笑说:“从我记事起,你就爱听这几出戏,整天翻来覆去地听,也听不够吗?”“咋会听够呢?”卢天元站起身,说,“我的毛笔和大纸应该还有吧,今天突然想写字了。”“您咋想起一出是一出呢?”“小时候,你太爷爷教给我那些师兄弟武术时,我偏不爱学,我喜欢读书写字。后来,我带着全家来济南讨生活,再后来咱们家就开了这个店,那时候,每晚都要练上一会儿大字。近些年,家里接二连三地出事,将写字的兴致给挫败得寥寥无几了。”大纸在橱子里,毛笔在笔筒里。笔筒是紫檀木的,是他五十岁生日时素香和卢峰送给他的礼物。素香那个孩子说起来也不是奸滑之人,到底是被那个男人给骗了,把自己的孩子丢下给他养孩子,这么些年了,也不知道把该抓的东西抓在手,如今落了这么个下场。也许她早就想回来了,只怕身不由己。
提起蘸了墨的笔后手竟有些抖,他站稳身子,深呼吸,气沉丹田,尽量将气息调得平缓,笔尖落在纸上时还是有了疏离感,他不敢停止,只得一鼓作气写下去,在写最后那个“点”时,手一哆嗦,“点”就变成了墨团。他将纸揭起想重写一张,不料带倒了桌上的墨,墨汁在白纸上纵横恣肆,桌上顿时一片狼藉。
爷孙二人一阵手忙脚乱之后,他看着垃圾桶里的那堆被污染的白纸,颓然地坐到了椅子上:“老了,老了哇!”
半夜里醒来,他撩起窗帘一角,见外面月光皎洁,当即从床上爬起。到了院子里,他将石桌打扫干净,摆好笔墨纸砚,提笔,深呼吸,落笔,这次倒是一气呵成,“守”和“放”两个大字跃然纸上,字体苍劲有力、浑然天成。他左看右看,顿觉爱不释手。不料,一只老鹰突然从半空中俯冲下来,叼起其中的一幅字转头便向墙外飞去,他一边喊叫一边紧追不舍。他追着老鹰到了一处园子,园子里锣鼓铿锵,唱腔激越,一帮人正在园子里唱戏,唱的是《华容道》。园子是用木头做的栅栏门,门挺高,他既推不开又爬不上去,园子里的人正唱到关键处,也没人顾得理他。待一出戏终了,那个扮关公的人提着大刀走了过来,他说了缘由,扮关公的人却不让他进,他好一阵软磨硬泡,扮关公的人终于让他进了。他从园子前面找到园子后面,那只老鹰正坐在一棵树上,对他是一脸的不屑一顾,树下是他的那幅字,早已被撕得稀碎。他抓起地上的一根木棍向老鹰打去,却被扮关公的人拦住了,那人安慰了他几句,他只得放下手中的木棍,叹了口气,转身向园子外面走去……
他睁开眼睛,见车窗外艳阳高照,他靠近车窗的半边身体经阳光抚慰后,有些松软,有些舒泰,是这份舒泰延缓了他从梦中撤退的速度。此时,他坐的长途车已开进了服务区,司机正在提醒乘客下车做短暂的休息,这么说已走了一半的路程。恰好,手机响起,他赶忙接通电话:“店里的钥匙放在我卧室的抽屉里,账本等都在前台的下面。以后这个店就交给你们娘儿俩了,记住,每天只做八十斤肉,千万不要多做,这是咱们店里多年来的规矩,得守住!你不用担心我,我很好,放心吧,我是不想操店里的心了,就想回老家过清静日子……”他又叮嘱了几句,才挂掉了电话。他下了长途车,活动了一下手脚,又打通另一个电话:“哈哈,老伙计,我马上要到家了,以后咱老哥儿俩就能天天泡在一起唠嗑喽!家里的老房子怎么样了?噢,这么多年没回去住,房子还没坏,多亏你经常修理。还是老房子好,冬暖夏凉……好哩好哩,见面再唠啊。”
挂了电话,他情不自禁地舒展了一下腰身,做了几个深呼吸。正是四月,阳光温存,春风和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