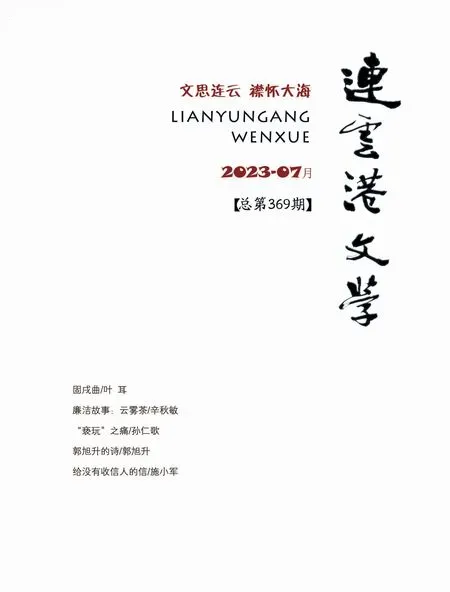黑子 白子
林伟宝
或许是生活好了的缘故,养宠物的多了起来。养貂的,养鼠的,养刺猬的,养蛇的……五花八门,稀奇古怪。养宠物究竟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至今没有琢磨透,倒是听过路边修鞋大爷的议论:吃饱了撑的。清朝的遗习,提个鸟笼子到处晃悠,怀揣罐子斗蟋蟀,据说那是八旗子弟爱干的事,现在极少见到了。修鞋大爷痛心地说:玩物丧志呵。对“玩物丧志”这类古训现在的人们并不以为意。为啥?古训丢得太多了,何在乎这一条呢。
遍观宠物界发现,虽然种类不同,但时下仍属狗猫居多。
时代在变,动物的地位也在变。譬如说牛。过去牛是主要的生产工具,生命受法律保护,随便杀牛违法。我小时候有个同学的父亲是生产队饲养员,因为工作失误导致社房起火烧死了耕牛,被判坐了两年牢。现在的牛没有了耕田、耙地、拉车的活,免了劳役之苦,轻松倒是轻松了,福也享了,可是却只剩下贡献肉和乳的份儿,寿命也比过去缩短了许多。可见盲目轻言“享福”不一定是件好事。
狗的功能是看家护院,协助人类做点儿安全方面的工作。无论过去或者现在,狗在这方面做得都算可以,它们知道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哪,如何定位、把握自己。尽管受宠,但是宠而不骄,头脑清醒,没有忘记自己的本分。虽然现在处处安装监控摄像,但狗们丝毫不敢懈怠,看家护院工作一直没有停。其他的如牧羊,搜救,破案等等也多有涉足,几乎随处可见它们的身影。据说一些专家呕心沥血,耗费大量的时间研究,并动用了大数据分析,最后煞有介事并确凿无疑地得出,年轻女士饲养大型宠物犬是有着安全方面的考虑的。
猫就不一样了。狗不嫌家贫,猫却嫌贫爱富,这一点一直为人们所诟病,所鄙视。鲁迅的厌恶猫有两点,其一,捕获雀鼠,往往玩弄后再吃,“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其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我小时候对猫的印象并不坏。猫的本职工作是捕鼠。如果撇开“嫌贫爱富”不谈,单就完成本职工作这一块,猫做得真不错。俗话说“能猫管三庄”。那时猫捕鼠,对鼠不对人,不管哪家的鼠它都逮,铁面无私,正气凛然,仅此一点,就足够让人们对它产生三分敬意。那时候我经常见到一只狸猫,搞不清谁家的,因为在哪一家都会见到它的身影,体型健硕高大,走起路来威风八面。有邻居曾经见到它夜里跟偷鸡的黄鼠狼打得难解难分。我亲眼见过它将整只的野兔拖到了床底下。看到它拖兔子时高昂的头颅,旁若无人,信心满满的架势,可以想见它在野地里和兔子搏斗时该是如何的威武、凶猛。现在的猫不行了。时代变了。时代的流行色不同了。说它的口碑一塌糊涂肯定有人不高兴,因为毕竟有那么一些人在宠着、爱着。他们爱它们的媚态,偏偏猫又深谙其道,懂得花心思琢磨人而不是捕鼠,琢磨如何投其所好,如何把献媚的技能发挥到极致。如此一来,不管白猫黑猫,本职工作的荒废肯定是无疑的。见到一个视频,猫鼠共处一处,鼠趾高气扬,如入无人之境,而猫却表现得战战兢兢,畏畏缩缩,见到老鼠绕道走。猫和鼠的位置完全颠倒了。看到这样的视频,令人啼笑皆非,唏嘘不已,不由得联想起社会上随处可见的类似面孔,联想起网上一些吃软饭不务正业的无良之人。
我养过狗,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事情。母亲病了,到处求医不见效果,村里好心人说了,换个法子,养条狗驱驱邪吧。外祖父托了好多人,觅得一条小黑狗,通体无一根杂毛,黑得发亮,我们把它叫作“黑子”。黑子来了,全家视为宝贝。可是,懵懂的黑子对肩负的责任并无意识,我们也没有发现它有什么祖传的驱邪避灾的特殊技能。当然,我们不会因为母亲的离去而责怪黑子。我们知道,正儿八经的心脏病连医生都无能为力何况黑子呢?怪只能怪我们愚昧,贫穷,条件差。可是黑子自己倒觉得感情上受不了,母亲走的那几天,它不吃不喝,一直趴在窝里不动。
黑子不需要人宠,我们也无意去宠,只是彼此给予对方必要的尊重。弟弟每天放学回家,黑子要跑出大半里路迎接。扭动的腰肢如呼啦圈演员的表演,带动尾巴疯狂地左右摇摆。它将两只前爪抬起搭在弟弟的腿上,鼻子在裤子上使劲地嗅,亦如久别的恋人。现在宠物的待遇黑子一天都没有享受过,它只知道恪尽职守与主人共同度过艰难的岁月。它的窝在草垛下面,每天晚上当它意识到我们已收拾就绪准备结束一天疲劳的时候,便自觉地回到自己窝里。无论天寒地冻还是刮风下雨,它都会在窝里默默地坚守。夜里发现周围有什么动静便发出“汪汪”的报警声。它的报警是有选择性的,如果觉得并无大碍,只“汪汪”几声了事。如果觉得兹事体大,则一直叫下去,直到把主人唤醒,起身查看,这时它便悄无声息地从窝里走出,伸出舌头舔一舔主人的手,以示交接。
那时候生活条件差,但是只要有我们吃就有黑子吃的。我们没得吃了,黑子自然饿着肚皮。不过它绝不在我们面前转悠,增添我们的尴尬。它会独自跑到桑树下面捡桑籽,去草地里逮蚂蚱,去大地里刨地瓜。夜里,它会悄悄地寻到猪食槽旁,捡拾槽里的残渣。
细究黑子的死因,我们是有责任的。如果我们有足够的食物,黑子不会跑到苹果树下面去刨东西吃。如果刨到的东西不是被农药毒死的鸡,黑子也不会丢了性命。可是,难道因为这个我们去责备埋鸡的人吗?显然不能。埋鸡的人哪能轻易舍得毒死自己的鸡呢,鸡肯定是误食了浸泡农药的种子。如果种子不泡农药呢?……哪有那么多如果。总之是黑子的命不好。黑子死了,轮到我们全家人吃不下饭。整整一个星期,我们全家才从失去黑子的哀伤中走出来。
以后三十几年我再没有养狗,直到“白子”的出现。
二〇〇〇年,我搬到新的居所。作为迁新居的礼物,我的邻居也是同学兼好友的张君给我送来一只狗。他家有两条宠物狗,纯白,花重金买来的。什么品种,他曾经当面告诉过我而我却没花心思去记,只当它是条狗就完了。两条狗像是双胞胎,一样白色,长毛,短腿,滚圆的腰身,笑眯眯的面孔。一条叫“奔奔”,一条叫“宝宝”。他将宝宝给了我。我心想怎么能叫“宝宝”呢,“宝宝”这个称呼是留给我儿子和孙子的,不行,我就叫它“白子”吧。
促使我下决心留下白子是因为它的表现。那天张君抱来,对着它说了一声,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结果白子果真不走了,将它抱回去,它又立刻自动地跑回来。我心里在说,或许这就是缘。
以后我的生活里便多了一项内容。三五天给它洗一次澡,用吹风机给它吹干。每次在食堂,在饭店,用完餐后要打包一些它爱吃的剩菜带回来。自己整天忙得要死,还要为一条狗操劳。我有时候在心里笑自己,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有烦恼也有乐趣。晚饭后和妻子散步,狗绳牵着白子,短腿在地上高频率地移动,带动全身颤颤的,毛茸茸的如一团雪白的球在脚边滚动。蛮讨喜的。
最恼人的是为白子打理毛发。白子一年换一次毛。换毛那段时间家里到处散落着狗毛。白子身上的旧毛结成了块,我和妻子耐心地用剪刀剔除旧的毛块,再一点一点用梳子将毛梳通理顺,嘴巴、眼睛周围的毛要剪短,修齐,以免影响进食和视物,接着是洗净、吹干,整个工程要花费足足两个晚上,直忙得腰酸背痛。有时候跟妻子开玩笑,这才叫“吃饱撑的,没事找事。”如果有个女儿恐怕也未必能有如此耐心。
白子的小窝设在院子里,虽然玉体高贵,也只能委屈了。好在它很聪明,也很自律,没有我的允许,它绝不会踏入房间半步。每天晚上它会自觉地在自己的小窝里蹲守,密切注意周围的动静,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早上我没有起身,它便老老实实地坐在我的房间门口等候。
人说,狗活一岁相当于人活八年。白子活了十五六年,应该是一百多岁的老人了。最后的那段时间里,白子吃东西很困难,眼里布满了眼屎,视力明显减退,走路颤颤巍巍,经常撞墙,完全不见了当年既俊且俏的倩影,如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看着真叫人心疼。黑子的死,给我的是遽然而至的撞击般的打击,白子的老去给我的是钝刀割肉般的绵延的疼痛。一天,白子不见了。我担忧它眼睛看不见出了意外,到处寻找,后来看到它在小区一家空调的室外机下方躺着,全身被空调的冷凝水浇得透透,我赶紧将它抱回家,洗净,吹干。
白子死了。我选择我家南边玉带河北堤一棵标志性的大树下作为它的墓地,那个地方很好找,我坐在家中楼上的书房里,抬眼就可以看到。可惜那棵大树后来被挖了,那片土地被整成了沿河绿化带。也好,让白子化为一片绿色,守护这座城市。
那天给它下葬的时候,我把它使用过的我从国外带回的一套合金餐具全部给它陪了葬。完事以后,我在大树下足足坐了两个小时。我在心里发誓,以后再不养狗了,感情上受不了。
把人当狗看待是社会的悲哀,而有些人确实不如狗,同样是社会的悲哀。
爱狗爱动物是好事,值得提倡。可是养宠物的人们必须明白,凡事有个度,动物毕竟是动物,千万别把动物与人的位置搞颠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