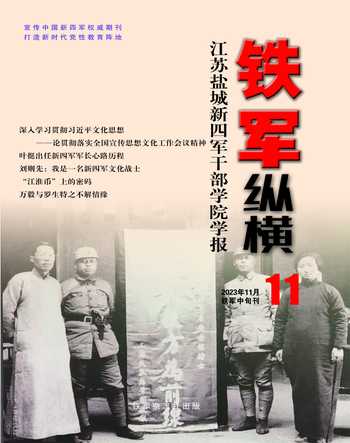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心路历程
刘顺发
研究新四军,首先要了解广州起义后出走境外10年之久的叶挺,何以出任新四军军长的?
含冤出走未忘党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作为起义的前敌总指挥,受到中共党内和共产国际不切实际的责难和不公正的处分,心中十分郁闷。1928年夏末,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申诉无果,竞直接出走德国,脱离了党组织,过起了无边的流亡生活。生活中的无靠,政治上的无依,曾使他痛苦沉闷;但是,他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他的报国之心一直是热的。他又开始不倦地读书学习,他选购的一部德文版百科全书就有几十本之多。他还在德国、法国等欧洲几个国家进行考察。他钻研哲学、历史、军事、文学,而他专攻的依然是军事,他潜心研究军事学、军事工程学和军事化学。他甚至在自己的住处做过爆破试验,他期待有朝一日回国后重上战场。
特别是1930年4月底,周恩来从莫斯科取道欧洲回国途中,在柏林与他的一次交谈,兄弟情的诚挚,战友间的规劝,使他久不忘怀。周恩来告诫他:“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干革命成功不必在我”,既语重心长,又富于哲理,使他从愧疚中振奋。叶挺从周恩来的谈话中,从传到柏林来的讯息中,了解到毛泽东等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知道了创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经过。他对比周恩来,对比朱德、贺龙、周逸群、聂荣臻、叶剑英和陈毅等人同参加起义,都曾经历过起义的失败,却都不以个人得失为重,不注重个人委屈,而以革命为第一生命,自觉汗颜。这时,国内政治局面的变动,也给叶挺很大触动。他一生痛斥的蒋介石,竞不断地“围剿”红军,招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还杀害了他的好友、抗日反蒋的邓演达,接着叉在“一二八事变”中向日军妥协。强烈的思念祖国之情,报效祖国之心,促使叶挺决定立即回国。
1932年秋,叶挺怀抗日救国之志,离开德国,举家迁回澳门。澳门是叶挺的“避难所”,南昌起义与广州起义后,他都曾回到澳门隐蔽。这次回澳门,他要从这里走向抗日救国的战场。可是,面对山河破碎的祖国,内忧外患的政局,自己又是一个脱离共产党多年的人。到国民党,虽有老朋友盛情相邀,他不愿去;到共产党,又不能去。抗日报国之路怎么走?成了一个大难题。他经常到香港,往来于港澳之间,他在联络,他在寻求。1933年11月前后,他曾以客座参谋的身份,同李济深等人从香港到福州,参与了福建事变的谋划运筹,希望通过这次事变,公开表示抗日反蒋的立场,对停止内战、团结御侮有所推动,但对事变的成败,没有寄予多大期望。他仍在困惑中寻觅抗日报国之门。他给阳翰笙写过信,在找党,他在等待着党组织的理解和谅解。
“家里来人”访叶挺
“家里来人了,约你在弥敦饭店见面。”1936年5月中旬的一天,当以行医为业的柯麟同志把这个消息通知叶挺时,着实让叶挺喜出望外了。因为“来人”是中共中央的一位要人——潘汉年同志。
潘汉年怎么会到香港来?叶挺心中有些纳闷。然而,这毕竟是接触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一次好机会,万万不能错过。
叶挺太需要这样的机会了。
潘汉年的约见,不啻给叶挺干涸的心灵滋润了雨露甘泉。叶挺麻利地换了一件长袖白衬衫,脚穿一双黑色短帮皮鞋,迅速整理好军容风纪,出了大门,直奔约会地点九龙弥敦饭店。
葉、潘两位在北伐时期已经相识。叶挺对出身在苏南宜兴县书香门弟的江南秀才,早有所闻。1927年初,只有2l岁的潘汉年,已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革命军日报》的总编辑。时任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副师长的叶挺,与潘多有接触。
潘汉年见到叶挺时,立即起身相迎。他一向对年长自己10岁的北伐名将敬慕有加。
“希夷兄,我们都很想念你。恩来同志嘱咐,途经香港,一定要找到叶挺。”潘汉年没等叶挺开口,就先表达了老战友们的思念。
“健行(潘的化名)老弟,不,健行同志,你们能来看我,太高兴了。”叶挺有些兴奋。
柯麟同志要堂倌随即上茶水、点心,一阵寒暄之后,谈话便转入正题。
潘汉年向叶挺介绍了许多情况,有些是叶挺已知道的,比如从国民党方面、其他方面的报纸上已经得知国民党军队多次“围剿”红军,红军被迫长征;更多的是叶挺不知道的。此时,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内都在考虑抗日救亡大局。
“我和廖陈云在长征途中接受中共中央洛甫同志指派,于去年8月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情况。这次同胡愈之回国复命,特地取道香港。”潘汉年向叶挺简单介绍了行程。他早已从周恩来那里得知叶挺的经历,所以也把叶挺当作党内同志一样看待。
“这么说,你一定会告诉我们很多新情况,是吗?”叶挺急切地问,同时感受到党的信任,心头一阵温暖。
“我到港已经几天了,看望了一些老朋友。去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向全世界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不久,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奋斗,争取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几天,我联络了一些同志和朋友,请各位都要宣传团结抗日。”
“看来,我们有工作做了。”叶挺高兴得打断了潘汉年的话。
“是的,希望诸位多做工作。中国共产党将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再次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我党将有重大的战略转变,将由推翻国民党统治转为联合国民党抗日,将改反蒋抗日为联蒋抗日。”这些重要内容,扣动着叶挺的心弦。
“可是,老蒋至今还在叫嚷‘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主张,不知能否改弦更张哟。”叶挺的担心,不无道理,中山舰事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反动本质给叶挺的印象太深刻了,
“我这次来港,也是专程请教叶挺将军的。想借着叶挺将军在国民政府军中的影响力,促进联合抗日的目标早日实现。”北伐名将的声望,在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中可谓首屈一指,叶挺自己并不看中这些,他崇尚做实事。
“叶将军在两广地区的影响更大些,当然,包括其他地方的反蒋实力派人物,请您多多疏通,促使他们适应我党这一战略性转变。”听到这里,叶挺完全明白了党组织的期待。
夫唱妻随心贴心
潘汉年这次的约见,对叶挺太重要了,它甚至改变了叶挺生活的进程。
这天晚上,叶挺情绪激动,同夫人李秀文谈了很久很久。他说:“我现在好了,和家里(中国共产党)有了联系,不是孤家寡人了。”
李秀文太理解丈夫了。流落海外的几年间,是叶挺最郁闷的岁月。离开了共产党的组织,就像个没娘的孩子;离开了革命军队,犹如失去了生命的价值。他渴望党组织让他对广州起义的成败有个说明功过是非的机会,渴望党组织真正了解自己。李秀文多次听他对友人说过,国民党是没有希望了,将来都要走共产党的路。友人也问过叶挺:为什么不找共产党?叶挺说:“我已经离开几年了,要找也需要重办手续。”他的内心始终向往着共产党,却又夹杂着为难,这是李秀文非常清楚的。因为,他们当时还弄不清楚,中共中央对叶挺的脱党问题,到底怎么看待。
今晚叶挺的情绪,使妻子十分高兴。多年来,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她一直担心着,担心着叶挺精神上的压力。叶挺的愉快,就是她的愉快。
“秀文,潘汉年主动来找我,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战略转变也告诉了我,还要我继续为党工作,这说明了什么?知道吗?”
“知道,当然知道,这不就是你多年的期盼吗!”
“这说明了党中央对我的理解和谅解。”叶挺顿了顿,接着说,“虽然现在我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我还是应该按党的要求去做。”
“他们相信你,我更相信你。”李秀文为叶挺喜悦和求战的心态而高兴。
“秀文,我想到内地走走,到上海,到南京,会一会那边(指国民政府军中)的朋友。”叶挺像是自言自语,也像是对爱妻说。
“好呀,你定心地去,家里有我,你放心好了。”
“不,我要你陪着我,这样更方便。”叶挺是个非常细心的人,他要以此避开国民党特务的怀疑、盯梢。
这年夏天,叶挺心中装着潘汉年同志转达的使命,出发了。他带着妻子、孩子一同游历了上海、苏州、杭州等地。
此时,为了护卫南京,预防日军再次从上海进攻,国民政府军4个师兵力,正在南京以东的苏州、江阴、常熟、嘉兴等地修筑防御工程。叶挺逐个看望了执行这一任务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与之推心置腹,倾心交谈。叶挺坦言,蒋介石竭力“围剿”红军,走的是亡国之路;中国军人,要以抗日救国为天职,诸位同窗、袍泽,要与一切坚持抗战的军队团结一心,抗日御侮。
这年11月,叶挺又到广西苍梧,专程拜访了好友李济深和其他一些著名反蒋人士,希望他们坚守抗日要义,达成共同逼蒋抗日之势。叶挺还向他们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逼蒋抗日,绝非易事。尽管全国抗日救国的怒潮迅速兴起,反对日本侵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响彻中华;尽管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并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尽管中共中央屡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尽管国民党内有识之士和爱国将领纷纷提出抗日主张,蒋介石却依然坚称:“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直到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出面,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才被迫同意停止“剿共”,聯合红军抗日。
恩来面见叶希夷
丙子年仲冬下旬,公历已进入1937年元月,南国澳门的气温宜人,身着长衫的叶挺与妻李秀文正在屋内说着话。
由于国内局势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全国反对内战,团结御侮呼声日高,蒋介石在强大舆论压力之下,已不再“围剿”红军,抗战已成国人期望之大势。
叶挺夫妇正在商量何时归回故里,投身抗日大潮,老人、孩子如何安顿,秀文是否同行,都成为叶挺不能不细致考虑的事情。
丁丑年春节已是公历1937年2月中旬,多年战乱和外敌人侵给民众带来的精神压力和心理阴影,使中华民族传统的旧历年也失去了往年的繁荣和喜庆。澳门人民除了让孩子们享受过年的欢乐,不致让传统节日从生活中抹去,大多也欢乐不起来了。叶挺、李秀文夫妇则是另一番忙碌。安排老人的生活,整理着简单的行装,不断地与国民党内老朋友联络。春节过后不久,叶挺在国民政府军队中的朋友、袍泽帮助之下,举家迁往上海,住在静安寺路一座庭院式的小洋房里,终于结束了10年流亡(德国5年、澳门5年)境外的生活。一位挚友还赠给叶挺一部红色的德国轿车,方便外出使用。
此时,国共两党关于合作抗日的谈判,正在西安进行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周恩来接受中共中央新的使命,同国民党关于合作抗日之事开始正式谈判,于是就留在西安。由于蒋介石在“反共”与“抗日”之间患得患失,对国共谈判,多次出尔反尔,反复无常,横生枝节,百般刁难,谈判过程异常艰难曲折,周恩来从1937年2月开始,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四地,同国民党进行了5次谈判,历时7个月。谈判的对手,先是顾祝同,后来是蒋介石本人。8月下旬,这场旷日持久的谈判,在客观形势发展推动下,终于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
叶挺寓居上海后,经常在苏州、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走动,与在国民党中任职的黄埔校友、北伐军袍泽陈诚、张发奎、黄琪翔等相见、交谈,围绕着抗战话题,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得到不少消息。他也常和共产党在上海等地的党员、领导同志交往。潘汉年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在此期间,曾多次陪同周恩来等往来于延安、西安、杭州、南京、上海之间。潘汉年与叶挺也几次得以见面。叶挺按潘汉年嘱咐,设法公开往南京,利用袍泽关系,通过友人探听国民党亲日派的行动方针。
是年8月10日,周恩来、朱德与叶剑英受蒋介石密邀,从西安飞抵南京,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国防会议,并继续谈判红军改编等问题。直至18日,终使蒋介石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8月22日正式发表)之令。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在上海期间,请潘汉年安排,专门同叶挺作了一次短暂的见面。
“恩来兄,你辛苦了。柏林一别,不觉7年了。”叶挺一见到周恩来,便有些激动,看到周恩来消瘦许多,心中颇为怜惜。
“希夷兄,知你来沪已久,很高兴,早打算来看望你和秀文的,一时难以抽身。”
“你这是哪里话,你为国共谈判共同抗日,乃国家之大事,辛苦万般,我知你多次来沪,亦未敢打扰。兄在柏林之劝诫,至今言犹在耳,只盼第二次国共合作早日实现,挺即奔赴前线,杀敌报国。”
“希夷兄,我正有要事与你商谈,我现正与蒋介石谈判陕北红军部队改编问题,这项任务实现之后,将会把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一事提上议程。我意由你出面改编并主持这支部队,组成一个军为妥,不知你意如何?”叶挺正欲回答,周即以手示意,让自己把话说完,“可否在适当时机向陈诚、张发奎等表达你愿意领导这支部队,藉此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并由陈诚出面争取蒋介石同意?”周恩来简洁明了,一口气说完自己的建议。
“恩来兄放心,此亦为希夷之所期望者,希夷必前往力争,亦不辜负共产党之期望。”叶挺因为周恩来的信任而激动,又因为有机会率部杀敌而兴奋。
“如蒋首肯,我意沿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番号,可称新编第四军,并蕴涵继承红四军深意。”周恩来对叶挺的表态十分满意。
周恩来与叶挺的这次见面和谈话,短暂而紧凑,但在中国抗战史上有重要作用。周恩来点将叶挺,激活了国共谈判中改编红军游击队,共同抗日的大局。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叶挺亲眼目睹大队日军飞机深入闸北、浦东市区狂轰滥炸,痛恨至极;见到中国空军机群奋起应战,英勇搏击,又为之高呼助威。只可惜,中国机群力量太弱,难以扼制敌机肆虐。淞沪抗战异常艰苦,中国军队将士顽强抗击,付出重大伤亡。然而,蒋介石打了10年内战,弄得国贫军弱,以至无力抵御外侮,中国军民惨遭屠杀。这些严峻的现实,使叶挺十分悲愤,痛苦难言,更加激发了重上战场、杀敌报国的强烈斗志。
叶挺请缨组四军
叶挺想到恩来同志的建议,此时正是时机,于是,他找到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表明心意。
“辞修,日寇如此狂妄暴虐,挺自倍受煎熬,肝胆欲裂,愿即率部杀敌,以身报国,请为我说项。”叶挺与陈诚同出保定军校;叶挺六期毕业、陈诚八期毕业,同在粤军第一师任过职,叶挺任步兵营长,陈诚任炮兵连长,算是老同学、老袍泽。叶挺的为人、性格,陈诚均了解。叶对陈直陈己愿,陈诚心中已自高兴,言词中不免流露同情,显得恳切。
“希夷兄,弟等多次邀兄从军辅事,均未允诺,今兄主动出山,意在抗日报国,可见兄之一片忠心。但不知兄意欲何往,可否明示?”陈诚深知,这位北伐名将是中国难得的战将,正是国民革命军急需之高级军事人才,极愿推荐。但,如非一线主官,则必可惜其才,况且叶断不会屈就,故问得仔细。
“辞修不必深虑,我之所愿,其实不难。当今国共两党正为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之事作难,我倒愿主其事,参与其改编。”
“哦?果真有此诚意?”陈诚窃喜,他也想拉拢叶挺,故追问道。
“当然!只要严格训练,必能成为一支正规化的抗日部队,挺亦免受鸠占鹊巢之嫌耶。”叶挺对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深信不移。
“主意甚好,有何打算?请详叙。”
“我意将其组建为一个军,继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称号,定名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你看可行否?”叶挺抓住机会,步步深入地贯彻周恩来的嘱托。
陈诚觉得,叶挺的建议确实很好,于是当即答应为其向蒋介石疏通。
“希夷兄之人品、才干,弟一向钦佩至极。兄为抗战报国,主动请缨,精神可嘉,更为弟敬仰,弟当速向蒋委员长鼎力保荐。”陈诚殷勤至极。
果然,蒋介石采纳了陈诚的推荐。他一面接受共产党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合编为一个军的改编方案,一面又没有征得中共中央的同意,就于9月28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出通报,宣布经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提议的原意在于,继承北伐战争“老四军”的优良传统和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蒋介石则心怀鬼胎,另有所图。他抢先任命叶挺为这个军的军长,是借以拉拢叶挺,他以为叶挺已脱离共产党多年,可为其所用,会帮助他把这支部队改造成国民党的军队。如叶不就范,便将这支部队送上前线,假日寇之手消灭之。
经过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軍”的命令。此时,其实蒋介石对于国共合作,并非真心诚意。当月下旬,叶挺接受中共中央赴延安面谈的要求,从南京出发,于11月3日到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热情欢迎与接待。此行,叶挺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军事战略,表示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率领新四军将士,坚决抗战到底。
作者系《铁军》杂志社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宋慧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