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与近(创作谈)
刘兆亮
这一年,我写了一些东西,貌似写的是人,其实我想表达的是空间。按理说,空间(环境)不是为人所设置、服务的吗?这是常识。但很多时候,你设身处地进入一种空间时,又好像不是那么回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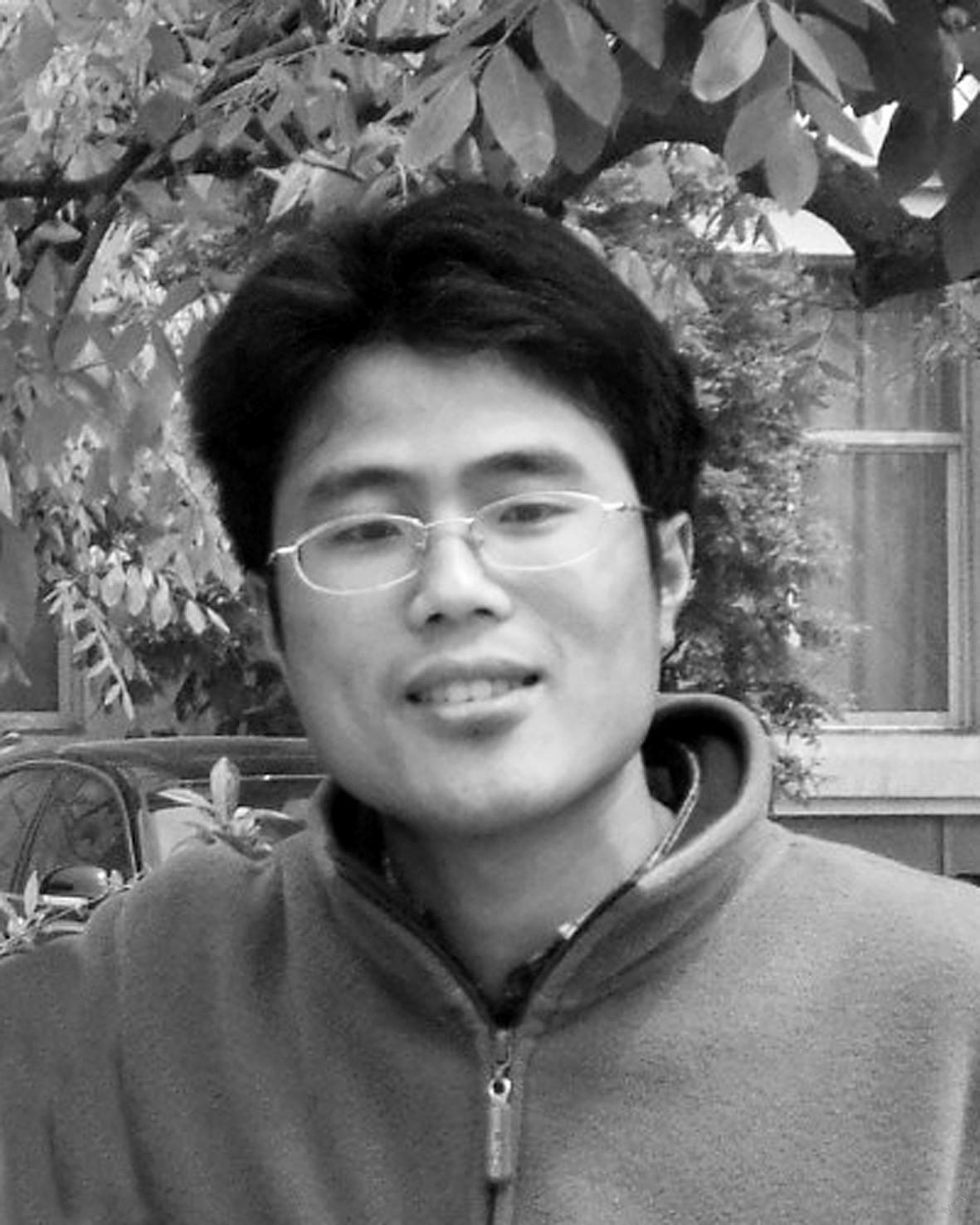
比如,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去浙江省的两处遗址公园:一个是位于湖州市安吉县的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里有古代越国的古城遗址和越国贵族墓群;另一个是位于杭州余杭区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这个古城遗址年代更久远,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地方,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尽管多次探访,但仍然能感受到空间带来的新鲜感、浩渺感。这种历史的纵深所带来的感觉,既真实又虚幻。你根本不敢相信,你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印刻着三千多年前一匹战马的蹄印,更会怀疑五千年前的良渚王城如海,水利发达。时间真的是从这些空间与实物上倾泻而逝的吗?
正是基于对空间的感受,我找出一个空间的视觉维度——远与近,来写我所熟悉的人。这些人必须无限接近真实,又能够自如地置身在“远方”与“近处”。《五梁》的主人公,我是熟悉的,直到念初中之前我都时常见到他。他是一个抱着收音机到处走的人。我早就想写他了,可怎么写,我没想好,直到我有了对空间的感觉才动起指尖。我把“五梁”放到远方去,让他在远方产生故事,再拉到近处来打量。在哪里打量呢?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五梁看似颓废不堪,是一条闲鱼,但他在任何空间内——无论是酒馆里还是孩子们游戏的场所,无论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村头的杨树上——都是充满期待的。人群中、地平线上、高高的树梢,就是一个个空间的支点。这些近处的空间跟远方的空间,形成一種关联,最后由五梁的二嫂在村头的巷口(这些弯弯曲曲的巷道空间,既打开了村庄,又压抑着村庄)堵住跟他一起闯关东的老乡,这样就能够把两个空间合体,让忧伤填满历史的、更是现实的空间中来。
同样,在《麻雀》中,水珍奶奶窗口的那个投喂麻雀的木槽,是全文最核心的空间。这个空间要尽量考究一些,所以才有那个在堵漏的盖子上描画上小小的树的细节。这是远景,是斯人已去的远景,也是虚景、虚空间。实景则是窗下栽种上的、不断被麻雀粪便“饲养”的水杉树。水杉树支撑起来的空间,是水珍奶奶的独立的养老气场,也是她对爱人无限的思念。甚至,我想表达,水珍奶奶撒小米时,那些麻雀腾空让出地方时,在空中构成的,像是甩干一块布似的空间。这些空间里,我都想灌入一种爱意,有时候还有一种思念。
再观《谈年》,最小的空间从一开始就设定好了:故乡那个房檐下,雨水滴出的小小的水洼。我很多次躲雨在房檐下,看到过房檐的雨珠滴落的场景,那小小的水洼里盛满的是小小的、跟雨水滴出的空间等量的乡愁。而这些小小的坑洼,还有打麦场上那些三三两两的村人“谈年”的场景,也是一个空间,这个空间跟此后父母在上海城中看到那些亮着灯火的高楼大厦,形成了多个空间的对比。这同样是空间视角“远”与“近”的参照,其间流动的亦是城乡之间的情感接续。你想靠近亲情与乡情,必定要远离那个空间。
我在历史的空间中感受到了力量,这个力量因为时间的累积而显示出空间的开阔。必须要有一个合适的空间,才能够盛放那么多人出场,容纳那么多情感流动,并且在这样的空间中展开一场盛宴或围炉夜话。我在远与近的空间比对之中,恰好看见了我和你。
[责任编辑 王彦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