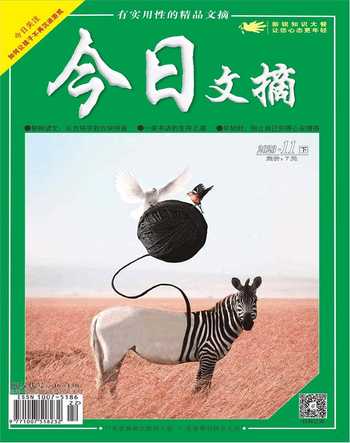做父亲是一件很难的事
[日]大江健三郎
我的两个发育正常的孩子一天天长大,他们很自然地开始支配自己的自由时间。也就是说,他们正逐渐从我和妻子身边独立出去。看着这一变化过程,有时我眼前会出现一种充满真实感的影像,仿佛在我和儿子、妻子和女儿、女儿和儿子之间有一条宽松的纽带,把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相互连接在了一起。尤其是次子已经长大成人,即将成为一名循规蹈矩的公司职员,假如我和他之间的纽带绷得太紧,他肯定无法忍受,我也会疲惫不堪。
因此,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的纽带总是松弛地垂着,然而,必要的时候,一方就会轻轻一拽,让对方靠近自己,或者自己顺着纽带走近对方。即使不依靠这条纽带的引导,也能用眼睛确认对方所在的位置。这样的连接方式就更不会产生束缚感了。而且在生活中,若是在面临犹如立于万丈悬崖般的危急关头,一方将要滑落下去,另一方就可以从容地站稳自己的脚跟,以便用力拽住对方……
我现在把这个用宽松的纽带维系起来的家庭想象得非常美好。只是长子大江光有残疾,今后也不能独立生活,我们夫妻只能和他共同生活下去。其实我们觉得这倒是件幸运的事,尽管知道这种感情出于自己的私心。可以说连接着我和光以及妻子之间的纽带虽然不总是紧绷着,但也没有松弛到垂在地上。
至少从我的角度我一直喜欢这么想。不过,我现在重新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仔细审视一下我与光之间的关系。
一次,次子为了硕士论文实验总结报告的中期发表去了秩父,要在那儿住一个晚上。过去,我们一直都是让他送光去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的,所以这天早晨,我只得放下一早就开始的工作,送光去福利院。
下了电车,走在新建的高层公寓旁的人行道上时,光的癫痫病突然发作了,根据我们平时积累的经验判断,属于中度发病。我把他扶到人行道边的长椅上躺下。等着他恢复平静的工夫,我抬头去看身边的枫树和比它更高的榉树上开始变黄的树叶。
光中度发病时比较麻烦的是,恢复平静后会大小便失禁。这回也是如此。发作过去后,我们继续朝着福利院走的时候,光就发生了这种情况。本想打出租车回家,可是光满身臭味,很不方便,所以只好继续朝着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的方向走。
光大概也是这么想的,照样走着。见他还走不稳当,我想要搀扶他,被他拒绝了。但我还想搂住他的肩膀,光轻微地、却很坚决地扭了一下后背,摆脱了我的臂膀。就这样,一直到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我也没能扶他一下。
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的早晨,夸张一点儿说,就好像战场。尤其老师们,个个精神头十足,紧张地忙碌着。我跟一位熟悉的男教师说明了光的情况,请他拿来更换的内裤,然后,我带着光去厕所。
从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出来后,我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似的,一个人乘电车回家。在电车上,我想起刚才光不让我搀扶的事,这种情况以前也常有,也许是光发病后心情不好的缘故。不过,他应该不会认为发病是父亲造成的,所以应该不是对我表示敌意。只不过因为发病后感觉不舒服,使他忘记了以往对父亲的关照。实际上,平时他走在人群中或者上台阶的时候,总是宽容地让我搀着他的胳膊或者扶住他的肩膀——我被赋予这样的特权。
这件事终于使我意识到,正是由于光平时忍耐着没有表现出来,自己就一直在伤害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独立性。当然,我对自己的这种性格并不是一直毫无反省,我想起曾经有过多次机会使我思考上面这个问题。
在一次关于残疾儿童的研讨会上,一位在国立大学教授残疾人教育理论的年轻学者批评我说:“你这样过分呵护儿子,会妨碍他的自立,尤其是你还公开表示,担心自己和妻子死后,儿子将如何生存下去,这是在教育残疾儿童上的大忌,这样的父母对于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是非常有害的。即使你们夫妻不在了,你们的儿子照样会好好生存下去的。你的小说里还有这样的情节,女儿表示自己要带着残疾哥哥出嫁。这不就等于女儿决心一辈子不结婚吗?你们夫妇的这种态度,连女儿都跟着遭受不幸啊!”
看样子,这位年轻的学者无法容忍我过分注重家庭的态度。如果有人反问我:“你说家庭相当于自己的根据地,那么没有家庭的人该怎么办呢?”我也觉得自己目前还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还收到过一个立志当作家的人的来信,他说:“文學不正是起始于对家庭的否定吗?你应该好好想想太宰治的名言:‘父母应该比子女更重要!”我常常受到这样的指责,但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离不开孩子的。
我每天都和光在同一个房间里干着各自的事情,听着同样的音乐;在兴冲冲地去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接他回来时,为了弥补这一段分开的时间,一路上还不停地和他聊天。这样日复一日,我竟不知不觉地暗自认定了光需要我,没有我他就无法正常地生活,当然这话我很难说出口。我现在才发觉,光靠着自己的意志力一直在忍耐着、包容着这样的我。
(武温书荐自《小品文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