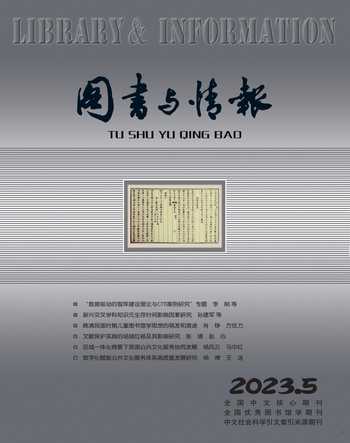从“启发民智”到“合于国情”:晚清民国时期儿童图书馆学思想的萌发和演进
肖铮 方仪力
摘 要:近代儿童图书馆学的发生是晚清教育改革和分科治学的产物,亦是民初“儿童的发现”之产物。晚清社会遭遇民族危机,广开书阁,形成了以“开启民智”为基本目标的图书馆学思想,12岁以上儿童被正式纳入到读者范畴。继而,得益于民初以来“儿童”观念的重塑,以“提供必需且易晓的知识”为宗旨的儿童图书馆学思想得以萌发。在此基础上,通过“新图书馆运动”的助力,图书馆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为世人所承认,图书馆学人逐渐形成专门的科学共同体,进一步发展了“合于国情”的儿童图书馆学的通用表达方式和共同价值。从儿童图书馆学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环境和逻辑入手,重审作为分支学科的儿童图书馆学的历史演进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是理解图书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路径。
关键词:儿童;儿童图书馆;儿童图书馆学;学科史
中图分类号:G258.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23070
From Enlightenment to Localization—— Reflections on the Evolution of Childrens Library Science in th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China
Abstract The childrens library science in modern China was the result of the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division of disciplines in the national turbulence of late Qing dynasty. It was also the product of the discovery of children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late Qing era, when Chinese society was experiencing a worsening national crisis, many state-and privately-owned libraries were constructed, and the library science movement with its primary objective of educating people's wisdom formed. Children beyond the age of 12 were recognized as readers and were allowed to enter libraries. As the concept of children was reshaped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library science thought with the main purpose of providing necessary and understandable knowledge came into being. On this basis, with the help of “New Library Movement”, library science was recognized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Chinese library scholars began to form a specialized scientific community. What mentioned above further developed children library sciences common expression of conforming to national conditions as well as shared values. Reassess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library science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has enormous significance of academic history, which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library science.
Key words children; children library; children library science; academic history
兒童图书馆学是与儿童图书的收集、组织、管理、利用、研究相关的知识与技能。作为图书馆学的分支学科,儿童图书馆学的建立和发展反映了图书馆学作为独立学科的专业化程度,可作为检视图书馆学学科体系整体发展的有效路径。但与同为舶来品的图书馆概念不同,儿童图书馆学并未遵循“翻译开道,本土建设”的发展模式。其学科的发生、发展完全是近代中国本土学术建设的成果。这是因为,居于儿童图书馆学思想本位的“儿童”不仅不是古已有之的概念,其本身还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现代性概念,伴随着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和教育焦虑而产生。在“儿童”逐渐脱离了儒家“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成为了与成人一样的独立存在后,为满足儿童知识需求的儿童图书才随之产生。可以说,儿童图书馆学是分科治学这一现代化进程的直接产物,因而必须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儿童图书馆学思想。
从历时层面观之,晚清遭遇“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变”①,“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②成为了社会整体诉求,知识界和教育界通过藏书楼建设,鼓励阅读,推动了传统官私藏书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型。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启发民智”为基本目标的图书馆学思想,12岁以上儿童被正式纳入到读者范畴。继而,得益于民初以来的大量西学引介,传统学术思想与西学融合,完成了从传统“六艺”③和“四部分科”④向分科之学的转化,“科学”概念为社会所熟知,以“提供必需且易晓的知识”为宗旨的儿童图书馆学思想得以萌发。在此基础上,通过“新图书馆运动”的助力,图书馆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为世人所承认,图书馆学人逐渐形成专门的科学共同体,如何进一步发展“合于国情”的儿童图书馆学,为儿童提供关于图书的知识成为了1930年以来儿童图书馆建设的基本宗旨。概言之,近代中国儿童图书馆的建设以及儿童图书馆学的发展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且完全服务于近代中国的民众。虽然一个学科的内部发展过程无法凭借线性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和呈现,但重新审视上述三个不同阶段,厘清晚清民初儿童图书馆学思想的演绎却能清楚地展现儿童图书馆学思想的“在地性”,呈现中国图书馆学的学科活力,因而被赋予了特殊的学术史意义。
儿童图书馆是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是学校教育的补充和延伸,有利于全面推进儿童的素质教育。近年来,儿童图书馆和儿童图书馆学逐渐成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热门领域。晚清民国是我国儿童图书馆学萌芽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研究这一时期儿童图书馆学思想的演进,是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思想史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就晚清民国的儿童图书馆学而言,现有研究多集中于:(1)对部分学者的儿童图书馆思想的研究;(2)聚焦于儿童图书馆的某个侧面,如独立建制、儿童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和阅读服务等;(3)对儿童图书馆学的发展进行事实性描述。上述研究为理清中国近代儿童图书馆学的发展脉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仍有改进空间。现有研究较少从学科史和学科体系建设的角度看待晚清民国儿童图书馆学思想的生发和演进,同时有重叙述轻阐释的倾向。本文并不局限于图书馆学本身,而是将研究视野拓展到社会发展和学术体系建构的层面,旨在从宏观上展现中国早期儿童图书馆学思想的动态演进过程。推进儿童图书馆学史相关研究,可以知古鉴今,鉴往知来,为当前儿童图书馆工作和中国图书馆儿童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启示和借鉴。儿童图书馆学作为图书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考察其早期发展历程,也是审视反思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关键路径,具有学术史和学科史的双重意义。
1 “启发民智”:晚清儿童图书馆学思想的萌发
晚清社会是中国近代儿童图书馆学思想的生发语境。在求新求变的时代氛围下,铸造新民和开启民智迫在眉睫。传统的藏书制度已无法满足社会对于“新知”的渴望,官私藏书制度逐渐开始向近代图书馆过渡。在这一过程中,部分满足年龄要求的儿童被纳入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此外,清廷的教育改良运动推动了蒙学革新,蒙学开始进入西学译介活动的视野之中,蒙学教育的内容和知识结构得以更新和扩大。
1.1 开通民智:从藏书楼向图书馆过渡
近代儿童图书馆学思想源自古代藏书制度的变革及其向近代图书馆的过渡。官私藏书制度的变革缘于传统社会开启民智的整体诉求。三代以后,朝代虽更迭变换,但传统文脉并未断裂,以“经学”为主的传统学术思想一直延续到了清朝。然而,随着晚清科举制度的废止,西学以“混混之势”[1]进入中国,以经学为中心建立的思想体系已无法满足社会的知识创新,“古胜于今”或“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很快被国人所扬弃。明末以来通过翻译引介的新书籍,业已传播了农、商、工、法、医等各领域新思想和新学说,并逐渐激发出“开眼看世界”的愿望,国人对天下的认识也因新书的传播发生了质的改变。如王国维所总结的,“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2]以严复译《天演论》为例,该书所提出的“天演”①思想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不仅奏折和报刊上频繁出现“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等经由“天演”衍生的概念,民智也因《天演论》的翻译为之一开,世人逐渐认识到开民智、新民德和鼓民力三位一体的“力本位”思想,甚或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人也能借用“生存”“竞争”“淘汰”等新名词谈论日常生活。西学思想经由翻译引入中国后,传播速度之快,需求之大,由此可见一斑。依靠书籍所发挥的社会效应由此引发了社会的持续关注。对当时的士人而言,西方的“富强”主要源自其发达的“格致之学”②,引介“格致之学”,广置图书,扩大国民见闻不啻为开启民智的有效方法。因此,戊戌前后,大量士人主张清廷效仿泰西,开启书藏,建立书阁。士人的呼吁推进了藏书楼建设。李瑞棻在光绪二十二年所呈《请推广学校折》明确了改革藏书制度与民智开启之间的紧密关系。即若赋予人人入藏书楼读书的权利,则成学者众:“妥定章程,许人入楼观书,由地方择好学解事之人,经理其事,如此则向之无书可读者,皆得以自勉于学,无为弃材矣。”[3]广开民智在成为全社会认同的救国之路后,各地增设了大量藏书楼,“载宣统二年(1910年)各省一律开办图书馆。”[4]“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流览而广天下风气。”[5]
值得注意的是,戊戌前后,藏书楼虽转向了近代图书馆以“公开”为宗旨的服务体系,尝试推行“人人皆可入阁”的思想。然而,囿于彼时的社会条件,以“开启民智”为圭臬的图书搜集范围局限在后来所谓的“专业书籍”上,搜录的新学各书以算学、化学、汽机等各译书局所译应用技术和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书籍居多。尤其是在 1902 年中外商约版权论争之后,“各国书籍中国译印种种为难”,而“现在中国振兴教育,研究学问,势必广译东西书,方足以开通民智”[6],江南制造局等译书局所出译书是各省图书馆搜集图书的主要渠道。“仅识字之人”和童蒙因而不属于“入楼读书”之人。在年龄上,各省图书馆章程中大多将入馆年龄定为12岁,这与传统蒙学的年龄限制基本对应[7-8]。显而易见,戊戌前后,儿童图书馆学思想并未萌发,开设图书馆在寻求富强,启发民智之外,只是辅助教育。在黑龙江图书馆和归化图书馆创设奏折中都能见到保存国粹,辅助教育[9-10]等表述。儿童图书馆学相关思想也只有在社会重新考量其读者群体范围后才有生发的可能性。
1.2 学制改革:蒙学图书范畴的更新与重构
年龄和学识程度尚未引发若干图书馆倡导者的关注,但与广增书楼同时发生的学制改革却切实促发了儿童图书馆学思想的萌芽。知识界虽已提出“民智未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11],但就社会现实而言,戊戌以来译印和搜集专业书籍未能尽开“小民”之智。在反思民智开启的有效途径时,清廷将关注点放置到了传统教育改良上,由此也引发了社会全面根除沉疴宿疾的教育改良运动。受此影响,新译西书逐渐将蒙学书籍纳入了理想的翻译对象。嚴复在主持京师大学堂后拟定了新的翻译原则:“官局所译西书,宜从最浅最实之普通学入手,以为各处小学蒙学之用。其书期使中年士子汉文精通者,一览瞭然,以与旧学相副为教”[12]。以“小民”为目标的仅“西人各种工艺之书”,且需“译成浅语,使其能知其法,通其用。”[12]显而易见,至少在京师大学堂这一晚清极其重要的翻译平台内部,“小学蒙学”的需求已经成为西学引介的目标,蒙学书籍也属于需引介的西学新知范畴。考虑到传统蒙学和西学之间的差异,蒙学改良显然扩大了传统蒙学的受众。先秦以来,传统蒙学业已形成完整的体系,是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课本、书籍或图册,主要包括日常生活等杂细事宜和儒家伦理规训。朱熹在《童蒙须知》中业已指出:“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13]任何开蒙的儿童均需身体力行地学习儒家的孝悌忠信和礼义廉耻。蒙学图书内容的更新能够说明知识界有意识重塑12岁左右儿童的知识范畴。而对年龄更小的儿童而言,也即梁启超所谓“幼学”,“非尽取天下蒙学之书而再编”,“大率5岁至10岁一种教法,11岁至15岁一种教法。”[14]新编教科书被视作了实现知识传输的主要手段。清朝政府尝试通过建立新式学堂改良教育,规范西学的引介,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实现教育改革。童蒙教育改革逐步展开。光绪十一年学制改革,高中实行分科制,新学制教科书随之出现。据《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搜录学制改革后蒙学图书目录,除修身、记诵类读物,算学、国文、英文、博物等已有专门教材,甚或手工、珠算教材也陈列其中。学制改革真正推进了“开启民智”的伟业。
总体而言,从戊戌运动开始,直到宣统时期,儿童图书馆学思想虽未有专门的书写记载,但伴随着近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思想的萌芽,12岁以上的儿童被划定为社会“开智”的对象,获得了入馆阅读的权力,从而也被赋予了阅读译书局所译新书的机会,成为了现代意义上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对12岁以下的幼童,得益于清廷的学制改革,在传统经学无法为社会提供科学技术相关知识和方法论指导后,社会出现了为童蒙教育编写的新教材,引入西学新知,尝试分科教育,融会中西、新旧、古今之言。新书籍和阅读材料的出现为民国儿童图书馆学思想的萌发准备了必要的思想和物质条件。
2 “提供必需且易晓的知识”:民初儿童图书馆学思想的发展
晚清的学制改革以“兴学育材”为主要目标。图书馆作为文明输入的重要手段为民众所熟知,图书馆之于教育的重要性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创立系统性图书馆学知识,尤其是如何保存、组织和管理新书也随之成为彼时知识界的重要任务。但图书馆学思想和儿童图书馆学思想存在差异。相较之下,民国以来儿童图书馆学思想的萌发和发展主要得益于以下两点:其一,现代意义上“儿童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children);其二,对大量童蒙图书、报刊的保存和和管理之社会现实。“儿童的发现”突出了儿童图书以“符合阅读需求”的图书分级思想。搜集、整理和开发儿童图书彰显了民国时期儿童图书馆学强调“输入必需知识”的通俗图书馆服务宗旨。
2.1 “儿童的发现”,注重“儿童之兴趣”
从本质上而言,“儿童的发现”既是一种社会学考量,也是一种历时性的历史认知。考虑到图书馆学所处理的儿童图书的知识和技能皆由儿童读者的范围决定,若对“儿童”,尤其是“儿童图书”的理解是儿童图书馆学思想的本体,那么“儿童的发现”对“儿童”的界定预先规定了民国时期儿童图书馆学思想本体范畴。
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儿童的发现”是现代社会的表征之一,赋予儿童和妇女平等的社会地位显现了社会思想的进步。法国历史学家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在《儿童的世纪:家庭生活的社会史》中考察了12世纪以来的欧洲儿童观念。对阿利埃斯而言,“儿童”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理概念,而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概念。“儿童”概念的内涵取决于社会认知水平。用此方法论审视清末民初社会中的“儿童”,不难发现,一方面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知识水平和认知需求通过晚清学制改革得以凸显;另一方面晚清的教育危机彰显了“儿童”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儿童”的理解已较传统观念有所不同。进一步而言,按照晚清以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15]的主张,“儿童”是解决民族危机的关键,儿童问题关系到民族的未来发展。儿童不能被放置到家庭生活中加以审视。而一旦“儿童”跳出了狭隘的家庭生活,传统社会所依赖的“父父子子”的伦理规训也就失去了其效应。道德知识的输入也就不再成为教育的第一要义。重新理解儿童所需知识转而成为整个社会的重要任务,“儿童图书”概念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被重新定义。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儿童图书馆学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以“进步”为指向的现代性思想,依赖线性时间的形塑。
儿童图书馆学以儿童图书的相关知识为研究对象,“儿童的发现”使得儿童图书分级成为可能,这为儿童图书馆学创造了独特的研究对象。现代儿童图书分级多以儿童年龄为标准,分为六级,分别是3岁-4岁,4岁-5岁,5岁-6岁,6岁-7岁,7岁-9岁和9岁-11岁。但如上文所言,民初“儿童”概念尚在建构之中,民初的图书分级并不完备,多简单分为3岁-10歲和10岁-12岁两级。以晚清民初发行的报刊为例,1897年创刊的《蒙学报》发行2年,从第八册起调整为上下两编。“上编为三岁至十岁用”,“下编为十一岁十三岁用”[15]。上编涉及文学、数学、修身与舆地四类,不论及史事和格致。除《蒙学报》之外,《儿童画册》《儿童世界》《幼学报》等大量儿童报刊陆续面世。这说明儿童已经成为特定期刊的目标读者。民国二、三年间,周作人谈及童话时专门提出,童话应用到教育时,需要从“幼儿期”开始,“计自三岁至十岁止”[17]。可见,戊戌以来,社会对“儿童”的理解日趋深入。陈独醒于1933年撰文总结了晚清以来儿童图书发行情况,指出民国以来儿童图书以童话为其开端——宣统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集童话,民国二年中华书局以童话为开端,未见其他图书。民国二年后出现了适合少年智识的知识型书籍,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童话和少年丛书。“民国七年出现了千里眼,空中战,照相术等常识谈话,民国十一年出现了儿童理科丛书,文浅图析,种类还多,颇受欢迎。”[18]鉴于“儿童”内部已出现了年龄分级,儿童图书内容之深浅应与目标读者定位相符。分级阅读以儿童本身的知识储备能力为基点,满足了儿童的阅读需求,专门的儿童图书馆应运而生。
翻译首先为儿童图书馆学提供了学理参考。在儿童图书日渐丰富后,自1910年起,民初报刊上陆续出现了儿童图书馆学的相关引介。如1910年《教育杂志》上刊登《儿童图书馆》一文,介绍了东京的儿童图书馆:日本东京日比谷图书馆长渡边又次郎在公众图书馆内附设儿童图书馆,分开架和闭架两种借阅方法,种类分为:图书、画册和挂图类;游戏、运动和唱歌类;童话和探险小说类;历史谈、人物传和地理书类;理科和数学书类;读本、字书和作文书类;修身、兵事书类;实业书类和他种图书[19]。儿童图书馆不仅是专门图书馆,还根据儿童图书馆种类区分了开架和闭架两种借阅方式。1913年,《新中国报》也刊发了题为《儿童图书馆》介绍型文章,对美国纽约图书馆附设的儿童图书馆进行了简要介绍,特别指明纽约儿童图书馆是“供十四五岁以下儿童观览”,且其“所藏3000余册图书主要涉及历史传记地质博物,目的是引起“儿童之兴趣”,并在“自然与科学上增速其进步”[20]。自此,按照儿童图书的类型,依照儿童兴趣的专门儿童图书馆为国人所认识。
2.2 输入儿童“必需知识”
1916年,京师通俗图书馆成立,下设儿童阅览室。所谓通俗图书馆是指为“启发一般人民普通必需之知识为主”所设的图书馆,“其中采集之图书,以人民所必需且易晓者为宜”[21]。隶属通俗图书馆的儿童阅览室显然也是为启发儿童必需知识为目的,所搜录的图书符合儿童年龄,根据儿童图书内容用子丑字分编四部,后用地支字改编十二部,增加了8部。“子丑寅卯”的分部方式沿袭了传统藏书楼的图书分部,与上文所示美日儿童图书馆学截然不同。儿童阅览室吸引了大量儿童读者。据1917年通俗图书馆年度工作报告,开馆第二年,普通阅览券收回72150张,儿童阅览券发放使用了113398张。儿童读者的数量远在成人读者之上。此后,小学堂和各省图书馆陆续增设儿童阅览室。此前的巡回文库未将儿童纳入到读者群中,相较之下,儿童阅览室明确将儿童作为读者,充分说明了“儿童”重要的社会地位。1898年,扬州医时学会在“章程”中记录了《蒙学报》的搜录情况,但并未有记录表明,彼时该馆已经根据《蒙学报》的内容对12岁以下儿童读者开放。清末不同“图书馆章程”或各学会组织章程中虽曾出现了收录和陈列时报的记载,却未有分馆陈列儿童图书和报刊的记录,反响和论争寥寥。这似乎说明图书馆学思想在本质上是一门应用型学科,无法在真空在产生。只有在“儿童”真正为国人所“发现”,大量儿童图书产生以后,儿童图书馆学思想才真正获得了供其萌发的社会土壤。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报刊引介,国人已对美日两国儿童图书馆学思想有所了解,但并未参照效仿,既未遵循西方图书馆编目的义例,也未按照西方图书以阿拉伯数字代表类目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彼时的儿童阅览室仅开放阅读,尚未按照闭架开架的方式开放图书借阅。可见民初的儿童图书馆学思想是应中国国情所需而设,参考西学,却又坚持融合传统思想,以应国情。所谓的参考西学是指,儿童阅览室尝试将汇集的图书随儿童读者的需要自由活用,输入必备的知识。所谓的融合传统是指,传统官私藏书以保存图书为宗旨,民初儿童阅览室完全承袭了这一思想,通过把有用的图书汇集起来妥善保存。不过,虽然阅览不同于借阅,但儿童阅览室的开放打破了儿童只能通过传统蒙学获得知识的方式,为儿童提供了必需书籍和阅读场所,实现了儿童的新知启蒙。传统编目的改良也促进了儿童图书的管理和收集,实现了以儿童分级图书为基础的儿童图书分类。总体而言,得益于“儿童的发现”,民初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儿童图书馆学思想,针对大量童蒙图书的管理服务也使得系统性的儿童图书馆学思想成为了社会必需。
3 “合于国情”:“新图书馆运动”与儿童图书馆学思想的体系化建构
即便社会已为儿童图书馆学的萌发提供了思想先导,但学科知识的发生和发展却始终有赖于科学共同体的出现。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本土图书馆学思想初步形成,建立了完全“合于国情”的本土图书馆学新范式。“合于国情”也因而成为了引导儿童图书馆学的纵深发展的基本宗旨。图书馆学人所倡导的“新图书馆运动”提出了“服务大众、服务平民”的服务宗旨,基于“儿童本位主义”的服务意识为儿童图书的分类、编目、管理等儿童图书学的专业原理深入实际提供了借鉴,实现了原理与应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3.1 科学共同体的形成
从科学史角度而言,学科的发展首先需要科学共同体,即从事相同的特定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士。继而依靠专业人士,学科逐渐形成共同拥有的通用表达方式、共同信念、共有价值和具体范例。图书馆学作为舶来之物,是在近代中国建构分科之学中引入的。传统四书五经提倡“格物致知”,从“知”“行”及其相互关系出发展开讨论,反复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22],学脉传承是传统学术的根本。但西方分科之学主张“科学”,意在通过专门理论、特定的方法、可预测的原则形成系统性的专门知识,重在学科的专门性。20世紀20年代后,“文华一代”和留美学人从美国和日本引入了图书馆学基本原理,尝试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图书馆运作的各种必备知识。而图书馆运作的必备知识包括知识资源的搜集、整理、管理和利用,与传统文献思想相同,但更多的基于编目、索引、读者服务等图书馆学的根本观念和工作理念。图书馆学人正是通过建构学科“硬核”的过程中划定了学科的边界。在儿童图书馆学中学科通用的表达方式主要涉及“儿童图书”的定义、分类、编目、管理和利用。共同信念和共同价值关涉到“输入知识”或“引起儿童必要之兴趣”等价值观念问题,具体范例是指供全国所效仿的儿童图书馆的日常工作。
3.2 儿童图书馆学的本土化探索
就儿童图书和儿童图书馆的基本观念而言,图书馆学人完全体现了“合于国情”的学科建设宗旨。图书馆学人注重引介美日等国的图书馆学原理,但其重心仍在学术中国化,也即构建本土化的“中国图书馆学”。这是因为,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图书馆学始终以本土的图书情报为研究对象。诚如杜定友所言,“没有一所外国的图书馆学校能够养成完全的图书馆学者,以应中国图书之用。”[23]晚清“儿童的发现”促发了“儿童本位思想”,儿童图书大量上市。不过,民初以来的儿童图书主要用于输入必要知识,儿童的阅读兴趣不是儿童图书的主要关注点。儿童图书限于“孔子、诸葛亮、司马光、文天祥、拿破仑等传记式的读物,寓意较深,事理朴素,使儿童获得历史智识上的补充以外,一点也钩引不出他们的兴趣。”[15]刘国钧最早提出的儿童图书馆学“三要素”也体现对图书“正当性”的规定:“合法的设备、适宜的管理员和正当的书籍”[24]是完善的儿童图书馆必定的“三要素”,而完善的儿童图书馆是国民教育所不可少的利器。
进言之,如果图书馆是“人民增进知识和修养”[25]的场所,儿童图书馆以搜集知识型图书为目标。此种观念彼时已广为社会接受。1924年,教育部儿童图书馆藏书约一千二百种之多,“以供儿童阅览增进知识”[26]。1932年,青岛的小学图书馆仅收录书籍四类:义;常识;文艺;杂志[27],完全以知识输入为主要目的。到1940年,儿童图书馆已由教育部官方督促开设,成为了学校之外实施儿童社会教育的指定场所,并按照附设于中心学校或民众教育馆的原则,省会所在地设置一所,专为所属地儿童服务。其中,上海儿童图书馆的使命是要摈弃诲淫诲盗的劣质图书,专门搜集优良图书,通过图书馆的阅读指导,为儿童的阅读和理解把关[28]。
值得一提的是,图书馆学人开始从生理方面重新审视儿童读者。“年龄大小于脑髓发达有密切的关系,年纪太小脑髓未发达,不可使用过度,儿童图书馆对于儿童年龄限制大约在十岁或十二岁,不满以上的年纪不许入馆。虽觉严厉,但为保护儿童起见,却不能不是这样。”[29]除小学儿童图书馆外,儿童研究所也开始筹办儿童图书馆。到20世纪30年代,报刊上已能见到对儿童生理和心理的相关描述:“儿童得到的益处:参考,实验,应用,自学力和研究心,适用于成人的,并不适用于儿童。”[30]杜定友等图书馆学人成立了专门的儿童图书馆委员会,拟定儿童流通图书馆计划,筹办儿童图书展览,儿童读者与成人读者生理区分已成共识。
基于上述“科学”认识,儿童图书馆学在图书分类和编目上进一步发展。儿童图书分类开始以年龄为界,分为浅易、较难,完全以儿童年龄和方便为宗旨。曾宪文在引介梭亚氏夫人《图书馆及其内容》后,重新提出了儿童图书的分类。她认为儿童图书分类应以书籍的难易程度为分类标准,分为“浅显”和“较难”两类,并将浅显的图书放置到矮架上,方便年龄较小的孩子阅读。较难的图书放置到稍高的书架上方便年龄较大的孩子阅读。又根据内容将童书分为神话故事、科学类、文学书籍、儿童诗歌、个人及集合传记、历史类游记和小说等七类书籍。另在编目方面,尤其是在制作书名卡时,需特别标注该书的内容,方便儿童了解该书的详情,面对较难理解的书目,尤应添加注释,以求清楚明了。“儿童书籍分配适宜,布置合法,使儿童幼小之记忆力,不至混杂,但求便于应用足矣。”[31]曾宪文提出的儿童图书馆学原理完全体现了本土学者的融合创新。
分类、编目和管理之外,图书馆学人也开始有意识利用图书馆提供更多服务。1936年,《浙江民众教育辅导半月刊》报道,市儿童图书馆举办故事演讲赛。图书馆已不仅仅被视作输入知识的有力武器,也成为了大众文化传播的场域,为吸引更多儿童读者利用儿童图书创造了条件。总体而言,儿童图书馆学在20世纪20年代后进入飞速发展阶段。对本土国情、儿童图书和儿童读者的深入认识是推进儿童图书馆学发展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儿童图书馆学无疑遵循了“合于国情”的本土化建设路径。
4 结语
“儿童的发现”是现代西方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如果把“儿童”这个概念纳入到晚清以来的民族意识和学术体系建构进程中加以研究,那么汉语中的“儿童”并不是一个既成的概念,而是一个被逐渐挖掘和建构的知识范畴。区分“成人”“少年”“少儿”“儿童”,一方面为“铸造新民”“启发民智”确立了明确的教育目标,另一方面为如何便于人民,如何促进国民教育,如何增进知识等“现代性”话题划定了讨论范畴。近代以来的教育焦虑通过儿童的发现一触即发,对新兴教育理念和分科式教育体系的建构和转型的期待与日俱增,也直接导向了晚清知识界对儿童阅读的关注。仅涉及“杂细事宜”的蒙学图书显然已无法满足彼时的教育需求,确立社会认同的“儿童图书”的概念范畴,为儿童教育提供全面的图书资源,如何为儿童输入必要知识也由此切实推进了儿童图书馆的系统性建设。然而,虽然晚清以来“儿童”和“儿童图书”的建构为儿童图书馆学的萌发提供了话语资源,但作为学科的儿童图书馆学却始终是民初以来分科治学的产物。得益于图书馆学人所创造的共同拥有的通用表达方式,共同信念、共有价值和具体范例,儿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得以建构,实现了本土化创造转换。从这个意义而言,近代儿童图书馆学思想是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若对其萌发和发展历史没有一个清晰认识,就无法真正理解这一漫长过程。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A].方麟选编.王国维文存[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682-685.
[2] 王国维.论政学疏稿[A].谢维扬,房鑫亮.王国维全集(第14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211-217.
[3] 李瑞棻.请推广学校折[A].吴晞.从藏书楼到图书馆[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107-113.
[4] 云南提学司叶尔恺详拟奏设云南图书馆请准奏咨立案文[A].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2:158-159.
[5] 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A].王杰,祝士明.学府典章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初创之研究[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147-155.
[6] 张元济.张元济书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4.
[7] 湖南图书馆暂定章程[A].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2:152-158.
[8] 云南图书馆章程[A].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2:159-164.
[9] 奉天总督徐世昌等奏建设黑龙江图书馆折[A].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2:166-167.
[10] 署归化城副都统三多奏创办归化图书馆片[A].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2:167-168.
[11] 严复.与张元济书[A].王栻.严复集 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524-557.
[12]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A].王栻.严复集 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557-565.
[13] 朱熹.童蒙須知[A].徐梓,王雪梅.蒙学须知[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20-25.
[14] 梁启超.论幼学[A].付祥喜,陈淑婷.梁启超集[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210-223.
[15]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A].梁启超文集[M].北京:线装书局,2009:43-47.
[16] 梅家玲.晚清童蒙教育中的文化转译、知识结构与表述方式[A].徐兰君, 安德鲁·琼斯.儿童的发现: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中的儿童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5-72.
[17] 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M].长沙:岳麓书社,2019:8.
[18] 陈独醒.全国出版界所发行儿童图书的概况[J].中国出版月刊,1933,2(2-3):77-79.
[19] 儿童图书馆[J].教育杂志,1910,2(2):15-16.
[20] 兒童图书馆[N].新中国报,1913-08-03(11).
[21] 京师通俗图书馆成立之经过[A].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2:266.
[22] 章学诚.校雠通义序[A].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目录学研究资料汇辑 第2分册 中国目录学史[M].1983:202-203.
[23] 王子舟,廖祖煌.图书馆学本土化问题初探[J].图书情报工作,2002,(1):22-28.
[24] 刘衡如.儿童图书馆和儿童文学[J].中华教育界,1922,11(6):1-7.
[25] 俞爽迷.图书馆学通论[M].南京:正中书局,1936:3.
[26] 西四大街教育部儿童图书馆[N].社会日报,1924-10-31(4).
[27] 双山小学儿童图书馆[N].青岛时报,1932-05-12(10).
[28] 胡祖荫.上海儿童图书馆的使命[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1,15(6):2-3.
[29] 杨昭悊.图书馆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282.
[30] 献.小学界同人们,请注意儿童图书馆[N].西北文化日报,1935-07-30(9).
[31] 曾宪文.儿童图书之分类与编目[J].武昌文华图书科季刊,1929,1(4):24-32.
作者简介:肖铮,女,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史、戏剧翻译;方仪力,女,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西翻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