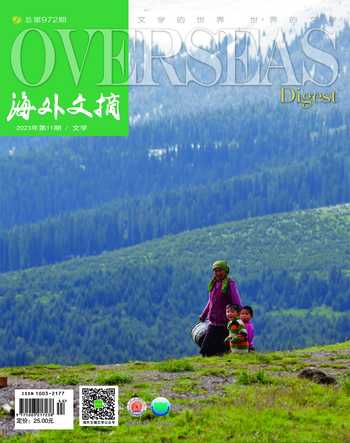杨家沟的冲锋号
王守贵

1976 年元宵节刚过,我受家乡园子辿生产队委派,前往黄河天桥电站做民工。天桥电站是山西陕西两省8 县上万人参加建设的水电工程,是拦腰截断黄河的第六坝。
我来到府谷营第六连所在地杨家沟报到时,民工没有住房,借居在天桥电站附近的几个村庄。府谷营部驻扎在西山村,所属各连住在西山、东山、黑山、杨家沟等附近的村子。杨家沟村驻扎2 个连,第六连由武家庄、碛塄两个公社的民工组成,第十一连由田家寨、王家墩两个公社的民工组成。第六连连部在杨家沟村头一面打谷场旁边,谷场面积很大。场面一隅一排简易的椽檩房住着连部的领导。我在这里报到,六连指导员(党支部书记)郝侯七以及连长等领导接见了我。寒暄一番后,安排我到杨大爷家里居住。
杨大爷的院子,有简易的围墙,有一个起脊大门,大门是框架式木格的。透过大门可以看到院子里因势就形一排五孔土窑洞,五孔土窑不是一条直线,门面呈弧形,靠东的两孔显得阴暗。不像南乡整齐一排的石窑洞。每个窑洞门面都在门窗上方建了一个避雨撇子,保护木质门窗不受日晒雨淋。叫开大门,见到一个面黄无须的老者,鹰钩鼻,两手留着长指甲,拄着拐棍,踉踉跄跄地走出来,就是杨大爷了。我说明来意,大爷把我引进他的家。
大爷年龄已有80 岁了,显得老态龙钟,一进门明显就闻到一股尿臊味。窑洞里由于长时间不打扫,脚地靠墙处的躺柜上积了一层灰。我把屋子打掃了一下,大爷对我有了明显的好感,脸上有了笑意。我看到大爷的炕上白天也有一个尿盆子。我说:“大爷,您就让我睡您的躺柜吧?这样您老人家在炕上也宽敞一些。”大爷点了一下头。我就把铺盖放在躺柜上。当时我也并不是为杨大爷着想,只是不爱闻到上了年纪的那股“老人味”。我住下后,让大爷把尿盆放在前炕,第二天一早我倒出去,窑洞里的尿臊味几天后就慢慢消失了。躺柜睡人,长度管够,宽度严重不足。躺柜有一米二三高,晚上掉下来肯定够呛。
我把躺柜偷偷往外移了一下,枕头放在靠墙那边,即使跌下去,也一定是腿先着地,避免把头摔伤。有这么个栖身之所,也就没什么可挑剔的了。
第二天听得一阵嘹亮的军号声,我按时起床。
原来,吹号的是碛塄公社(乡)齐家寨的齐二连。他在解放战争中,曾经是一名司号员。冲锋号吹得贼亮,震耳欲聋。由于他有军功,又有吹号的专长,他的差事人人羡慕。每天吃饭上工的集合,他能吹出两种不同的曲调。特别是上工出发吹的冲锋号,和电影战斗片吹得一模一样。一听激动人心的冲锋号,人仿佛亲临前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老齐一天的工作也就是按时吹几次冲锋号,就凭借这个,连队就能给他记一个工。民工们都很羡慕,话说回来,谁叫自己吹不了!
下连队灶上吃饭,一层又一层码起来的大蒸笼,有半个人高。从村子四面八方来的民工挤在院子里,两个五大三粗的厨师在灶房里给窗外的工人们递馍挖菜。外面的民工更是不安分,专门用筷子敲打着大海碗,小洋瓷盆。来这里吃饭的民工都用比家庭和学校大两个号码的餐具。原来劳动强度大的民工饭量出奇的大。一百多号人在小院子挤不下,有许多人停留在半坡上。分到白面馍的人边走边吃。啊呀,那个白面馍就像小孩枕头那么大,打听一下:小馍每个8两面粉,大馍每个是一斤面粉。在学校也吃过大灶,都是四两或者半斤面做的。我要了小馍,厨师挖了一大勺山药糊糊。外面有一盆化开的红盐水,谁嫌没味道,自己去加盐水。院子里安放一个比人高的锅炉,水已烧开,工人们把剩下的山药糊糊掺进半碗开水,连吃带喝。在露天外面吃饭,没有什么讲究,圪蹴在院子内外,左手拿馍,右手用竹筷挑糊糊,也有用汤匙挖的,速度真快,不长时间盆清碗空,工人们用筷子敲打着碗盆如同奏交响乐,照着原路全部散去。回到各自的住房,等待出发的冲锋号。我高中念书刚完,半斤的肚子,怎能撑进去8 两?同村的老民工怀兴哥告诉我:“必须要多吃,要不你拉不动那一斗子大沙。”
我撑死也吃不进去。把剩下的馍拿到杨大爷家中。杨大爷看着我吃剩的白馍,一眼盯住不放。我说,大爷,我已经吃饱了,如果不嫌的话,您吃了吧。
我也不是思想境界有多高。只是在出发前父母一再叮咛嘱咐,要省事,要尊敬别人。宁愿吃亏,不敢占人便宜。不要和人比高低,出门就该小三辈。当时是大集体分粮,各家自己烧火做饭,饥一顿,饱一顿,哪里有那么多讲究?大爷吃着我吃过的白馍高兴地说:“白面馍比红面馍、黄面馍好吃多了。”红面馍是高粱面做的,从外到里,红里带黑;黄面馍是玉米面做的,从里到外,黄里带白。这两种食物,都是粗粮,口感不好,中看不中吃。
后来才知道,杨大爷人缘不太好,脾气大,爱发牢骚,人称“大王八”。儿子儿媳不和他一个院子住,每天吃饭,给他送来一些吃食。经常听到他骂骂咧咧的,年轻时的英雄好汉已经沦落成惨不忍睹的老鳏夫。同院住的他的兄弟,人称“杨二善人”,七十多岁,儿女孝敬得非常周到。二善人有一个漂亮又柔情似水的儿媳妇,能按时给公公端来可口的饭菜或者跑来专门给公公做饭。二善人的土窑也被这个美丽媳妇收拾得一干二净。每当这个年轻女人婀娜多姿地出现在院子里,民工们总爱搭讪她几句。看她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样子,大家喜欢得不得了。
杨大爷弟兄两个有罅隙,从来没见过他们一起说话。西边一线三孔明亮的土窑住着杨大爷和民工,东边两孔比较阴暗的土窑洞住的是他的弟弟杨二善人和民工。一个大院两个老鳏夫是房主,另外有十大几个年轻的天桥电站民工。我估计电站一定给他们一点房租,修电站的工人总不能白住老乡的房屋。房租当然是象征性的,当时国家也很穷。要不怎么能让民工一天来回翻两座山走20 里路上班。电站劳动可是重体力劳动,光是从工地到住宿地空走一趟,也让人望而生畏。
吃罢早饭,大概是6 点半的样子,工人们回到各自的宿舍,等待上班的集合号。不到7 点,只见号手老齐拿着他那锈迹斑斑的小铜号,走出连部,上了杨家沟村最高点,开始吹出振奋人心的战场短兵相接的冲锋号。听到这个号声,工人们根本坐不住了,工人们一听到这个号声,神经马上紧张起来了。就像娶媳妇吹喇叭打鼓拍镲的乐队,你不赶快行动是不行的。立马把自己的圆头洋铁锹扛在肩上,从村子里各家各户走出来,奔向打谷场的连部。民工既然是部队建制管理,所有活动都按队伍来要求。
以排为单位站成4 列。每个排由排长领头向连部领导汇报人数。(排以下还有班,班长是最基层的领导。)连部领导讲话进行战斗动员。接着一长溜队伍开始向天桥电站出发,不过,肩头扛的不是长枪短炮,而是一个样式的圆头洋锹。这洋锹可不同于农村使用的方头土锹,方头土锹是农村铁匠打造的。洋锹是洋铁皮在机器上加工的,配上机器加工过的一样长短粗细圆圆的木头把子,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很带劲。我拿着这么一张圆头洋锹,往黄土里插了一下,无比锋利,非常高兴。
4 列长长的队伍依次走成一长溜,从住宿地杨家沟村出发,到天桥电站的建设工地。队伍基本上都是不上40 岁的青壮年。肩扛长把圆头铁锹,雄赳赳,气昂昂,先下沟,后翻山,再走一段山梁,来到晋陕大峡谷边缘的高山上,俯视整个天桥电站,面对如此浩大工程,你不心潮澎湃,那是不可能的。马上就要投入拉平车的战斗,那是何等激动人心的一幕。
在杨家沟村,我整整住了一年,和工友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电站的艰苦劳动淬炼了我的性格。
后来,我考上大学,做了教师,吃到了向往已久的公家饭。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