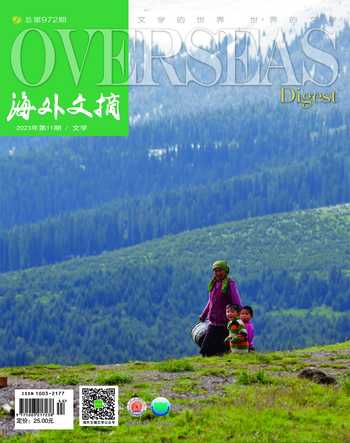瞬间
何锡联
一
站在两面镜子的中间,那镜像中的层层身影无穷地远去。对于我,影子越小越好,如果因视觉引发争议,我不会选站任何一边。
有时想说说前途和命运,说说梦过想过做过或更多的瞬间。冬天的雪是清白的,没有花草的遮掩,有的是足够的冷漠让你呵护。
在大雪覆盖的小路边,白桦树的枝头没有一片叶子。我知道,它们生性就不会以拯救者的形象来掩饰冬天。在冻僵的身体里,它们的呼吸依然有着巨大的能量。我站在河堤上,看到了隐匿在树林身后的茅屋,以及从它窗户里透露出来的昏暗的灯光。然而,守候它的已不再是那个穿红色绒衣的人了。
今夜,我不能为一份忘却了签名的试卷而失眠,因为我对抵达所确立的目标充满自信。将答案放在心里,走夜路也不会害怕。
我是熄灯以后才摸到那只茶杯的,杯中的茶水有夜的庇护,很难看到它内心的光影。虽然我从未对它的存在产生过怀疑,也从未凭自己的感觉去体验茶多酚或黄酮类的成分对睡眠的影响。然而,那些外部因素的存在的确让我的神志受到了提醒。
园子里的蜡梅初心点点,它们对前方的春天好像有着本能的冲动和追求——虽然那些褐色的枝杈间还挂着雪后残留的冰碴,但它们依然毫不迟疑地坚守着、仰望着。即便在夜里,它们也会在黑暗中洞悉烟火——尽管黎明总要开启。
敞开门窗,时间也不会回来。但对时间序列的原生意识,总会让我对事物的运动形式产生好奇,甚至有着重新再造的心理。这样,我的愿望便会在新的存在感召下发出别样的音调,且细水涓流。
二
天空以漫无边际的延伸试探我的想象,直至远离生活的体悟而置于冷酷与空茫。我真的能以自己的德行汲取外空虚弱的文明吗?在倾泻的光里,我时常用颤抖的手抚摸着石碑上的痕迹。
有时我感到一支香烟真的能在懵懂之时恢复我对于陌生事物的清醒认识,让我关切起一样痛苦的逻辑以及思辨的内涵,以维系我对于信仰的持久忠诚。
我在离天空最近的草棚里休憩了很久,于无人之境分享了更多的未知。那里既没有对地域的掠夺与赠予,也没有对光阴的挽留与驱离。
世外桃源让我荒唐地回避了做人的抗争,世间的虚荣又让我拼搏着做人的尊严,而梦醒之后的骨感依然让我攥紧拳头。
我是从黎明的音乐中走出树林的,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走多少路程。当天空以透明的蓝敲响我的骨骼,我却不能为其填词和注音。
我与阳光是在同一个码头上船的,在溯流而上的行进中,由浅入深的天空着力排除两岸树木的遮掩,大有陪我走到底的意思。我真不愿打扰隐居于水下只有七秒记忆力的朋友。我希望自己能在这清澈的河水洗礼下,将离散的事物结合到一起。
沿着河流向上看,我无意间产生了与时光隧道有关的幻觉,那由红、绿、蓝三色交织的光色散现象对我的视觉产生的巨大冲击。我不能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对那些磁场、电荷、温度以及折射、散射、透射等自然现象横加干涉,将尚未明了的运动变化加以否定。在那深藏不露的隧道里,时间好像可以被随意改写,黑与白也可以颠倒使用。
幻觉之后亦非幻觉,存在与消亡只在一瞬之间。我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冷暖,并不能在当下的时空中表现出多元色彩,尽管它们依然保留着原本构造的基础,但那些带有意识性的光斑图像在时光的进程中依然没有得到真实验证,因此我不能为其陈述和辩护。
三
路过夕阳编织的图景,前方有许多问题在等待着回答。譬如,祖先们留下的空间是否还有可塑的余地?我们修正的旧有道路是否还有更多的方向?
沿着思维的出口向前走,夕阳的光芒洒满新耙的河堤。河水静流,没有联想,只有倒影将两岸的楼群与树林加以对照,至于岸上发生了什么,好像并不是它们要关心的事情。
此刻,夕照的红云、耸立的山峰、天空的飞鸟、水中的游鱼组成了一幅恍若虚构的画卷:它们均匀地调节了向晚的空间,给我的行程予以了引导;给苍凉的穹顶增添了抚慰。
生活中有一长串的规则,它们从头到尾都处于支配地位,在它的直线上,每一个时点都有它自身的尊严。我从读书时开始就被支配着,像是受命前来,又像在完成某个约定。
虽然我时常调整自己的坐标,但在局部的空间里,我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被相对的神经节点所控制,如同地球总要绕着太阳沿着它的椭圆轨道运行。因此,若问我的观点对身边事物的演化过程有何影响?其答案一定是表面上的结果。
有时,我会用心地领悟时间的艺术流逝,归纳整理出夕阳下的山坡、田野、村庄、炊烟、桥梁、高铁以及黑猫与白狗是如何在不含矛盾的概念中均匀地呈现出它们的几何状态,抑或证明出那些假定的原理。
我的影子尾随在时光身后,我无法返回到生命中的任何一个原点。因此,时空中不可简约的相对性常让我产生忐忑与惊悚,抑或陷入深夜的冥想之中。
四
我何时走进了一条杳无踪迹的堤岸?
徘徊于漫长的流逝,我毫无知觉地被一种意识所控制,它一次次盘旋上升又一次次鸣啭降落。在它的结构中,原始的积累像细微的沙尘,它们在相互碰撞中形成颗粒,使缥缈不定的幻想不免落空。
借用灯火的视觉去感知更远的村庄,风雪中的镰刀、木犁、锄头、箩筐、草绳和更多的物象都毫无表情地占据着空间,这让我怀疑起它们存在的理由。
现在,我不能把精力用在如何尋找另外一个自己的心思中去,即使在遥远的异域有一个思维与感觉和我完全一致的人,我们也不能同时看到同一个风景和同一面社会现象。就像我不能用已经建立起来的逻辑与原理去类比并以此求得在伦理推演和道德讲坛上的谐音和均衡。
此刻,如果有人要我放弃同音共律的实践,我会关闭所有门窗,隐去以大山为背景的猎猎显现。每天,黎明守时地攀上我的额头,而我却并没有听到它的夜半钟声——那些不带任何意识的共鸣,让我获得自由平衡的艺术。
有时,我会在夜里停下脚步,或伫立水边,或凭栏远眺。我发现事物的差异是很难用自身的经验去判断它们的远近或产生的距离的。
当寒冷与落寞贴近我的胸口,我并没有苍凉与悲摧的感觉,面对无边的静寂,我油然产生了无人察觉的信心。
我在接续吹来的风中伫立着,轻松的旋律在我的耳际萦绕。在后续延伸的时段里,我的眼前浮现出了与旋律构成相符合的离散与聚合。而那些存在于旋律中的变换,只呈现于我意识的瞬间。
五
我确乎感觉到了河水的深浅,而它们在行进中已忘却了自己。泥沙俱下,我要计算一下黑暗与光明的重量,让生活不再怀疑痛苦与快乐是一样真实的存在。
当云朵在水中线性地流淌,它的力量仍蓄势在更高的源头。在波浪连续拍打岸边的声息中,浪花遮蔽了礁岩上的伤痕。我与河流平行进退,听众多支流缓步轻吟。
选择左岸或右岸都没有过错,只要生活超越了自己而自己依然热爱生活。我的焦点并不在水下的隐形效应,而是如何让事物的真相清晰地浮出水面。
我时常进入河流的梦里,获取稍纵即逝的信息,尤其当我发现深层次的矛盾需要荡涤和清理。
不用怀念,我也能推测到去而不返的光阴。河水流过安静的黄昏和墓碑,而它们却不愿揭示与呈现那段历史。
如果想象力可以驱动河水,语言能够托起峰巅,那又何必去证明时间与空间的统一。对河水的奢望越少,对前方的渴望就会越多。
我不会用别人的成功绘制未来的途径,也不会用水能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警示当下。我曾对抽刀断水水更流的论断产生过怀疑,而对上善若水的说法一直予以肯定。但作为带有臆想的认识,我始终坚持用实践去检验。
我的身体难以分开流淌的河水,而流淌的河水已分割了更多的荒野。岸上的铜钟敲响了无数个年代,与水相关的理论却一直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
多一条河流就多一条途径,完善自己也勿陷入无穷的追溯。并非水有多深就有多深领悟,汹涌的现象亦是理性与欲望的博弈。
六
生活蛊惑出一根根白发,风雨之夜偷袭了我的双鬓。人的命数如何定夺,趋近平行的看待才会有更远的交点。许多白发否定了黑发,许多黑发又在寻求新的路径。
理性的生活不断超越原来的结论,所有的推理均蕴含着假定的可能。我对黑发白发向来一分为二,从不作试探性的叩问。
一种事物不能取代另一种事物,各种分歧都可能催生出新的思维。不因荒谬而千篇一律,不因瞬间而放弃寻求;物种相克才有共生,事物相争才有推手。
知道忧愁已不再年少,与意识较劲从未有过结果。我的身体被房子困扰,我的房子被风雨困扰。所有的心思都藏搁在一本大书里,所有的追求都在反思中践行。
我希望所有的事物都有各自的位置,即使处在危险的境地,也不会因个人的情绪而对抗流水、对抗洪荒之力。
我想了解人情以外的事情——草木、荆棘、悬崖、瀑布、霜雪、风雨。它们从不纠结于别人的猜度,并且在阳光下也从未发出过碰撞的声音。他们借助夜晚的星光思索黎明,从未显露谄媚的神情。
我不会预设规则漫游山水,也不会像路边的沙尘沾黏秀慧的衣裙,在各种传闻中我只想亲身体验,鹰一样俯视与滑行。
七
我在并不均等的人世间从不轻易直言,对不同的理念也从不说三道四。
然而,我又不得不让固执的手指容忍带有心机的触碰。夜晚的风,云中的雨,一直向我暗示它们的机理和背景,而这些又恰是我不愿思考且终究会明白的事情。
我担心那些智能化系统一旦获取了人的意识,抑或形成了自己的觉悟,那它们到底是人类的保护者还是破坏的力量——至今我不敢往深处去想。在缺少体温的状态下,我怕天空混淆了思想与智能的概念。
如果将没有灵魂的感观当作存在的基础,那大片的罂粟还能造成臆想与幻觉?在被智商忽略的辨识中,用比喻能说清人在物中的蜕变过程吗?
许多拟人化的想象具有很强的穿透力量,但生存与死亡的求解只需一元二次方程。在纯粹的时空里,没有人能用敏感的神经计算出未来的时日。
走过湍急的河水,我需要隐匿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尽管我正处在思想与目标叠加的实践之中。
我不愿纯朴的诗句在很高的塔顶体验坠落的快感,也不愿黑鸟的忧伤鸣叫成无助的争议。当乌云为修饰诡异的形态而在风中纠缠,我将闭上眼睛漫游不占空间的风景。
我心怀感激地被忽略,准确地说,是漠然与冷淡,尽管我在正反两面的天空下竭力权衡用数字还是用文字对相互作用的粒子进行旁证与表述。
八
黑夜充满廉价的回忆,想象没有任何成本;祝福弄不清加减法的意图,欲望常让人上当受骗。有一种蝴蝶能感觉到十公里以外的存在而前往约会,有一种诗歌从情感的源头出发从未出现血栓。
如果不是直观对比,我能深化对于众多观念的理解吗?我时常问自己,数学难道真的是从生活中虚拟出来又被人为定义的一种形式?
当河水撞击散乱的石头,激溅的泡沫不断飞向天空,然后又在天空不断消失,在它们重复的现象中并没有重复完全相同泡沫。就像我在行进的人群中终究会消失一样,而人群则会永远在行进的路上。
仿佛是一只猫蹲在漏雨的屋檐下,在它占据的位置里,已经排除了收拢起来的两只前爪。它注视着窗户里的光亮,不时地发出“喵喵”的哀怜,从它的声音中我听到了对主人的忠诚和抗拒逆境的意志。
今夜,如果没有像轻敲着密电码似的雨水在房屋的瓦棱上跳跃;如果没有风的哄抬与聒噪,那还有什么可以成为忧郁的理由呢?
此刻,窗外正下着初春的雨水,它们数遍了今夜的河流、山脉、农田与房舍;数遍了那些感知存在的地域。在比夜色中的玫瑰更加鼓舞人心的房间里,我能经得住近距离的审视吗?
九
放下茶杯,一只猫投下了原生的形象,而我却并没有留下恰切的身影。
转向内心,玻璃幕墙竖起了精美的欺骗,而各种想象却并未出现转折性的省悟。基于引力的原理,事物总是把弱小的粒子拽到自己的圆周以内,但在美其名曰的自由运行中却早已抹去了它们的自主性选项。我就是那只蹲在漏雨屋檐下的猫,无论树上树下,都走不出被意识划定的圈子。
我曾企图从确认的定律中退场,但任何试图改变规则的努力始终徒劳无益。在寻求与大自然兼容相济的循环中,我希望发现与自己相向而行的更多事物——哪怕那些事物倍受曲解与责难。
夜幕降临,万籁俱寂。所有事物都在不停地变化,包括正在沉睡中的人。在他们毫不知晓的情况下,衰老的细胞不断被新生细胞所取代。然而,从他们黏滞的梦里却无法摄取带有云状的画面,许多与幻觉相近的成分非常廉价,但我却很难感受到这一领域的更多现象。
并非人人都能切入到伤口深处,我身边的人与事充满着矛盾。有人告诉我那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并随时可能改变人的命运。但在深夜的梦里我额头上的皱纹还是记下了流逝的光阴。
我努力探究夜晚的意图,但月光并未传递天空的活力。尾随我的影子正发生惊人的意外,它们在弯曲的形象中尽显虚无与茫然。
如果有人能在河水的边缘平滑地描绘出时空的演化,那一定有人能从揉皱的波光里绵延出与生命有关的预言。
十
像进化的玫瑰攀附更高的阶层,我对荆棘丛中的陷阱不抱怨言,它们在草木的掩映下依然有着可贵的警惕。
我的忧虑来自原有概念中不能用图像表达出的意识,亦如高大的楼宇不能在数字的聚合中得以成长。我的思想在阳光的漂洗中删繁就简,光脈动荡的天空有风戏谑沙尘。
荒野无垠,唯有萤火隐现于芦苇。在冷风堆砌的夜晚,隐喻不占逻辑的空间。被理论证实过的黑洞,我理解也就是太空中丢失的一个瓶子。
瓶子里装满自然界的存在,却隐匿了追逐扩散和一波又一波的涟漪。我的大脑在不停地思考,有灯为夜而操劳。
我在宽阔的水面上荡来荡去,两岸的光影恍若纤尘。我借助辩证法的力量精心计算,那宇宙以外的第三种可能。
我没有营造意象的能力,也没有分辨真伪的依据。但我不会将溅出的血看成花朵,也不会将会飞的鸽子卖成不许出血的肉体。为了凸显伦理依然的一面,有时我也会赔上几滴泪水,然后做一个纯粹的人,并在外力的推动下,沿着既定的轨迹不偏不离。
我在弯曲的光波中滑行,失重的感觉让我摆脱了疲劳。我还得往前走,为明日的旅程做些准备。
责任编辑:蒋建伟、杨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