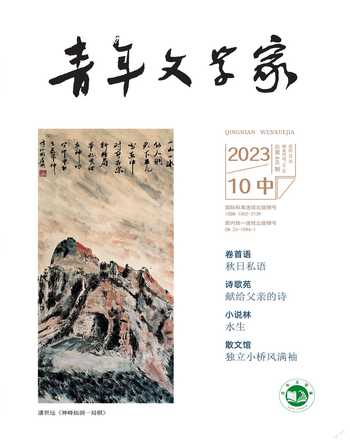赚趾
范智荣
一
古坊村的大龙叔有个稀奇古怪的称谓—“赚趾”。在我的故乡古城,一些上了年纪的风雅之士还称他为“浸润朝阳的赚趾”。
浸润朝阳,听起来挺有诗意的吧?其实,无论在旧时江湖,还是在今日古城,这“浸润朝阳”都是染坊的一个别称。当然,“浸润朝阳的赚趾”也不是什么诗人,只是染坊的匠人。“赚趾”,是染匠的旧称。染坊是给帛、布、衣、物染色的作坊。染色是门古老的手艺,据说在唐代就已盛行。千百年来,它成为人们美化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过,在染坊里埋头苦干的这些人称“赚趾”的染匠,十分辛苦,而且地位低下,总被人瞧不起。
作为赚趾的大龙叔姓刘,与我小姑母家同村,所以我从小就熟悉他。这染匠长得高大结实,平时少言寡语,只顾默默地忙碌,心情好时,爱哼唱几句绍剧。他也属龙,大我十二岁。小姑母叫他“大龙”,叫我“小龙”,我便尊称他“大龙叔”。他跟自己父亲学了一手草木染的古法染色绝活儿,就是选用植物的根、茎、花、叶、果实、果皮、干材等天然染料,给布、纱等纺织品上色。他用蓝草叶染青,用茜草根染红,用栀子果实染黄;还根据不同的织品来料和上色要求,选择生叶染、煎煮染、发酵染等各式染法。最绝的要数他的套染,用色素不同的植物染料进行叠加,取得多样又多变的不同色彩。我曾亲眼看他用蓝草浸泡和发酵而成的靛蓝,与槐花套染取得油绿色的全过程。
大龙叔十九岁时,父亲去世了,两个姐姐也已出嫁,家里只有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全靠他当赚趾的收入来贴补家用。农闲时,大龙叔常挑着上百斤重的染匠行担,手拿一根搅和染料兼打狗驱蛇的拇指般粗的棍棒,游走于古城一带,吆喝生意。到了春耕、双夏、秋收、冬种等农忙时节,大龙叔在生产队劳动之余,还起早贪黑忙碌在自家的“刘记染坊”。这个典型的家庭式染坊,是以染零星杂色布料及旧衣物为主,就大龙叔一个人忙活。
浸润朝阳的艰辛,没有动摇大龙叔做赚趾行当的信心。毕竟,这大小也是个生意,不光能挣点儿现钱,还能给别人的生活增添色彩。辛苦之余,他常会自得其乐,唱上一段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虽然植物染料无毒无害,但由于长年接触靛青染料,大龙叔身上总有一股难闻的靛青气味。尤其是他那双手,呈现出一种洗不干净的青黑色,恰似农村某一土鸡品种脚爪上的颜色。可是,他明明长得魁梧英气,算得上一个帅小伙儿,不少人却在背后称他“青爪佬”或“青脚鸡”,充满轻视。姑娘们要么对他嗤之以鼻,要么避而远之,少有拿正眼瞧他的,致使他二十几岁了还没有对象。
二
古坊与古城隔湖相望,地处山乡门户和水陆要冲,向来有不少作坊。大龙叔的“刘记染坊”距村口的牌坊不远,倚着山坡,傍着溪流,听说是在1947年前后开张营业的。这在古坊的多家染坊中,属于开业最迟的一家。然而,古坊人却将它的草创过程传为趣谈。
大龙叔的外祖父是名厨师,人称“刘大厨”,他没生儿子,只养育了三个漂亮的女儿:大丫已经出嫁,二丫也已订婚,小丫还待字闺中。刘大厨与妻子、小丫达成共识,要找个上门女婿。他在古城物色到一合适人选,是个孤儿出身的挑行担的赚趾小伙儿。刘大厨借着替二丫置备嫁衣和婚被的由头儿,雇请赚趾小伙儿上刘家染布,叫妻子和二丫协同小丫,一起暗中考察。
这赚趾小伙儿健壮端庄,人很质朴,很踏实地在刘家后院操劳,手艺十分高超。小丫听其言,观其行,感觉他诚实可靠,芳心暗许,便热情地给他沏茶续水,不时送上体贴。刘大厨但凡在家,总要亲自掌勺,烧出拿手好菜,给赚趾小伙儿下酒。刘妻更似岳母待女婿般疼爱赚趾小伙儿,还带着二丫去村中游说,动员乡亲们陆续送来布料,让他加工染色。这就使赚趾小伙儿延期待在刘家,有足够时间确保小丫展开魅力攻势,也让他日益感受到“家”的温暖。很快,他俩就情投意合了。
有一天晚饭后,刘妻和二丫又出门去帮赚趾小伙儿揽生意。受雇出工的刘大厨尚未回家。小丫情不自禁,投怀送抱……从此,这赚趾小伙儿就不想走了。事实上,他想走也走不掉了!
不久,刘家好事成双:赚趾小伙儿正式入赘;同日,“刘记染坊”正式开张。小两口儿每天都在染坊操劳,苦是苦点儿,却恩爱甜蜜,先后生育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就是大龙叔。从上小学那年起,大龙叔便利用空闲时间跟着父亲学染色手艺,成了一个小赚趾。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刘大厨夫妇先后过世。大龙叔的父亲大赚趾,也因过度饥饿、劳累、悲伤,一下病倒在地,似乎没了心跳。大龙叔的母亲小丫惊慌失措,全然失去了昔日的机灵和果敢,只会一个劲儿地拳打丈夫的胸膛,冲他耳畔哭叫:“你个大赚趾,不能死啊!你死了,叫我和小赚趾还有女儿们怎么办啊!”说来也巧,生怕丈夫死去的小丫带有怪怨和撒娇的下意识拳击,恰如医生施救的心肺复苏术,使得大赚趾又有了心跳。大概他也知道自己还不能死,便起死回生了。
此后,大赚趾硬撑着身体,手把手地将一整套染色技法传授给了大龙叔,直到他的技艺精湛,成为真正的赚趾,可以接班当家了,而他的两个姐姐也都结婚了,大赚趾才真的撒手人寰了。
三
我去小姑母家,进入古坊村后,就要路过大龙叔的家院。那是个偌大的农家院落,高高的篱笆围着一排白墙黛瓦的平屋,形成前后两院。前院门楣上挂着“刘记染坊”字匾,两扇竹门总有一扇敞开着,方便顾客进出。往里瞧,有染后稍干的小件衣布,挂在晾架上待取。后面一排平屋,由于年久失修,好几处已是破墙裂瓦,风化剥蚀。往往只见小丫阿婆那风韵犹存的身影在辟做店面的堂屋里晃动,她忙着接来料、记账,或收费、发成品,却老是望不见大龙叔的人影,只是偶尔能听见那后院飘出的他的粗嗓音。
我和小伙伴们常去挨着大龙叔家的山坡上玩耍。坡边有棵高高的老槐树,粗大的树枝歪斜着伸进他家后院。每每爬上樹去掏鸟窝或者坐在枝杈上乘凉时,我总能看清整个院落。很显然,“刘记染坊”是前店后坊的格局,后院作为大龙叔染色和晾晒的作场,比前院宽阔得多,也更向阳通风。在平屋后檐下,放置了一排大大小小的缸,主要有用来浸泡剥离的酸缸,用来染色的染缸和汰布用的板缸。我多次将大龙叔操作染色的一举一动瞧个清楚,印象最深的是他用靛青给布料染蓝。最初染出的只是浅蓝色,他将布料放上竹架晾干,再放入染缸去染;每染一次,颜色就深一层。他能由浅而深依次染出月白色、二蓝、深蓝、缸青,直至最深的近于黑色的“青”等不同层次的蓝颜色。我想:或许,“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便是由大龙叔这样浸润朝阳的赚趾在古法染蓝过程中提炼而得的吧?
那年月,附近的山乡农民十分节俭,凡是旧衣裤、旧毛线,在以旧翻新和由大改小之前,总会先送入大龙叔的染坊。古城一些家境好的人家,为了藏富,也将不少色彩艳丽的染色布、花格床单、丝织被面等送来染坊加工。特别是城乡大批青年男女,喜欢将各色布料染成草绿色,仿制军装。大龙叔的染坊,一下红火起来。眼看着后院那一排排高大的晾架已完全饱和,大龙叔索性将染好的衣布用竹筐担到家门前的溪滩上去晾晒。这时候,他就会欣然扯开嗓子,唱起绍剧。他唱得高亢激越、豪放不羁,充满了男性的阳刚,似乎还带有光棍儿的苦恼和对异性的渴望!
同村的水莲阿姨听到了大龙叔的高唱,也懂得他的心声了。
四
水莲阿姨是我那位干裁缝的小姑母的小姑子兼艺徒。发现她和大龙叔的秘密,是在我第一个本命年的暑假。
我待在小姑母家时,忽然“长猪头”了,也就是得了腮腺炎。她的婆婆说只要涂抹蓝靛染料,过几天就好。正在吃早饭的闪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的水莲阿姨听到后,自告奋勇要陪我去大龙叔家“就医”。这位号称“古坊村花”的姑娘,换上了自己新近缝制的一件红花格短衫和一条青色长裤,拖着一条粗长的黑辫,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活脱脱就像《红灯记》中的李铁梅。出门后,她走得欢快,兴奋得像去捡宝似的。
热情的小丫阿婆引我俩来到后院的染色作场,就见屋檐下那排大小缸前,大龙叔正弯腰弓背地将一块又宽又长的绿布从染缸转移到板缸去汰。他古铜色的躯体上仅穿一条短裤,一身汗水淋漓,胸膛的肌肉被朝阳映照得亮晶晶的。瞬间,水莲阿姨木然而立,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一副迷恋相。大龙叔转头间发现了她,冲着她咧嘴笑了笑,那笑容很憨厚,但他不时瞟向她的目光是火辣辣的,甚至有点儿放肆。水莲阿姨羞红了脸,低垂着头,明显有点儿心慌意乱。很快,她掩饰性地瞧着院中挂满的绿布、蓝布、红布、黑布和花布,故作惊叹道:“哇……”
这是我首次走进浸润朝阳的场所,零距离观看赚趾的劳作!也是我最初发觉他俩的秘密,原来,大龙叔便是水莲阿姨的心中之宝!大龙叔将汰好的绿布拿去晾晒。水莲阿姨生怕失去他一般,慌慌张张地尾随而去。这时,小丫阿婆笑眯眯地拿调羹去靛缸舀了一些蓝靛,往我发炎的腮帮子上涂抹。扭头间,我望见那挂布间,水莲阿姨在大龙叔眼前转了一圈,指着自己的衣裤问他:“我这套好看不?”大龙叔赞美地点点头。水莲阿姨笑容迷人:“是你手艺好,给我染得好看!”想不到五大三粗的大龙叔也巧舌如簧,很会甜言蜜语:“不,不,是你人太好看了,所以穿什么都好看!”“是吗?”水莲阿姨白了大龙叔一眼,忍不住发出了笑声,调皮中带有几分诱惑……
后来,水莲阿姨不顾父母反对,死心塌地嫁给了大龙叔,婚后生了个可爱的大胖小子。头脑活络的大龙叔从娇妻和爱子身上发现了商机,他去古城收购了价廉物美的白棉土布,精心染成几种好看的颜色,用这每式色布给水莲阿姨和她的儿子分别缝制了一套衣裤。母子俩穿着一新地去乡亲们面前“显摆”,引得大家纷纷上门来定制服装。
大龙叔夫妻俩夫唱妇随、举案齐眉的小日子越来越好!
五
转眼,跨入了20世纪80年代。大龙叔怎么也想不到,就在他准备扩大染坊大干一场时,周围的一切正无声无息地发生着大变化。原本织土布的原料—棉花,竟没多少人种了,织土布的顾客也自然减少。从古坊到古城,男男女女的穿着打扮变得多彩多姿,各种款式的面料,各种颜色的花布,令人眼花缭乱。眼看染坊的顾客日益稀少,大龙叔心急如焚,困惑不已。幸亏水莲阿姨头脑活,先是选购流行布料搞缝纫加工,零售成衣,接着便倒卖流行服装,随后又和我小姑母合伙开了个服装厂,生意还很不错。有了资本积累,水莲阿姨想拉长产业链,发展前端性现代印染,也好让丈夫有所作为。但大龙叔借口他俩没多少文化,更不懂科技,予以否决。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龙叔的儿子考上了大学。水莲阿姨叫儿子去学染整技术专业,以求学成还乡,发展印染业,好与父亲大干一番。不料,大龙叔硬是反对,说当今化学印染技术不成熟,不如去学建筑,好为百姓安居添砖加瓦。结果,他们的儿子就去学了土木工程,毕业出来,恰好赶上了住宅市场化改革大潮,他在一家建筑公司大显身手,之后又自己搞房地产开发,生意风生水起。
大龙叔虽然为儿子高兴,却一直守在“刘记染坊”里。每当接到一些染色活计,他总是很认真、很努力地去染,他说这样心里踏实。有一天,染坊来了几个摩登女郎,请大龙叔染了几块方布,还执意给他很高的价钱。事后,大龙叔才听说,古城一家商店把他古法染的土布挂在墙上,不少人都喜欢这种叫“壁挂”的布。更让他惊喜的是,自己染的色布还被做成了时装,受到了城里不少年轻人和一些海外人士的喜爱。
他上高中的孙女说,这叫“时尚”。大龙叔虽不懂时尚,却坚持认为古法染色还是有用的,尽管他已是古稀之年,還执着地去染坊守着。早已成富婆,正安享晚年的水莲阿姨对他的“冥顽不化”颇为不满,她说:“时尚就是适应潮流,随着现代印染技术取代古法染色,染坊绝迹也是必然。”大龙叔听了,用眼瞪着水莲阿姨,一副生气的样子。还是在旁朗诵唐诗的孙女,逗得他老人家开心地笑了。
浸润朝阳的赚趾,其实就像诗人,他是用植物染料“作诗”,彩绘着人们的美好生活。而这传统的民间工艺散发出的古典之美,大有返璞归真之感,深受有识之士喜爱。这就好比中国古诗,虽说早已不是主流诗体,但它不会沉寂无声,更不会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