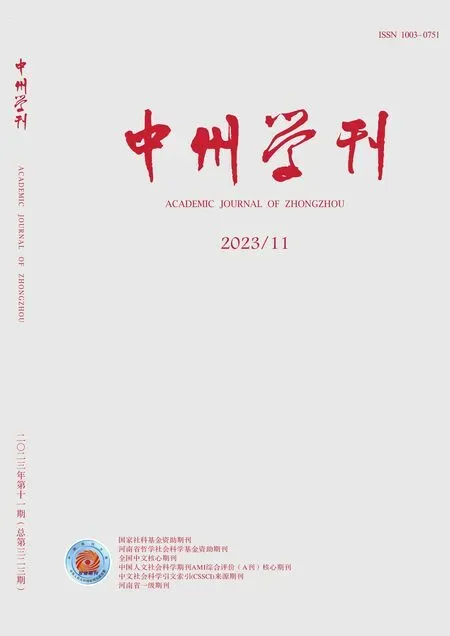道家与名家形而上学的历史纠葛及其影响和意义
高华平
《周易·系辞上》曰:“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现代中外学者论中国哲学之形而上学,皆常以《周易》和道家(特别是《老子》)为例。黑格尔尽管对中国哲学存在偏见和误解,认为在整体上“中国不存在纯粹思辨的哲学”,但仍然认为《周易》的“太极”说和道家的《老子》的“道”论多少有一些接近于形而上学的地方。黑格尔说:“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是论原则的书,是这类思想的基础。”又说:“据雷缪萨说,‘道’在中文是‘道路,从一处到另一处的交通媒介’,因此就有‘理性’、本体、原理的意思。综合这点在比喻的形而上的意义下,所以‘道’就是指一般的道路。‘道’就是道路、方向、事物的进程、一切事物存在的理性与基础。”[1]自魏晋玄学以来,中国学术界讨论哲学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也常以“太极”和“道”相比附。但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除了《周易》和道家的形而上学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形而上学,即名家(包括“墨辩”学者)的形而上学。《周易》和道家《老子》的形而上学,是一种以儒、道、“道法家”为代表的“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①,也是中国哲学中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形而上学。名家(包括“墨辩”学者)的形而上学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纯粹的形而上学。研究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无论就其内部各家各派比较,还是进行中西哲学比较,将以道家《老子》为代表的“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和以名家为代表的纯粹形而上学比较,都是最好的选择。
一、道家的形而上学:“道”

也因此,在中国哲学中,唯一一个与道家之形而上学的“道”(“天道”)相对的概念(词),很显然不是“太极”,而是“名”,又称“常(恒)名”。称“太极”为中国哲学中与“道”(“天道”)相对的本体论概念(形而上学),是儒家学者和魏晋玄学家提出的看法。“道可道,非常(恒)道;名可名,非常(恒)名”,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二、道家之“道”与名家之“名”的比较
“道”即“天道”。关于“道”或“天道”的特点,学术讨论实繁。1940年金岳霖先生完成的《论道》和20世纪80年代末期张立文先生的《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对此都有最全面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考察。而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则可以说道家《老子》的形而上学是“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而先秦名家的形而上学则是一种纯粹的形而上学。老子的“道”即是“天道”,是“常(恒)道”,无形无名,先天先地,神鬼神帝,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和本根。《老子》第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但这却并非《老子》“道”或“天道”的全部。《老子》第二十一章曰:“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第十四章又说:“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可见,《老子》的“道”(“天道”“常道”“恒道”)又并非绝对的抽象者,并非纯粹的“理念”,故现代新儒家多称其为“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
名家没有专门的“道论”,甚至也没有专门对“名”的形而上学论述,但由其相关概念、命题却似不难看出。“墨辩”学者的《墨经》中的《经上》和《经说上》曾讨论具体的“名”(形式逻辑上的“概念”)。《经上》曰:“名:达、类、私。”《经说上》曰:“名,物,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必止于是实也。”即将“名”(概念)分为最高的类概念、一般的类概念和个别事物的概念③。但从名家最著名的“白马非马”等命题来看,名家对“名”的分类实如道家老子一样,也是将“名”分为一般形式逻辑所说的“名”和形而上学的所谓“常名”(“恒名”)的。
名家的“白马非马”命题,学术界一般皆从形式逻辑上“白马”概念与“马”概念内涵外延的不同来理解。这种理解虽然正确,却存在明显局限,至少没有看到道家《老子》对“名”的分类的意义,因此也就没有看到名家之“名”的形而上学意义。实际上,名家公孙龙等人“白马非马”命题中,“马”已不再是形式逻辑上的“一般的类概念”(类),甚至也不是“最高的类概念”(“达”,即物,动物),而是《老子》所说的“常名(恒名)”。“白马非马”,即是“名可名,非常(恒)名”。所以,“白马非马”命题实际上包含有三种“马”:一是绝对抽象的不可“名”的“常(恒)名”的“马”,二是作为形式逻辑上为“一般的类概念”甚至“最高的类概念”的“马”,三是作为“个别事物的概念”的“白马”。这三者之间正如柏拉图所说三张床或三张桌子的关系。柏拉图认为,世界上有三张床或三张桌子:一张是画家画的,一张是现实的,一张是概念上的床或桌子。画家画的床或桌子是模仿现实的床或桌子,最不可靠;其次是现实的床或桌子,既不完善也不能永久保存,所以也不可靠;最可靠的是概念的床或桌子,作为概念永久存在,是“纯粹理性”或“绝对理念”[3]。对名家的“白马非马”命题,我们也应作如是观,发现其中纯粹形而上学的意蕴。
三、道家和名家形而上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演变与影响
中国哲学史上,先秦诸子中道家和名家的两种形而上学产生的具体时间如何、谁先谁后,没有文献可征,殊难论定。然依理而论,道家“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即为其“道”(“天道”)论,“道”绝对超越而又不离“象”“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还不是黑格尔所说的“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故其产生应早于名家作为“纯粹的理性”或“绝对理念”的形而上学。但至少从老子开始,中国哲学已探索这两种形而上学的交流和融合。《老子》第一章所谓“道可道,非常(恒)道;名可名,非常(恒)名”,将“常(恒)道”与“常(恒)名”等量齐观,即可见其用意。
先秦时期对道家和名家的两种形而上学进行整合的努力,一直不断。儒家《易·系辞上》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把形而上的本体与形而下的阴阳二气、本体论与宇宙生成论联系起来,建构战国儒者的形而上学。《庄子·大宗师》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豨韦氏得之,以挈天地……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这里,庄子认为“道”虽“无为无形”,“在太极之先”,“先天地生”,十分神秘,但却“可传”“可得”,即在形上形下之间——此可谓庄子对道家和名家两种形而上学的整合。
当然,战国时期系统地对道家和名家的两种形而上学进行整合的,当数稷下黄老学者。他们以“道”为世界的本体和本源,以“法”为中介,对道家和名家的两种形而上学进行整合,并形成了两种整合的思路和两个重要的学派:一个是以《管子》学派为代表的“道法家”或“法道家”,另一个是以惠施、尹文为代表的“名法”学派。
“道法家”或“法道家”对“道”的形而上学论述最大的特征,就是将“道”与“法”联系起来,以“道生法”(《黄帝四经·经法》)的命题既确立了“道”的现实社会“法”的形上根据地位,反过来又借助现实社会“法”的权威保证了“道”的这种形上根据地位。接着,他们还进一步依《易传》的思路,更明确地将“道”之“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的“精”“信”,具体化为“气”及其属性。《管子·内业》曰:“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民(名)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谓成德,德成而智出,万物果得。”由此真正完成了先秦儒家《易·系辞上》开创的将形而上的本体与形而下的元气、本体论与宇宙生成论的结合,以更多地讨论形下的社会政治哲学——在“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路上走得更远了。
以惠施、尹文为代表的“名法”学派,在“道生法”的原则下,将“名”“法”等同,把《老子》“道可道,非常(恒)道;名可名,非常(恒)名”中的“常(恒)名”完全取消了,因而也就同时将名家原有的纯粹形而上学完全取消了。《尹文子·大道上》曰:“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大道不称,众有必名。”又曰“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云云,以为“名”即是“法”,“法”即是“名”,“正名”即是“定法”。这就以“道法家”或“法道家”的“法哲学”取代了名家原有的纯粹形而上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惠施、尹文为代表的名家“名法”学派已彻底抛弃了名家原有的纯粹形而上学,完成一次本学派在形而上学上的自我革命。
两汉时期中国哲学对道家和名家的两种形而上学的整合,儒家主要沿袭着《易传》的思路,而道家则基本继承了稷下黄老学派的传统。
魏晋玄学在哲学思想上整体体现为兼综儒道、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特色。但在形而上学上则主要是对先秦道家和名家的两种形而上学进行重新整合。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派,以“无”代“道”,“以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列子·天瑞》引何晏《道论》云:“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王弼《论语释疑》曰:“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老子指略例》曰:“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不温不凉,不宫不商,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这样,何、王二人虽然有时也仍然使用“道”这一概念,但却以“负的方法”,彻底地抽空老庄“道”论中任何“可传”“可得”和“可体”的成分,使之变成了“纯无”——以名家的纯粹的形而上学取代了道家的“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何晏认为“圣人无情”,嵇康主张“声无哀乐”,都是这种形而上学思想的体现。以向秀、郭象为代表的“儒道合派”则持“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自然矣”的“独化论”,虽表面上对当时本体论上“贵无”和“崇有”两派,包括对先秦道家“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和名家的纯粹形而上学都予以了否定,但实际则因为当时思想界普遍流行“浩浩太素,阳曜阴凝”(嵇康《太师箴》)、“元气陶铄,众生禀焉”(嵇康《明胆论》)的“元气”说,故“儒道合派”实际上只是加强了道家“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
而到了宋明理学时期,理学家借佛、道二教的心性学说,继承了儒家原有的以《易》《庸》联结形上、形下而整合道家和名家两种形而上学的思路,以“天命之谓性”、性静情动、心统性情的本体论,建构起理学“道德的形而上学”。但从本质上来说,因为理学家“道德的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乃是人的道德心性与“天道”合一,即所谓“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故可以说理学“道德的形而上学”,乃是一种真正的“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从此以后,以“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为特征的名家的纯粹形而上学就被完全淘汰,放逐出了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领地,“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则确立了它在中国哲学中独领风骚的历史地位。而也正是这种“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影响和形塑了中国哲学和中国人的文化性格。
四、道家和名家形而上学的文化价值及产生的历史根源
中国哲学史上以道家《老子》为代表的“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和以名家为代表的纯粹形而上学,是两种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形而上学。而这两种形而上学从一开始就处于互相纠葛和交融的历史语境之中,并最终形成了“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导地位。可以说,以道家《老子》为代表的“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和以名家为代表的纯粹形而上学,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和人类的思想文化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地位和价值。道家“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代表了中国哲学和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文化特征,也形塑了中国哲学和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性格。名家纯粹的形而上学,则显示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文化中也存在“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代表了中国哲学和中国人的思想文化与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的某些共同之处,为中西哲学和文化的对话、交融、接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和结合点。
历史地看,中国哲学之所以会形成以道家《老子》为代表的“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和以名家为代表的纯粹形而上学,与中华民族在中国五千年以上的文化史或文明史中的多元互动密切相关。中国有五千年以上的文化史或文明史,而根据历史和考古学者的研究,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炎帝、黄帝和东夷等大的氏族或部落群体已经基本形成,而作为后来华夏族主体的炎、黄二族原本居住在今天的陕西境内,后来黄帝族的一支“跟着中条山与太行山逐渐向东北走”,“炎帝氏族也有一部分向东迁移,他们的路途大约顺渭水东下,再顺黄河南岸向东”[4]。最后他们在今冀、鲁、豫三省交界处这一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区域,与东夷族相遇了——由此拉开了中华民族各族群之间互相冲突和融合的序幕。“大汶口文化的绝对年代,据碳14测定,距今6100—4600左右”;“就目前已公布的资料来看……在大汶口文化时期,有一支势力强大居民由东向西、向南,直到今天的洛阳和信阳地区迁居”[5]。而在“大约从公元前2600年至前2000年”,中华民族早期的“民族文化区域”已基本成形,“一些考古学文化往往可以同古史传说中的族系相照应”。
龙山文化分布于黄河下游山东和苏北一带,当是东夷的史前文化;黄河中游的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分布着“中原龙山文化”,它本身又包含后岗二期文化、造律台类型、王湾三期文化、陶寺类型和客省庄二期文化等,应是诸夏的史前文化;长江中游在屈家岭之后是石家河文化,应当是苗蛮各族的史前文化;长江下游杭州湾一带是良渚文化,它可能是古越人史前文化的一支。[6]
而根据笔者的最新研究,自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以来的“诸子出于王官”说,其中的所谓“王官”,在上古三代实际就是一些氏族、部落或方国(酋邦)及其首领或酋长的名字。如“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的“史官”,即是东夷族颛顼氏氏族、部落及其首领或酋长。《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均将“史官”的源头追溯到了颛顼氏的重、黎(重黎)二“子”。《史记·太史公自序》曰:
昔在颛顼,令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
这也就是说,道家哲学“历纪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以自持”(《汉书·艺文志》)的特点,与其说是源于上古“史官”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报任安书》)的思想文化追求,还不如说它更深远的源头乃在于上古三代悠久的颛顼氏特别是其中重、黎(重黎)二系的历史文化之中。
同样,《汉书·艺文志》曰:“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而由《尚书·尧(舜)典》及《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记载,现今可知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礼官”,是尧舜时代担任“秩宗”的共工氏的伯夷——亦是出于共工氏氏族、部落或方国(酋邦)及其首领或酋长。而根据《国语·郑语》“姜,伯夷之后也……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之说,又可知伯夷属于炎帝族,为其中共工氏一族的成员。《汉书·艺文志》在“序”“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之后,接着又“序”名家之学的特点曰:“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故《礼记·乐记》区别二者的特点为“乐合同,礼别异”——长于细致深入地分析事物,以求寻找其中的细微差别,即所谓“钩析乱而已矣”(与今所谓“纯粹形而上学”近似)。所以,我们似也可以仿照上文言道家实源于上古三代悠久的颛顼氏特别是其中重、黎(重黎)二系的历史文化之论,同样说名家与其说是源于上古三代“礼官”对“礼数”的考究,不如说它更深远的源头乃在于上古三代悠久的炎帝族特别是其中共工氏一系的历史文化性格。
而根据《尚书》《史记》等文献记载,先秦诸子中儒家、阴阳家、法家所从“出”的“司徒之官”“羲和之官”“理官”等,也与道家所源出的“史官”一样,亦同出于东夷族的颛顼氏一系;而《汉书·艺文志》所谓“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的“清庙之守”,实际应该是“司空之官”——出于炎帝共工氏之中的“垂”(又作“倕”,即“工倕”“巧倕”)胞族或子部落④。但《史记》《山海经》等上古典籍同时又记载说,上古传说时代的华夏炎黄二族与东夷族各氏族和部落间还存在着广泛的婚姻和血缘关系,已走向了早期华夏各民族及其文化的融合。因此先秦诸子中儒家、阴阳家、法家所从“出”的“司徒之官”“羲和之官”“理官”等,也与道家所源出的“史官”一样,亦同出于东夷族的颛顼氏一系,在思维方式上具有惊人的一致性,都显示为一种“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而墨家和名家的思维方式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都表现为一种纯粹的形而上学的特征——由此也引发了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先秦诸子关系中是墨家源于名家还是名家源于墨家的争论。但炎帝族共工氏由于与帝颛顼一系有着长期的婚姻和血亲的交融关系,故此二族裔在思维方式和思想文化上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和互相交融。黄帝很早即“作”冠冕礼乐、推迎日、祭祀封禅(《世本·作篇》),这些亦皆被名家吸收到他们制定的礼仪制度之中;颛顼氏东夷族的最大特点是“夷俗仁”,而儒家之“礼”的根本精神亦在于“仁”,这显然更多的应该是吸取了东夷族颛顼氏文化的养分;而由炎帝族共工氏“礼”文化演变而来的先秦诸子名家思想,又与儒家的“礼“和法家的“刑”合流为刑名礼法之学,成为战国中后期中国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时代特点。源于东夷族的颛顼氏一系的道家“史官”和阴阳家“羲和之官”,则因其在与炎帝族共工氏的融合中深刻洞悉到各种礼仪制度的本质,而走向了对“恒名”或“天道”的追求以及对世俗社会之“名”或“礼义”的批判。老子贵“无名”,以为“名可名,非常(恒)名”,曰:“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老子》第三十八章)庄子也认为“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礼法度数,刑名比详,治之末也;钟鼓之音,羽旄之容,乐之末也”(《庄子·天道》);仁、义、礼、智,“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庄子·骈拇》)。因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而道家的史官及阴阳家的“羲和之官”,皆属于东夷族颛顼氏的重、黎(重黎)之后,故其深谙阴阳消息之“天道”,以为“人道”之仁、义、礼、智,实皆源于自然之“天道”,故应“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向最高的“礼义”本源回归。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似可以说,先秦诸子中以道家为代表的“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和以名家为代表的纯粹形而上学的矛盾与差别,也是上古三代炎帝族共工氏氏族或部落与东夷族颛顼氏氏族或部落在思维方式和思想文化上的差别与冲突。道家是一直强烈反对所谓“智巧”或技巧的,甚至提出要“绝圣弃智”“绝巧弃利”(《老子》第十九章)和“攦工倕之指”(《庄子·骈拇》)的主张,对源于炎帝族共工氏氏族或部落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文化特别是名家的分析智慧和墨家的技能工巧,采取一种近乎敌视的态度;而名家、墨家则对源出于东夷族颛顼氏氏族或部落的道家、儒家之将“死生存亡、穷达富贵”等社会现象皆视为“命之行也”(《论语·颜渊》《庄子·德充符》)的言行[7],予以明确的“非”之(《孔丛子·公孙龙》《墨子·非命》《墨子·非儒》)。上古传说时代中华民族中炎黄二族与东夷族各氏族和部落的长期冲突和融合,最终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既“道术分裂”,彼此“争鸣”,又互相借鉴和交融的诸子百家之学;而名家、墨家的形而上学与道家、儒家及法家等不同学派之间形而上学上的历史纠结,实际也是上古传说时代以来中华民族各成员间文化基因的一种延续。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