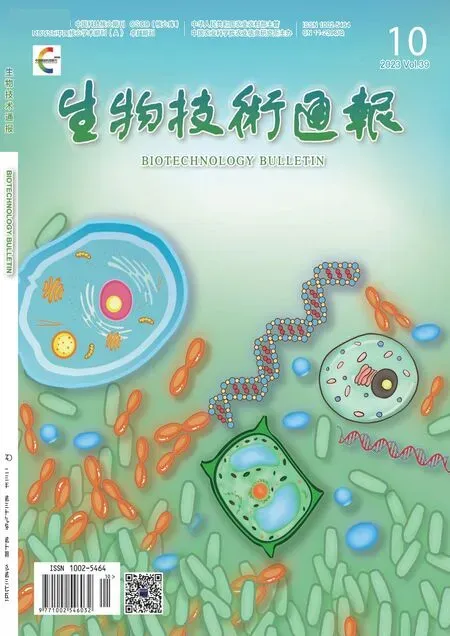观赏植物花斑形成调控机制的研究进展
齐方婷 黄河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花卉种质创新与分子育种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国家花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083)
花色是植物重要的观赏性状,被子植物的花色多样性不仅体现在颜色的多变,还包括形成一些独特的色彩图案即花瓣彩斑(花斑)。花斑一般是指花瓣上不同区域出现的差异着色模式[1],能给花朵增添极大的观赏性。此外,花朵斑部内含物具备吸收可见紫外光的特质,使得花斑在昆虫眼中呈现特异的颜色,能够减少传粉昆虫的搜索时间[2-3],因此,相较于单色花来说,带有花斑的品种在繁衍上占据优势地位,更能吸引传粉者如蝴蝶[4]、苍蝇[5]和黄蜂[6]的注意。而一些植物也可以利用花斑来抵御食草昆虫[7]、防护紫外线以及适应不同的温度[8]。可以说花斑是植物进化、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重要方向,在现代花卉业中具有重要意义[9]。因此,对花斑形成机理的探究尤为重要,目前,色素合成途径研究较为透彻,而花斑的形成还涉及多种发育和环境信号参与,更具多变性和复杂性。已有研究对花斑形成过程中的化学物质组成和分子调控模式进行深入挖掘,就观赏植物花斑的形成提出多种模型和假说,本文对此进行总结归纳,以期促进对观赏植物花斑的深入研究。
1 花斑的分类及遗传规律
1.1 规则型花斑
花斑可分为规则型花斑和不规则型花斑两大类,规则型花斑主要包括脉络状(venation)、斑块(blotch)、点状(spots)、二色(bicolor)、花边(picotee)、星型(star)、花眼(bull‑eyes)以及蜜导(nectar guide)等类型(图1‑a-h)[1],能按照遗传的基本规律进行世代传递。部分植物的花斑性状由单基因控制,在树棉(Gossypium arboreum)[20]和猴面花(Mimulus lewisii)[21]中发现,花斑性状在杂交子代中的分离比遵循简单的显性单基因遗传规律。夏堇(Torenia fournieri)在腹瓣或背瓣表现出的多种着色模式也由单基因决定且通常为显性性状[22],而Kondo等[23]在夏菫的一个品种中发现背瓣白色和紫色株系杂交后,F1花均为背瓣白色带紫边表型(半色系),半色系自交后代中白色∶半色∶紫色的分离比为1∶2∶1,属于不完全显性遗传。克拉花(Clarkia gracilis)中心斑点和基部斑点花朵杂交F1代表现出双斑点表型,F2中基部斑点∶双斑点∶中心斑是1∶2∶1,为共显性遗传[24]。

图1 规则和不规则型花斑Fig. 1 Regular and irregular flower spots
1.2 不规则型花斑
相对较为简单的规则型花斑,不规则型花斑是指花瓣上有非固定的异色散点或条纹,形成园艺学上所谓的“洒金”“跳枝”“二乔”“二色”等(图1‑i-m),在牡丹(Paeonia suffruticosa)[25]、桃花(Prunus persica)[26]和矮牵牛(Petunia hybrida)[27]中发现,转座子(transposons)或小片段插入、甲基化(methylation)和small RNA等均有可能形成不规则型花斑,其花斑性状也可以遗传给子代,但往往具有随机性和可变性,遗传过程不遵循孟德尔定律。此外,病毒感染也会导致不规则型花斑的产生,如病毒感染兰科(Orchidaceae)植物后会出现花瓣坏死、色素不均以及嵌合条纹等现象[28],大丽花(Dahlia pinnata)感染了烟草坏死病毒(tobacco streak virus,TSV)后会出现杂色花[29]。因病毒感染产生的不规则型花斑一般不能通过杂交的方式稳定遗传给后代。
2 影响花斑形成的理化因素
花斑的本质是呈色上的差异,而花色在视觉上的呈现通常是由于色素对光的选择性吸收和花内部结构的光散射性[30],因此花瓣内色素物质的组成和分布是花斑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15]。此外,细胞内环境(液泡pH、金属离子及其络合物[31]等)也影响着植物花斑的形成。
2.1 花瓣中色素的组成和分布影响花斑形成
自然界中,植物花朵的成色主要由类黄酮(favonoids)、类胡萝卜素(carotenoids)和甜菜色素(betalains)三大类色素决定。其中,最为广泛分布的类黄酮是形成黄、红和蓝色系花朵的重要组分,包括花青素(anthocyanins)、黄酮(flavones)和黄酮醇(flavonols)类化合物。花青素主要分为天竺葵素(pelargonidin, Pg)、矢车菊素(cyanidin, Cy)和飞燕草素(delphinidin, Dp)三大类及其衍生色素芍药素(peonidin, Pn)、矮牵牛素(petunidin, Pt)和锦葵素(malvidin, Mv),它们共同组成了从橙红色到蓝色的花色区间。类胡萝卜素决定了花色从黄到橙的变化区间。而甜菜色素目前主要在石竹目中发现,参与黄色系或红色系花朵的形成[32-33]。
色素在花瓣中的不同位置或细胞中差异积累,使得花朵呈现独特的色彩图案。牡丹‘二乔’粉色区域主要积累1种芍药花素衍生物,而红色区域积累2种矢车菊素衍生物和2种芍药花素衍生物[25];克拉花花瓣有斑区积累Cy和Pn,无斑区积累Mv[24]。猴面花[21]、向日葵[34](Helianthus argophyllus)和金鱼草[35]中黄酮醇和橙酮类(aurone)化合物的累积使得花朵靠近花心的部位出现不同于花瓣背景色的白色或黄色斑区。一些兰科花卉(orchids)如大花蕙兰[16]和金黄石斛兰[36](Dendr‑obium chrysotoxum)中花青素和类胡萝卜素在不同花瓣中差异积累并形成了丰富的彩色图案。东方黑种草(Nigella orientalis)花瓣发育早期只积累叶绿素,中期类胡萝卜素含量上调,后期花青素在花瓣特定区域汇聚,共同组成了黄色花瓣带有绿色眼状斑点、紫红色横条纹和飞溅斑纹的复杂图案[37]。
2.2 细胞内环境理化性质改变
花瓣细胞内部条件的改变会导致原本的色素分布出现变化,进而产生新的花色变异。花瓣细胞内pH的变化会使得原本纯色的花朵出现脉络或斑块状花斑,矮牵牛中PH5(P‑type H+‑ATPase 5)和AN1(ANTHOCYANIN1)都能通过促进局部花瓣细胞内部H+的跨膜运输引起液泡内环境酸化,导致了多种花斑突变体的出现[38]。杜鹃花(Rhododendron oldhamii)中也发现红色花瓣上部的紫红色斑块内细胞的pH高于其他部分[39]。除pH变化外,高浓度的Fe3+与山奈酚(kaempferol)类化合物形成的络合物累积是郁金香[40](Tulipa gesneriana)和北海道紫菫[41](Corydalis ambigua)紫色花瓣出现蓝色色素沉积的原因。
3 色素代谢途径关键结构基因影响花斑形成
3.1 结构基因的时空表达影响色素积累
色素物质在花瓣不同区域的定位积累是花斑产生的重要原因,类黄酮的自然合成途径目前已较为清晰[33],因此,花瓣中控制色素物质合成的基因的时空差异表达对花斑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Martins等[24]在克拉花中发现,花发育早期,花斑区域F3′H(flavonoid 3′‑ hydroxylase)和DFR2(dihydrokaempferol 2)表达显著提高,积累Cy,而在发育后期,无斑区中DFR1和F3′5′H(flavonoid‑3′,5′‑hydroxylase)开始表达,并积累Mv,形成较浅的背景色。矮牵牛中CHS(chalcone synthase)在花瓣中的空间差异表达是星型和花边型花斑形成的原因[14,27]。牡丹‘和谐’中一个在无斑区高表达的糖基化基因(UDP‑glycosyltransferases, UGT)PhUGT78A22,使得花瓣有斑区和无斑区中色素的糖基化程度不同,引发花色差异[42]。此外,花青素转运基因(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GST)也会影响花斑的形成,在白色红斑品种的树棉中沉默GaGST后红色斑点减少[43]。亚洲杂种百合中PSY(phytoene synthase)和HYB(β-ring hydroxylase)的差异累积导致了‘Connecticut King’和‘Virginale’花被片上分别出现橙黄色斑块和窄椭圆形斑纹[44-45]。
此外,结构基因的序列差异如转座子或小片段插入会改变其原有的时空表达模式,进而产生不规则型花斑。转座子是指可从一个位置“跳跃”到另一个位置的一段DNA序列,日本牵牛花(Ipomoea nil)Tpn转座子(transposable element of Pharbitis nil)与花斑性状密切相关,在DFR、EFP(enhancer of flavonoid production)和3GT(flavonoid‑3‑O‑glucosyltransferas)中分别发现Tpn1、Tpn13和Tpn10转座子在非编码区以及启动子区域的插入,导致了矮牵牛花瓣斑块或者杂色花的形成[46-48]。康乃馨(Dianthus caryophyllus)CHI(chalcone isomerase)和DFR上的Ac/Ds(activator/dissociation)超家族转座子dTdic1的插入会在花朵上产生白色的斑点或条纹[49]。而在‘二乔’牡丹F3′H编码区的小片段插入,会使得花瓣部分区域花青素积累减少出现杂色[25]。
3.2 结构基因的竞争表达促进色素差异分布
色素物质的合成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结构基因编码的酶作用于同一底物的情况,使得结构基因之间存在竞争表达。在类黄酮代谢途径中,FLS(flavo‑nol synthase)和DFR竞争同一底物柚皮素(narin‑genin),猴面花DFR促进外侧花冠合成花青素呈红色,FLS使得内侧花冠积累黄酮醇变成白色[21]。牡丹‘二乔’双色花中粉色区域FLS的上调表达抑制了花青素的积累[25]。C. trapeziformis兰花唇瓣的斑块中CtrDFR和CtrLDOX(leucoanthocyanidin dioxygenase)的表达上调,CtrFLS表达下调,激活该区域花青素的合成[50]。黄色向日葵的花心中检测到HaFLS1的高表达,促进槲皮素苷(quercetin)和二咖啡基奎宁酸(di‑O‑caffeoyl quinic acid, CQA)的积累,出现独特的UV着色模式[34]。夏堇中,有斑区VwDFR、VwF3′5′H和VwANS(anthocyanidin synthase)的表达量远高于非斑部,使其形成了积累Dp和Cy的黑色斑块,而无斑区中花青素通路在柚皮素处被阻断,只积累二氢槲皮素(dihydroquercetin),呈现黄色[51]。
4 花斑形成中的转录调控机制
在花斑形成的过程中,结构基因的差异表达影响着不同色素物质的积累,其受到多种转录因子的控制,因此转录调控是整个调控网络的核心,已有大量研究揭示了花斑形成过程中的多种转录调控机制,主要包括单个以及多个调节基因直接或间接控制结构基因的定位表达等。
4.1 MYB转录因子调控花斑形成
在色素合成途径中,MYB类转录因子发挥最重要的调控作用,其中,R2R3类MYB转录因子中的S5和S6亚家族能激活色素的合成;而S4亚家族因具备EAR(ERF‑associated amphiphilic repression)和TLLLFR抑制基序,从而负调控色素积累[52];R3类MYB转录因子则是一类花青素合成的抑制子[53]。已有大量研究显示MYB转录因子参与花斑的形成,棉花(Gossypium hirsutum)BM位点(beauty mark)编码的R2R3类MYB基因MYB113编码区的单碱基突变(SNP)导致了花瓣基部斑点的出现[54];夏堇和蝴蝶兰TfMYB1内含子和PeMYB11启动子区域的转座子插入引发了多种着色模式的变化[55-56]。百合R2R3‑MYB转录因子(如LhMYB12、LcMYBSPLATTER、LhMYB19L和LhMYB19S)参与双色、点状、刷痕状、凸起式等多种斑点类型的形成[57-59],其中,LhMYB12的等位基因LhMYB12‑Lat在编码区多了一段核苷酸序列的插入,能够控制飞溅式斑点的形成[60];而LhMYB19L在点状和刷痕状斑点中均能检测到表达,但LhMYB19S仅在点状斑点中表达,推测是因为LhMYB19S相较于LhMYB19L有一段序列的缺失以及若干SNP[58-59]。
MYB转录因子能够通过直接激活或遏制花青素合成途径结构基因的表达来控制花瓣不同区域色素的积累。百合中LrMYB15通过激活LrANS和LrDFR的表达促进凸起状斑点处的色素累积[61]。牡丹中PsMYB30和PrMYB5可以分别与PsANS和PrDFR的启动子结合来激活基因表达,导致花瓣基部出现紫红色斑块[62-63]。除调控花青素合成途径结构基因外,MYB转录因子还可以通过控制类黄酮的分支代谢参与花斑的形成。猴面花的花冠喉部白色区域的形成是因为LAR1(leucoanthocyanidin reductase 1)位点编码的R2R3‑MYB转录因子激活FLS的表达进而合成黄酮醇,而不再积累花青素[21]。向日葵花朵中花心部分主要积累能吸收紫外光的黄酮醇,其在紫外光下呈现黑色,过表达HaMYB111能够激活花心处HaFLS的表达,促进槲皮素等黄酮醇类物质的积累,使得深色花心范围不断扩大[34]。MYB转录因子还可与bHLH(basic helix‑loop‑helix)和WD40转录因子组成蛋白复合物(MBW复合体)激活下游基因的表达,从而共同调控色素代谢途径[64]。彩色三叶草(Trifolium repens)中MYB转录因子RED LEAF和RED LEAFDIFFUSE都是通过与bHLH转录因子JAF13结合,正调控花青素合成促进叶脉斑纹的形成[65]。在百合中LhMYB18和LhMYB6需要与bHLH转录因子相互作用激活DFR的表达进而在花被片上形成斑点[66-67]。紫斑牡丹PsMYB12与bHLH和WD40蛋白组成的MBW复合体直接激活下游结构基因PsCHS的表达促进斑点形成[68]。
MYB转录因子对花青素的正向或负向的调控作用决定了色素物质的有无,不同于纯色花,带有花斑的花朵中不同区域积累的色素并不相同,这需要依靠多个MYB转录因子的协同调控。在金鱼草中,MYB转录因子ROSEA1和ROSEA2决定了花瓣和花蕾的呈色模式,而VENOSA控制上唇瓣脉络斑纹的形成[10,35];在矮牵牛[69]和蝴蝶兰(Phalaenopsis spp.)[70]中也发现了相似结果。克拉花CgMYB6控制背景色的形成,CgMYB1控制斑点处色素积累,CgMYB1在花瓣不同位置的表达分别形成了基部斑点和中部斑点,而CgMYB11和CgMYB12是花青素合成的激活子,它们在花瓣中的差异表达以及基因突变形成了更丰富的色彩图案,如基部“白杯”的产生是因为CgMYB11仅在中上部表达,而花斑基部CgMYB12的等位基因CgMYB12W出现过早的终止密码子进而不积累花青素;而中部条纹的出现是因为CgMYB11在上部表达,CgMYB1在基部表达,而花瓣中部CgMYB12出现缺失,只检测到350 bp的外显子,最终呈白色[71-73]。
近年来,一些研究深入挖掘了多个MYB转录因子共同控制花斑形成的调控机制,Ding等[74]在猴面花中提出了一个由2个MYB转录因子构成的“反应-扩散”模型,该模型由花青素激活子NEGAN(NECTAR GUIDE ANTHOCYANIN)和抑制子RTO(red tongue)组成,NEGAN激活RTO的表达,反之RTO能抑制NEGAN的活性,这两个转录因子在花瓣中动态扩散并相互拮抗,在猴面花蜜导中形成了分散斑点。后续Zheng等[75]又在猴面花中鉴定出了一个NEGAN的同源基因MYB5a,发现它也能与RTO形成类似的模型,进而调控花斑形成。这种“反应-扩散”模型通过基因之间的此消彼长来形成斑点,这也导致形成的斑点大小不一,呈现一种动态模式。东方黑种草中激活子NiorMYB113‑1负责在花瓣中上部积累花青素,而抑制子NiorMYB113‑2能在花瓣背景色和花青素之间形成隔绝带,控制色素在花瓣上积累的区域和边界,最终构建出复杂的花斑图案[37]。
4.2 其他转录因子调控花斑形成
虽然参与色素合成的结构基因是整个花斑形成中的关键基因模块,但是花朵的着色模式是伴随着发育进程逐步建立的,并受环境因素影响,因此一些参与发育进程的转录因子能够直接或者上游调控花斑的形成。MADS‑box(MCM1、AGAMOUS、DEFICIENS和SRF‑box)转录因子中的A类(APETALA1)、B类(PISTILATA和APETALA3)、C类(AGAMOUS)和E类(SEPALLATA)是花器官发育的ABCDE模型的重要组成[76-77]。近年来,MADS‑box转录因子被报道参与花朵差异着色模式的形成,在卡特兰(Cattleya hybrid)中,与唇瓣的发育和分化有关的AP3(APETALA3)‑1/2/3/4s和AGL6(AGAMOUS‑like 6)‑2s也参与了上下唇瓣的差异着色[78]。百合中抑制花被片中B类MADS‑box基因TrihDEFa(DEFICIENSa)的表达,会使得花瓣由红变白,斑点变淡或消失[79]。矮牵牛中单独沉默C类MADS‑bos基因pMADS3时,深蓝色花瓣中部分区域的色素积累被抑制,出现蓝白双色的表型[80]。瓜叶菊中鉴定出了2个在白斑区高表达的C类MADS‑box转录因子ScAG(AGAMOUS)和ScAGL11,它们相互作用形成二聚体,并通过直接结合ScF3H1(flavonoid 3‑hydroxylase 1)和ScDFR3的启动子来抑制花青素的积累,最终形成花斑[13]。
发育基因除了直接影响色素合成途径结构基因的表达外,还可通过控制MYB基因的表达进而层级调控花朵着色模式的形成。在蝴蝶兰‘Sogo Yukidian’中发现斑点仅在侧萼片中出现且由PeMYB11控制,该基因受到一个变异的AGL6类MADS‑box转录因子OAGL6‑2调控,OAGL6‑2可与OAP3‑1结合形成蛋白复合体,能够在改变花瓣下侧萼片结构的同时上游调控PeMYB11的表达进而形成斑点,说明色素的差异定位积累可能是发育基因产生新功能的结果[81]。夏堇中CYC2(CYCLOIDEA)和RAD类(RADIALIS‑like)转录因子RAD1在背侧花瓣中特异性表达,其可直接结合MYB1基因,抑制该基因在此区域的作用,从而影响花青素合成途径下游结构基因的转录,最终建立了夏堇背腹不对称的着色模式[22,82];而当TfCYC2的外显子上插入一个Ty1/Copia‑like型LTR(long terminal repeat)逆转座子TORE2时,会导致TfCYC2和TfRAD1表达下降,白色背侧花瓣腹侧化并开始着色[23]。拟南芥(Arabidopsis thaliana)中TCP4(TEOSINTE‑BRANCHED1/CYCLOIDEA/PCF 4)能够直接结合叶绿素合成途径结构基因PORB(protochlorophyllide oxidoreductase)和DVR(divinyl reductase)或者转录因子SOC1(SUPPRESSOR OF OVEREXPRESSION OF CO 1)的启动子来降低花瓣远端叶绿素的积累,促使tcp2、tcp3、tcp4、tcp5、tcp10、tcp13、tcp17 七个基因突变体的远端花瓣的叶绿体转化为白质体,绿色花瓣尖端呈现白色[83]。
5 花斑形成过程中的其他调控机制
目前,对于花斑的研究多集中于对转录因子的挖掘及其转录调控机制,观赏植物复杂的颜色图案模式的形成需要依靠多种调控手段的层层协作,并不局限于转录调控,而是包含了转录后调控、翻译后调控、基因序列差异以及甲基化等不同水平的调控机制(图2)。

图2 花斑形成的多种调控机制Fig. 2 Multiple regulation mechanisms of the flower spots formation
5.1 转录后调控
转录后调控(post‑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是指真核生物对转录出的mRNA进行加工,在转录后水平对基因表达起到重要的调控作用[84],如可变剪接(alternative splicing)、小干扰RNA(small interfering RNA, siRNA)和microRNA(miRNA)等均被发现能够调控观赏植物花斑的形成。可变剪接能够产生多种mRNA,翻译出不同功能的蛋白,但也可以引起翻译的提前终止,使蛋白改变或丧失原有功能[85],因此,在花朵着色过程中,可变剪接极易产生不规则型花斑。跳枝桃就是因为可变剪接使得ANS在红色花中有两种不同长度的转录本,而在白色花中仅检测到一种转录本[86]。
small RNA(sRNA)是指一类小片段的不编码蛋白的RNA分子,能够通过引起基因转录后沉默来参与花斑形成[87]。在日本龙胆(Gentiana scabra)[88]和秘鲁三角梅(Bougainvillea peruviana)[89]的双色花中都检测到了sRNA在花朵白色部位的大量累积。sRNA又可进一步分为siRNA和miRNA,植物内源性siRNA来源于长的双链RNA(dsRNA),双链siRNA与Argonaute(AGO)蛋白形成基因沉默复合体RISC(RNA‑induced silencing complex)降解互补配对的靶mRNA从而抑制基因表达[90]。siRNA引起的基因沉默能够调控花瓣的差异色素沉着,遗传过程中的染色体重排导致了矮牵牛星型和花边型的花中存在两个头尾串联的CHS‑A,它们能够产生21 nt的siRNA并降解花瓣白色区域CHS‑A成熟mRNA,引起色素的差异空间积累[14]。金鱼草花冠中一个含有Am4′CGT(chalcone 4′‑O‑glucosyltransferase)反向重复序列的SULF优先表达,产生sRNA抑制Am4′CGT的表达,使得蜜导更为醒目,以此吸引授粉者[91]。Liang等[92]在猴面花花冠中发现显性的YUPL(YELLOW UPPER)等位基因能够产生靶向MYB转录因子RCP2(reduced carotenoid pigmentation 2)的siR‑RCP2,抑制花冠中的类胡萝卜素积累,而RCP1可能位于YUP的上游抑制siRNA的产生并在蜜导中特异表达。这一发现也证明siRNA可能通过控制MYB转录因子参与花斑形成中的层级调控。
miRNA是一类18-25 nt的非编码小分子,来源于具有碱基对折叠结构的初级miRNA(pri‑miRNA),成熟的miRNA组成RISC复合体,抑制靶基因的表达[93]。miRNA‑mRNA模块参与植物着色模式的形成,miR156能够靶向SPL(SQUAMOSA)基因的启动子序列,而SPL转录因子通过破坏MBW复合体的稳定来抑制花青素的合成,在拟南芥[94]和芍药(P.lactiflora)[95]中发现,miR156‑SPL模块能够影响花青素在拟南芥茎秆或侧枝上的定位积累。现有研究显示,miRNA也影响花斑的形成,蝴蝶兰品种‘Panda’中PeMYB7和PeMYB11控制花瓣紫色斑点的形成,而靶向这两个MYB基因的miR156g和miR858在非斑点区域积累,抑制了花青素的合成[96]。百合LhMYB12是花青素的激活子,在很多双色花中均能检测到其表达[57],Yamagishi等[97]发现miR828在百合双色花中的下半部分的积累高于上半部分,并且通过靶向LhMYB12的mRNA降解其转录本积累,导致花被片的下部呈现为白色。牡丹‘岛锦’中鉴定出2个可能参与双色花形成的miRNA(miR858和miR156a‑5p),推测其可能通过调控PsMYB12来影响花瓣中花青素的差异积累[98]。
5.2 翻译后调控
泛素化(ubiquitination)是常见的翻译后修饰,是指泛素信号被26S蛋白酶体识别,从而降解靶向蛋白质的过程[99]。泛素化参与植物的多种代谢途径并影响花斑的形成,牡丹‘和谐’E3泛素连接酶PhRING‑H2(ring domain‑containing protein)与PhCHS相互作用,通过降解PhCHS抑制花发育后期花瓣中色素的积累,参与斑块的形成[100]。菊花‘Noble Wine’(NW)粉色舌状花上带有紫色斑纹,与纯紫色品种相比,NW中编码F‑box(泛素化途径中特异识别底物的蛋白)的基因高表达[101]。
5.3 DNA甲基化
DNA甲基化是指在甲基化转移酶(methyltrans‑ferase)的作用下,基因组的核苷酸对的胞嘧啶上结合一个甲基基团,形成5‑甲基胞嘧啶(5‑methylcy‑tosine),植物中甲基化位点一般为对称的CG位点、CNG位点和不对称的CHH位点3种,甲基化能够在不改变DNA序列的情况下,通过改变DNA或组蛋白(histone)的结构或稳定性来调控基因表达[102],甲基化往往会使得基因失去原本的功能,主要参与不规则型花斑的形成。文心兰(Oncidium spp.)CHS基因上游启动子区域的甲基化导致基因失活,使得蜜导区域丧失了红色的色素斑点[103];牡丹‘岛锦’bHLH1的甲基化是其花瓣呈红白双色的原因[104];而桃花杂色花蕾的形成是因为LDOX的甲基化降低了基因活性,花青素的合成减少[105]。紫斑牡丹花瓣中PrF3H和PrANS启动子处于高度甲基化状态,而随着花瓣发育,其在斑部区域的甲基化水平显著降低,非斑部依旧维持较高水平,进而导致了花青素的差异积累[106]。
6 展望
花斑促进了自然界中花色表型的多样化,显著增加了花卉的观赏和经济价值,同时也折射出被子植物在适应环境变化和提升生存能力过程中的进化趋势。因此,探究花斑形成的机理对生物多样性形成和生物进化具有重要意义。已报道的转录调控机制主要围绕类黄酮代谢通路,MYB转录因子仍然是大多数植物花斑形成的关键转录因子,而一些发育类基因也逐渐被鉴定出具备调控花青素合成的新功能。虽然现今的研究无法提出一个完整的具有普适性的分子调控网络,但在不同植物中发现的多种调控模式极大地促进了花斑研究的进程(图2)。新的转录因子挖掘、转录因子的层级调控、生物代谢的协同选择以及套用数学模型(位置效应和“反应-扩散”等)解析花斑形成[107]都是后续研究的诸多方向,有望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解析并完善观赏植物花斑形成的分子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