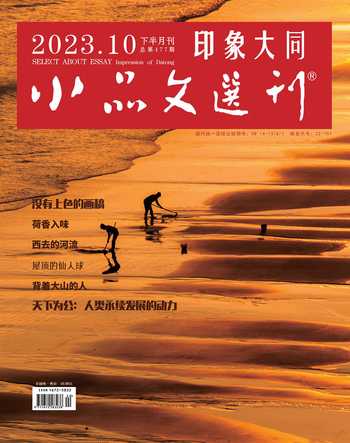弱水
卜布

水从脑际涌来,泊在记忆的弦上。一个穿绿衣服的女孩,提着一双红色的塑胶凉鞋光着脚站在大堤上,与之呼应的是堤岸外的一片绿,一大片沉静自如的绿,仰卧于波涛之上,身体曲线随波涛起伏。阳光穿过尘埃,照在上面,光耀之后,才能看清那是一个母亲的形象,她凝视着女孩,眼神里是疼爱,宠溺,以及忧伤。
这忧伤让我一次次从梦中惊醒,随之而至的,是那一场刻骨铭心的记忆。记忆之初,女孩和我坐在棉田的坝上,蟋蟀,狗尾巴草和沟渠里水的流动,谱成一曲田野的歌。长年的湖风湖水,让女孩皮肤并不白皙,但久居青山绿水间,性情也就上善若水,为人温温柔柔,从不发愁,不动气,脸上总是挂着微微笑。村里的爷爷奶奶将她比喻为湖里的“江猪儿”。“那是湖里的神仙,身姿矫健,转体灵活,很美,很爱笑,跟你一样。”女孩并没有见过“江猪儿”,自打她出生,“江猪儿”就没有出现过。这并不让她觉得十分遗憾,人对从未相识的事物缺乏情感。但那刻她拨弄狗尾草的手势有些迟缓,原本明亮的眼睛也犹如蒙了一层薄如蝉翼的湖雾。
湖面上,是很容易生成雾的。尤其是水汽充盈的夏季。以至于没有谁能真正看清这片水域。天地间总是一派烟波浩渺,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流淌。视野的远方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没有山,连芦苇也长成波浪的模样,与地平线连在一起。村庄、油菜花、棉花、在棉田里劳作的农人、湖心里撒网的渔人,都仿佛是湖心中飘荡起伏的黑点,不,是珍珠,大湖孕育出来的珍珠。
女孩的村庄,就是大湖孕育出来的一粒。村子里布满了水,一刻不歇地静静流淌,水稻、西瓜、蔬菜、谷仓就在水的滋润里涨了起来,随之一起生长的,有清晨、露水、花骨朵、星空,还有女孩和她的小伙伴们。她们在水的怀抱里长大,白天,择水而戏,夜晚,枕着水流的声音入眠。
和她们一起住在大湖里的,还有翠鸟、白头鹎、棕背伯劳、苍鹭、池鹭、牛背鹭、董鸡和水鸡,它们在芦苇丛中筑巢,产卵和繁殖。
还有鱼!许许多多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鱼。它们和大湖的亲近程度更甚于女孩。不,鱼和湖本就是一体的。
女孩最爱拿起妈妈做的鱼捞子,做爸爸的小跟班,划船出湖打鱼。
船是简朴的,不过五六米长,一米多宽,木制的船舱和甲板,头形如弯月微微上翘,船底平滑便于水流通过,船尾呈斜面内收,船舱上扎着竹篾编制的弧形船篷,船篷上蒙着油布。女孩喜欢站在甲板上,看阳光落在波光粼粼的河面,朵朵发亮的浪花在脚下跳跃。间或也会遇到撑着划子出门劳作的同道人,他们穿蓑衣,戴斗笠,将三四米长的竹篙往河里使劲一撑,又或坐在木筏子的舱内,双手拿桨,一前一后地用力一推一摇,划子往前走,人也朝前看。他们或扬臂撒网,或采摘菱藕,撑起一个家。
此时的大湖是那么和蔼,像个含笑的好脾气的妈妈,耐心地配合着天上彩霞的炫技。先是漫天金芒,她就变成奇大无比的黄色绸缎。倏尔变成浅浅的银红,她就变成稀薄的像遮盖新娘子的粉红面纱。再过一会,许多碎锦似的杂色小片跑了出来,她便送它们随着淡宕的微风向天尽头去了。
待到五颜六色都褪了,四围如雨的虫声冒了出来,银盘般的月亮也从湖里钻了出来,女孩和爸爸的谈话声便渐渐低了下去。他们轻摇着船,拨弄着浪,把网一抛一撒,湖心里长出一朵朵“莲花”,花瓣一层裹着一层。等“莲花”渐隐,网就被收了回来,一起来的,还有大鱼,小鱼,螺蛳,蚌壳。除却大鱼,其他的都是不能要的。爸爸说,大湖是有规则的,任何不守规则的人都会受到惩罚。女孩不知道是什么规则,但爸爸说的肯定是对的。她小心翼翼把网里的小鱼择出来,轻捧着放进水里,银白的月光一股脑倾泻在她的脸上,泛出光。“哗哗,哗哗”,那是湖水撞击两岸的拍浪声,还有湖畔芦苇、杨柳被风拂动后发出的声响。夜归的打鱼人,披着月光,不慌不忙,划着小木船登岸,将船停稳,掬一捧水饮了,带着劳作一天的收获回家去。
什么时候,这一切变了?等她从中学毕业回来,爸爸再也不愿意去大湖打鱼,说鱼小,煮出来还有股煤油味。
变了的何止是鱼的味道,整个大湖,都变了。湖水定是不能喝了,从里到外,都已然混浊发黑,还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柴油味和农药味。站在大堤上,女孩想起爸爸曾经说过的话:“不守规则是会被惩罚的。”
那个六月,村里的劳力又被抽调到防洪大堤。沙包,卵石,一层层地被码到堤上。一车车穿着橙色救生服的抗洪勇士和“抗洪救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大红横幅标语,在绿色棉田间的乡村公路上呼啸而过。村头的喇叭好长时间都不唱流行歌了,播音员扯着嗓子喊着这样那样的提示:“别睡太熟,别下田,随时准备转移……”管涌、穿堤、内渍,这些专业术语早已不陌生了,防洪堤上的战事时不时会传到村里,夜晚偷溜回来的男人告诉自家的堂客:“真到了那天,可别记挂着你的坛坛罐罐,带上孩子和钱就行了。”
女孩坐在棉田里,她手里捏着一根狗尾草,却忘记了跟它玩耍。她微仰着头,侧着耳朵,仔细,认真,紧张,似在等待什么,又像是在害怕什么。当她终于听到由远及近的摩托车鸣叫,单车摇起的丁零声,人群的奔跑声,急促、慌乱的哭喊声,噌地就从地上跳了起来,来不及穿上脱掉的红色凉鞋,甚至来不及拍掉粘在屁股后头的枯草。她在漫野的棉花地里使劲地奔跑,炙热的大地灼伤了她的脚板,棉花树一排排从身边倒退,风,汗,快要跳出喉头的心脏……她拐进村头,闯进一户一户人家:“决口了,倒垸了,快点逃。”变调的声音在村子上头回旋,散发着招魂般的死亡气息,恐怖多于悲伤。
当大湖一点一点逼近村子,女孩只能站在防汛楼顶,感受她的愤怒,狂躁。木制的门脱离了原来的禁锢冲向远方,书柜、床、桌、椅、板凳打着转转地追了出去,原以为坚不可摧的红砖瓦房,发出一声剧烈的哀鸣,轰地倒了下去。蘆花鸡跳上棉秆柴垛瑟瑟发抖,与它对峙而立的是吐着芯子的水蛇。还有她的小黄!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它还没有学会游泳,浮浮沉沉中来不及吠叫,惶然地用那双流泪的眼睛寻找往日爱护它的主人。她多想如往日一样,把它搂在怀里。她的嗓子突然哑了,失去水分的嘴唇干裂,让她无法再张嘴说半句话。
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对立。
女孩和她侥幸从水荒里逃出的乡亲们回来,捡起砖瓦、檩条、门窗,再度重建自己的家园。这一次,他们把防汛楼、防洪堤都建得特别牢靠。但大湖却突然瘦了下去。还是站在大堤上往下看,原本一望无垠的水面,变成了沙漠,许多树木已经枯萎了,湖床上长满了荒草,随处可见晒干的蚌壳、螺蛳,失去生命的小鱼。她穿着钉子鞋在干涸的湖滩上走,也只能踩出浅浅的干干的脚印。这个季节,正是雨水丰沛的时候,实在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却又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女孩已然走到了湖心,这大概是她怎么也想不到能够抵达的深处。她茫然地环顾四周,只有沙,被风吹起来的沙,一阵阵,一层层地朝她而来。水呢?她在寻找,找了好久,终于,她看到了。那是一口浅浅的狭长的水塘,在太阳的照耀下发出光,像眼泪。
没有鸟,它们似乎比人类更早预知灾难,早早地从这里迁徙了。
救救大湖!
发出这声呐喊的,是女孩,是女孩的爸爸,是揪紧了心的湖乡人。从开始的一两个人,到后来的三四个,五六个,一个群体。
有些奇迹真是不可思议的。就像人类当初用钢钎、铁锨、锄头、箩筐,在大湖造田,筑坝,安营扎寨,创造了一场专属于人类的文明一样,如今他们要以断臂求生的决心与意志,再度打响一场战役。
这是一个又苦又累又不讨好的活。如果没有一种信仰的力量,或者说一种理想主义的奉献精神,很难想象这一场坚守他们是如何完成的。平均每天,他们要围绕大湖走上四五个小时,和他们相伴的,是寒冷的风,潮湿的雨,被湖风掀起的不那么好闻的空气,还有一不小心就找上来的血吸虫。他们倔强地守望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有大湖。
我终于再度看清大湖的真相,那分明是澄明之境,那里面似乎啥也没有,又似乎有万物,婆娑的树,葳蕤的草,悠悠的云,風儿在波纹上写诗,白鹭在湖心中弹琴……这分明是一条天性善良的河流,简单,纯粹,温驯。这无辜的湖,我们竟然将她归咎于灾难的祸首。
一只神兽出现在我们面前。它远远地站在草丛里,用一双晶莹的透亮的眼睛和我们对视,我想走近它,它却飞一样地逃进了树林。
我从守望者的口中得知了它的神奇身世,相对始终保持微笑的“江猪儿”,这头像马、角像鹿、颈像骆驼、尾像驴的奇兽更具神秘色彩。在口口相传的神话故事里,它曾是姜子牙的坐骑,为兴周灭纣立下赫赫战功。而在历代帝王的眼里,它是吉祥兽,驯养于皇家园囿,“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有关于它在洞庭之滨的传说,大概可溯源到战国时期,典籍《墨子·公输》记载:“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而它在历经气候变化,人类活动,清朝末期外国联军的洗劫后绝迹中原,更成为人们心中的痛楚。
这个神奇的物种,它们是怎么样找回家的?
“人心好不好,动物都知道。”带我去看麋鹿的向导这样讲,他是本地的渔民,也是保护大湖的志愿者。禁渔政策对他而言,是有伤害的,“那又怎么样呢?欠下的债总是要还的。”他扫一眼一望无垠的大湖,领着我环行在这条岁月大湖的边上,地面松软,走在上面有种绵绵的舒适感。我感谢他在环行之前,给我递过来一双黑色的带齿的塑胶套靴,这是湖乡人的必备,才二三十块一双,环走大湖却是相当实用。我的向导也穿着这样一双套靴,他已年过六旬,但身子骨还相当硬朗、结实,一双大脚板踩得很响亮,又很快,我一路小跑才能追上他,上了船。
向导对两岸的麋鹿很熟悉。他每日早晨六点入湖,晚上七点返回,数次穿行在河道中,都能碰到鹿群在河床边缘喝水或者休息。那一年,湖水漫过了大堤,水退后,一头小麋鹿的角被网兜住,是他帮它解困,送它回到了芦苇丛里。“起初只有几只,现在小崽子们都长成大鹿了,”他说,“比牛都大。”
似乎为了印证他的话,船没开多久,一头大麋鹿就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它似乎已经习惯往来的船只,即便我们离它不过四五百米,它也还在那里慢悠悠地吃草。我没有靠近打扰,有些事物知道它在,知道它安好,就够了。
风忽然大了起来,是从大湖面上吹来的风,很清凉地掠过耳边,将我的头发吹起,一些飞舞,一些抚摸我的脸。大湖温柔地待在那里,她略显衰老的面容,满含泪水的眼眸,依然深情地凝视着我们。当我的目光和她接触,我看见了一幅画,那些苍老的岁月,那些相爱、相杀、相随的故事,那些守望洞庭的孤勇者,在画卷里发出耀眼的光。在光里,我还看到一个人,他站在一条河流的面前,神情严肃,眼神深邃。我顺着他的眼神望过去,那是一片苍茫的天地之外。那过于遥远的地方,我是看不见的,也许一辈子都无法抵达的,譬如说这水的源头。但我知道,天下之水,岂止大湖。
事实上,战役开始的地方,也远不止大湖。大江的治理似乎开始得更早一些。
我看见了传说中绝迹多年的“江猪儿”。当漫天的霞光纷纷落在波浪上,一些活泼的身影在浪花里跳舞。先是又窄又長的嘴巴像鸭嘴兽般向前伸出,又像鸟喙一样微微向上翘起,再是那隆起的额头,它们的鼻孔竟然长在头顶上。随后,它们又露出像一弯银辉闪烁的新月般的三角形的背鳍。“嘘哧,嘘哧”,它们自由畅快地呼吸,时不时喷出一股亮晶晶的水珠子,这飞溅的水珠被朝霞或夕阳照亮,宛若一道斑斓的彩虹。
我开始相信老人们所说,这是江中的神仙。在晨雾刚刚散去的浪头上,它们对着日出的方向出神地仰望,像一群朝圣的精灵,那仰望的姿态,是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渴望。而在那些月光如水的夜,光影流转的江面上,一个个优美的身体跃出了水面,朝着月亮一仰一仰拜月的姿势,更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神圣和敬畏。我想起了我的女孩,那个与这精灵同名的她,为江湖哭泣的她,是否有曾看到。
我闭上眼睛,像是醒着,又像是睡去。在恍惚间,我听见女孩在低吟浅唱,不,不是女孩,是大湖,是一汪清水,像外祖母带着宋家嘴方言的摇篮曲。在熟悉而又遥远的旋律中,那青蓝的、蔚蓝的、深蓝的液体朝我涌来,开始是一种无法阻挡的浩荡,后来渐渐变得平缓,轻轻漫过我的脸,钻进我的耳朵、眼睛、嘴巴、鼻腔,进入我的大脑乃至我身体的最深处。那些往事,宛若水草,在若水的抚慰下,渐渐松弛,清晰,最终,完全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选自《湖南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