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成:获得尊严,比出名更重要
罗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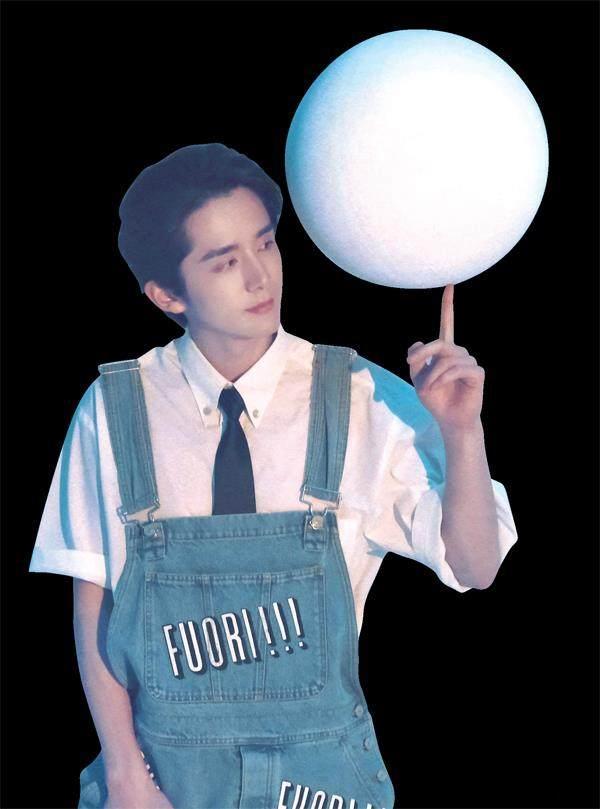
必须得往前走
我喜欢小李子(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刚出道的时候,特别希望自己将来能成为像他那样的演员,什么类型都演,而且都演得好,多厉害!
入行后慢慢发现,那样的演员身后是需要一个好的创作体系支撑的,但很多条件在当下并不是都具备的。那段时间我有些迷茫,给自己放了假,出去旅行,找很多事做来填满时间,但始终屏蔽不了心里那个追问的声音。消沉了一阵,最终也没找到答案,但不能一直那么下去啊。最终我确定了一件事,就是不能停滞不前,必须往前走。
以前我演《你好,旧时光》里的男主角林杨,剧里爸爸说过,当你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候,就争取把当下的一切做到最好再说。道理我早就听过了,但直到真正这么做了后,才体会到它的有效。那些短期的、一点一点具体的努力,能够帮我克服一种更大的虚无感。
像《县委大院》一开始找过来的时候,我的时间不巧排满了,没办法接。结果之前定好的一个拍摄项目推迟了,空出了一段时间,我就赶紧联系剧组,想看看还有没有机会。
当时我在三亚工作,孔笙导演打来视频电话,我们聊了8分钟。其实没聊太多,我一见到前辈就有些放不开,孔导话也不多。之后就定了让我演小林,也没有试戏。孔导跟我说,小林是男二号,我当时拿到的幾集剧本里,戏份确实很少。没想到随着拍摄进程推进,小林的戏越写越多,他的成长成为剧里的另一条重要故事线,演这个角色也成了我挺有满足感的一件事。
不太焦虑的大学时光
我一直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出道算是比较顺利。开始拍戏的时候我还在中央戏剧学院上大三,音乐剧专业。回想大学时光,真是特别快乐的几年。
现在大家的焦虑好像来得特别早。刚上大学,甚至更早的时候,对未来的担忧已经开始了。但我上大学时的氛围跟现在不太一样,没那么多年少成名和一夜爆红,所以整体都不太焦虑。
大三下学期,我遇到了《你好,旧时光》,当时试戏演的是男主角林杨坐在学校门口,跟同学说自己喜欢的女孩几点吃早餐,几点出门,还有几分钟会出现在视野里。中戏有反复排练的传统,演完一遍,我说可以换种方式再演,一共提供了三四种表演方案。可能导演觉得孺子可教吧,就被选上了。
刚知道被选上演林杨时,我有点纠结。当时我们已经开始准备排练毕业大戏《为你疯狂》,定了我演男主角。戏里有踢踏舞,我特别喜欢,练了好长时间。
但排大戏不允许请假,人生就一次毕业大戏,我不想放弃。结果被经纪人骂了一顿,说,选上了你不去演?
播出后,《你好,旧时光》反响不错,还有件幸运的事就是,毕业大戏最终我也参与了。因为班里一个同学不演了,我就得到机会顶替他演了一个小角色。大戏里有个设计,需要一个人从阳台上翻下来,单手抓着栏杆晃几下,再落到地上翻跟头。一套动作下来挺危险的,所以没人愿意上。老师让我上,我因为害怕也不太愿意。老师说,红了是吧?耍大牌啊?我赶紧说没有没有,我翻,我翻。
表演就像搭房子
差不多就是我在中戏上学那几年,影视行业的大环境慢慢发生了变化。有了“流量”的概念,类型片也多了起来。年轻演员很多都是演类型片出道的,我也拍了不少。
类型剧有个特点是会突出角色的人设,比如,很高冷,跟谁都不说话;或是很帅,头发必须梳成什么样。它是很极致的一个东西,生活中基本看不着,必须从表演上设计。比如,《大宋少年志》里的元仲辛,为了表现他的“皮”和“痞”,我会设计挠头、翻白眼这样的习惯动作,还有计谋落空时的惊愕慌乱。
但逐渐我发现,拍戏其实是有很多即兴部分的。总想着设计好的东西,脑子里容易有杂念。一直到前几年,我觉得在类型化的角色上已经到了某种极致,老那么演也没什么意思,感觉自己没有进步。好吧,那就举起锤子,把它砸碎。
正好那时我接拍了《天才基本法》,我演的裴之很帅气,又是数学天才,其实也是有偶像剧味道的。但我观察发现,演员们的表演方式都很生活化。像子枫,大家都说是天才少女,聪明有灵性。佳音哥(雷佳音)就不用说了,戏特别好。还有演老师的骁哥(王骁),演我爸爸妈妈的演员耿乐老师和刘琳老师,都长期演现实主义题材,能不着痕迹地带出所有细节。我就跟着他们的节奏走,放松下来,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手和环境上。只要反应合理,很少有演不对的时候。
我的声乐老师以前说学声乐就像搭房子,把积木一块一块搭起来,再把它推倒,就达到境界了。我觉得表演也是这样,我不敢说自己现在在“推倒”,也不敢说这种方式一定正确,但我觉得可以去尝试,还年轻嘛。
尊严比挣钱、出名都重要
我始终认为从事某个行业,得到应有的尊严是最重要的,比挣钱、出名都重要。大家认可表演这个行业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一种形式,我觉得这就是尊严。
近两年我也上了一些综艺。原本不太习惯这些,因为中戏教出来的老观念,觉得拍戏的时候好好拍,不拍戏时最好藏起来,保持演员的神秘感。但后来我发现时代变了,除了拍戏还得“营业”,要多露出。
刚上综艺时,我挺容易紧张的,觉得比演戏累多了。我性格特别较真,加上当时又有新人心态,做游戏也要认真,想让自己看起来很有用,结果反而显得有点用力过头。之后我想,我确实不是那种很有梗的人,那就不强扭。在节目里想说话就说,不想说就不说,更放松一些。“营业”或许是必要的,不过我也无法把自己彻底变成另一个样子,最后就选择折中,保持一个大致的平衡。
就像我马上要拍的《艰难的制造》里的男主角,他在干事业的过程中会触碰到很多社会规则,会有一些无奈,自身也因此有一些改变,但他内心最坚持的东西始终都在。我总觉得,王阳明说的“知行合一”特别难,但如果哪天真能做到,人可能就自由了。
静静//摘自人物微信公众号,本刊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