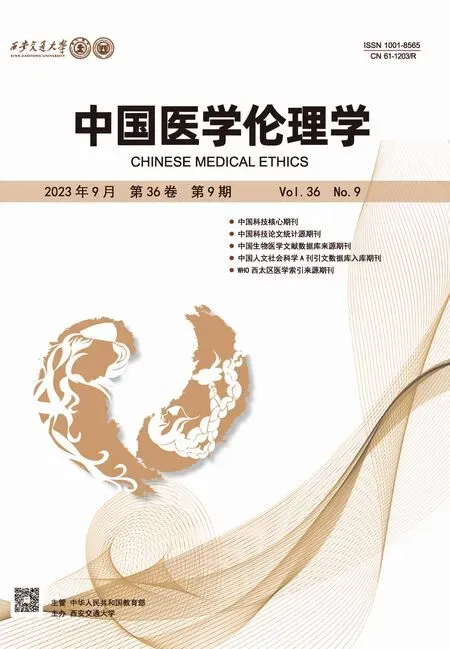精神医学医患关系模式探讨
——基于萨斯-荷伦德模式*
胡 蝶,郑亚楠,2,尹 梅,张维帅**
(1 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1;2 赣南医学院心理学系,江西 赣州 341000)
医患关系模式是对不同情形的医患关系进行概括或总结的基本式样,主要作用在于描述医患之间的技术关系和非技术关系[1],其回答了医患双方之间如何互动,如何自处的问题[2],为医生的行为和临床决策提供理论指导,对预防纠纷,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具有一定意义[3]。目前广为人知的医患关系模式是最具代表性的美国学者萨斯和荷伦德根据医患双方在诊疗决策中的能动性大小提出的三种医患关系模式,即主动-被动型、指导-合作型及共同参与型[4]。然而萨斯-荷伦德模式只涵盖了一般医学情境,较少涉及特殊医学情境,需结合不同专业特点,进一步探讨特殊情景下的医患关系适用模式。
精神医学由于患者所患疾病的特殊性,其医患关系是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探讨精神医学医患关系适用模式对于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及精神医学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1 构建精神医学的医患关系模式
1.1 精神医学的特点
精神医学是医学的一个分支,是涉及精神健康相关内容的一门学科。随着20世纪中后期健康范畴的扩大及医学模式的转变,心身疾病愈加受到关注,精神医学的范畴从狭义的精神病学范畴延伸到广义的精神卫生,其研究内容不仅包括精神障碍疾病的发生、发展、诊疗及预防等,还包括精神卫生相关内容,即研究心理及社会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5]。但不同于其他医学分支,精神医学具有敌对性、强制性及社会性特点。其他医学分支中的患者多为自愿前往医院就诊,其目的是为了促进自身疾病的康复及健康情况的改善;而精神医学中,由于患者所患疾病的特殊性及精神医学污名化等原因,仅有少数患者是自愿来医院就诊[6],多数是由其家属或社区强制入院,可能对医生或医院产生不信任甚至敌对心态,因此精神医学具有敌对性特点。此外精神医学中存在如重型精神分裂症等无法辨认或控制自身行为的患者,在其疾病发作期间,可能存在伤人或伤己行为。为保障患者或他人生命健康安全,医院会对其采取保护性约束等强制措施,因此精神医学具有强制性特点。同时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不仅取决于医患之间,更取决于社会认可,因此精神医学还具有社会性特点。基于上述特点,构建精神医学医患关系模式有其必要性。
1.2 构建精神医学医患关系模式的意义
构建精神医学医患关系模式对精神医学医患关系、医疗服务质量、精神医学的发展及医患关系模式的深入研究方面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如下:①指导临床决策,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在精神医学领域医患关系模式对于医务人员的行为和临床决策具有指导意义,有助于精神医学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②缓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由于精神医学领域存在医患双方立场不一致或患者不信任甚至敌对医务人员的情形,精神医学医患关系模式的构建有助于指导医务人员面对不同情境及不同特点的患者有针对性地选择相应的医患关系模式,进而更好地预防医患纠纷,从而促进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③促进精神医学发展。本文所探讨的精神医学医患关系模式指出由于社区精神医学的发展,在社区康复的患者应更适用于共同参与型,因此该模式的构建有利于社区精神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对于精神医学本身发展也具有一定意义。④促进医患关系模式的深入研究。本研究所探讨的精神医学医患关系模式具体结合了精神医学的特点,为医患关系模式的深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2 精神医学医患关系模式的探讨
2.1 以萨斯-荷伦德模式为基础的医患关系模式
在萨斯-荷伦德模式中,根据能动性大小,患者可被分为三类:难以表达自己主观意愿的患者、能配合治疗但对医生诊疗措施提不出异议的患者、能主动参与诊疗决策的患者。这三类患者涵盖了医学中大多数情境,因此该模式对于精神医学医患关系模式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可被运用至精神医学情境中,具体如下:
共同参与型,即医患双方共同参与诊疗方案的制定和讨论等,医患双方地位平等。在该模式中,医生的责任在于“帮助患者自疗”。该模式适用群体的特点为能够表达自己主观意愿且能够积极配合医生、具有参与的能力及意愿,如轻度心理障碍患者、具有一定精神医学知识背景或长期反复发作的精神障碍患者。由于精神医学还具有社会性特点,因此该模式还适用于在社区进行康复的患者。共同参与型模式的使用能够提高医患双方的积极性,有助于患者早日回归社会,并促进社区精神医学的发展。此外由于精神医学的治疗方案涉及心理治疗,不仅需要医生的指导,更重要的是患者的主动参与,医患双方需共同努力才能帮助患者康复,因此精神医学中共同参与型应成为普遍适用模式,但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有主动参与意愿及能力的患者较少,该模式目前在中国成为普遍适用模式仍是一种理想状态。
指导-合作型,即在该模式中,患者具有一定主动性,能够积极配合医生诊疗,但对于医生提出的诊疗措施等提不出反对的建议,医生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在该模式中,医生的责任在于“告诉患者做什么”,该模式适用群体的特点为能够表达自己主观意愿且能配合医生的患者,如处于疾病恢复期的精神分裂症等患者。目前,国内较多患者在寻求心理咨询时希望得到医生的具体指导建议,被动接受,而非主动参与诊疗[7],因此该模式相对于共同参与模式的使用占比更多。该模式的使用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积极性,促使患者向共同参与模式发展。
主动-被动型,即医生处于主动地位,患者处于被动地位并以服从为前提。在该模式中医生单方面向患者发生作用,医生的责任在于“为患者做什么”,适用于无法表达自己主观意愿但能被动配合医生的患者,即处于疾病发作期但不存在伤人或伤己行为的患者,如昏迷或注射镇静剂后的精神障碍患者等。该模式的适用有助于发挥医生积极性。
2.2 建议增加“保护-约束型”的医患模式
萨斯-荷伦德模式虽涵盖了大多数医学情境,对于精神医学医患关系模式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在精神医学领域中,由于患者疾病的特殊性,为维护患者健康,存在保护性约束及其他强制性措施,虽根据患者的能动性大小可将其匹配至主动-被动模式中,但其中涉及伦理及法律等问题,属于精神医学特有情境,在一般医学情境中较少涉及且探讨不够深入,对于临床指导意义较为局限,因此有必要将该情境从萨斯-荷伦德三模式中细分出来。萨斯及荷伦德提出的三种医患关系模式中医患之间的立场基本是一致的,即患者愿意配合医生,积极治疗疾病,医生想要帮助患者恢复健康。而在精神医学情境中,存在医患间对立冲突的情况,如存在有部分患者出于病耻感或正处于精神障碍疾病发作期不愿或无法前往医院就诊,出于患者健康考虑,最终由其家属或社区强制送往医院。在此情形中,患者会抗拒医院及医生的帮助,不积极配合、反抗,甚至对医院及医生“怀恨在心”。基于此,笔者团队结合精神医学的特点建议增加一种医患关系模式,即保护-约束型。
保护-约束型即由于患者处于精神疾病发作期,无法辨认或控制自己的行为,可能存在伤人或伤己行为时,医生为保护患者或他人的生命健康,对患者实施保护型约束。此时,医患之间的模式可称为保护-约束型医患关系模式。在该模式中,医生的责任在于“为保护患者及他人生命健康,强制为患者做什么”,适用于无法表达自己主观意愿且不能配合医生的患者,即处于疾病发作期且存在伤人或伤己行为的患者,如处于疾病发作期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或躁狂症患者等,因此该模式的使用具有阶段性,当患者恢复主观意识或不存在伤人或伤己行为后,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转为其他类型医患关系模式。该模式的使用有助于保护患者及他人生命健康安全。
保护-约束型模式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①在适用对象方面,共同参与型与指导-合作型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能够表达自己主观意愿的患者,而主动-被动型与保护-约束型的适用对象都是无法表达自己主观意愿的患者,但区别于主动-被动模式,前者适用于无法表达自己主观意愿但能被动配合医生的患者,而保护-约束模式适用于无法表达自己主观意愿且不能配合医生,并存在伤人或伤己行为的患者。②在医生责任方面,保护-约束型模式中,医生的责任在于“为保护患者及他人生命健康,强制为患者做什么”,其与其他三个模式的区别在于“强制”二字。基于此,保护-约束型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医生的行为应符合伦理四原则,不得以该模式为己谋私利,伤害患者生命健康利益,且事先应征求意识清醒时的患者或其家属知情同意。③在医患立场方面,其他三个模式中医患双方的立场均处于一致,双方目的皆为促进疾病的康复和健康的改善;而在保护-约束型模式中,医患双方立场可能是对立冲突的,医生的目的和行为都有利于维护患者及他人健康,而患者由于疾病发作且存在伤人或伤己行为时,其行为举措不利于健康,患者可能对医生产生敌对反抗心理,尤其在医生对患者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后。有研究发现,不同患者对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态度不一致,甚至在医护人员对患者实行保护性约束措施后,对医护人员产生敌对、恐惧等情绪[8], 因此二者立场并非一致,存在处于对立冲突立场的可能。④在伦理与法律方面,不同于其他三种模式,保护-约束型由于涉及强制性行为,在临床适用过程中,医务人员应注意保护患者的相应权利,不违反伦理原则及法律规定。
3 “保护-约束型”医患关系模式在临床中的实践
基于保护-约束型的特点,该模式在临床实践中涉及伦理及法律等诸多问题,因此有必要对该模式的实现路径进行详细阐述,具体如下:
3.1 评估精神患者的行为能力及意识状态
判断患者是否丧失主观意识,无法辨认或控制自己的行为是保护-约束型模式的实施前提。建议由2名及以上的精神科医生对患者的行为能力及意识状态进行评估,若家属或处于清醒状态下的患者对评估结果提出异议,应再纳入1名或多名精神科医生组成评估组对患者的行为能力及意识状态等重新评估[9]。该举措有利于减少患者家属或医生出于个人利益损害患者自主权的情况发生。
3.2 征得知情同意
为保护患者的健康及相关权益,有必要在保护约束等措施实施前征得患者的知情同意。在征得知情同意的过程中涉及以下几个关键问题:①谁享有知情同意权。②如何进行告知。知情同意权的享有与使用与患者是否具备享有该权利的能力相关,即患者是否具备知情同意能力。由于保护-约束型所适用的对象为丧失主观意识且不能配合医务人员并存在伤人或伤己行为的患者。从法律角度出发,其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者,但无民事行为能力者并不完全等同于无知情同意能力者[10-11]。Grisso等[12]研究发现精神分裂患者即使处于疾病发作期亦具备一定知情同意能力。不同精神症状患者及处于精神症状不同阶段患者,其知情同意能力亦有不同[13],因此不能简单根据患者的民事行为能力来判断患者的知情同意能力。对于有知情同意能力者,其未必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应由其本人对保护约束等措施的使用与否进行知情同意;对于无知情同意能力者,其应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者,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可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即可由其家属等进行对保护约束措施的知情同意。关于知情同意能力的评定一般由精神科医生进行评定。若患者具有知情同意能力,应在其疾病发作前,提前告知患者保护约束性措施的必要性、目的及影响后果等内容,征求患者的知情同意。在其疾病发作过程中,若其丧失知情同意能力,自主权由其家属代理,因此当医务人员对患者采取保护性约束等措施时,应将相应情况详细告知患者家属,并征得知情同意[14]。若事前未征得患者或其家属的知情同意,但患者可能存在伤人或伤己行为时,此时不能一味地尊重患者的自主权,应先强调对健康权的尊重,保护患者及他人的生命健康,在约束过程中随时注意观察患者的情况,完善约束细节,事后对患者进行解释说明,加强对约束患者的观察及心理疏导,提供人性化服务,保障约束患者的身心健康,将约束伤害降至最低[8]。
3.3 规范干涉权的使用
疾病发作期的患者由于其无法辨认或控制自己的行为能力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医务人员不得利用此情境为自身谋私利,损害患者权益。医院应注重医务人员医德医风的提高,加强对干涉权的规范限制。对于干涉权的使用应遵循医学伦理四原则及相应的技术规范。当患者意识清醒后,应及时停止对患者的约束措施以保护患者权益及身心健康,对于滥用权益的精神卫生人员,应追加法律责任[9]。此外仅依靠医务人员医德医风的建设,难以有效防范干涉权的滥用。建议强调伦理委员会在保护-约束模式临床应用中的监管作用。如遇干涉权滥用行为或保护-约束模式运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由主管医生或副主任以上专业医师提出建议,征得患者监护人同意,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批准。
3.4 退出机制
保护-约束模式临床应用的过程中较为关键一点即何时何境取消或退出对于患者的“保护-约束”。由于保护-约束模式运用的重要指标为患者存在伤人或伤己行为,因此判断其是否应退出该模式的指标亦为患者不存在伤人或伤己行为。同时对患者的保护时间每次不应超过4小时,若超过4小时,应由医生重新评估,再次作出决定[15]。此外保护-约束模式的应用过程中,可能存在干涉权滥用的情况,比如,若患者已不存在伤人或伤己行为,应向其他模式转换,然而医院或医生出于利益关系,蓄意不停止或退出对患者的“保护-约束”。建议加强伦理委员会的监管作用,确保能够及时取消或退出该模式。此外一些地方的医疗机构存在着扩大化的被精神病问题,本身并不患有精神障碍疾病的个体被他人出于利益等各种因素造谣或污蔑存在精神问题,并被采用非法手段送入精神病医院长期关押。对于此类被精神病患者,其已被强制入院、实施“保护-约束”措施,建议使用“三查”机制,即入院前审查(由精神科医生评估患者行为能力及意识状态),入院后立即审查(伦理委员会监管),住院过程中不定期审查评估(每保护时间超4小时,重新评估决定),并在发现后及时对相关人员追加法律责任,以防范干涉权的滥用。
4 小结
本研究结合精神医学的特点,以萨斯-荷伦德模式为基础,探讨了精神医学医患关系适用模式,介绍了共同参与型、指导-合作型及主动-被动型在精神医学情境下的具体应用,并基于精神医学特有情境,建议增加保护-约束型模式,该模式在适用对象、医生责任、医患立场、伦理与法律方面均不同于其他三种模式,且由于该模式在临床实践中涉及伦理与法律诸多问题,该模式在临床具体运用中需注意评估精神患者的行为能力及意识状态、征得知情同意、规范干涉权的使用并具有退出机制以确保患者能够及时取消或退出该模式。该模式的探讨对于精神医学医患关系、医疗服务质量、精神医学的发展及医患关系模式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