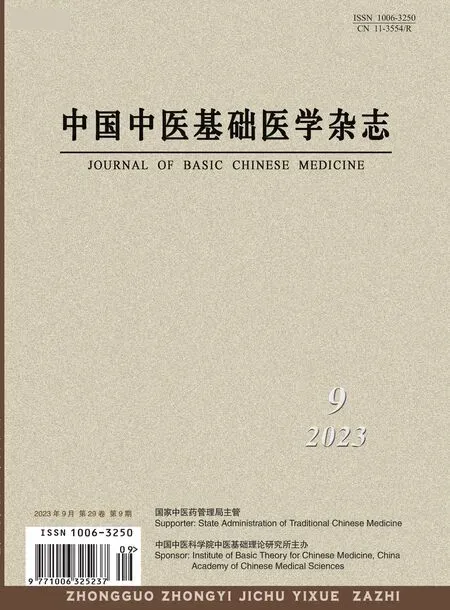陈纪藩从“肺脾相关”理论辨治系统性硬化症❋
郑雪霞,刘连杰,刘敏莹,刘小宝,钟晓琴,吴 琪,林昌松△
(1.广州中医药大学,广州 510405;2.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州 510405)
系统性硬化症(systemic sclerosis,SSc)是一种累及皮肤和内脏的多系统结缔组织病,最为显著的临床表现为皮肤增厚变硬,因此亦称之为硬皮病。该病特征为慢性炎症伴受累组织不同程度纤维化、外周和内脏血管闭塞,晚期常累及消化道、肺、心脏和肾脏等重要器官。目前尚无控制病情的治疗方法,仅有针对器官特异性表现的相关治疗推荐,治疗方法有限,长期疗效不佳[1]。陈纪藩教授系广东省名中医,第三、四批全国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陈纪藩教授从“肺脾相关”理论出发,提出“培土生金”法治疗SSc,临床取得较好疗效,现将其经验介绍如下。
1 肺脾相关理论概述
肺脾相关理论是中医辨证论治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从五行属性上,脾属土,肺属金,培土能生金。脾胃为后天之本,主运化水谷,气血津液生化之源。脾胃健运,精气得以上输于肺,肺气方能充盛。从经络起源循行上,肺经起于中焦脾胃,受中焦脾胃之精气鼓舞推动。肺脾同属太阴经,同名经脉同气相求[2],交于肺经中府穴。肺与脾经脉相通,由此加强脏腑之间交通联络的方式。从营卫生化运行上,《灵枢·营卫生会》曰“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卫之气来源于饮食水谷,先由脾胃化生,后由肺气输布。肺脾二脏相辅相成,以助营卫二气生成运行。肺脾在生理上的密切联系,为临床应用“肺脾同治”“从脾治肺”提供了理论依据。
2 基于肺脾相关理论SSc的病机
中医学中并无“硬皮病”相关病名及概念,现代根据其发病特点和临床症状,将其归为中医“皮痹病”范畴。有关皮痹的论述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痹论篇》言“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以秋遇此者为皮痹……皮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肺”。严用和《济生方》曰“皮痹之为病,应乎肺,其状皮肤无所知觉,气奔喘满”[3]。所描述症状与现代医学SSc的皮肤表现和肺纤维变高度符合。
《素问·五脏生成篇》曰“肺之合皮也,其荣毛也”。“肺主皮毛”理论对SSc的治疗具有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从脏腑形体关联性来看,肺与皮毛关系最大,皮病可从肺论治。然李东垣强调“脾胃一虚,肺气先绝”[4],认为肺病源于脾胃虚弱不能养肺。当代名老中医如邓铁涛教授、范永升教授均认为SSc的中医论治,应从肺脾而入[5-7]。陈纪藩教授认为肺脾两虚为SSc的中医核心病机,可从以下多个维度进行解析。
2.1 营卫失调是发病的重要因素
《灵枢·本脏》云“血和则经脉流行,营覆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营卫调和能保证机体皮肤、肌肉、筋骨和关节行使正常功能。《素问·逆调论篇》云“荣气虚则不仁,卫气虚则不用,荣卫俱虚则不仁,且不用”。《类证治裁》明确指出“诸痹…良由营卫先虚,腠理不密,风寒湿乘虚内袭,正气为邪所阻,不能宣行,因而留滞,气血凝涩,久而成痹”[8]。提示营卫失调为SSc皮肤麻木不仁、肌肉失养无力的重要因素。而营卫来源于水谷精微,其生成运行与肺脾功能关系密切。肺脾虚弱则营卫失调,皮肤肌腠失于濡养,风寒湿邪乘虚而入,最终发为皮痹。
营卫失调是促使风寒湿邪侵袭肌表的根本原因,也是助长病邪向内传变的重要因素。SSc素体本虚,外邪缠绵经久不去,内舍肺脏,则出现短气、咳嗽、咳痰等症。SSc皮毛失养,腠理开泄失调,寒邪稽留,久而引起阳虚,则出现畏寒明显、雷诺现象,或手指僵硬、难以屈伸等寒胜阻滞证候。
2.2 肺脾虚弱是发病的内在原因
《傅青主女科》言“肺衰则气馁,气馁则不能运气于皮肤矣;脾虚则血少,血少则不能运血于肢体矣”[9]。皮毛与肺脏相表里,受肺气熏泽。SSc肺气虚弱,无法充分濡养皮毛,出现皮肤变硬、感觉减退和毛发生长受限、脱落等临床症状。
SSc日久还可出现皮肤深层组织纤维化,造成永久性关节周围挛缩,累及相关肌肉,引起肌病。绝大部分SSc患者存在肌肉骨骼症状,表现为肌无力、肌萎缩[1]。此外,SSc患者常见口唇薄而紧缩,张口受限、口裂变小。《素问·五脏生成》云“脾之合肉也,其荣唇也”。肌肉为脾胃所主,由脾胃化生水谷精微所滋养。脾之华在唇四白,脾胃精气显露于口唇周围,精气不足则见唇缩。由此反映脾虚也是SSc的内在病因,非独肺虚而已。
2.3 土不生金是SSc肺脾两虚的病机关键
《类经·藏象类》云“脾主运化水谷以长肌肉,五脏六腑皆赖其养,故脾主为卫”[10]。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之气支持五脏六腑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脾胃健运则正气充足、卫外有权[11]。
陈纪藩教授认为土不生金是SSc肺脾两虚的病机关键。因SSc患者常见脾胃虚损证候,几乎所有的SSc患者均可出现胃肠道症状,出现吞咽困难、胃轻瘫、消化不良、便秘、腹泻等表现[1]。脾胃功能虚弱,水谷精微运化无力。脾土为肺金之母,母病及子,脾虚则肺气宣发不足,水精无法四布到达周身四末,出现皮毛肌肉失养证候。
3 基于肺脾相关理论SSc的治法
3.1 肺脾同治,调和营卫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出“脾主营,肺主卫”[12]877,强调营卫二气与肺脾脏腑功能的密切关系。调补肺脾可兼顾调和营卫,从而顾护腠理肌表、抵御外邪入侵。因此陈教授认为在SSc的治疗中,调补脾肺应贯穿疾病始终。
SSc素体肺脾亏虚,营卫不固,早期风寒湿外邪侵袭肌表,引起营卫不和。《素问·痹论》认为“其留皮肤间者易已”,故应在健脾益肺基础上祛除邪气、调卫和营。中后期,疾病迁延不愈,营卫两虚,正虚邪恋,《素问·痹论篇》言“病久而不去者,内舍于其合也”,当以调补肺脾、顾护营卫为主,以扶正祛邪,先安未受邪之地。
3.2 从脾治肺,培土生金
陈纪藩教授取“虚则补其母,补母则子安”之意,临床常以“培土生金”法治疗SSc。“培土生金”法是五行相生、肺脾相关理论实际应用的体现。“培土生金”法亦称为“补脾益肺”法,是指通过调理脾胃以达到补益肺气的一种治法[13]。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记载“培土生金”法的实践运用,如《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的麦门冬汤及《千金》生姜甘草汤、《血痹虚劳病脉证治》的黄芪建中汤。隋唐时期,“培土生金”法相关理论得到补充完善。宋金元及后期,“培土生金”法得到更多运用和发展,如宋朝《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参苓白术散[14],金元时期《内外伤辨惑论》的补中益气汤[4],至今仍为现代广泛应用。
《石室秘录》有言“治肺之法,正治甚难,当转治以脾。脾气有养,则土自生金”[15]。陈教授认为培土健脾能助气血生化,润泽肌肤,充养肌肉;同时有益肺气,以助肺脏宣发,发挥“熏肤充身泽毛”的生理功能。另一方面,SSc患者常见气机失调,出现吞咽困难、胃痛、反酸等脾胃升降功能失常的症状。而肺金具有肃杀、收敛、变革的特性,调理肺气、扶持肺金从革之性,有助脾胃斡旋气机。因此“培土生金法”能兼顾肺脾虚弱,达到金土互济的效果。
4 基于肺脾相关理论治疗SSc的方药
4.1 补中益气汤培土生金,兼顾调和营卫
陈纪藩教授认为补中益气汤具有肺脾同治、气血双补,兼顾调和营卫的功效,临床应用该方加减治疗SSc常取得较好疗效。补中益气汤是“培土生金”法的典型方剂,首见于李东垣的《内外伤辨惑论》,“黄芪(劳役病热甚者一钱),甘草(炙以上各五分),人参(去芦),升麻、柴胡、橘皮、当归身(酒洗)、白术(以上各三分)”“夫脾胃虚者,因饮食劳倦,心火亢甚,而乘其土位,其次肺气受邪,须用黄芪最多,人参、甘草次之。脾胃一虚,肺气先绝”[4]。方中君药为黄芪,主入肺脾二经,具有健脾补肺之功。黄芪、人参、白术、炙甘草健脾益气、固护卫表,当归养血和营。少量升麻、柴胡佐助升阳,同时具有解表祛邪作用。
该方在临床使用中应根据病人情况做一定调整。如人参常用党参代之,阴虚火旺明显者用太子参代之。升麻、柴胡、陈皮应少少用之,常用3~5 g,取其清扬上升之意。陈纪藩教授根据原方剂量,认为方中黄芪应重用,以补益肺气、充养皮毛和固表防御。临床常用剂量为30 g至60 g,如用至45 g以上,当予先煎。一是增加药物的补益之性,二是增加药物的有效成分溶出。现代研究表明,黄芪具有双向免疫调节的作用,在治疗自身免疫疾病方面具有疗效[16]。黄芪的主要有效成分黄芪甲苷可改善SSc动物模型皮肤纤维化程度,抑制成纤维细胞细胞外基质的过度生成,调控TGF-β/Smad3/Fli1通路减轻SSc原代成纤维细胞过度纤维化的表型[17]。
4.2 取象比类,以皮治皮
陈纪藩教授取象比类“以皮治皮”,喜用桑白皮、地骨皮、牡丹皮等入肺经的皮部药物治疗SSc。用意有三:一有宣发、清透皮毛之意,二有引药入肺经之用,三有调理肺气之效。欧阳恒教授团队亦发现“以皮治皮法”能改善系统性硬皮病患者的临床及实验室指标,包括皮肤硬度积分、最大齿距、最大指距、TGF-β1、TGF-β2、IgG、IgA、IgM、C3和C4等[18]。
4.3 辨证论治,用药精专
SSc临床症状多样,常需临床辨证加减。风湿痹痛者,常用桂枝、鹿含草等草木药舒经通络,乌梢蛇、全蝎等动物药活血止痛。外邪犯肺者,出现短气、呼吸困难、咳嗽咳痰等症,可用桔梗、炙麻黄等宣肺化痰。胃阴虚者,可加用石斛、玉竹等滋生津液,加用五指毛桃益气且不伤阴;兼有胃痛、反酸者,加用乌贝散,以海螵蛸合浙贝制酸止痛。脾肾阳虚明显者,出现畏寒、肢冷症状,加用炮姜、鹿角胶、鹿角霜、巴戟天和菟丝子等,以补肝肾、益精血、壮阳气。其中,鹿角胶为血肉有情之品,为补益阳气之上品,且有软坚之功效[19]。据《本草纲目》对鹿茸的记载“头者诸阳之会,上钟于茸角,岂可与凡血为比哉”[12]1243。鹿茸为补益阳气的上品,但因其昂贵、难得,陈教授以鹿角胶、鹿角霜代之。鹿角霜为鹿角熬制鹿角胶后的骨渣,用量须比鹿角胶大,如常用剂量为15~30 g。但鹿角霜需先煎30分钟,方能取得一定效果。
5 医案举隅
病案举例:患者,女,27岁。患者外院确诊系统性硬化症及间质性肺炎2年余。
2019年3月13日初诊。症见双手指尖及前臂皮肤紧绷感、麻木不仁,皮肤稍变薄,提捏困难,双臂上举受限、下蹲困难,觉皮肤牵扯感,颜面多发淡红色皮疹,伴色素沉着,另有气短、畏寒肢冷,腹胀、反酸、呃逆、心慌。纳眠可,小便频,夜尿1次,大便溏烂,日1~2行。月经规律,月经量少,经期3~4天。查体:硬指,双前臂、手指皮肤僵硬,不能提捏,雷诺现象(+),面具脸(-),伸舌稍受限,色淡红,苔白微腻,脉弦细滑。中医诊断:皮痹;西医诊断:系统性硬化症。中医辨证为脾肺不足,气血亏虚。从2017至2019年规律服用醋酸泼尼松 7.5 mg qd、来氟米特 20 mg qd及补钙、护胃等对症治疗,保持原西医方案不变。在此基础上加用补中益气汤治疗,处方:黄芪30 g,党参15 g,白术、当归、柴胡、地骨皮、桑白皮各10 g,陈皮5 g,炙甘草、升麻各6 g。7剂,每天1剂,水煎至200 mL,饭后分次温服。
2019年3月27日二诊。皮肤症状基本同前,天气变动受风寒后出现全身散在皮疹,脱发明显,气短、乏力,四肢活动较前灵活,时有反酸烧心、呃逆,晨起恶心干呕,纳眠可,二便调,舌淡红苔薄,脉沉弦。西医方案维持不变。考虑患者期间复感风寒湿邪,风寒入里,加强扶正祛邪、壮阳驱寒,在原方基础上加上鹿含草20 g、巴戟天15 g,处方:黄芪30 g,巴戟天、党参各15 g,鹿含草20 g,白术、当归、柴胡、地骨皮、桑白皮各10 g,陈皮5 g,炙甘草、升麻各6 g。30剂,每天1剂,水煎至200 mL,饭后分次温服。
2019年4月29日三诊。患者遗留颜面部、前胸散在红疹,四肢、躯干红疹基本消退,雷诺现象明显,双前臂、手指皮肤较前柔软,四肢活动较前自如,仍有脱发,纳眠可,小便调,大便溏,日一行,无余明显不适。舌淡红,苔薄白,脉沉滑。西医方案维持不变。考虑二诊处方治疗有效,续上方,处方:黄芪30 g,巴戟天、党参各15 g,鹿含草20 g,白术、当归、柴胡、地骨皮、桑白皮各10 g,陈皮5 g,炙甘草、升麻各6 g。30剂,每天1剂,水煎至200 mL,饭后分次温服。
2019年5月29日四诊。患者颜面、前胸红疹较前减少,伴有色素沉着,双前臂皮肤增厚,皮肤绷紧感减轻,期间时有头痛、牙痛,胃脘时有胀满感,纳眠可,小便可,大便烂。舌暗红,苔黄腻,脉虚数。西医方案维持不变。考虑患者风寒已祛,原方温补,渐现虚热、血滞之象,去巴戟天,加牡丹皮15 g。处方:黄芪30 g,党参、牡丹皮各15 g,鹿含草20 g,白术、当归、柴胡、地骨皮、桑白皮各10 g,陈皮5 g,炙甘草、升麻各6 g。30剂,每天1剂,水煎至200 mL,饭后分次温服。
2019年6月26日五诊。患者头面及前胸部散在皮疹减少,前胸部见色素沉着,双前臂皮肤自觉较前丰满、柔软,可稍提捏,偶有晨起恶心干呕,纳眠可,小便调,大便烂,舌暗红,苔黄腻,脉虚数。西医方案维持不变。考虑患者现无明显虚热之象,去牡丹皮。处方:黄芪30 g,党参15 g,鹿含草20 g,白术、当归、柴胡、地骨皮、桑白皮各10 g,陈皮5 g,炙甘草、升麻各6 g。30剂,每天1剂,水煎至200 mL,饭后分次温服。
2019年7月24日六诊。患者头面少量散在皮疹,胸部皮疹消退,少量色素沉着,双前臂皮肤绷紧感减轻,皮肤可提捏,活动后自觉气短,无恶心呕吐,纳眠可,二便调,舌淡红,苔薄白,脉弦滑。西医方案维持不变。考虑原方有效,气短加大黄芪用量以补中益气。处方:黄芪45 g(先煎),党参15 g,鹿含草20 g,白术、当归、柴胡、地骨皮、桑白皮各10 g,陈皮5 g,炙甘草、升麻各6 g。30剂,每天1剂,水煎至200 mL,饭后分次温服。
随访患者4月,症状未见反复,脸部红斑已大致消退,双前臂及手指皮肤绷紧感明显减轻,雷诺现象少发,恶心呕吐偶发。
按:五脏相关是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有机结合的理论体系,在临床医学辨治中有重要指导价值。本案患者为SSc合并间质性肺病,属慢性疾病但持续进展。该患者出现皮疹、皮肤绷紧增厚、短气和乏力等肺气不足、营卫失调现象,并见四肢肌肉乏力、反酸呕吐、大便溏烂等脾胃虚弱证候。抓长期主要病机为肺脾两虚、气血不足,故执“补中益气汤”一方不变,随证加减。抓住主要矛盾,以“培土生金”为大法,结合祛风除湿、温阳散寒等扶正祛邪,证候随之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