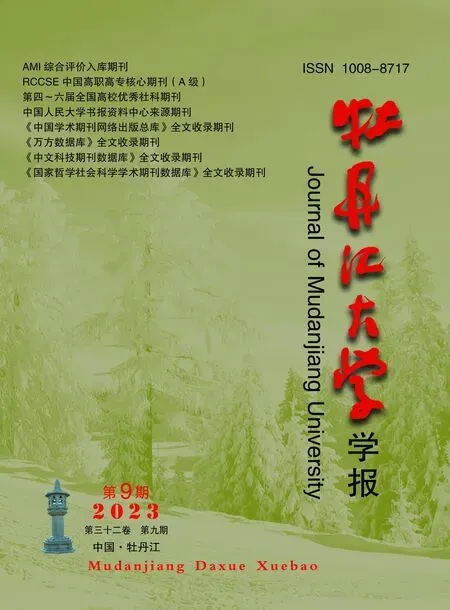论《远山淡影》的个体创伤叙事策略
徐佳宁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石黑一雄的处女作《远山淡影》在形式与内容方面皆糅合其初步的创作主张与艺术风格,作者放弃宏大叙事转而聚焦平凡普通的人物个体,人物各不相同的创伤体验实际又影射背后某种普遍层面的心理现实。本文立足叙事策略与叙事内涵两个方面,主要借助不可靠叙述、二项对立、多元视角等叙事学理论,探究文本主要人物个体创伤的不同形态、即悦子在个性与母性冲突中的分裂体验,绪方在个体与集体矛盾中的他者体验,景子由家庭到社会的复杂创伤体验,进而发现溢出战争、移民等具体创伤成因背后的深层规律:个体存在为权力话语困惑的普遍心理现实。
一、 不可靠叙述:悦子在个性与母性冲突中的分裂体验
《远山淡影》讲述二战后移民英国的日裔妇女悦子对往事的回忆,悦子借小女儿妮基探望自己的契机,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回忆起早年在日本长崎的战后生活,其特别提到曾结识的佐知子母女以及两人不融洽的亲情关系,直到故事接近尾声事实真相才浮出水面,读者发现原来这对母女即为悦子与其大女儿景子的投射。换言之,在众多的人物身份选择中,石黑一雄首先以一位母亲为叙述者,借助其不可靠的叙述引导读者窥见了人物悦子在个性与母性冲突中的分裂体验,至于该心理创伤的由来,则主要源自权力话语对母亲(妻子)角色的刻板定义。
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艺术的力量通常就是回忆的力量。”[1]文本采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模式,第一人称本身存在极大的主观随意性,回忆也正如叙述者悦子所说是不可靠的东西,这种对事实构成双重否定的叙述视角,暗示不可靠叙述修辞的存在。读者进行阅读时需转移焦点,从梳理叙述者讲述的事件转向“双重解码”,正如申丹所阐释的“其一是解读叙述者的话语,其二是脱离或超越叙述者的话语来推断事情的本来面目”[2],并能深入叙述者的心理状态,进而发现叙述话语与事实真相存在差异的原因。由此,在这样一种不可靠的回溯型叙事中,不论悦子如何竭力编织完美无憾的谎言,明白作者用意的读者仍能发现表层文本背后的叙事暗流,勾勒叙述者在“事实/事件轴”层面的不可靠叙述。
石黑一雄曾这样评价自己书中的人物:“通常在我小说的结尾中,叙述者对痛苦的事有了部分的适应,他或她终于开始接受那些原先无法接受的痛苦事情,但这里面常常仍有一个自我欺骗之类的因素存在,足以让他们能继续生存下去,因为人生的悲哀之一便是它很短暂。”[3]即使悦子在经历创伤多年以后能初步面对过往,但由于创伤体验过于沉重,只能借自我欺骗式的不可靠叙述来获得某种意义上的心理平衡。学者王娅姝也指出“在石黑一雄的叙事和语言机制中,兼有两种彼此竞争的内驱力,讲述者在揭示、坦陈的同时,又着意对特定事件或细节进行否认与隐瞒”[4],悦子同这些讲述者一样,叙述过往记忆时显然存在“事实/事件轴”层面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5],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充满空白的遮掩型叙事。叙述者的话语留白随处可见,如悦子被绪方收留时是孤苦无依的独身状态,对被收留以前的境况,悦子有意无意一言半语,当藤原太太提起死于战争的准儿媳,悦子也说起“中村君”,男性名字出现的特别语境暗示两人某种暧昧不明的关系,至于具体如何,听者无从得知。此外,悦子如何被收养又是经历怎样一番周折才与绪方的儿子结合,叙述者只字未提,只有其他人物不经意间的一言半语。如绪方忆起悦子答应二郎求婚的条件之一是在新房门口种上杜鹃花,婚后悦子总是深夜拉小提琴,如血一般鲜艳的花色、深夜孤独的琴声显然溢出读者的视觉与听觉,在原有文字的基础上无限驱入人物感伤的心理情感空间。过往经历的空白和隐约的忧伤暗示悦子心理创伤的存在,徒留空缺的虚无与孤独。
其二,疑点重重的矛盾性叙事。相较前者这是直接解构叙述者话语权威的力证,书的最后“那一天,景子很高兴,我们坐了缆车”①,短短一句拨开叙述者精心布置的重重迷雾。读者回顾前文发现只有佐知子母女同悦子坐了缆车,景子与万里子由此构建起关联。此外,还有一处关于人称变化的细节,悦子劝说万里子同佐知子离开日本时说道“你要是不喜欢那里,我们可以随时回来,可是我们得试试看,看看我们喜不喜欢那里,我相信我们会喜欢的”②,即将前往美国的是佐知子,在两人对话中却变成了悦子,“我”“我们”的指称暗示悦子与佐知子身份的重合,再结合两人相似的人生经历,读者察觉佐知子实际为悦子的另一个自我,万里子则是其女儿景子的投射。疑点重重的矛盾性叙事成为悦子人格分裂的外化形式 。
细究叙述者的叙述话语,不难发现悦子叙述的不可靠性实际源自其别样的个体创伤心理,不论是内心空缺的虚无感还是双重人格的分裂感,都指向其在个性与母性冲突中的创伤体验。许多评论家将悦子这一创伤体验的具体内涵定义为战后体验、移民身份认同等,本着文本细读原则,结合作者的创作主张,战争、移民等大范畴背后的隐微叙事现形,尤其是无法被大背景忽略的人物个体特征即悦子的母亲(妻子)角色。
在众多的人物关系中,作者聚焦悦子与二郎的夫妻关系、悦子与景子(佐知子与万里子)的母女关系,怀着对个体生命独特经历的关切,呈现人物关于个性与母性冲突的分裂体验。悦子的不可靠回忆中存在形象截然相反的双重自我,即前文所述的分裂人格:一个是仿佛家庭天使的日本传统女性,二郎接待同事时示意悦子准备茶点,稍不遂意便面带怒色,即使这样她仍旧一一顺从。回溯的点滴往事里还有悦子对万里子无微不至的关心与其好母亲人设,由此读者不难发现,回忆中的悦子扮演着为社会权力话语认可的温柔、体贴又善解人意的母亲(妻子)角色。另一是崇尚个体自由却受到社会舆论制裁的佐知子,她常留女儿一人在家,只身追寻所谓的爱情,即使女儿乱跑晚归也少闻少问,佐知子崇尚少女时代从父亲那里习得的对美国自由生活的憧憬,不顾女儿感受残忍溺死其最喜欢的小猫,又一意孤行带女儿来到美国,万里子由此形成了冷漠、压抑、易怒等异于常人的性格,其性格悲剧显然与佐知子对母性的脱缰有着不可否认的直接联系。
出于越是缺乏则越是幻想越是呈现的心理机制,在悦子的不可靠叙述中,脱离母性的佐知子才是其真正的潜意识自我。尽管分裂的两个自我都在向读者辩解好母亲的设定,景子的自杀也就意味着个性与母性的冲突达到高潮,所有好母亲人设不过是叙述者悦子心怀愧疚的美好想象。在弗洛姆看来,潜意识代表整个的人性,意识则代表社会历史环境对人的限制,一个人若是由自己所不知的冲动所驱使,而这些冲动又与他有意识的思想相违背,则他就会把他自己无意识的欲望投射出去,成为他人的欲望[6]。换句话说,悦子的分裂体验较大程度源自社会权力话语关于母亲刻板印象为其个性戴上的镣铐,因为社会认可的一致性始终排除以佐知子为代表的他者女性的存在,例如邻居们关于佐知子教育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非议,正是出于对流言蜚语的警惕,悦子的真实自我只能隐藏于冠冕堂皇的话语表象下,完整的个体分裂成两个形象截然相反的存在。叙述者悦子出于与听者共谋的考虑,将自身不为社会权力话语认可的一面转化为他人的故事来诉说自己的难言之隐,其个人介于母亲(妻子)身份形成的分裂体验由此成为必然存在。
总而言之,作者聚焦人物悦子独特的个体经历,顺应人物心理,运用不可靠叙述修辞,引导读者就更为深广的层面窥见了悦子在个性与母性冲突中的分裂创伤体验,尤其关于权力话语对人物个性的规约与压抑,折射出文明时代个体存在为权力话语吞噬的普遍心理现实。
二、 二项对立:绪方在个体与集体矛盾中的他者体验
石黑一雄在呈现绪方的个体创伤经历时,显然设置了关乎人类元价值体系的二项对立组:传统/现代,个体/集体。两组之间以人物绪方的他者经历为媒介构建起关联,作为个体存在的他深陷传统与现代的时代裂隙,放弃宏大叙事的作者则借其个体社会价值在新旧时代断裂期的巨大变化,演绎个体存在为时代权力话语湮没的他者体验。
故事背景安排在日本新旧断裂时期,这也是传统/现代二项对立的具象化形式。传统日本拥有一套普通民众引以为傲的信仰价值体系,受这些社会集体信仰约束的人民崇尚忠诚与纪律,正如绪方所说“纪律,忠诚,从前是这些东西把日本人团结在一起,也许听起来不太真实,可确实是这样的,人们都有一种责任感,对自己的家庭对上级对国家 ”③,社会普遍信仰同日本传统政治空间宣扬的武士道精神一脉相承。正是出自这样的旗帜导向,以绪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者们献身教育,将未来更多个体引向时代定义的正确道路,他们曾解雇并监禁带有异端思想的其他教育者,鼓吹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坚船利炮而非人民胆小或社会浮浅,受限于具体历史文化语境的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社会集体的民粹主义倾向。然而,随着社会文明演变,各领域的现代化对日本传统信仰价值体系构成了有力冲击,一系列于传统社会而言无疑是消极因素的存在如伦理观的颠覆、人的“异化”状态喷涌而出。
关于传统伦理观的颠覆,如绪方与二郎父子伦理关系的倒置。日本传统伦理视域下的父子关系类似于中国古时的“父为子纲”,强调父亲的绝对家庭地位,然而绪方与二郎的尊卑关系却截然相反:一方面表现在二郎对父亲话语权威的不置可否。面对父亲对美国舶来品的负面评价,受新式思想影响的二郎辩解美国人带来的东西不全是坏的。当父亲提及本国孩子对国家历史一无所知的怪现象,二郎有意说道:“不过我也记得我上学时的一些怪事,比如说我记得以前老师教过,神是怎样创造日本的,我们这个民族是多么的神圣和至高无上,我们得把课本一个字一个字地背下来,有些事情也许并不是什么损失”④,否定历史记忆,肯定外来事物,鲜明的态度对比构成绝佳张力,消解了父权话语权威。另一方面还表现在父与子的身份倒置。绪方每日像孩子一样等待二郎回来下棋,面对宁肯看报打发时间也不愿陪自己的儿子,老人只能迁就与忍耐,值得注意的是,儿子总以工作忙碌为由推诿父亲请求且屡试屡成,这暗示功利时代的到来,有市场价值的年轻一代占据主导话语权,曾屹立于旧时代巅峰的年老一代则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成为失去社会价值的他者存在。
至于夫妻关系的“异化”状态,例如,花田因妻子投票给不同政党而大打出手,本没有参与谈话的绪方听闻此事加入讨论,日后他与藤原太太闲聊时再次提及此事,可见绪方眼中这件事的重要程度。与文学批评视域的异化内涵不同,前述加上引号的“异化”指向与读者期待视野相区别的人物心理,即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绪方,其关注点不在丈夫打妻子这一违背现代伦理的行为,而在夫妻两人不同的政治见解。有着天皇信仰的传统日本断然不会允许出现丈夫与妻子政见不同的情况,文中花田与妻子投票给不同政党的细节,暗示日本政治空间已然进入受西方民主观念强烈影响的语境,读者由此可以推测绪方视域下夫妻关系的“异化”内涵,实际源自其个人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共通感缺失,即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绪方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现代社会推崇的民主政治。传统与现代、个体与集体的裂隙便由人物与新时代的格格不入具体演绎出来。
战争并不是造成日本新旧时代断裂的元凶,与急于为任何历史风云寻找担责者的无意识群体不同,石黑一雄刻意规避宏大叙事,旁敲侧击地说明具体历史事件未必是引起日本全局变化的根本原因。所谓具体历史事件,不过是历史深层规律的外化形态,规律即为文明必然演变,而该过程带来的现代化进程意味着一个时代必然向另一个全新时代更迭,形成两重阵营,即代表本时代的“自我”和脱离本时代集体的“他者”。学者王烨认为“自我是在与他人的相互联系中形成的,同自我一样他人也是一种主体,他人的沉默和边缘性并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历史与社会意识的构建物”[7],与之同理,旧时代的佼佼者必然会缄默于以权力话语为标志的新时代洪流,徒留个体永恒的不确定性与创伤的他者体验。
石黑一雄正是借助旧时代的佼佼者绪方的个人眼光窥见个体/集体的裂隙,呈现其随时代变换的社会价值与由此而来的他者创伤体验。除却上述列举的两类事件,对绪方个人信仰造成毁灭性冲击的莫过于其学生松田重夫,松田写下一篇文章《新教育文摘》,批评以绪方为代表的旧时有影响力的教育者,如其所说“我们现在的生活和过去……过去您是位有影响力的人物时不一样了,您那个时候老师教给日本的孩子们可怕的东西,他们学到的是最具破坏力的谎言”⑤,绪方作为旧时代著名的教育家,为顺应过往时代集体话语导向,将传统历史文化语境认可的民族主义发扬到极致,当个人社会影响力达到高峰,猝不及防的时代更迭却将原本引以为傲的一切贬得一文不值,由社会价值定义的个体存在瞬间跌入低谷。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意义上的“话语”已然不再是简单的语言事实,而是填充有种种政治、经济、文化等现象的复合体,烙上了权力的印记。孙隆基在其著作《历史学家的经线》中写道:“我们几乎可以万无一失地假定:口腔的确是对监狱的构想产生过一种无形的影响,当监狱还是用刑室的时代,它们与一张充满敌意的血盆大口就有更多相似之处。”[8]松田重夫发表文章指名道姓地批判以绪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者,形成顺应新时代权力话语的公共舆论导向,将以绪方为代表的失去社会价值的个体置于他者境地,该行径无疑是权力监狱的具体形式。以松田为代表的众人之口塑造着他人的命运状态,加重命不由人的虚无感,构成绪方的他者创伤心理。集体在定义个体社会价值时的权力话语取向,对绪方乃至更多个体而言,无疑加剧了其生存的荒诞意味,徒留虚无的他者创伤体验。
总而言之,作者书写传统/现代、个体/集体等二项对立组,并非止步于呈现战争创伤和传统失落,正如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所述“石黑一雄以巨大的情感力量,发掘了隐藏在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幻觉之下的深渊”,这种伟大的深渊跨越狭隘的民族视域,无限驱入人类隐秘心灵,作者借绪方在传统/现代、个体/集体矛盾中的他者体验,于无形中实现了权力话语塑造个体存在虚无意义这一人类隐秘经验的传达。
三、 多元视角:景子由家庭到社会的复杂创伤体验
作为更加弱势的儿童群体,景子的创伤体验与前述第一代创伤个体有着明显不同,主要可以追溯至冷漠的亲情关系带来的家庭创伤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文化创伤。文本存在多元视角,即人物妮基的眼光、“经验自我”的眼光和“叙述自我”的眼光,它们分别从不同的阅读位置呈现景子由家庭到社会的复杂创伤体验,揭示权力话语的隐秘操作。
据人物妮基的眼光,景子与自己和父亲的关系冷漠疏远,其家庭创伤体验一览无余。妮基认为“姐妹之间应该是很亲近的,你可能不是很喜欢她们,可你还是和她们很亲近”⑥,然而她和景子并非这样,甚至觉得后者只是一个让自己难受的存在,以至于在景子死后很快便忘记其模样,姐妹关系的冷漠疏远由此可见一斑。妮基感慨起父亲对姐姐的不公正态度“我想爸爸应该多关心她一点,不是吗?大多数时候爸爸都不管她,这样真是不公平”⑦,即使两人关系疏远至极也不妨碍妮基对父亲偏心行为的吐槽,这反而从侧面衬托出继父在景子家庭创伤心理的形成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透过人物妮基的有限视角,读者只能窥见景子复杂创伤体验的一隅,由此,承担主要叙事责任的叙述者视角显得重要且必要。
景子的复杂创伤体验主要由第一人称叙述者悦子通过回忆的方式半遮半掩地呈现。申丹在其著作《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中指出,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通常存在两种眼光,“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时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9]。结合文本具体语境,前者指向“叙述自我”即现居英国的悦子,后者指向分裂的两个“经验自我”即日本长崎的佐知子和悦子。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前文第一部分阐述,日本长崎的悦子实际为“叙述自我”悦子的美好想象,两者眼光具有一致性,即使她们都不约而同地掩饰自己的罪责,介于其特殊的叙述者身份,两者相较,“经验自我”佐知子更能揭示事实真相。
据“经验自我”佐知子的眼光,自己是甘于为万里子(景子的投射)奉献一切的好母亲。佐知子多次辩解前往美国首先是考虑到女儿的利益,因为“那里更适合孩子成长,在那里她的机会更多,在美国女人的生活要好得多”⑧,悦子的所见所闻则与其形成鲜明对照,构成颠覆佐知子话语权威的叙事暗流。悦子发现佐知子寻找走丢的万里子时,显然更加关心前去美国的问题,“没必要这么慌张,她不会有事的,其实悦子,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些事情,你瞧事情终于定下来了,我们过几天就要去美国了”⑨,该行为与其辩解的好母亲人设显然格格不入,暗示母亲的冷漠自私与万里子家庭创伤心理的形成有着必然联系。此外,还有多处富于隐喻意味的细节。例如,悦子发现万里子总是喜欢背对着母亲,其中的间隔影射母女关系的隔阂状态,至于隔膜的具体形态则表现在两人的无法沟通。在藤原太太的面馆里,佐知子命令万里子回厨房,万里子思绪却始终停留在幻想的女人身上,两人无法形成有效沟通,佐知子的严格命令与强行带女儿移民的行为前后呼应,而其自身对这些行为的话语遮蔽都象征着权力的必然存在。相较母亲佐知子,万里子的命运更大程度上是由家庭而非社会直接决定的,也更难摆脱家长的专制话语,即使悦子的解构将万里子从话语监狱释放,使读者意识到权力话语的隐性操作,冷漠疏远的亲情关系给万里子(景子的投射)带来的家庭心理创伤也已然无法挽回。
据“叙述自我”悦子的眼光,读者发现景子被母亲强行移民英国后遭受的社会文化创伤体验,这从文本两处细节可以得出。其一,英国报社报导景子自杀时刻意强调其为日本人,这一做法在悦子看来十分奇特,仿佛日本这个民族天生热爱自杀。报社是社会公共舆论的化身,该做法实际代表英国对日本的集体想象,基于这样的社会语境,景子生前交不到朋友极可能与其民族身份息息相关,死后个人特殊体验又消解于西方权力话语对日本民族的刻板印象。而母亲的冷漠与自私在景子心里留下的创伤被对日本民族的习惯性偏见抹除,由此文化刻板印象实际为景子带来了不容小觑的心理创伤体验。其二,悦子反驳丈夫有失偏颇的看法,“我的两个女儿有很多共同点,比我丈去承认的要多得多,在他看来她们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他形成这么一种看法,认为景子天生就是一个难相处的人,对此我们无能为力,其实他虽未直说,但是他会暗示景子是从她爸爸那里继承了这种性格”⑩,悦子认为出生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景子和妮基童年时有着同样的脾气,只是后天因素造就两人不同的结局。然而在英国丈夫看来,景子的性格天生异常,且源自其日本生父的基因遗传,文化隔阂使得景子始终被继父当成非正常的存在,继父也只是千千万万个英国人中的一个,文化隔阂成为构成景子复杂创伤体验的因子之一。尽管景子想通过将自己关在房屋来逃避社会筑起的更高围墙,但越是逃避越是孤独,最终带着由家庭到社会的复杂创伤体验走向自杀的终结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隔阂心理与文化刻板印象实际也是权力话语在国际层面排除异质性的体现。作者作为人物的共谋者,借悦子之口表达对民族刻板印象与文化隔阂的决然否定,呈现出世界主义的创作倾向。石黑一雄提及自己身份时曾说“我没有明确的角色,没有能够让我辩护或抒写的社会或国家,没有人的历史是我的历史(我没有历史)”,正是这种既非日本人又非英国人的主体间性,使作者得以在创作中客观冷静地呈现某种事实,不受权力话语左右进而传达超越意识形态层面的人类普遍经验。总而言之,景子的创伤体验主要可以追溯至冷漠的亲情关系带来的家庭创伤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文化创伤,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影射了其背后权力话语的隐性操作。
权力所制造的创伤并非仅仅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效果,同时也是一道生存的谜题,无论是文本呈现的悦子在个性与母性冲突中的分裂体验,绪方在个体与集体矛盾中的他者体验,还是景子由家庭到社会的复杂创伤体验,石黑一雄笔下的普通人在对权力进行抵抗时,受创的感知和伤痕的意味也许是个人的,但其后果与冲击却是公共的。文本主要人物的个体创伤可以给予普遍存在的个体即读者关于个人与权力话语、民族与世界的辩证思考,文本也凭借作者赋予的隐喻内涵由上下文语境自足的个别存在升华为富于哲理意味的一般存在。
《远山淡影》虽是石黑一雄的处女作,但其对叙事艺术的自觉运用与超越具体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哲学眼光和人文关怀,已然为其后来的作品创作奠定了整体的框架与风格,尤其是对人物个体心理现实乃至人类普遍心理现实的长驱直入,呈现出世界主义的创作倾向,这种别具一格的写作特色也使石黑一雄得以在“移民三雄”中脱颖而出进而享誉世界。
注释:
①选自石黑一雄的《远山淡影》,张晓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2011年版第237页。
②选自石黑一雄的《远山淡影》,张晓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2011年版第224页。
③选自石黑一雄的《远山淡影》,张晓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2011年版第79页。
④选自石黑一雄的《远山淡影》,张晓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2011年版第80页。
⑤选自石黑一雄的《远山淡影》,张晓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2011年版第188页。
⑥选自石黑一雄的《远山淡影》,张晓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2011年版第4页。
⑦选自石黑一雄的《远山淡影》,张晓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2011年版第228页。
⑧选自石黑一雄的《远山淡影》,张晓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2011年版第52页。
⑨选自石黑一雄的《远山淡影》,张晓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2011年版第40页。
⑩选自石黑一雄的《远山淡影》,张晓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2011年版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