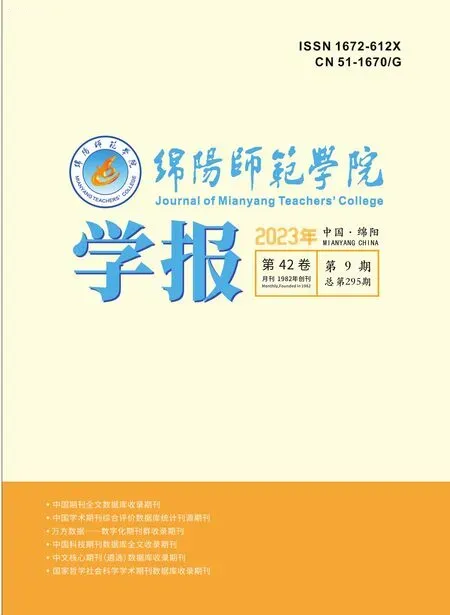论竟陵派诗论中的“厚”
彭容丰
(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四川成都 610041)
厚,本义指“山陵之厚”[1]106,是一个用来形容物体广大而有厚度的自然概念。但在古人类比思维的作用下,“厚”与人的品格产生关联,如“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2]12“含德之厚,比于赤子”[3]274等,逐渐发展为品评人物的重要术语。同样,与大多数文论术语的生发过程相似,“厚”也经历了从人物品评到文学批评的衍变,直至明清时期,大量出现在文论作品中,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之一。是故,“厚”这一文论术语必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管见所及,学术界对“厚”的研究主要包括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主要表现为对“厚”的美学意蕴进行阐释等;就后者而言,集中于对明清竟陵派诗论“厚”与“灵”之关系进行讨论、对贺孙怡《诗筏》中有关“厚”之诗论进行阐发等。其中,蒋寅教授《论中国古典诗学中的“厚”》一文最具代表性,文章从“厚”的概念史角度出发,对古典诗学中“厚”的诗歌表现、成为文论概念的渊源、在清代的丰富与发展、妨碍“厚”的艺术要素等方面展开论述,为研究“厚”这一理论范畴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
本文以竟陵派诗论中的“厚”为研究对象,与前人讨论“灵”与“厚”的关系不同,本文将从竟陵派论“厚”之渊源、“厚”之具体内涵以及竟陵派“厚”论之弊端三方面展开论述,以期能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发掘竟陵派诗学“厚”论之独特面貌。
一、竟陵派论诗以“厚”之渊源
竟陵派诗论“厚”的形成与内涵有着特定的时代特征,与其诗论“幽深孤峭”在明末清初形成的广泛影响不同,除了贺孙怡在《诗筏》中对竟陵派诗论“厚”有所阐发之外,鲜少有诗论著作涉及于此。故而想要了解竟陵派诗论“厚”的渊源与内涵,应当回到明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语境中去探寻。
与明代诗歌创作水平的整体声名不显相比,明代的诗学理论却颇有建树。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对此有过阐发:“古今诗赋文章,代日益降,而识见议论,则代日益精……沧浪号为卓识,而其说浑沦,至元美始为详悉。逮乎元瑞,则发窾中窍,十得其七。继元瑞而起,合古今而一贯之,当必有在也。盖风气日衰,故代日益降,研究日深,故代日益精,亦理势之自然耳。”[4]348可以看出,许学夷论述的“识见议论”,实则是论诗的体系性和精细程度。其论严羽诗论为“浑沦”,而王世贞(字元美)诗论则“详悉”,直到胡应麟(字元瑞)《诗薮》,诗论方为深刻,这是因为理论成就是在一代又一代的积累之上呈现的,所以他会认为明代的“识见议论”高于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当然,许学夷的此番论述也可认为是他对本朝诗学理论发展的肯定。
总体而言,有明一代诗学理论的发展基本与诗歌流派的发展保持一致,以复古为倾向,同时伴随着反复古的论争。陈良运先生在《中国诗学批评史》中将明代的诗学分为以“格调”为核心的复古诗论和以“性灵”为核心的文学解放思潮两大阵营[5]429-473,从这一宏观角度可以大致把握明代诗学的总体风貌。复古诗论阵营所追求的“格调”,其内涵由李东阳的以“声”论诗,到李梦阳以“情”论诗,再到王世贞将“格调”升华为“神与境合”的最佳审美状态。无论对“格调”作如何阐发,都离不开师古与学古这一路径,正因此,前后七子的拟古、泥古弊端在末学旁支中愈加严重,以致诗无本色,亦无真我。正如徐谓所言:“人为学为鸟语者,其音则鸟也,而性则人也。鸟有学为人言者,其音则人也,其性则鸟也。此可以定人与鸟之衡哉。今之为诗者,何以异于是?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独窃于人之所尝言,曰某篇是某体,某篇则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则否。此虽极工逼肖,而已不免于鸟之人言矣。”[6]519诚然,当作诗如鹦鹉学舌,诗歌则废。为纠此弊,以“性灵”为核心的文学解放思潮相伴而生,其中有如徐谓提倡的“真情”与“本我”,李贽发扬的“童心说”,汤显祖高举“情致”为诗歌生命之源等。最具代表意义的则是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舒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7]567可以说,钱谦益对公安派一扫“七子”复古派理论与诗风的成就给予了很大的肯定。但是,“性灵”的弊端依然十分明显,袁中道也曾言:“其意以发抒性灵为主,始大畅其意所欲言,极其韵致,穷其变化,谢华启秀,耳目为之一新。及其后也,学之者稍入俚易,境无不收,情无不写,未免冲口而发,不复检括,而诗道又将病矣。”[8]462袁中道发现的弊端不仅仅出现在公安派追随者身上,在三袁的创作中已见端倪,只是公安末流以俗以俚为诗的情况愈加严重,使诗歌失却雅正之音。钱谦益也对此作出评价:“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灭列,风华扫地。”[7]567由此“竟陵代起,以凄清幽独矫之,而海内之风气复大变”[7]567。
按钱谦益的观点,竟陵派兴起的原因是为了矫正公安派诗学的流弊,而矫正的方法为“凄清幽独”。当然,这一诗论的弊端不言自明,致使明末清初各家对竟陵派的批判尤为激烈,特别是钱谦益、王夫之等人,直以“诗妖”“亡国之音”看待之。但我们应该认识到竟陵派能够在明末文坛屹立几十年不倒,绝对不仅仅只以“凄清幽独”行世,其过人之处应当值得关注与思考。
竟陵派以钟惺、谭元春二人为代表。与钱谦益所论不同的是,竟陵派的兴起不单单只针对公安末流的率意诗风,也针对“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从钟、谭的诗学观念中可以发现,除了备受后人指摘的幽深孤峭之外,他们对真性情也多有论述。
钟、谭主张性情是在“后七子”拟古的时代潮流中提出的,这一主张当归之于前文所述的“性灵”阵营。在钟惺的文集中,多处对“性情”的阐发值得注意。
如:“夫诗,道性情者也。”[9]275(《陪郎草序》)
“古诗人曰风人。风之为言,无意也,性情所至,作者不自知其工。”[9]263(《董崇相诗序》)
“世未有俗性情能做大文章者。”[9]571(《题马士珍诗后》)等。
在谭元春的文集中,
如:“诗者,性情之物。”[10]678(《朴草引》)
“诗以道性情也,则本末之路明,而今古之情见矣。”[10]613(《王先生诗序》)等。
除了对“性情”的追求与阐发,竟陵派对真诗的追寻也不应被忽视。在《诗归序》中,钟惺云:“今非无学古者,大要取古人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使捷者矫之,比于古人外自为一人之诗以为异。要其异,又皆同乎古人之险且僻者,不则其俚者也,则何以服学古者之心?无以服其心,而坚其说以告人曰:‘千变万化,不出古人’。问其所为古人,则又向之极肤、极狭、极熟者也。世真不知有古人矣。”[9]236钟惺认为,世人学古却未学得“真古”,只是多摹拟“七子”所作。且“后七子”标举的复古诗论,在延续“前七子”的诗论同时,又将其推向极端。所谓“夫诗莫盛于唐,自唐以后,寖以弱靡极矣。”[11]582虽然王世贞曾认为“骨格既定,宋诗也不妨参看”[12]98,将学习对象扩大到宋诗,但其弊端仍不可自救,尤其是在大量追随者出现后,于创作上一味模仿,缺乏创造力,以至剽窃成风,使得文坛风气大坏。即便“前七子”中的李梦阳曾提出“格调”的核心为“情”,但“前后七子的诗学理论及诗歌创作在当时所产生的实际效应,却出现了所谓‘格调优先’而非‘性情优先’的偏差”[13]319,所以在公安派高举“独抒性灵”的大旗时,钟、谭也将“性情”拈出,并主张要以真古诗之面目示人,以彰显真诗之面貌。
与此同时,针对公安派论诗的弊端,钟谭想要以“厚”矫之,而非前文钱谦益所言仅以“凄清幽独”矫之,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详细论述。此处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厚”非竟陵独创,其实在格调派的诗论中,“厚”已然是其一部分。如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序中言:“诚使吟咏性情之士,观诗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时,因时以辨其文章之高下,词气之盛衰,本乎始以达乎终,审其变而归于正,则优游敦厚之教,未必无小补云。”[14]9又李梦阳在给何景明的信中言及诗当“柔淡、沉著、含蓄、典厚”[15]567等。“温柔敦厚”历来被看作诗教之正统,明代“格调”派的整体创作趋向亦是在儒家诗教背景下进行的。而竟陵派一方面用以“情”为主导的诗学理论对儒家诗教背景下的“格调”派弊端进行反拨;另一方面又吸取“格调”派诗论内涵之一的“厚”,对公安末学俚俗的现象进行批判。以此看来,或可认为竟陵派诗论在当时其实是具有调和作用和中和意义的。
故而,从客观的文学史进程看,竟陵派的崛起与发展是文学代兴之必然;从主观的文学发展角度看,竟陵派能够综合“性情”与“厚”这两种分属于性灵阵营与格调阵营的诗学主张,并以此对当时诗坛普遍存在的泥古与空疏不学问题进行纠正,在一定程度上为竟陵派长期屹立于晚明诗坛提供了内在支撑机制。要之,竟陵派论诗以“厚”,不仅是对当时诗坛弊病的纠偏,而且也是在明末诗坛鼎革之际寻求的通变之术。是故笔者将从《诗归》入手,着重探讨竟陵派诗论“厚”的具体内涵。
二、竟陵派诗论以“厚”之内涵
当下对竟陵派诗论“厚”的研究多从钟惺《与高孩之观察》入手,探讨“灵”与“厚”之关系,但是,钟、谭以“厚”论诗集中出现在《诗归》之中。钟惺作《与高孩之观察》说道:“向捧读回示,辱论以惺所评《诗归》,反复于‘厚’之一字,而下笔多有未厚者,此洞见深中之言,然而有说。”[9]474即高孩之观察针对《诗归》中虽多用“厚”来品评诗歌,但选诗与评诗却没有达到“厚”之标准的问题,向钟惺提出意见,钟惺对此作出阐释,从而引出“厚”论。是故,探讨钟、谭所论之“厚”,更应当在以“厚”论诗的《诗归》之中寻觅真相。
据笔者考证,《诗归》中以“厚”评诗者多达115处,正如贺孙怡所言:“严沧浪《诗话》,大旨不出‘悟’字,钟、谭《诗归》,大旨不出‘厚’字。”[16]141而这些“厚”字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用词用字的贴切有力
钟、谭主要指用虚字。如评张九龄《望月怀远》,钟云“虚者难于厚,此及上作(《初发曲江溪中》)得之,浑是一片元气,莫作清(轻)松看”①(《唐诗归》卷五)。评刘昚虚《寄阎防》,钟云:“看他首首下虚字,皆有力。”又云:“入虚甚深厚,莫只作轻微看。”(《唐诗归》卷六)关于虚字的用法,贺孙怡在《诗筏》中也做了相应的解释:“下虚字难在有力,下实字难在无迹。然力能透出纸背者,不论虚实,自然浑化。彼用实而有迹者,皆力不足也。”[16]140贺孙怡所言之“力”,与钟惺所评之“厚”应具有相似的内涵。虚字的使用在古典诗歌创作中占据重要地位,除了能够“托精神而传语气”[24]11,更是促使诗歌形成一个完整有机体的粘合剂。而虚字的滥用又极易造成诗歌语言直白、声势暗弱的缺陷,故不论是钟还是贺,二人所说的虚字使用法则,实则是指能够准确传达情理,并能使整首诗浑然一体,遒劲有力,这一要求最终指向诗人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字功底。
(二)表现手法的含蓄蕴藉
评蔡伯玉妻《盘中诗》“山树高,鸟鸣悲。泉水深,鲤鱼肥。空仓鹊,常苦饥”云:“六语比兴之体,最厚,最远。”(《古诗归》卷四)比兴作为传统的诗歌表现手法,以不直言其事为特征,钟、谭认为比兴为远为厚,便是对这种含蓄表达手法的推崇。又如评选《疾邪诗》云“此诗有二首,前者太露,故删之”(《古诗归》卷四),正是此意。曹学佺曾说钟、谭《诗归》“和盘托出,未免有好尽之累。夫所谓有痕与好尽,正不厚之说也”[8]474,“好尽”便是直露而无韵味,需矫之以“厚”。钟、谭认为初唐之诗为厚,却未做具体解释,参看张谦谊之观点或许可了解一二,其言:“初唐人作诗,先不作态,所急者笔势飞动,通体匀圆,意不求暴露,故味厚。”[17]791即初唐诗厚在蕴藉,所以钟、谭对此大加推许。除此之外,钟、谭对怨而不怒的表达方式也十分推崇,评陶渊明《乞食》云:“妙在无悲愤,亦不是嘲戏,只作寻常素位事,便高便厚便深。”(《古诗归》卷九)评李白《赠柳圆》云:“悲调而厚,最难。”(《唐诗归》卷十六)这一追求,更接近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旨。
(三)风格的自然天成
如评高适云:“五言律只如说话,其极炼、极厚、极润、极活,往往从欹侧历落中出,人不得以整求之,又不得学其不整。”(《唐诗归》卷十二)又评岑参云:“高岑五言律只如说话,本极真、极老、极厚。”(《唐诗归》卷十三)“只如说话”,即不事雕琢。钟谭以“炼”“厚”“润”“真”“老”来形容这种自然浑成的诗风,而“厚”是由“‘老’的成熟、稳重的意味引申而来”[18]64,这些与“厚”相关联的概念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成熟与稳妥,似有与“清新”对立之意。“清新未免有痕”,便是不厚,则“须由清新入厚以救之”,故诗歌风格的浑然一体当有成熟稳健之技巧与浑厚深沉之气度。
(四)内容意义的深刻丰富
评储光羲《同王十三维偶然作》云:“寄兴、入想皆高一层、厚一层、远一层。田家诸诗皆然,有此心手,方许拟陶,方许作王、孟,莫为浅薄一路人便门。”(《唐诗归》卷七)在钟、谭眼中,储光羲是深得陶诗真谛的,他的诗习得了陶诗深厚的特征,此深厚则指内容层面。钟、谭曾言:“人知王、孟出于陶,不知细读储光羲、及王昌龄诗,深厚处盖见于陶诗渊源脉络,善学陶者,宁从二公入,莫从王、孟入。”(《诗归》卷十一)当然,学陶从储、王入这一认知受到了后人不少指摘,但仅从钟、谭对储、王学陶而得其“厚”来看,这一“厚”便是指思想立意的深刻与丰富。
(五)人的稳重深沉之气
诗人之气韵往往通过文字行诸作品,而读书养气是作品得以深厚的必要途径。钟惺在为周伯孔所作的诗序中曾劝诫他“多读书,厚养气,暇日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文行君子,其未可量”[9]254。指出不仅要通过读书使气厚,更要通过践行儒家的君子教养来达到“文行君子”。同样,钟、谭评韦应物,认为世人只知其诗“清”,却不知,此“清”之一字并不好学,“不读书,不深思人,侥幸假借不得。”(《唐诗归》卷二十六)是故,气厚而能诗厚,即便是书写俚俗琐碎之语,亦能有浑厚之感,如杜甫《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钟、谭认为此诗虽写得细碎,但却不觉其俚,只因杜甫“笔老气厚。”(《唐诗归》卷二十)又如评杜甫《旅次丹阳郡遇康侍御宣慰召募兼别岑单复》云:“诗中论时事语露矣,而不伤其厚,其气完也。”(《唐诗归》卷二十五)以钟、谭之意观之,表达太露则为不厚,但杜甫能够在直言其事的情况下做到厚,亦是诗人自身浑厚之气在作品中的体现。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钟、谭论“厚”的内涵,不论是用词用字、表现手法、风格、还是内容立意,最终都指向人之气韵修养。而人之气韵修养可通过读书来获得,除了前文所举之例,钟、谭在《诗归》中还常常使用反证法来说明读书与养“厚”之气两者的关系。如评仲长统《述志诗》“大道虽夷,见机则寡”云:“‘见机’二字,是学道之根,浅人说不出。”(《古诗归》卷四)“见机”通“见几”,语出《易经·系辞下》:“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2]250表示从事物细微之处预见其先兆。仲长统此诗所要表达的便是对能够识见出大道之奥妙的至人达士的仰慕。故钟、谭云“浅人说不出”,便是不读书之人说不出。又评孟浩然云:“浩然诗当于清浅中寻其静远之趣,岂可故作清态,饰其寒窘?为不读书、不深思人便门。”(《唐诗归》卷十)即后人学孟浩然,只着眼于其清淡,却全然不知孟浩然之诗自有“温厚”处,不读书不深思之人因自身没有渊永之气,故只能得其皮毛。诸如此类不学则浅的论说还有多处,此处不再一一举例。
当诗文之“厚”指向人之“厚”时,便需要加强对个人气质的培养,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显示了钟、谭之论其实是忠于个体的“性灵”派阵营。故而在面对嘉、隆间诗人所学为“取古人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的问题时,钟、谭一方面提出诗当抒发性情,另一方面提出“约为古学,冥心放怀”,以“期在必厚。”[9]593(《谭友夏诗归序》)但与同样身为“独抒性灵”阵营之内的公安派相比,在对“学”的态度上二者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袁宏道认为:“夫趣得之自然则深,得之学问则浅。”[19]463而钟、谭则提出“灵慧而气不厚,则肤且佻矣,”(《唐诗归》卷十二)解决方式便是钟惺对周伯孔的劝戒“多读书,厚养气”。可见,与公安派只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不同,竟陵诗论在一定程度上也重视人之精神与涵养,故而以“学”补之,以“厚”出之。
由此看来,当竟陵以“厚”论诗时,它的阵营其实已经在摆动了。标举“性灵”,是由内而外自主发动,是个体对世界的自然感知。而养“厚”,则需要依靠学与识来对个体心性进行修持,这便是与任性自然的对立。正因此,有学者指出“竟陵的这种心性修持的要求,已始偏于儒学功夫论,并在抽象的意义上与宋儒中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有一致的倾向”[20]80。是故,竟陵所论“厚”,既是一种文学实践原则,也是种指向个体涵养的修炼目的。但即便如此,明末清初诗论家对竟陵派诗论的评价仍然只从其幽深孤峭处入手,却鲜少关注竟陵派诗论“厚”,这一现象与时代背景有关,当然主要原因也在于竟陵派论“厚”存在缺陷。
三、竟陵派论“厚”之弊端
有学者认为钟、谭提倡的读书学道,厚养其气对于“狂飙突进的晚明新思潮已经成就的发展进程来说,无论如何,是一种极大的倒退”[13]351。这是就文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而言,是后人对前人思想的总结与评价,而如果立身于明末清初时代背景之下,钟、谭的读书养气之论应当是符合绝大多数文人价值观的。但是在明末清初,文人对竟陵派的评价无不充斥着讥讽甚至认为诗道亡于此。除了贺孙怡对竟陵派有较为客观的评价,并在竟陵论“厚”的基础上又对“厚”这一概念进行完善阐述外,其他诋毁竟陵者却只字不言竟陵所论之“厚”,这一点确实值得思考。这里从钟、谭论“厚”的出发点谈起。
钟惺曾指出:“明诗无真初盛,而有真中晚、真宋元。”[9]522这一论述针对复古派而发。竟陵对复古派的抨击,与当时的公安派不谋而合,且二者均主性情,于是,后世往往以“楚声”指代公安与竟陵。如叶燮在总结明末文学风气嬗变时说:“于是楚风惩其弊,起而矫之。抹倒体裁、声调、气象、格力诸说,独辟蹊径,而栩栩然自是也。夫必主乎体裁诸说者或失,则固尽抹倒之,而入于琐屑滑稽、隐怪荆棘之境,以矜其新异,其过殆又甚矣。”[21]591其中,“体裁”云云指“后七子”阵营,“琐屑滑稽、隐怪荆棘”显然是指公安与竟陵。叶燮以“楚风”共称之,可以认为这两家论诗有着相似之处。
据陈广弘教授的《钟惺年谱》考证,万历三十七年(1609),钟惺与袁中道在金陵相见。也正是这一年,二人结识周伯孔,袁中道作《花雪赋引》,曰:“友人竟陵钟伯敬意与予合,其为诗清绮邃逸,每推中郎,人多窃訾之。自伯敬之好尚出,而推中郎者愈众。湘中周伯孔,意又与伯敬及予合。伯孔与伯敬为同调,皆有绝世之才,出尘之韵,故其胸中无一应酬俗语,意诗道其张于楚乎。”[22]卷六可以看出袁中道引钟惺为同调,对钟惺颇加称赞。又,钱伯城先生认为,袁中道对袁宏道的主张没有信从到底,且“中年以后,小修(袁中道字)的诗风就开始转变了,有意识地转向了幽深奇崛。写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一首《雨变诗》,就是小修诗风转向奇崛的具体代表性的作品”[8]10。如此可知,袁中道已经认识到公安派诗论存在的缺陷,想要引入幽深奇崛来救其弊,而此时钟惺的诗学主张在发扬性情的同时也推崇幽深奇崛之风,只有这样,袁中道才会称钟惺“意与予合”,也才会说“予三人誓相与宗中郎之所长,而去其短”[22]卷六。但也在这一年,钟惺在为周伯孔所作的诗序中告诫他“多读书,厚养气”,以此来摆脱其诗的“袁石公”语,表明钟惺想以读书养气来补救公安派的俚俗之弊。因此,钟惺的转向为钟、袁二人由同道走向对立埋下伏笔。
再看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袁中道条:“小修又尝告余:‘杜之《秋兴》,白之《长恨歌》,元之《连昌宫词》,皆千古绝调,文章之元气也。楚人何知,妄加评竄,吾与子当昌言击排,点出手眼,无令后生堕彼云雾。’”[7]569这里的“楚人”则单指钟、谭,也可以看出袁中道对钟惺的态度与前文所引《花雪赋引》中的描述大相径庭。不仅如此,《雪花赋引》仅存于《柯雪斋近集》,据陈广弘教授考证,在《柯雪斋前集》中,该文有关钟惺的内容已完全被改,《柯雪斋集选》与《前集》同。而《前集》刊刻时间为万历四十六年(1618),“《近集》与《前集》的刊刻时间不会超过一年”[13]172。又考谭元春《退谷先生墓志铭》:“甲寅、乙卯间,取古人诗,与元春商定,分朱蓝笔,各以意弃取,锄莠除砾,笑哭由我,虽古人之不顾,世所传《诗归》是也。”[10]681即,钟、谭编选《诗归》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四十三年(1615)间,而钟惺《诗归序》作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故结合《列朝诗集小传》中袁中道就选诗对竟陵进行抨击这一内容,可以认为,袁中道是在《诗归》刊行后,尤其是钟惺《诗归序》流传后,对钟惺的看法发生巨大转变,由同道转为敌对,并毫不留情地将《柯雪斋近集》对钟惺的赞美之词删去。
由此可以理解为袁中道对钟惺的抨击实不在“幽深”,而是另有他处。《诗归》的刊刻风行对袁中道造成的冲击,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学古为其一,以“厚”论诗为其二。学古是复古派的核心,钟、谭宣扬学古便是对性灵的背叛;以“厚”养气是儒家诗教的要求,钟、谭论“厚”是对袁宏道标举“趣”的背叛。进而袁中道从《诗归》内容出发,对钟、谭大加击排。
同时,“厚”的提出,也是钟、谭对自身诗论弊端的弥补。蔡复之在阅览《诗归》时发现钟、谭选诗论诗之弊,于是寄书与谭元春说道“《诗归》中有太尖而欠雅厚者,宜删去一二”[9]758,钟、谭对此做出了回复“确哉兹语”[9]758,对其弊病毫不避讳。且钟惺在为谭元春《简远堂近诗》所作的序中言“近乃颇从事汎爱容众之旨,欲以居厚而免于忌”[9]249,即钟惺认为谭元春近来诗作有走向浮浅平庸的倾向,应当以“厚”补救。
“厚”作为古典诗学中关于诗美的概念之一,蒋寅教授将其归为绝对正价概念[18]60。试看与“厚”相关的词语,如“深厚”“温厚”“敦厚”“柔厚”“端厚”等,都是充满正气的,但在《诗归》中,却时常出现这样一个词——“幽厚”。如评《归园田居》云:“幽厚之气,有似乐府。”(《古诗归》卷九)评沈约《别范安成》云:“字字幽,字字厚,字字远,字字真,非汉人不能。”(《古诗归》卷十三)评周弘让《留赠山中隐士》云:“陈隋靡靡中,忽有此古韵幽厚者,亦是元气不断于诗文之中。”(《古诗归》卷十五)评虎丘鬼《大历十三年虎丘寺石壁鬼诗》云:“此诗出于大历,其语气幽厚,决是唐以前高手。”(《唐诗归》卷三十二)从这些评价中可以发现,“幽厚”多是钟、谭对唐以前诗歌的评价,在钟、谭心目中应当是一个极高的评诗标准。
此外在《诗归》中,与“幽”相关的评语如“细”“奥”“远”“奇”等也大量存在,这些词语都可看作是对“幽”的阐发。如评李白《寻紫阳极宫感秋作》“静坐观众妙,浩然媚幽独”云:“取太白诗,贵以幽细之语补其轻快有余之失,如此等句,即妙矣。”(《唐诗归》卷十五)“轻快”是不沉稳,一般而言,要沉稳则须养“厚”,钟、谭却认为当以“幽细”补轻快之失。结合上文,可以认为“幽”与“厚”在钟、谭诗论中有着相通与相似之处,如此,“幽厚”方可连字成词。但是“幽”与“厚”在钟、谭心目中的地位却并不平等。
重看《诗归》的评选,钟、谭选古诗,极力舍弃“古人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所谓“极熟,便于口手”即世人争相传颂学习的名篇,也是传统意义上被认定的经典。钟、谭舍此而另辟蹊径,选古诗以奇以新,有宁奇毋平之倾向,意在向世人展示所谓的真古与真诗并非前“后七子”模仿古人之作,而应越过“七子”向唐前直寻。这一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钟、谭倾心于对古诗之“幽”的探寻,认为“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诗归序》)即真诗的获得途径便是通过体察蕴含在诗人内心深处的幽情,再加上钟、谭有意识地对幽隐风格诗文进行搜寻,如钟惺“平生好搜剔幽隐诗文”[9]488,谭元春“每有搜集古今诗文之意,盖专在幽潜”[10]750,使得《诗归》所选,无可避免地具有幽深尖新的风格特征。
如此看来,钟、谭提出的“厚”虽以多读书,厚养气为要义,但最终仍不可避免地走向了通过多读书,探求古人古诗幽奇之处的道路,表明“幽”才是钟、谭论诗之旨归。所以,即便钟、谭对“厚”有所阐发,也对复古派强调诗歌之“厚”有所借鉴,更期望通过“厚”来救己之弊,但由于他们的最终追求和目的并不是使诗歌走向复古派所谓的温柔敦厚,而是求新求异,求幽远之境和幽邃之情。故而,仅就竟陵派自身而言,“厚”是在以追求“幽”为目的的基础上提出的,它不可能改变竟陵论诗之核心。也因此,竟陵派自身对“厚”的实践并没有真正地落在实处。
竟陵派中其他人,如商家梅,“从伯敬游,一变而为幽闲萧寂,不多读书,亦不事汲古”[7]589。可见学竟陵者只学到其“幽”,却没有学到“厚”。又如林古度,王士禛为其编选诗集作序曰:“翁少与曹氏游,发三山,来建康,上匡庐观瀑布,游阳羡探善权、玉女之奇,其诗清华省净,具江左,初唐之体。逮壬子以还,一变而为幽隐鈎棘之词,如明妃远嫁后,无复汉宫丰容靓饰,顾影裴回,光照殿中之态。”[23]1993也是说林古度学竟陵,诗风转向幽隐,失却诗歌原本之“厚”。
综上所述,钟、谭作为竟陵派的领导人物,由于没有从根本上做到以“厚”救“幽深孤峭”,反而有以“厚”寻“幽”的倾向,致使其“厚”论不仅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公安派诗歌创作的俚俗之弊,也使自身创作陷于幽深孤峭不可自拔,竟陵后学也因此形成愈加尖新幽深的诗歌风格,由此造成论诗家群起而攻之的局面。
四、结语
竟陵派诗论之“厚”,虽然存在缺陷,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把“厚”这一文学批评范畴提到了世人眼前。贺孙怡《诗筏》在此基础上对“厚”的阐发,更使得“厚”的理论价值逐渐浮出水面,对此,有学者认为:“《诗筏》对‘厚’的密集讨论,不要说在历代诗话中绝无仅有,在古代诗学文献中也罕见其俦,不能不让我们感觉到其中隐藏着一个较大的理论抱负”[18]65。由此可见,“厚”在古代文学与文论中的重要性。本文通过对竟陵派诗论“厚”的分析,认为,竟陵诗论“厚”在针对不同对象时,有不同的意义。当钟、谭想要以“厚”矫公安之弊时,“厚”便有了复古派所倡导的温柔敦厚的诗学内涵。但当竟陵派想要以“厚”救己之失时,因竟陵派对求新、求奇、求幽的追求,致使他们追求的“厚”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厚”有所偏离,且有了以“厚”寻“幽”的倾向,这就成为了竟陵诗论为人诟病的原因之一,也是其诗论的独特之处,值得深究。
注释:
① 钟惺、谭元春《诗归》五十一卷,明刻本,为《古诗归》与《唐诗归》合刻本。文中所引《诗归》均出自此处,不再一一注释,仅在文中标注卷数。
——竟陵派对晚明文学的反思与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