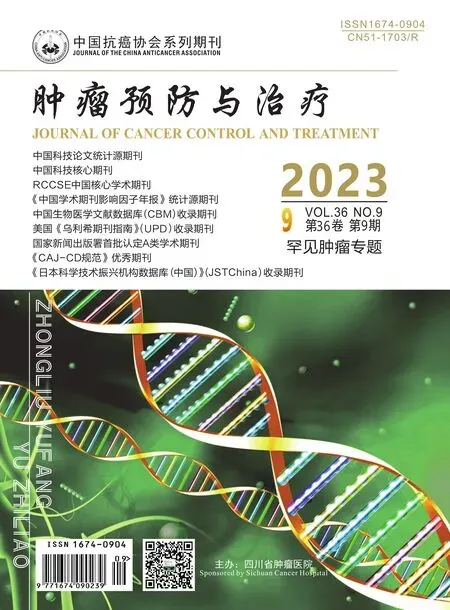复发转移性腺样囊性癌的治疗进展*
葛俊,林桐榆
610041 成都,四川省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四川省肿瘤医院·研究所,四川省癌症防治中心,电子科技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肿瘤内科
腺样囊性癌(adenoid cystic carcinoma,ACC)是一种罕见的肿瘤,大部分原发于头颈部,约占所有头颈部恶性肿瘤的1%。它主要起源于涎腺,约占所有恶性涎腺肿瘤的20%。ACC 是小涎腺最主要的恶性肿瘤,占小涎腺肿瘤的60%。其也见于大涎腺,包含腮腺、下颌下腺和舌下腺。罕见原发部位包括鼻旁窦、鼻咽、泪腺和乳腺、肺、宫颈和皮肤的腺体组织[1-2]。据报道,ACC 的发病率在每百万人中约为3~4.5 例,其发病高峰年龄在40~60 岁,女性占60%[3-4]。ACC 虽然生长缓慢,且初治时常不伴淋巴结转移,但其极易复发和远处转移,长期预后不佳[5]。欧洲一项大规模的研究显示其10 年生存率为65%[6],而另一项研究显示其5 年、10 年和20 年生存率分别为68%、52%和28%[7]。法国一项大型前瞻性研究的最新结果显示,患者5 年和10 年存活率分别为85%和67%[8]。5 年后局部复发率接近40%,而远处转移率8%~60%,平均转移时间为5 年[9-10]。其转移途径主要是血源性转移,肺(70%)、骨(6%)、肝(3%)是最常见的受累部位,而脑部或多个部位的受累则很少。罕见的情况下,可以出现沿颅神经的神经周围扩散所致的颅内转移瘤[11]。由于复发转移性腺样囊性癌(recurrent or metastatic adenoid cystic carcinoma,RM-ACC)的治疗手段有限、疗效欠佳,本文将主要从临床病理特征、分子特征、放射治疗、全身化疗、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等方面介绍治疗进展,为临床提供参考。
1 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
组织病理学上,ACC 有筛状、管状或实体型肿瘤三种类型,其主要结构类型决定了肿瘤的分级[12]。实体型生长模式的ACC 侵袭性更强,预后不良。局部浸润是该疾病的特征,容易接近或累及切缘,切缘阳性是其不良预后因素[1,4,13]。 神经周围浸润 (perineural invasion,PNI) 可见于40%左右的患者,也是预后不良的独立因素[14]。无症状的PNI 可在组织病理学中检测到。临床上也可以通过颅神经相关症状及影像学发现PNI[15]。神经侵犯是ACC 一个重要的病理特征,也是肿瘤扩散到颅底的直接途径[16-17]。
淋巴血管侵犯 (lymph vascular invasion,LVI) 可能发生在5.2%~72.5%的患者中。LVI 与实体型肿瘤、淋巴结转移、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降低和无病生存期缩短相关[18]。区域淋巴结受累不常见,但少量研究也报告17%~29%的病例有淋巴结转移。淋巴结转移是重要的预后因素,与远处转移和生存率降低相关[19-21]。选择性颈部淋巴结清扫术主要适用于T3 和T4 的肿瘤,对临床评估N0 的患者进行选择性颈部淋巴结清扫术未能带来确切的生存获益[22-23]。
ACC 患者术后远处转移很常见,累计发生率近60%。血行扩散常发生在肺、肝和骨,其中最常见的转移部位是肺,发生率在 50% 以上。大多数远处转移发生在诊断后 5 年内,但10% 的患者在10 年后也可能发生远处转移[7,21]。然而,对于其中侵袭性较强的病例,75% 的患者在诊断后3 年内死亡[10]。因此,ACC 的自然病程往往是在经历无疾病生存期之后出现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预后并不理想[24]。Girelli 等[25]分析了从原发性疾病首次治疗结束到出现转移的无瘤间隔时间(disease-free interval,DFI)与总生存率呈正相关。DFI>3 年的患者的OS 为76.5 个月,而DFI < 3 年的患者为47.7 个月。 Hirvonen 等[26]也证实了DFI 对5 年OS 和疾病特异性生存率有显著影响(P < 0.001)。
2 分子特征与预后
ACC 的分子特征可能有助于识别预后不佳和需要进行积极治疗的患者,并有助于发现新的治疗靶点。最常见的基因突变是是t(6;9)(q22-23; p23-24) 易位,导致原癌基因MYB 和转录因子基因 NFIB融合为MYB-NFIB, 从而引起MYB 蛋白过表达[27-28]。研究也发现MYB 家族的另一个成员MYBL1 基因与NFIB 基因的融合突变[29-30]。约88%的ACC 包含MYB、MYLB1 或 NFIB 基因易位[31]。11%~29%的ACC 发生Notch 基因突变。Notch 通路激活突变会促进癌细胞的生长和抑制细胞凋亡。Notch 基因改变与实体型肿瘤、转移及预后不良有关[32]。MYB 和Notch 通路可能是潜在的治疗靶点[33-34]。
在局限性ACC 患者中,目前研究发现对预后有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NOTCH1 突变[35]、TP53 突变[36]、SOX2 扩增[37]和EGFR 突变[38]。MYB-NFIB融合基因对预后的影响仍不清楚[39]。另外,ACC 复发转移病灶中的基因突变可能会在原发性疾病基础上发生改变。这也提示了二次活检的意义,基因的变异可能有助于研究基于分子改变的靶向治疗[40]。有研究者分析了RM-ACC 和局限性ACC 之间的不同遗传特征,复发转移灶的NOTCH(尤其是NOTCH1)、染色质重塑基因(KDMSA、MLL3 和ARID1B)和TERT 启动子突变发生率更高[32]。在ACC 的原发灶和转移灶中,分别发现8%和26%的NOTCH 家族(主要是NOTCH1)突变。此外,研究也证实NOTCH1 突变的患者预后不良。在复发转移病灶中,比局限性疾病中更常见的其他突变还有KDM6A(15.2% vs 3.4%;HR:5.12,P = 0.0001)、MLL3/KMT2C(14.3% vs 4.0%)、ARID1B(14.1% vs 4.0%)、ARID1A(13.7% vs 2.3%)、BCOR(13.3% vs 1.7%)、MLL2/KMT2D(12.8% vs 4.5%)和CREBBP(11.1% vs 4.5%)。与KDM6A 野生型基因的患者相比,KDM6A 突变提示预后不良。然而,在RMACC 中,MYB/MYBL1 的改变并没有提示不良预后,但MYB 野生型/NOTCH1 突变型和MYB 突变型/NOTCH1 突变型均预后较差[41]。
3 目前的治疗进展
3.1 手术
初治的局限性ACC 治疗的基本原则是根治性手术后辅助放疗[42]。头颈部ACC 的解剖位置、局部侵袭性和神经周侵犯的特点,决定了其治疗往往需要进行广泛的头颈部手术。然而,在50%~64%的患者中,切缘太近或被肿瘤侵犯,依然很难达到切缘阴性[1,4]。但是,即使切除后显微镜下切缘阳性,手术治疗联合术后放疗也能带来局部控制获益[43]。例如,在1 项晚期颅底受侵的个案报道中,虽然许多患者显微镜下切缘阳性,但其5 年和10 年局部区域控制率仍然达到88.2%[35]。
转移瘤切除术的价值目前也有争议。回顾性研究调查了在肺转移患者中转移瘤切除术的作用。结果表明,DFI 大于3 年,且转移瘤切除术后无残留病灶,是预后较好的两个相关因素[25,44]。对于肺转移的ACC 患者,仍缺乏足够的研究评估其他局部治疗的作用;对于其他部位转移的ACC 的局部治疗手段,也仅有少量的个案报道,如肝转移的栓塞或射频治疗[45]。因此,目前局部治疗的主要目的依然是延缓疾病的发展,延迟全身治疗的时间,以及缓解症状。
3.2 复发和转移病灶的放疗
术后放疗可降低初诊ACC 术后的局部复发率。虽然对于RM-ACC 术后放疗的数据相对较少,但依然建议在患者二次手术后进行放疗。尤其是在多病灶复发、淋巴结包膜外侵犯、神经周围扩散至颅底的患者中,放疗的作用更为重要[46]。对于局部复发无法行根治性手术的患者,根治性放疗也作为一种有效的替代方法。目前采用光子、重离子等放射治疗技术均能在疾病部位达到相对较高的剂量[47-49]。重粒子放射治疗(如碳离子、质子)有助于降低危险器官的剂量[50]。然而,重离子放射治疗也有其局限性,比如对于既往进行放射治疗后的区域内器官的剂量控制,及其在辅助治疗中使用,疗效仍不确切。此外,临床评估可通过放射治疗延缓疾病进展或缓解症状的患者,也可考虑接受寡转移灶的放疗。
3.3 化疗
RM-ACC 全身化疗的证据水平仍然较低,因为该疾病生长缓慢,药物敏感性差。Hanna 等[45]在72个RM-ACC 的队列研究中报道了与仅接受观察等待的患者相比,至少接受过一次全身治疗的患者预后没有改善(HR:2.01, P = 0.35)。目前主要将化疗用于不适合手术和放疗,且有症状或肿瘤增长较快的RM-ACC 患者[51-53]。由于癌细胞生长缓慢,大多数接受化疗的患者最佳疗效仅为疾病稳定(stable disease,SD)。
Dodd 等[54]对2006 年之前所发的关于ACC 化疗方案的 25 篇文献进行总结,单药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从高到低依次为氟尿嘧啶39.5% (33%~46%)、顺铂35% (0%~70%)、蒽环类26.5% (10%~43%),烷化剂、甲氨蝶呤均为0%,但很多研究的样本量都较小。缓解率超过氟尿嘧啶(39.5%)的联合方案有CAPF (环磷酰胺、阿霉素、顺铂、5-氟尿嘧啶,46.5%)和CA 方案 (环磷酰胺、阿霉素,40%)。CAPF 方案似乎ORR 占优,但是这种联合治疗方案的毒性反应并未评价。因此,必须要注意4 药联合方案化疗的不良反应。Airoldi 等[55]的研究也发现在ACC 中,接受联合化疗(顺铂、表柔比星、5-氟尿嘧啶或环磷酰胺)的患者[完全缓解(complete remission,CR):9.1%;部分缓解(partial remission,PR):36.3%]比接受单药化疗(顺铂或阿霉素)的患者(PR: 23%,CR: 0%)表现出更好的客观缓解和更长的缓解时间。
Cherifi 等[56]在2019 年对头颈部RM-ACC 的内科治疗方案做了系统评价,顺铂、米托蒽醌、长春瑞滨单药,以及顺铂+长春瑞滨联合方案的ORR均< 10%。Laurie 等[53]对 1950 年至 2010 年发表的晚期转移性ACC 进行了系统评价,总体缓解率为0%~15.4%。紫杉醇(EPRTC 24982)、吉西他滨(E1394)ORR 为0%; 顺铂、长春瑞滨的ORR 均为15.4%,所以在晚期转移性ACC 中不推荐使用紫杉醇和吉西他滨。与单药化疗相比,含铂蒽环类的两种药物联合化疗具有更好的疗效(ORR: 25%vs 15%);三药方案(如含顺铂、阿霉素和环磷酰胺的CAP 方案)并未比双药方案明显增效。
3.4 靶向治疗
ACC 的肿瘤突变负荷较低,而且到目前为止,还缺乏可明显改变疾病发展的靶向驱动基因。采用靶向EGFR、干细胞因子受体、蛋白酶体、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或蛋白激酶B 的单药治疗并未带来明显的肿瘤缓解和生存获益。几项小型II 期试验的对几种药物的疗效进行了评估,包括在接受西妥昔单抗[57]、伊马替尼[58]、硼替佐米[59]、多维替尼[60]和达沙替尼[61]单药治疗的患者中,ORR 非常有限。化疗联合伊马替尼或硼替佐米的治疗方案,也没有显示出协同效应[50,59]。下面,我们将分别介绍几类靶向药物在RM-ACC 中的进展。
3.4.1 抗血管生成药物 MYB 过表达可能导致包括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干细胞因子受体、成纤维生长因子和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受体等基因上调,并参与肿瘤血管生成[62]。NOTCH1 突变也可诱导新生血管生成和高微血管密度,成为肿瘤生长和转移的机制[63]。因此,在ACC 中使用抗新生血管的药物具备理论依据。探讨索拉非尼(Sorafenib)的两项II 期临床研究分别在19 名和23 名RM-ACC 患者中进行。研究发现,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分别为8.9 和11.3 个月,中位OS 分别为26.4 和19.6 个月。治疗中分别有20%和50%的患者发生了3 级或以上不良反应。两项研究中患者客观反应率均为15%。探索性分析发现在获得客观缓解的肿瘤基质中,有较高的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64-65]。阿昔替尼(Axitinib)是第二代抗血管生成药物,其在ACC 患者中的有效率约10%,在OS 方面与化疗相比无明显优势[66]。一项在ACC 中进行的随机试验将过去9 个月内病情进展的患者随机分为阿昔替尼(5 mg,每天两次)或观察组,并允许在进展时交叉使用阿昔替尼。 阿昔替尼组中位 PFS 延长(10.8 个月vs 2.8 个月,P < 0.001),阿昔替尼组6 个月PFS 率为73.0%,观察组为 23.0%。治疗组ORR 为0.0%,但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DCR)为100.0%,观察组DCR 为51.9%。阿昔替尼组中位OS 未达到,观察组为 27.2 个月(P = 0.226)[67]。仑伐替尼(Lenvatinib)是也一种口服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对VEGFR、c-KIT、FGFR 和RET 有显著抑制作用。最近有两项将该药用于ACC 患者的II 期研究[68-69]。一项研究结果显示,75%的患者SD,15%的患者PR,中位PFS 为17.5 个月。62.5%的患者发生了3~4 级不良事件,1/4 的患者由于药物相关的原因退出了研究。在另一项意大利的II 期临床试验中,11.5%的患者出现PR,77% SD,中位PFS 为9 个月。2019 年欧洲肿瘤学会报道了采用新型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抑制剂安罗替尼(Anlotinib)在复发转移性涎腺恶性肿瘤患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21例复发转移性涎腺肿瘤中有11 例ACC(52.4%),ORR 为19.1%,DCR 为81.0%,安罗替尼显示出较高的DCR,毒性可耐受(NCT 03591666)。阿帕替尼(Apatinib,Rivoceranib)是一种新型口服小分子血管生成抑制剂,通过靶向VEGFR-2 有效抑制肿瘤血管生成并降低肿瘤生长。Wang 等[70]2017 年报道了1 例多线治疗后的气管ACC 患者,口服阿帕替尼后肿瘤缩小,症状明显缓解。Zhang 等[71]2021 年观察到1 例泪囊ACC 患者采用阿帕替尼和奈达铂为基础的同步放化疗后3 周CR,并在治疗后 22 个月仍未复发。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医院朱国培教授团队在2021 年发表了采用阿帕替尼治疗RMACC 的II 期单臂前瞻性研究结果。在可评估疗效的65 例患者中,6 个月、12 个月和24 个月的PFS发生率分别为92.3%、75.2%和44.7%。研究者评估的ORR 和DCR 分别为46.2%和98.5%,中位缓解时间为17.7 个月。3~4 级最常见的不良事件为高血压(5.9%)、蛋白尿(9.2%)和出血(5.9%)。该研究观察到令人鼓舞的疗效和生存获益[72]。该团队另一项采用全反式维甲酸联合低剂量阿帕替尼治疗头颈部RM-ACC 的II 期研究在2021 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ASCO)报道了研究结果。共有16 名患者入组,4 例(25%) 患者为 三线治疗,12 例(75%) 为二线治疗。其中,ORR 为19%,DCR 为100%,同样带来了令人鼓舞的结果。由于采用低剂量阿帕替尼,副反应明显降低。全反式维甲酸作用于ACC 的原理可能是抑制ACC 中MYB-NFIB 融合基因和NOTCH1 突变基因的表达[73]。该疗法的II 期随机研究还在进行中(Aplus 研究,NCT04433169)。2022 年ASCO 大会上,研究者们报道了阿帕替尼在RM-ACC 患者中开展的II 期RM-202 研究的结果(NCT04119453)。在美国和韩国的11 个中心入组的80 名患者中(72 名疗效可评估),既往接受过或未接受过全身治疗的患者里,ORR 分别为13.9%和16.9%,按照CHOI 标准评估的总人群ORR 为50.8%。阿帕替尼已经获得FDA 治疗ACC 孤儿药资格,其疗效数据值得期待。总的来说,目前多项研究初步证实了抗血管生成药物在RM-ACC 中具有一定的疗效,但同时也应该综合考虑这些药物的毒性。
3.4.2 靶向EGFR 的药物 EGFR 在约85%的ACC病例中高表达。然而,抗EGFR 治疗在ACC 的治疗中显示的疗效有限[57]。EGFR 单克隆抗体(mAb)通过抗体依赖性细胞毒作用(antibody dependent cell-mediated cytotoxicity, ADCC)、抑制磷酸化产生抗肿瘤作用[74]。西妥昔单抗中的IgG1 结构是ADCC 的有效介质,其清除肿瘤细胞的机制有别于小分子络氨酸激酶抑制剂对肿瘤细胞的抑制作用[75]。目前有多项采用西妥昔单抗、小分子EGFR抑制吉非替尼和泛HER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拉帕替尼单药治疗RM-ACC 的小样本I~II 期研究,但都未观察到明显的客观缓解[76]。尽管抗EGFR 治疗在肺癌、乳腺癌、肠癌等其它肿瘤中的结果令人鼓舞,但旁路信号的激活或靶点的过表达可能导致耐药[77-78]。不同类型肿瘤的异质性也可能导致肿瘤细胞中EGFR 靶点在跨膜区和细胞内的水平存在差异[79],因此抗EGFR 治疗不一定对所有表达EGFR的肿瘤中都起效。然而,Hitre 等[80]采用西妥昔单抗联合顺铂和氟尿嘧啶方案化疗,在EGFR 阳性的转移性ACC 患者中,观察到了42%的ORR,提示靶向治疗联合化疗或许是一种选择。最近,一项采用小分子EGFR 络氨酸激酶抑制剂治疗晚期ACC的研究(NCT04974866)还在进行中。
3.4.3 靶向HER-2 的药物 在HER-2 阳性的ACC中,一些研究已证实曲妥珠单抗联合多西他赛,或曲妥珠单抗联合帕妥珠单抗能为患者带来60%~70%的ORR 及8.5~8.9 个月的PFS[81-82]。除此之外,恩美-曲妥珠单抗及德喜-曲妥珠单抗等抗体偶联药物也显示了潜在疗效[83]。
3.4.4 靶向罕见驱动基因突变的药物 RET 基因融合突变在唾液腺癌中很少见。塞普替尼是一种选择性RET 激酶抑制剂,一项开放性I~II 期篮式试验(LIBRETTO-001)在41 例既往全身性治疗期间病情进展的RET 融合阳性患者中评估了该药物[84]。在4 例唾液腺肿瘤患者亚组中,2 例(50%)获得客观缓解,未达到中位缓解持续时间。3 级及以上毒性包括高血压(22%)和血清氨基转移酶升高(13%~16%)。但由于患者数量有限,尚不清楚塞普替尼用于唾液腺肿瘤的真实临床获益,还需要进一步的数据证实。基于这些数据,FDA 加速批准了塞普替尼用于既往全身性治疗期间或治疗后病情进展或者无满意替代治疗的RET 基因融合阳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实体瘤成人患者。BRAF V600E 也是在实体瘤中存在的一种罕见突变。对于BRAF V600E突变且无其他有治疗意义的基因突变的转移性唾液腺肿瘤患者,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显示出较好的疗效和安全性[85]。达拉非尼和曲美替尼已获FDA的加速批准,用于有BRAF V600E 突变、前线治疗后病情进展的任何不可切除或转移性实体瘤。
3.4.5 其它靶向药物 针对表观遗传学变异的药物在治疗ACC 方面进行了尝试。在一项前瞻性试验中,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istone deacetylase, HDAC)抑制剂伏立诺他单药显示出一定的ORR(7%),6 个月的SD 为75%[86]。然而,HDAC 抑制剂在联合治疗中可能发挥协同作用。在临床前模型中使用伏立诺他联合顺铂显示出杀伤肿瘤干细胞并降低肿瘤生存的能力[87]。此外,HDAC 可能通过上调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1)表达来影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疗效。然而,在一项II 期研究中,伏立诺他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治疗RMACC 依然疗效欠佳,在12 名接受治疗的患者中,只有一名患者获得了部分反应[88]。另外一项评估西达苯胺在头颈部ACC 患者中疗效和安全性的研究(NCT02883374),结果尚待公布。MYB 易位突变的ACC 的另一个治疗靶点可能是IGF2-IGF1R 信号通路,但体外使用IGFR1 抑制剂获得的阳性结果尚未在体内得到证实[89]。RM-ACC 可能有NOTCH 家族基因突变,其与侵袭性强和预后较差有关。因此,靶向NOTCH 的药物在ACC 中也进行了研究。探讨Crenigacestat(NOTCH 抑制剂)的I 期研究显示,其安全性良好,但无客观缓解[90]。另一种口服NOTCH抑制剂(CB-103)及其联合抗凋亡药物venetoclax 的有效性正在验证(NCT03422679,NCT05774899)。Brontictuzumab 是一种针对NOTCH-1 受体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具有潜在的抗肿瘤活性,在一项I 期研究中,12 例RM-ACC 患者中有2 例出现PR,3 例SD[91]。AL101 是一种抑制γ 分泌酶的小分子抑制剂,γ分泌酶通过从膜上释放所有四种Notch 受体的胞内结构域在激活Notch 信号通路中起关键作用的酶。ACCURACY 研究[92]评估了AL101 在NOTCH 突变的RM-ACC 中的疗效和安全性。最近,第1 个治疗队列的数据显示,每周接受4 mg AL101治疗的患者中,15%的患者达到PR(NCT03691207),副反应主要是腹泻、恶心和疲劳。在RM-ACC 患者中BRCA1 或BRCA2 胚系突变率为4%[41]。Andersson 等[93]的试验表明,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和RAD3 相关激酶(ataxia telangiectasia and RAD3-related kinase,ATR)作为DNA 损伤修复的关键激酶之一,在MYB 突变的ACC 中过表达,可能成为潜在的治疗靶点。此外,在其它肿瘤中已被证实抑制ATR 可能逆转PARP 抑制剂耐药。ATR 抑制剂与PARP 抑制剂联合也可能是MYB 突变的RM-ACC的潜在治疗方式[93]。最近,一项体外研究结果提示CDK 抑制剂dinaciclib 在ACC 中可能增加化疗的疗效并减少副作用[94]。
3.5 免疫治疗
免疫治疗在肿瘤领域越来越重要。ACC 的分子和组织病理学特征表明其免疫原性较低,具有较低的肿瘤突变负荷、较低的肿瘤浸润淋巴细胞、树突状细胞、较低的PD-1 和CTLA-4 阳性细胞比例[95-96]。KEYNOTE028 研究中帕博利珠单抗治疗RM-ACC的初步数据显示,6 个月的OS 率为76%,6 个月的PFS 率为17%。在20 个月的随访中,3 名患者获得PR,ORR 为12%,没有CR 的患者。中位缓解时间为4 个月[97]。在1 项多中心II 期试验中,纳武利尤单抗的有效率为8.7%,中位PFS 为4.9 个月。2021 年ASCO 报道了nivolumab 和ipilimumab 联合治疗的II 期试验结果,在32 名患者中只有两名患者获得PR(NCT03172624)。RM-ACC 对免疫检测点抑制剂单药治疗的疗效不佳,可能与肿瘤中免疫细胞浸润较少有关,联合治疗或许能起到相对更好的疗效。Mahmood 等[98]2021 年发表的另1 项II 期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发现,与单纯免疫治疗相比,免疫治疗联合低分割放疗治疗快速进展的转移性ACC 并没有提高ORR 和PFS,但联合放疗降低了肿瘤生长速度。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MYB DNA 疫苗的临床研究正在进行[99]。另外,帕博利珠单抗联合仑伐替尼、avelumab 联合阿昔替尼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NCT04209660,NCT03990571)。
趋化因子受体-4(chemokine receptor type 4,CXCR4)在许多肿瘤中表达,其可能参与先天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在ACC 中,CXCL12/CXCR4 可能通过刺激肿瘤细胞通过Twist/S100A4 轴促进肿瘤细胞向Schwann 样细胞分化来促进周围神经侵害[100]。Klein Nulent 等[101]发现在81%的原发性ACC 中存在CXCR4 表达,其与神经和骨骼侵犯独立相关,CXCR4 高表达可能增加局部复发风险。目前已有研究证实在荷瘤小鼠模型中,CXCR4 特异性抑制剂AMD3100 显著降低了神经侵袭率。另外,正在研发中的靶向CXCR4 的放射性核素在未来能否用于ACC 的诊断和治疗也值得期待[102-103]。
4 总 结
本文主要介绍了复发转移性头颈部ACC 的临床病理特征、分子特征、预后因素,以及放射治疗、全身化疗、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等方面的进展。由于该类疾病十分罕见且具有惰性、侵袭性的生物学行为,目前尚无特别有效的药物。部分抗血管生成药物显示了一定的疗效。MYB、NOTCH1 有望成为未来治疗的靶点。而迄今为止,作用于其他途径(如EGFR、γ分泌酶、C-KIT 和HDAC)的靶向药物并不令人满意。免疫治疗的疗效欠佳,可能与这类肿瘤的免疫原性较低相关。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和对肿瘤基因组的深入研究对于开发针对这种罕见肿瘤的有效药物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