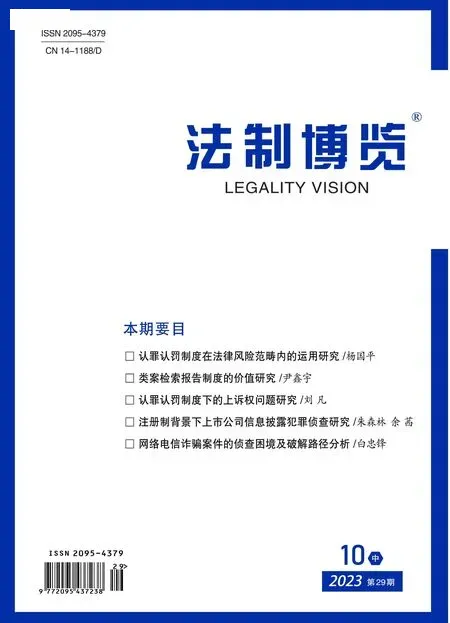遗赠扶养协议的不足及其完善
王 雷
江西理工大学,江西 赣州 341000
一、遗赠扶养协议制度的立法背景
在我国民法中,广义的“扶养”义务主要包含以下三种:一是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二是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三是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从这个角度来看,遗赠扶养协议制度所规定的扶养义务并不属于以上三种法定义务,而是一种意定义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已废止)第三十一条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条规定了遗赠扶养协议的扶养人必须是“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新修改的遗赠扶养协议制度通过明确扶养人的主体范围引入了社会力量来参与到养老事务中,彰显了我国立法工作的与时俱进。然而,我国的遗赠扶养协议制度尚不完善,仍有许多可以改善的空间。
二、遗赠扶养协议制度的不足
(一)扶养人权利难以保障
遗赠扶养协议签订后,遗赠人即享有扶养请求权,但是扶养人的遗赠请求权须待遗赠人死后向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主张。这两种权利产生的异时性和义务主体的错位性,导致扶养人可能无法在遗赠人死后取得遗赠财产。[1]具体来看,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遗赠人生前的处分行为
遗赠扶养协议成立后,遗赠人对扶养人的扶养请求权立即生效,但此时扶养人尚不具有遗赠请求权。按照《遗赠扶养协议公证细则》第十四条,遗赠扶养协议公证后,未征得扶养人同意,遗赠人不得另行处分遗赠的财产。对于未办理公证的遗赠扶养协议,现行法并未限制遗赠人的生前处分权限,遗赠人对遗赠财产当然享有处分权。因此,对于那些未经公证的遗赠扶养协议,是不能充分保障扶养人的受遗赠权的。不论财产是否特定,只要未经公证,遗赠人仍然有权进行生前处分,因为《民法典》第二百三十条①《民法典》第二百三十条:因继承取得物权的,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不再承认普通遗赠能够产生物权变动,因此,普通遗赠仅发生债权效力。如果第三人不是善意的,不满足善意取得的条件,那么尽管第三人并不能享有特定财产的所有权,扶养人此时也并不能对第三人行使任何权利,原因在于此时的扶养人并不享有遗赠请求权。
2.遗赠扶养协议效力优先性不明
遗赠财产与被扶养人生前所负债务等冲突时,缺乏对优先性的明确规定。遗赠扶养协议效力的优先性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中规定,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优先于其他继承方式。但是《民法典》又在第一千一百四十一条和第一千一百五十五条规定了继承人必留份和胎儿预留份,这就导致了此种情况的发生:一是如果遗赠人生前既同扶养人签订了遗赠扶养协议,同时又立有遗嘱,遗嘱对缺乏劳动能力同时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胎儿保留了必要份额,按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此时的遗嘱应当不发生效力才对,但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继承编司法解释(一)》)中第二十五条和第三十一条又规定了遗产处理时应当为上述继承人保留必要份额,使得《民法典》和《继承编司法解释(一)》的规定自相矛盾。再一个问题就是遗赠财产与被扶养人生前所负债务冲突时法律并没有给出具体方案。《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三条规定了限定继承原则,在限定继承的框架下,遗赠扶养协议的优先效力是受限于其框架而低于被扶养人生前所负债务,还是为保护扶养人获得遗赠的权利突破限定继承原则规定不明确。[2]
(二)扶养人范围过于狭窄
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条明确了遗赠扶养协议中扶养人的主体为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将法定继承人排除在外。尽管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①《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遗赠扶养协议的发生效力是优于法定继承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遗赠扶养协议和法定继承是互相排斥、非此即彼的,事实上基于血缘关系和情感纽带,被扶养人往往更愿意和法定继承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第一,法定继承人和扶养人是不矛盾的,一般情况下法定继承人和扶养人的身份是重合的,但在实践中法定继承人并不是扶养人,遗赠扶养协议制度解决的就是这部分问题;第二,赡养义务并不等同于扶养义务,实践中往往会出现老人的多个子女因为工作忙、嫌弃老人等原因而通过赡养费的形式履行赡养义务,并未尽到对老人生养死葬的扶养义务;第三,遗赠扶养协议是一种有关人身关系的协议,这种人身关系往往需要协议双方对彼此具有高度的信任感。例如,老人同小王签订了遗赠扶养协议,因突发疾病被小王送进医院,医生一定会因为小王不是病人家属而拒绝透露老人病情,小王也无法凭借扶养人的身份选择为老人保守治疗还是动手术,甚至扶养人小王还可能会萌生出消极扶养老人的念想。如果老人能够在众多法定继承人中选择一个信得过的并与之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上述问题仿佛都迎刃而解了。
(三)解除条件难
关于遗赠扶养协议的性质,司法审判实践中有三种观点,第一,认定遗赠扶养协议属于一般民事合同;第二,认定遗赠扶养协议属于人身关系的协议,但是可以参照合同法适用;第三,仍然认定遗赠扶养协议属于人身协议,基于信任关系的丧失赋予遗赠人以任意解除权。第一种是在“艾某与韩某、关某赡养纠纷”②参见“艾某与韩某、关某赡养纠纷案”,秭归县人民法院(2019)鄂0527 民初558 号。一案中,法院首先认定遗赠扶养协议属于一般民事合同,在此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已废止,以下简称原《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二项同意解除扶养人关某与被扶养人艾某的遗赠扶养协议;第二种是在“孙某君与张某军、刘某连遗赠扶养协议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③参见“孙某君与张某军等遗赠扶养协议纠纷案”,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2019)鲁0911 民初845 号。中法院认为,遗赠扶养协议是遗赠人与扶养人之间订立的有关遗赠和扶养关系的协议,但协议的解除须参照原《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情况进行;第三种情况是将遗赠扶养协议认定为人身协议,被扶养人或扶养人基于人身信任关系拥有任意解除权,如“韦某与吴某遗赠扶养协议纠纷一案一审民事判决书”④参见“韦某与吴某遗赠扶养协议纠纷案”,惠水县人民法院(2019)黔2731 民初987 号。中,法院因遗赠扶养协议具有人身属性,故支持原告解除双方遗赠扶养协议的要求。纵观以上三种观点,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没有考虑到遗赠扶养协议的人身属性和立法体例,尽管扶养人属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但是这种扶养关系的存在须基于信赖利益的存在,因此将其规定在《民法典》继承编而不是合同编;第二种观点,笔者认为是合理的,遗赠扶养协议属于一种人身关系的协议,《民法典》第四百六十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特殊情况下参照合同编适用,遗赠扶养协议在继承编无规定的情形下当然可以参照合同编条文进行适用;第三种观点笔者认为也是有道理的,扶养人与遗赠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具有很强的人身关联性,须基于双方对彼此的信任。
三、遗赠扶养协议制度的完善
(一)扩大扶养人主体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将法定继承人排除在扶养人主体范围之外,被扶养人与法定继承人之间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无效,这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在社会实践中许多老人确实希望通过与某个法定继承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的形式使其参与到自身养老中。扩大遗赠扶养协议的扶养人主体,将法定继承人纳入其中,基于情感纽带和血缘关系的扶养关系,更有利于维护遗赠扶养协议的稳定,使遗赠扶养协议制度得到最大价值发挥,也为老人养老创造一个身心愉悦的环境。
(二)明确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优先性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是优先于法定继承的,因此扶养人的受遗赠权一定是优先于继承人必留份的;但是在受遗赠权和胎儿预留份之间,尽管民法规定了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但是这里的胎儿是作为继承人出现还是法律的特殊规定我们无从得知。如果胎儿是作为继承人出现的话,那么其继承权将不能阻却扶养人的遗赠权;如果这是一条特殊规定,则其继承权将优先于扶养人的遗赠权。在受遗赠权和债务之间,债务分为普通债权、担保物权和公共债权,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受遗赠权作为一种金钱债权应属于普通债权,与其他普通债权相比应当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清偿,与其他优先债权相比受遗赠权的清偿效力要低一些,但是如果发生遗赠人在协议之前向第三人举债并以该财产遗赠给扶养人或者遗赠人在协议之后向第三人就遗赠物进行抵押,扶养人的受遗赠权很难得到保障。至于受遗赠权与公共债务,我国法律更是没有明确,虽然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效力要低于公共债务的清偿效力,但是我们无法据此得知受遗赠权与公共债务哪个效力更优先。
(三)发挥公证制度的优越性
针对遗赠人生前擅自将遗赠物进行抵押等行为,由于主体的错位性和权利的异时性,扶养人在履行完扶养义务后,其遗赠权低于担保物权的优先效力,很难得到保障。尽管我国法律并未强制规定遗赠扶养协议只有经公证后才能生效,但是却在《遗赠扶养协议公证细则》第十四条①《遗赠扶养协议公证细则》第十四条:订立遗赠扶养协议公证后,未征得扶养人的同意,遗赠人不得另行处分遗赠的财产,扶养人也不得干涉遗赠人处分未遗赠的财产。规定了遗赠扶养协议经公证后未经扶养人同意不得处分遗赠财产,这样的规定对于遗赠人来说限制了其生前处分遗赠财产的行为。缪宇老师在《遗赠扶养协议中的利益失衡及其矫治》一文中对该项规定是否对遗赠人的生前处分行为进行限制作了详尽的分析,笔者本人也更倾向于限制说,即该项规定对遗赠人的生前处分行为进行了限制。如果经公证后的遗赠扶养协议没有限制遗赠人的生前处分行为,那么该项规定毫无意义。《遗赠扶养协议公证细则》第十四条应当是起到了一种类似于效力待定的效果,非经扶养人追认第三人不能取得遗赠物的所有权,尽管在遗赠人生前扶养人不享有遗赠请求权,但是在遗赠人死后扶养人可以请求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行使对第三人的返还原物请求权,法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怠于行使的,扶养人可以代位行使;第三人已经善意取得遗赠物的,法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应当以遗赠物的实际价值为限对扶养人履行金钱债务。
(四)完善遗赠扶养协议的解除权
1.法定解除权
《民法典》第四百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了遗赠扶养协议这种具有人身性质的协议在规定不明确时可以参照《民法典》合同编适用,因此在当事人双方对遗赠扶养协议的解除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可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项下的条款解除协议。
2.任意解除权
司法实践中认为,由于扶养的内容包括扶养人对遗赠人在精神上的照顾、扶养人和遗赠人在感情上的沟通,②参见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中民一终字第00511 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2 民终2763 号民事判决书。且遗赠扶养协议的订立以遗赠人与扶养人特别的信任关系为基础,③参见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01 民终1243 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 民终9866 号民事判决书。因此,遗赠扶养协议具有一定人身性。④参见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威民一终字第1125 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 民终1989 号民事判决书。基于权利的异时性和主体的错位性,为了保护扶养人,应当赋予协议双方当事人以任意解除权,双方当事人也可以在信任关系丧失时行使该权利,但依约履行的扶养人可请求返还扶养费用,双方也可以通过协商根据各自过错程度而予以适当补偿。当然,扶养人还可以通过对具体条款的协商来减少扶养人的风险。例如,针对遗赠人生前擅自处分遗赠标的物的风险,扶养人可以要求在协议中约定“遗赠人不得擅自处分遗赠标的物”的条款以及相应的违约条款,尽管遗赠人仍然能够擅自处分该遗赠标的物,但是扶养人可以通过违约金条款进行相应的利益弥补甚至解除协议。再例如,针对扶养人先于遗赠人死亡的情形,也可适用这种违约金条款,此种情形下扶养人的继承人仍然可以依约要求遗赠人返还已产生的扶养费用,但也应支付遗赠人相应的违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