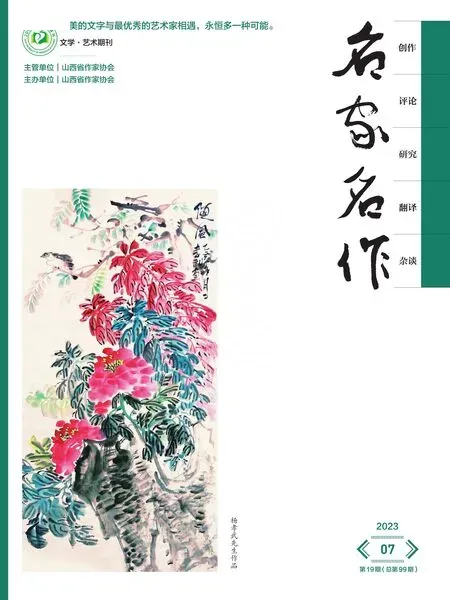父权下自我毁灭式女性文学形象
——以韩江《素食者》中“鸟”的象征意义为中心
王子鸣 张方明*
韩国女作家韩江凭借其女性主义问题小说《素食者》获得2016 年国际布克奖,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作家。《素食者》由原先分开发表的三个故事组合而成,将女主角英惠从“变异”到“解脱”的全过程串联起来。韩江对笔下人物的身体进行了极度细致且露骨的描写,而小说中除了“身体”主线,在每个故事中还存在着一条暗线,作者以“鸟”意象的三种形态来象征故事人物对于父权思想状态的变化历程,同时也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历程。象征手法是根据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借助某人某物的具体形象(象征体),以表现某种抽象的概念、思想和情感。[1]因此理解此问题小说中的象征物,有助于理解其背后深层次的社会性因素。此外,这样的运动并不只是某个国家的任务,了解其他国家的性别平权运动对于自身以及世界的平权运动都具有深刻的意义。
一、父权制作为社会现象
父权制也被称为家父长制,指的是父亲、长男或男性群体拥有在家庭、社会等各方面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性别特权主义制度。作为父权制的理论基础,父权主义与男性的性别优等论共生,将男性作为社会的主体来思考。此外,父权主义总是带有暴力、侵略性质的性别霸权,它标榜有爱心、有责任心的父亲,通过“为了你好”等形式的说法对其他社会成员进行规训。从家庭中“人生模范”型的父亲,到社会上的“男性权威”,都是父权主义的不同体现。
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是导致韩国父权思想浓厚的原因之一。丽末鲜初,朝鲜引入了朱子学,进一步深化其内涵,其结果便是出现了更加严格的纲常礼教,并且影响至今。而西欧国家则是由于私有制的出现而形成了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模式。虽然世界上形成父权制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其影响之深刻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一直以来,在父权和男权者的对立面——女性主义群体中,女性没有一个独立的阶层,作为劳动者,她们受到奴役;而作为资产阶级,她们寄生。[2]韩江把这种病态的社会现实融入自己的作品中,通过各种意象来表现女性在父权制下受到的迫害。如《素食者》中最主要的一个象征物是“树(植物)”——英惠想要变成一棵树来逃避父权。而作为与植物相对的动物,“鸟”这个形象也有多重含义——自我的消亡、自我的解禁和自我的觉醒。
二、鸟的象征性及社会意义
(一)《素食者》篇:自我的消亡
第一个故事以英惠丈夫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叙事,鸟以死亡的形象出现在故事结尾处:
我扒开妻子紧攥的右手,一只被掐在虎口窒息而死的鸟掉在了长椅上。那是一只掉了很多羽毛的暗绿绣眼鸟,它身上留有捕食者咬噬的牙印,红色的血迹清晰地漫延开来。[3]52
从原文中可以看出,鸟被捕食者咬噬过,最终还是被英惠自己掐死。这只鸟象征着英惠自己,她的心从她被送进医院时就已经死去了,而在此之前经历了父权的轮番暴行。从生命流动的时间来看,施暴者首先是父亲,他对英惠从小就采取暴力教育,幼年时的阴影一直没有散去,梦境中出现的肉块,以及梦到自己杀人,都是深层本我的投射。成人结婚后,霸凌英惠的人变成了丈夫,而父亲即使退居“二线”,却仍然以一个典型的家父从侧面控制着英惠的人生,一旦有违“正确的行为准则”,且丈夫控制不住时,英惠父亲就亲自“教育”她了。
男性在父权体制下所追求的,就是成为一位被父权文化所认可的男人。[4]按照父权主义的要求,处于统治地位的男性通常都要具备霸权主义男性特质。康奈尔指出:尽管霸权男性特质在统计学上不占主流,只有少数男性会实践它,但它成为男性特质的规范,是统治女性和其他少数群体的正当性依据。[5]父亲总是以越战自诩,在他尚武的世界观中,只有掌握暴力的强权者才符合他的标准。此后强行塞肉给女儿,也是因为女儿对他行使的父权进行反抗造成了他的进攻行为。父亲作为一个标准的霸权主义男性,是整部小说甚至是英惠生命中唯一的父权得利者。
比起叶霭玲来,白丽筠实在太出色了,以至于我忍不住当着叶霭玲的面谈起了她。我说我回来的路上,在那条绕着沙塘沿弯成一个弧度的半边街上,看见一位骑踏板电动车的女子,那车子款式新颖,造型别致,一边挂一个咖啡色的流线型音箱,真叫一个酷字,更巧的是骑车的女子竟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
此外,《素食者》篇的讲述者——英惠的丈夫,从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择偶原因:
我之所以会跟这样的女人结婚,是因为她没有什么特别的魅力,同时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缺点。……我那二十五岁之后隆起的小腹,和再怎么努力也长不出肌肉的纤瘦四肢,以及总是令我感到自卑的短小阴茎,这些对她来讲都是无关紧要的事。
跟世上最平凡的女子结婚便成了我顺理成章的选择。从一开始,那些用漂亮、聪明、娇艳和富家千金来形容的女子,只会让我感到不自在。
坦白讲,跟这样的女人生活一点意思也没有。[3]2-3
从丈夫的自白中不难看出,他也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缺陷,但是丈夫选择了将就——和一个自己不爱而是适合的女人结婚。从这里可以看出父权主义总是伴随着男性的性别优等论,当所谓的“男性气质”不足时,会以降低配偶女性的标准来平衡自己的不足。若丧失其优势,对于父权主义者来说是一个天大的不幸。因此宁可选择退而求其次也要实现自己的“男性权力”,取得自己的压倒性地位。
此外,母亲、姐姐和姐夫也是隐形的施暴者。康奈尔把男性气质分为四种,分别为霸权性(或支配性)(Hegemony)、从属性(Subordination)、共谋性(Complicity)与边缘性(Marginalization)。[6]小说人物中除了父亲角色的支配性,其他人都属于共谋性,依附于父权者。而每个现时的加害者曾经都是父权受害者:受强权父亲家暴的母亲、自强却自甘被支配的姐姐、经济弱势的姐夫。在面对英惠的反抗时,每一个人都站在了父权的一边——母亲哄骗、姐姐旁观、姐夫侵犯……
至此,可以对鸟的意象作出如下理解:父权及其附庸者即是“捕食者”,而被逼入绝境的英惠选择了对自己肉体的主导权——毁灭,即割腕行为。鸟的死亡也象征着英惠少女本心的死亡,也暗示此时英惠的人际关系出现了第一条裂缝——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告别,同原生家庭决裂。
(二)《胎记》篇:自我的解禁
第二个故事以姐夫的第三人称视角展开叙述,鸟以姐夫的内心世界的隐喻出现:
此时,如果奔向阳台越过她依靠着的栏杆,应该可以一飞冲天,从三楼掉下去的话,头骨会摔得粉碎。他可以做到,也只有这样才能干净地解决问题。但他仍然站在原地,像是被钉在了那里一样。他在这仿似人生最初也是最后的瞬间里,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如同炽焰的肉体,那是比他在夜里拍下的任何画面都要夺目耀眼的肉体。[3]123
如果说《素食者》篇的父亲和丈夫是典型的父权主义者,那么姐夫则比较特殊,是一个初具平等权意识的怀柔的男性形象,他尊重女性的自由选择权,但这样的男性在父权主义的角度下是被排斥的“他者”。作为男性,他自己也成为被父权迫害的对象。
姐夫通过沉溺于艺术工作来逃避男性之间无谓的竞争,文中写道他常常喜欢一个人的工作室,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自己的缺陷才能不为人所知,他才可以脱下棒球帽暴露真正的自己,而无须与其他所谓优质男性作比。从对姐夫的这些描写来看,他自己也是父权体制下无可奈何的牺牲者。最后当他看到英惠沉浸于重获身体自由的身体时,他惊叹于女性自由的光辉而停住要跳楼的脚步。象征姐夫的鸟并无实体,而是将他的姿态化为一只鸟,出现在《树火》篇中姐姐仁惠的观察——
眼前又静静浮现出了他以鸟的姿势想要冲出英惠家阳台栏杆的画面,他那么喜欢在自己的作品里加入翅膀,可当自己最需要的时候,却没有飞起来。[3]164
此外,同样是追求性别解放的姐夫,与英惠不同的是,他采取的做法伤害了他人——他无法自控的肉体出轨直接导致妻子仁惠的崩溃,这种不完全的自我革命便是造成他未能起飞的原因。在仁惠发现两人私通的现场,姐夫的意识立刻回到现实世界,而英惠仍沉浸在强烈的自我实现的世界。姐夫再次失去了性别话语的自由,而英惠已然领悟到了自由话语的重要性,并坚定了继续实现下去的信念。之后她被姐姐送进精神病院。从这里开始,她的人际关系出现了第二条裂缝,同外界的关系断绝,成了社会的局外人。以此为契机,在下一个故事中,英惠依照自己的想法,脱离凡世,如愿成了一棵“树”。
韩江在这部分中对姐夫的避世和精神醒悟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姐夫主动将自己边缘化,但最终因英惠获得了心灵的自由。他试图以飞出阳台的方式来达到彻底自由的目的,但最终却无法放弃生命。从他因英惠而最终无法放弃生命这一点来看,他已经从父权的枷锁中解脱了。
(三)《树火》篇:自我的觉醒
最后一个故事以姐姐仁惠的第三视角叙述,她看到在“树火”里飞出了鲜活的鸟:
救护车行驶在开出祝圣山的最后一个弯道上。她抬起头,看到一只像黑鸢的黑鸟正朝着乌云飞去。夏日的阳光刺眼,她的视线未能跟上那只扇动翅膀的黑鸟。
她安静地吸了一口气,紧盯着路边“熊熊燃烧”的树木,它们就像无数头站立起的野兽,散发着绿光。她的眼神幽暗而执着,像是在等待着回答,不,更像是在表达抗议。[3]188
如韩江自己所言:“那些逝者在帮助活着的我们。”姐姐仁惠作为父权制下沉默的女性,一直以来都无法理解英惠的反常行为,直到英惠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幡然醒悟。
《树火》篇中最后在精神病院强行插胃管的行为不仅是一种对侵略式的霸权男性主义的隐喻,也是医疗父权主义的体现。所有的行为都呈现了在当时社会女性无可奈何被侵犯的现象,赤裸裸地展示了在全社会浓厚的父权体制下始终处于被动客体的女性悲哀。
英惠最终在离开精神病院的救护车而得到了彻底解脱,同时,姐姐从英惠的逝去中也觉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识。此时在“树火”之上飞出的鸟象征着逝者对生者的拯救,逝者给了生者以生机;鸟冲向乌云,象征着她对父权的挑战。
姐妹直到死别时才形成了“姐妹情谊”。“姐妹情谊”(Sisterhood)是胡克斯所提出的,是指女性在共同受压迫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互相关怀、互相支持的一种关系。共同的境遇让女性深切地理解彼此、惺惺相惜,并联合起来,“女性之间的情谊是她们团结起来对抗父权文化,颠覆男权话语,建立女性身份的武器”[7]。前两篇的鸟都代表了英惠人际关系的破裂,而这里从树中孕育出的鸟则是关系的形成,自始至终对英惠不离不弃的只有姐姐仁惠。
三、结语
《素食者》中,女性从脱离父权到求得性别自由话语权的过程举步维艰。女性需要确立自己的人格主体地位,既不附庸,也不自甘边缘化,从被孤立的“他者”的角色中解脱出来。同时脱离依附于男性的独立女性之间还需要团结,建立牢不可破的“姐妹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