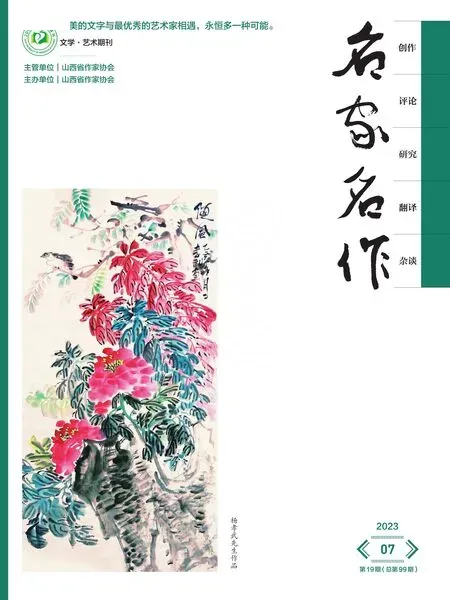拉图尔“非现代性”的批判
——读拉图尔的《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
柯睿铭
现代性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概念,它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的变革和发展。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就成为西方思想和实践的核心价值和目标,它代表了理性、进步、解放、民主等理想。然而,现代性也引发了许多问题和危机,如环境污染、文化冲突、社会分裂、道德失范等。因此,对于现代性的本质、意义和前景,不同的学者和流派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评价,形成了一场关于现代性的激烈辩论。
在这场辩论中,有一位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其独特而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就是布鲁诺·拉图尔。拉图尔是科学技术与社会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对科学实践进行了深入的人类学研究,揭示了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和社会性质。他认为,科学不是一个与社会隔离的纯粹领域,而是一个由人类和非人类(如技术、物体、自然等)共同参与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科学家不是发现自然规律的客观观察者,而是通过各种翻译、转换、联结等行动来创造自然现象的主动参与者。
基于这样的科学论视角,拉图尔对现代性进行了一种全新的解读和批判。他在其代表作《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中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且具有挑衅性的论断:我们从来都不是真正现代的①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安涅思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第96 页。。他认为,所谓的现代性建立在一个错误而虚假的前提下,即自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清晰而绝对的界限。②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安涅思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第102-120 页。这个界限使现代人可以将自己与前现代人区别开来,并将世界分割为两个互不干涉的领域:一个是由科学家探索并控制的自然领域;另一个是由政治家管理并规范的社会领域。然而,这个界限实际上是不断被打破和重建的,并且无法容纳那些既属于自然又属于社会的混合物(如核废料、基因工程、全球变暖等)。这些混合物是现代性的产物,却又威胁着现代性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因此,拉图尔认为,我们所讲的现代性,其根基是以二元对立为基本框架的,如果我们打破二元对立,那我们恰恰是非现代的。
一、我们为何是“非现代”——打破“自然—社会”的二分法
拉图尔的现代性批判是基于他对科学社会学和科学人类学的研究,他试图从人类学和符号学的视角揭示现代人所从事的两种实践形式——转译和纯化。转译是指将自然和文化这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杂合起来,科学和技术就是转译实践的典型例子;纯化则是指创造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本体领域——人类和非人类,也就是主体和客体、文化和自然③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安涅思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第163-168 页。。拉图尔认为,现代人的悖论在于,他们一方面不断地进行转译工作,创造出各种主客杂合的拟客体和拟主体;另一方面却又试图将这些杂合体纯化为纯粹的主体和客体,从而维持自然和社会之间的二分法④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安涅思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第163-168 页。。这种二分法不仅塑造了现代人与前现代人之间的时空界线,也塑造了西方人与非西方人之间的文化界线。他认为现代人所建立的自然与社会、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分法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杂合体的非现代世界之中。在这一部分,我将阐释拉图尔现代性批判中的三个关键点:我们为何现在是“非现代”的?自然与社会的二分法出现了什么问题?杂合体如何影响了现代人?
我们为何现在是“非现代”的?拉图尔认为,现代性并不是一种真实的历史状态,而是一种理论上的构想,它建立在两个伟大分界之上:第一个伟大分界是将自然与社会、主体与客体分开,第二个伟大分界是将西方与非西方、现代与前现代区别开来①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安涅思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第62-68 页。。这两个分界使西方人认为自己拥有了超验的自然和科学,而其他人只有文化和表征。然而,这种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在科学和技术的实践中,我们不断地将自然和社会、物和人混合在一起,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杂合体,如身份证、地铁等。这些杂合体既不属于纯粹的自然领域,也不属于纯粹的社会领域,它们构成了我们真正生活的中间王国②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安涅思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第96-101 页。。因此,拉图尔认为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成为过现代人,而是一直都生活在非现代的世界之中。这一观点挑战了传统形而上学和历史学中对于现代性的定义和划分,它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我们所处的时空和身份,并重新思考我们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自然与社会的二分法出现了什么问题?拉图尔指出,这种二分法导致了一系列的悖论和矛盾。在科学实验室中,科学家通过转译工作将自然和文化结合起来,建构出新的知识和事实;但当这些知识和事实被公布之后,它们却被赋予了超验性和客观性,成为科学的基础。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一方面,自然并不是我们的建构物,它是超验的,并且无限地超越我们;另一方面,自然是我们在实验室之中建构出来的,它内在于实验室之中。同样,在政治领域中,人类通过纯化工作将社会和自然分开,建立起利维坦等政治制度;但这些政治制度又必须超越于我们的建构,否则就会失去其合法性。这也产生了一个矛盾:一方面,社会是我们的建构物,它内在于我们的行动之中;另一方面,社会并不是我们的建构物,它是超验的,并且无限地超越我们。拉图尔认为,这些矛盾反映了现代人对转译工作和纯化工作的偏颇选择:他们否认了转译工作所产生的杂合体,并坚持了纯化工作所创造的二元对立。这种做法不仅是虚伪的,而且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杂合体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否认而消失,而是在不断地增殖和扩散,对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③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安涅思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第106-152 页。。这一观点揭示了现代人对于自然和社会、科学和政治之间关系的误解和困惑,它要求我们重新认识我们所建构出来的知识和制度,并重新评估它们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杂合体如何影响了现代人?拉图尔认为,杂合体是我们生活世界的真实面貌,它们既不是纯粹的客体,也不是纯粹的主体,而是具有流动性和可变性的拟客体和拟主体。这些拟客体和拟主体在我们的行动网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可以分有人的主体性,也可以分有物的客体性。而人又会在很多时候分有物的属性:对某些味道的辨认,对交通标志的识别,这些都是我们从物的世界中所学习的能力。因此,主体性并不是人单独具有的能力,更应该说它是流通于人和物的集体之中的一种属性。拉图尔认为,这种对杂合体和集体的关注可以帮助我们打破自然与社会、科学与文化之间的二分法,并建立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和民主政治④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安涅思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第286-299 页。。在这种新的形而上学和民主政治中,我们不再试图将自然和社会分开,并赋予它们超验性和不可逆性;将自然和社会视为同一过程中产生出来的结果,并赋予它们建构性和可通约性。在这种新的民主政治中,我们不再试图将科学和文化隔离开来,并赋予西方人以特权地位;将科学和文化视为同一网络中交织出来的实践,并赋予所有行动者以平等地位。⑤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安涅思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第286-299 页。拉图尔呼吁我们打破自然—社会的二分法,承认我们一直都生活在一个非现代的世界之中,一个充满了物与人所组成的“集体”的世界。这一观点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来理解和处理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如环境危机、伦理冲突、文化差异等,它要求我们重新定义我们与自然、社会、科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并重新构建我们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共同体。
二、在“非现代”中我们如何生活——对称性人类学
拉图尔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杂合体的非现代世界之中,这个世界既不是纯粹的自然,也不是纯粹的社会,而是由人和物、自然和文化、科学和政治等各种行动者组成的一个复杂的网络。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拉图尔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需要一种“对称性的人类学”。在这一部分,笔者将通过对拉图尔的对称性人类学的具体分析,阐述清楚“我们如何在‘非现代’社会里生活”这一命题。
什么是对称性的人类学?拉图尔认为,传统的人类学是一种不对称的人类学,它将人类与其他行动者分开,并赋予人类特殊的地位和能力。①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安涅思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第187-209 页。在传统的科学人类学中,科学被视为一种超越文化和社会的普遍性知识,而其他形式的知识被视为一种受制于文化和社会的相对性信仰。这种不对称的人类学忽略了科学知识是如何在实践中建构出来的,以及其他形式的知识是如何具有有效性和合理性的。拉图尔主张建立一种对称性的人类学,它将所有的行动者都视为同等重要和有价值的,并且不以任何先验的标准来区分它们②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安涅思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第187-267 页。。在对称性的人类学中,科学知识不再被视为一种超验性和客观性的事实,而是一种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产生的建构物;其他形式的知识也不再被视为一种次等和虚假的信仰,而是一种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展开的实践。
由此可知,建立对称性的人类学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所生活的非现代世界;二是为了更好地参与到我们所面临的非现代问题中。拉图尔认为,如果我们坚持不对称的人类学,我们就无法真正认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因为我们会忽略掉那些与我们共同构成这个世界的其他行动者,如物、技术、自然等。这些行动者并不是被动地服从于我们或者反抗于我们,而是主动地与我们互动和影响着我们。如果我们只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人与物、物与物、物与自然等各种关系,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拉图尔认为,如果我们采用对称性的人类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们会关注到所有参与到这个世界中的行动者,并尊重它们各自不同的存在方式和表达方式。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发现和解决那些涉及多元行动者之间互动和协调的问题,如环境危机、伦理冲突、文化差异等。
那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处在“非现代”的我们呢?我们应该承认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杂合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二元的世界。在上文中已经阐述,现代人试图将自然和社会、科学和文化、主体和客体等划分为两个互不相容的领域,从而建立了一种虚假的现代性。但在实践中,这种二元划分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我们总是在与各种行动者互动和影响着彼此。在环境问题中,我们不仅要考虑到人类的利益和责任,还要考虑到动物、植物、大气、水源等其他行动者的利益和责任;在医疗问题中,我们不仅要考虑到医生、病人、家属等人类行动者的知识和情感,还要考虑到药物、器械、病毒、细菌等非人类行动者的作用和影响。因此,我们应放弃那种试图将自然和社会、科学和文化等分开的做法,而是接受那种将它们视为一个整体的做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我们应该尊重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的各种行动者,而不是试图控制或否定它们。拉图尔认为,建立对称性的人类学需要我们改变研究方法和态度,从一种批判性的方法和态度转变为一种追踪性的方法和态度。批判性的方法和态度是指一种试图揭露和否定其他行动者的知识和实践的方法和态度,它以为自己拥有了更高的标准和更深的洞察力,而将其他行动者视为一种被误导和被操纵的对象。这种方法和态度是不对称的,因为它将自己置于一个特殊的位置,而将其他行动者排除在外。我们需要以一种试图理解和描述其他行动者的知识和实践的方法和态度,不要以为自己拥有了更高的标准和更深的洞察力,而是尊重其他行动者的选择和判断,并试图跟随它们的逻辑和动机。这种方法和态度是对称的,因为它将自己置于一个平等的位置,而将其他行动者纳入其中。若如此做,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并更好地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