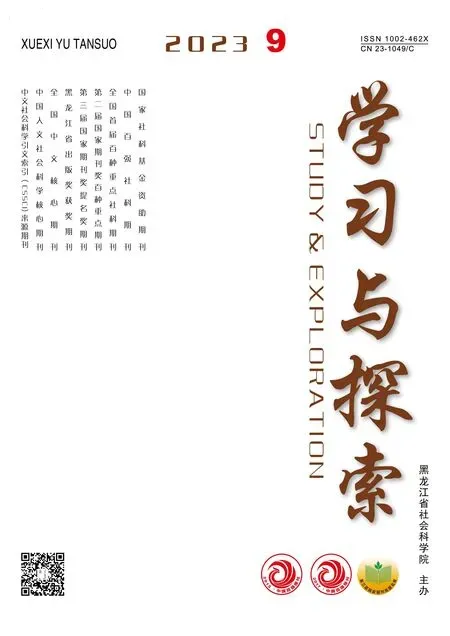当代原生数字视听文化生产的现实主义变奏
战 迪
(深圳大学 传播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数字视听文化的发展速度是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媒介文化所无法比拟的。研究表明,无线电广播的普及用了50年时间,电视用了20年,个人电脑用了15年,而互联网只用了4年[1]266。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中国原生数字视听内容就以传统机构媒体难以想象的扩张态势觅得空前繁荣的当下图景。源于广播影视却不断裂变、增生的数字视听内容催生了斑斓的文化谱系,并逐步改造和颠覆了长久以来的人际交往和社会认知模式,进而对社会文化产生强有力的影响。数字时代,在视听文化主流化趋势下,跨媒介叙事的常态化渐次导致了媒体间性的消逝。流动的、液态的视听产品栖居在以平台而非媒体为聚所的数字时空中,不断衍化出崭新的文化品类。综观活跃在当下用户视野中的数字视听文本,无论是承继和延展传统影视形态的网综、网剧、网络大电影、数字纪录片,还是与Web2.0技术环境相生相伴的移动音频和短视频应用,抑或正处于完善进程中的虚拟现实影像和互动剧,除新奇刺激、实时交互、场景化建构、沉浸式体验、参与式生产等技术赋权下有别于机构媒体的应用感受外,众多数字视听文本始终将生活流品性的挖掘和现实主义风格的架构作为创作基调。从李子柒作品的风靡全网、B站数字纪录片《二舅》登顶热搜并引发热议,到抖音博主“张同学”乡村短视频的爆火出圈、全息影像技术再现邓丽君风采的霸屏分享,与生活同步的纪实美学和秉承客观性、典型性、历史性法则的现实主义风格成为众多数字视听创作者不约而同的集体选择。
显然,现实主义创作的道德感召力和情感冲击力是中外文艺创作中历久弥新的风格取向[2]。数字生态下现实主义的创作空间大大拓展、科技手段迭代更新,表意技法日新月异,但在对诸多相关创意、创新实践的考察中,我们又不禁疑惑,同样宣称“忠实”于社会现实的数字视听和摄影影像,二者在表现形态和受众感知方面存在哪些区别和联系?数字化创作中强大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是否正在重构着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传统?那么,这一路径将是现实主义的新方向,抑或经典现实主义的终结?本文试图立足“技术—文化”共生论的立场,对当下原生数字视听文化生产中的现实主义变奏进行深度钩沉,进而图绘并反思其可能带来的文化影响。
一、从照相现实、感知现实到合成现实:数字视听文化现实主义表征的嬗变
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创作传统,现实主义(realism)于1795年诞生于席勒的著作《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在书中席勒指出:“现实主义者受自然的必然性支配……他的知识和活动……会被外在原因和外在目的所规定。”[3]155-156整个19世纪,基于全球范围内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发起激烈挑战的现实主义接连胜出,俨然成为文化艺术界的主潮。20世纪以来,伴随着现代主义思潮的崛起,现实主义在西方世界遭到冷遇,一度被视为过时的、枯竭的文化艺术传统。然而此时的中国,正值革命年代激烈的救亡图存斗争,现实主义创作因其对社会进程的深刻反思与批判力度反而获得了旗帜鲜明的追捧和浓墨重彩的褒扬。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欧美社会潜滋蔓长,各种表现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和荒诞派此消彼长,频繁地解构着现实主义的生存领地。新千年以来,随着中国影视产业的繁荣和大众文化的勃兴,现实主义在跨媒介叙事的浪潮中重又回归人们的视野,在我国同时受到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流行文化的推崇。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移动社交互联网文明播撒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原生数字文艺屡屡尝试挣脱其母体影视、文学的羁绊,大踏步走向遥不可知的未来。然而,作为一种带有强烈商业交换诉求的文化艺术形态,数字视听产品始终服膺于用户意识的变动不居。就此而言,近年来大量现实主义趣味浓厚的数字视听产品的流行,恰恰体现出相关领域内用户需求的旺盛。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现实主义总是像一个吞噬一切的怪兽,试图把错综复杂的事物全盘吸纳到自己营造的文学世界中来……直接与社会现实勾连在一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们身处其间的世界。”[4]然而也正是由于强大的包容性和辐射性,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解歧义不断。从影像现实主义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大体上经历了照相现实主义、感知现实主义和合成现实主义等几个连续且交叠的认识阶段。
照相现实主义(photorealism)源起于胶片电影时代的艺术理念和叙事技法,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着影像理论的“本体论”地位。尽管从电影艺术诞生伊始,就始终存在着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两大理论阵营的交锋,二者在争鸣对垒中驶向不同的轨道。以巴赞和克拉考尔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流派强调影像对“物质现实的复原”,认为“摄影的美学特性在于揭示真实……摄影机镜头摆脱了我们对客体的习惯看法和偏见,清除了我的感觉蒙在客体上的精神锈斑,唯有这种冷眼旁观的镜头能够还世界以纯真的原貌,吸引我的注意,从而激起我的眷恋”[5]13。受此影响,长镜头和景深镜头的纪实功能得到艺术电影创作领域的首肯。与此同时,作为苏联蒙太奇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和维尔托夫等人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符号学等视角出发,宣扬蒙太奇影像风格对物理现实的超越性。也正是由于形式主义理念的先锋性、离散性、易变性和多元性等特质,使得这一流派并未实现理论与实践的齐头并进。发展至今,巴赞式的现实主义影像话语始终在艺术电影理论集群中占据优势地位,蒙太奇学派逐渐归入商业电影的创研体系中。在巴赞的纪实世界里,现实主义手法被具体切分为本体现实主义、戏剧现实主义和心理现实主义等三种不同类型,而无论哪种类型,都附丽于客观、真实的整体框架之下。
时至今日,随着影视创作技巧的成熟和观众对多元表现手法的接纳,旷日持久的长镜头与蒙太奇之争渐渐落下帷幕。特别是随着数字特效技术的大量引入,巴赞思想中减少人为干预的、时空同步的、记录现实和揭示真相的“完整电影神话”逐步失去了必要的实践土壤,于是对长镜头纪实功能的捍卫也因此而偃旗息鼓。数字影像时代,广泛出现的数字长镜头“指的是由多个分开拍摄的片段通过数字技术而合成的一个完整的长镜头”[6]。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将若干时空异步的镜头“焊接”成观感平顺的长镜头,由此,在数字赋能下本应由蒙太奇承担的表意使命可以轻松让渡给长镜头,因而,数字视听文化领域中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区隔也随之松动。数字视听生态中观众所感知的现实主义,更多体现为影像创作机制和观众接受心理的合谋。在此过程中,“感觉”和“现实”并不对立,拟态现实仅仅是有别于物理现实的另一种存在方式而已。就此而言,斯蒂芬·普林斯首创的“感知现实主义”(perceptual realism)也就被赋予了阐释创作实践的合法性。该理论认为,“被感知为真实的影像,是指那些被建构为与观众在真实三维空间中的视听感知相符的影像……感知现实主义既包括那些指涉现实的影像,又包括那些不指涉现实的影像,凡是被感知为真实的影像,不管它是指涉物质现实,还是指涉虚构和幻想”[7]。而“银幕上的数码影像调动了观众更多的吸引力,令观众陷入影像世界中并认同其中的规则,从而‘感知’到真实”[8]5,继而,这一理论在无形中也呼应了社会成员对数字时代感觉结构(feeling structure)的认知。事实上,传统胶片电影大体上遵循着记录现实的功能,影像内容和物理世界具有对应和索引的关系。也就是说,胶片电影具有对应真实的指涉性(indexicality),而数字影像作为一种数码编辑的拟像(simulation)甚至不需要现实的对应物,就可以逼真地呈现在大荧幕上。与对应物断裂的虚拟性(virtuality)并不影响观影者体验的真实感,反而令其获得某种超真实的视听感受。在CGI(computer generated image)绘制的影像世界中,电影俨然蜕变为绘画的一种亚类型,自动生成技术与“数字画笔”[9]的结合消弭了电影与动画的边界。正如电影技术的进步并非线性发展的过程,电影理念的变迁也是回环往复的。“我们则需要将关注点从‘电影眼睛’(Kino-Eye)转向‘电影画笔’(Kino-Brush),更加深入地探索其中的“电影绘画性”(Cinegratography)。”[10]
如果说感知现实主义从官能性视角出发,重构了影像真实的内涵,那么秉持着数字唯物主义立场的列夫·马诺维奇所提出的“合成现实主义”(synthetic realism)则真正体现出计算机文化中通过元素组装来创建无缝对象的当下实践。“合成”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数字化操作手段。它与“选择”互为表里,通过模块化的组织方式将若干不同元素进行组接、合并、拆解、替换、删除,从而在“合并图层”(flatten image)的过程中组织视听内容。完成后,“新媒体对象作为一个整体的媒体‘流’进行‘输出’,其中的元素不能再单独使用”[11]140。沿着计算机文化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意识到,传统影视的概念已经逐渐被数字视听概念所置换。也就是说,运动影像的模块化、媒体数据格式的模块化正在形塑一种崭新的影像生产逻辑,就全媒体数字视听的技术特性而言,“与其说它们属于传统的图像或电影范畴,不如说它们更像结构化的计算机程序”[11]142。数字视听产品并不回避现实主义理想,早在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图形领域的相关研究中,科学家就对其正在研发的图像渲染器提出了高品质和复杂性的大胆设想。前者指数字视听文本的视觉清晰度应与实景电影拍摄相一致,后者则期望着视觉效果的丰富程度溢出物理实景。依此逻辑,列夫·马诺维奇认为,合成现实主义致力于实现两个目标,即“对于传统摄影规则的模拟,和对于现实生活中物体和环境的感知特性的模拟”[11]193。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合成现实主义并不排斥感知现实主义思想,二者间的关联性不仅在于产品维度和官能维度的不同切面,更在于关乎前瞻性与当下性的技术实践论眼光。
二、连续性、空间性、接受性:合成现实主义的创作进路与美学逻辑
从技术实践维度来看,数字视听实现了物理影像、数字影像到模块合成的迭代转换。这种后工业流程的推广不仅节约时间、经济和人力成本,而且后期可修改空间较大。数字合成技术可以有序完成无缝三维空间的创建、摄像机在空间内运动轨迹的模拟、高度逼真的视听工艺效果。那么试想,排除观影环境和终端设备等接受语境因素不谈,仅就媒体产品来看,电影、电视、新媒体短片、记录影像、手机游戏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曾经的媒体区别在未来或许将仅仅成为题材和体裁的区别。
近期,创作界对合成现实主义的质疑集中来自其真实性尺度。因诸多相关数字产品与物理现实并不形成镜像式的映射关系,于是其真实性广受诟病。当下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不仅动画电影已经基本实现了无摄影机创造,数字电影中大量使用动作捕捉、虚拟成像和表演捕捉等技术,并在后期进行精准修补和非曝光画面生成,近年来广泛流行的短视频应用还大量引进了合拍、同框、拍同款、链接等技术模板手段,最终建构起虚拟与现实难分难解的文化产品。常江教授将其概括为“一种立足于数字媒介的技术可供性,通过塑造和动员情感公众的话语和消费潜能,以及对文本意义和解读实践的严格规划与控制,来追求一种对真实的体验式、情感化再现的媒介文化”[12]。而就其真实观而言,数字视听产品“塑造了一种关于生活的本真性的集体想象,并不断激励人们去‘真实地’体验生活”[12],从而促成从本质真实到体验真实的认知转向。即便如此,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怎样能够让观众以现实主义的标准和信念去承认数字视听所呈现的体验真实呢?对此,菲利普·罗森认为,创作者需要令观众相信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数字影像背后存在一个参照原型,就像是人们普遍相信电影《侏罗纪公园》中数字合成的恐龙存在着一个对应物。事实上,数字视听产品的逼真性趋近于完美,其分辨率和精细度远远超过人眼所能识别的范畴。但为了追求电影摄影与数字影像效果的有机融合,创作者也会在产品制作过程中通过刻意生成噪点、降低饱和度和锐度等方式满足观影者对真实感的经验性认同,即人类亲近性。
数字视听产品在技术条件、传播界面、感知体验等方面与传统影视有着巨大的差异,但在审美理想和创作手段方面又与之形成怎样的联系呢?具体到现实主义美学的继承、变异与创新方面,数字视听将会遵循怎样的创作、生产路径呢?这些都是亟待回应的。
第一,数字视听媒体遵循着连续性美学的基本逻辑。传统商业影像的审美习惯与蒙太奇语言的非连续性剪辑直接相关。而蒙太奇技法诞生的初衷却是受制于摄影机胶片的长度。从对胶片黏合的物理性操作,到对影像片段的修剪,直至后来长短镜头之间剪辑、组接规则的确立、镜头语言习惯的形成,都是在对抗物理条件限制的前提下逐步演化、总结的。然而在数字视听文本中,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反蒙太奇倾向。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二更”数字纪录片中大量采用了Vlog拍摄形式,以创作者主观视角切入并贯穿叙事始终,以此来强化认知的纪实性、连续性、场景化和沉浸感。另一个相关的案例则是交互界面的大量涌现,使得多视窗模式迅速取代了曾经交叉蒙太奇、平行蒙太奇的表意功能,建构起更符合现实主义视听风格取向的叙事机制。就此而言,在计算机文化中,相异、相斥的时空都可以被合成为无缝的连续性时空,形成一个肉眼难于辨伪的完型体系。而这种数字化操作技法打破了蒙太奇美学中差异、冲突的对立关系,形塑了与人们视觉感知更为相似的体验场景。进一步讲,随着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技术的推陈出新,沉浸式数字视听产品的常态化已是大势所趋。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连续性美学体现在前期拍摄和后期制作两个阶段当中,前者以数字长镜头或Vlog等形式呈现,后者则通过缝合空间的方式打造镜头内部的连续性。就接受效果而言,“被虚拟影像所牺牲的现实规律促使主体的连续性感知成为影像制作的最终目标,召唤着偏重主观感知的连续性美学”[13]。诚然,数字合成技术翻开了现实主义叙事的崭新篇章,创造出了现实生活中不曾存在,视听感知却异常真切的运动图景,同时允许用户从不同视角和侧面观察、参与、体验虚拟时空中的一切,但这种连续性产品毕竟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因而广受指摘,被认为是现实的赝品。尽管如此,我们依旧可以借用巴赞的现实主义主张,“影片的最终含义更多地取决于影像素材的组织安排,而不是取决于这些元素本身的客观内容”[5]66。由是观之,数字视听产品与物理现实的索引关系并不是其现实主义价值的衡量标准,相反,连续性美学体验的真实感才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逻辑依据。
第二,合成现实主义通过建构本体蒙太奇和风格蒙太奇拓展空间美学新形态。早期蒙太奇语言是爱森斯坦等人为了推进运动影像的真实感而精心布设的视听剪辑、组接方案。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融叙事性、表意性和抒情性于一体的影像系统。然而在数字视听理念下,物理运动已经被以比特为单位的电脑合成影像所取代,在计算机技术和逻辑的操演下,空间维度的数值变化及其相互关系创造出了一种有别于既往以时间序列为主导的空间蒙太奇模式。数字合成技术取消了长镜头与蒙太奇、深焦镜头与浅焦镜头之间的美学冲突和表意区隔,营造出无缝连接的虚拟空间。空间合成技术早在电视时代的抠像领域就得到了相对成熟的实践应用,在今天数字社交应用中,各种琳琅满目的短视频特效插件更是能够将被摄主体与虚拟背景轻松融合。进一步讲,传统影像语言中蒙太奇组接需要充分考虑的空间差异、视角转换、比例协调和亮度匹配等问题都显得不再重要。以空间换时间的合成现实主义在海量实践中探索出一种始于技术终于审美的创作方案。具体体现为本体蒙太奇(ontological montage)与风格蒙太奇(stylistic montage)两种创作取向。
在列夫·马诺维奇看来,所谓本体蒙太奇,“从本体论角度来看,一些元素在同一时间和空间中是不能相容的,而本体蒙太奇实现了这些元素的并存”[11]159。从好莱坞大片《侏罗纪公园》到《阿凡达》,从央视中秋晚会中全息投影技术赋能虚拟与现实的巧妙融合,到江苏卫视跨年晚会上邓丽君与周深的深情合唱,随着虚拟现实、动作捕捉、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日益成熟,不仅时空同步、虚实相生、影游结合的现实主义体验渐渐被大众熟识和认同,而且从认同到行动转化率的大幅提升真正验证了合成现实主义审美意图的实现。因而,我们大可以不再将数字运动影像理解为传统影视文化概念下的一个子集,相反,从视听感知到时间序列,再到空间演绎的技术文化体认习惯的演进似乎才是本体蒙太奇的创作构想。就风格蒙太奇而言,就是“将不同媒介实时并置,从真人拍摄片段切换到一个拍摄模型的镜头或纪录片片段,也在同一镜头内适用同样的方法”[11]159。不难想见,风格蒙太奇的底层逻辑依然是数字合成技术,与本体蒙太奇不同的是,这种技法强调的是同一镜头内表现形式、特效手段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电影时代专业级的35毫米和家用级的8毫米胶片、数字时代大体积摄影机与便携式平板电脑、手机,尽管在成像格式上还会存在一定差异,但成像形态和合成效果方面却显然别无二致。这不仅加深了视听文化的全民推广,更在幻觉、意识层面夯实了人们对现实主义表达的全新理解乃至践行。
第三,数字技术的实践启发和观念引导催生了现实主义接受理念的统合与变奏。在文化艺术学界,现实主义议题绝非简单的关于真实与否的命题之争。其间包含着复杂的接受心理与期待视界。具体到影像文化的流变中,不同时期、流派学者的现实主义思想总会激发起不同的接受趣味和习惯的改变。在对比中可以发现,早期巴赞所推崇的经典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观念中的乌托邦想象;科莫利的现实主义与意识形态指涉息息相关,其进步之处在于,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强调了影像现实主义需要在一代代观看者之间达成默契并培育习惯;波德维尔的现实主义更多体现在影像产业层面,该流派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实用主义工具应用于消费美学和商业竞争领域。值得注意的是,波德维尔的功利性并非全然对艺术创作的冒犯,客观而言,它强化了行业协会在现实主义标准裁定方面的积极效能。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好莱坞的影像传统中,现实主义的工业标准、产品差异、质量体系都被赋予了严格的审查规范。在数字视听文化无与伦比的整合力作用下,用户所体验到的现实主义绝不是既往现实主义潮流的总括和集合。无论是受制于消费的创作生产,还是基于体验真实的参与式文化,都不断丰富着现实主义的时代意涵。
于整体而言,我们可以从呈现、幻觉和模拟三个方面对合成现实主义的接受美学加以理解和阐释。借用戈德史密斯(1934年美国的SMPE主席)的名言,现实主义注定是生产关于现实的、可接受的假象。由是观之,合成现实主义呈现的是用户心目中设定的索引物,无论其物理真实与否;与此同时,不管如何逼真的现实主义影像,都无法逃离幻觉的本质。数字技术大可以将每一个现实主义构造形态难题视为一道数学难题进行破译和解析,并不断生成超真实的视听体验;此外,合成现实主义的一大特点在于其史无前例的模仿能力,无论物理世界的形状、质料、光影、运动如何复杂,计算机图形学都会对其进行具体分析,并拿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当然,相较于传统的照相现实主义,合成现实主义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因为照相的最大特征在于对现实的还原,而合成却很可能先于或游离于现实。那么,在合成文化产品中就不会面面俱到,所有细节的策划和制作都服从于创作者对用户接受习惯的预判,因而,也就很难做到整体真实与细节真实的完满统一。于是,一种不平衡的现实主义随之诞生。无论如何,我们需要意识到,就技术审美而言,传统现实主义是指向过去的,而合成现实主义却更擅于面向未来,因而在审美拓展、思想超越和价值引领方面,合成现实主义的优越性遥遥领先于历史上任何一种现实主义文化文本。
三、超现实主义的创研构想与现实主义的归宿
客观而言,数字视听生态并非现实主义文化书写的绝佳土壤。因为流动性技术世界里包含了太多的可能性、渲染性、幻觉性和突变性。曾几何时,以粗粝的质感为表现特色的现实主义文学、文艺文本无形间转向了虚拟现实、幻觉现实的全新天地。特别是体感(haptic)经验的加盟,更大大加深了数字幻觉的真实体验,为现实主义文明营造出超现实主义的发展路向。保罗·罗德威认为,数字时代的体感“不仅指涉身体的触感和身体部位的动作,也涵盖了身体在环境中的移动穿越”[14]41。至此,人类文明与数字技术联手缔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具身性超真实文化时空。这不仅在相当程度上跨越了鲍德里亚“拟像”理论中仿造和生产两个阶段,更用有力的实践诠释并延展了其第三阶段“仿真”的文化内涵。从人们曾经广泛探讨的虚拟环境遮蔽现实环境,到今天被普遍认同的虚拟现实的体验真实,“‘超级真实主义’绘画抵达了对于计算机算法所生成的非真实之物的、虚拟符号的摹仿境界,而这正是同数字电影‘超级真实主义’美学所共享的一种美学观念及其文化诉求”[15]。
超级现实主义(hyperreality)的概念最早由鲍德里亚提出,他认为,超级现实主义“就是没有原型和现实性(reality)的真实,一种由现实的(real)模具制造的真实”[16]1。数字技术生态下的超现实主义创作首先建基于对传统真实观念的质疑与反驳。正如加洛蒂关于真实的辩证法,我们所关注到的现实生活中的所谓真实并非唯一的、永恒的真实,那或许仅仅是真实的某一个侧面、节点和环节。随着时间的流逝、文明的演进,曾经去中介化的肉眼观察已经逐渐淡出文化艺术的舞台,“而现实主义艺术作为一种捕捉现实的手段,也不能将描写对象当作永恒不变的事物,而是要发掘其相对性,揭示现实不断变化的特质,并努力引导‘真’朝着更符合人的本性的方向发展”[17]。从古希腊文艺的“模仿自然观”,到莎士比亚打破“三一律”、移步换景的戏剧观,再到詹姆斯·卡梅隆《阿凡达·水之道》中超现实主义的后殖民构想和刘慈欣科幻世界中宏大的宇宙观,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在当下合成现实主义的世界中,传统现实主义创作图景下的“透明感”不复存在,但作为建构主义话语体系而非本质主义判断,一股前所未有的超现实主义风暴正在席卷而来,并有望成为文艺创作的新常态。
超现实主义创作可以是幻觉式和想象式的,它在技术力量的加持下将情感与现实、感性与理性、环境与客体、当下与未来紧密耦合,通过陌生化的创作手法制造“延异”(differance)性效果,构造出视听文化产业维度的“吸引力经济”;超现实主义也可以是超级真实的,它形塑了比真实更为真实的媒介图景。就像是李安导演的《双子杀手》中数字特效团队精心打造的120帧+3D技术标准使得每一个快速对打动作都清晰可见,被摄主体高速运动下每一条肌肉纹理都能被肉眼捕捉,数字真人现身荧幕时丝毫不被观影者觉察。在真实感十足的数字合成技术面前,似乎现实生活反而被映衬得不那么真实了;不仅如此,超现实主义更可以是深情回望和超前展望式的。无论是数字媒体中运用AI换脸技术复活的李小龙影像,还是近年来《地心引力》《星际穿越》《沙丘》等好莱坞科幻大片未来主义视野下对技术叙事与心理描写的平衡,都在时间链条中重新唤起了人们对现实主义的感知、理解,甚至觉醒。
通过比对,我们可以意识到,传统胶片、电子影像时代,现实主义的表达往往是通过对真实主体的描摹、挖掘和反思得以呈现的;而在数字时代,真实主体的身份和行动在合成技术的操演下被赋予了不易察觉的人造属性,因而虚实主体也就在不经意间彼此重合,进而表现出同一性趋势。事实上,也有学者将超现实主义创作中的主体称为“伪主体”,认为“它不过是生命实体的网络表征,是自我‘主我’的技术‘客我’,是平台、算法和资本共谋下的网络傀儡”[18]。然而笔者却认为,当人类不可避免地走进数字技术的世界,并与之形成深度对话、协同的具身关系时,视听表达主体的真伪之争恐怕不再是现实主义理论聚焦的中心。在这一创作氛围下,即使是想象性、意象性、虚拟性的主体,也都不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哪怕是构造层面的反现实形态,其目的也不是漫无边际的空想和臆造,而是要强调现实世界的另一个不为我们了解的侧面。
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印刷时代就曾经论及的那样,现实主义“不是眼下紧迫的需要所概括得了的,因为它有相当巨大的一部分,表现为尚是潜在的、没有说出的未来的思想”[19]255-256。立足于“技术—文化”共生论的生态性立场,秉持着技术实践论而非技术工具论的文化主张,笔者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本就包含着太多曾经到来、已然莅临和必将存在的现实。既然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充满韧性和弹性的创作观念拥有着强大的包容性、辐射性和衍生力,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在数字技术的助力下,以现实主义的眼光追溯过去,把握当下,构想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照相现实主义、感知现实主义、合成现实主义,还是正处于研发、创造进行时状态的超级现实主义,都可以被视为现实主义的表达理念。这既不昭示着现实的终结,也不意味着现实主义的归宿。相反,它很可能启发着现实主义的发展趋势,有助于我们借助具体创作审思当下,遥望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