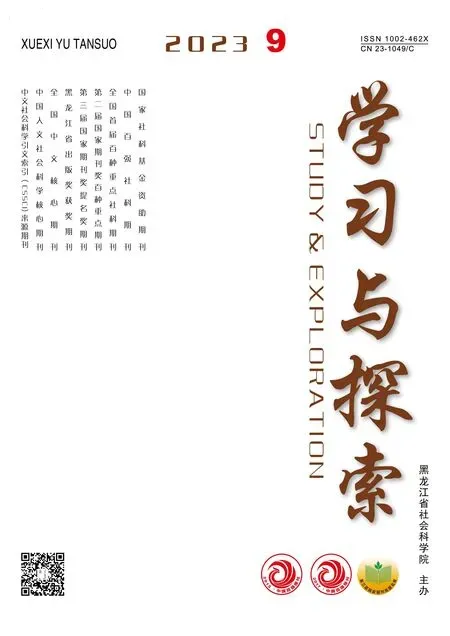九一八事变创伤叙事文本考论
——以平顶山惨案为中心
高 翔
(辽宁社会科学院,沈阳 110031)
一般就受创主体而论,创伤具有明显的突发性、被侵性和暴力特征;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它与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它包含战争、屠杀等多重义项,通过创伤记忆碎片的集聚,进而形成了一种集体创伤、种族创伤乃至文化创伤。创伤叙事被定义为“不仅包括创伤性事件的历史及文学表现, 而且还包括见证创伤历史的证词及电影等表现形式”[1]。广义上,纪实性的通讯报道等亦属其中。
由九一八事变连锁而来,发生在1932年9月16日抚顺的日军悍然杀害平顶山、栗子沟、千金堡三千余村民的屠村事件消息,最早便是经媒体披露的。但由于日军的焚尸和新闻封锁,相关报道还是滞后的。(1)据统计,平顶山惨案罹难者总计3271人。参见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日本殖民地文化研究会编:《伪满洲国的真相——中日学者共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佟达:《平顶山惨案》,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371、423页。时为日本驻奉天领事馆领事森岛守人在后来的回忆中承认:“由于禁止新闻报道而未能公诸于世的,还有昭和7年(1932年)10月,在抚顺发生的一起惨绝人寰的对满洲妇女儿童的大屠杀事件。”[2]86
抚顺平顶山惨案被视为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大规模屠杀中国平民的起点,当时由于此案被“禁止新闻报道”,屠杀消息先是在平顶山惨案后由抚顺逃难民众传播开来,连森岛守人也是经接抚顺警察署电话,从“煤矿工人擅自离开矿井,正沿铁路线集体向华北撤走”的动向中查知的[2]86。在公开媒体中,最早是经《盛京时报》报道当地伪县政府发布所谓“宣抚”布告所流露出来的。报道诬抗日义勇军为“胡匪”,九月十五日袭击当地一些采碳所,日军为维持所谓地方秩序和居民安全,“于彻底搜查之下,对附近村落民房,有忍痛焚毁之举”,系属“一种不得已之军事行动,揆与保民初衷,原无二致,万勿误会”[3]。自找借口,却不打自招,欲盖弥彰。《新闻报》(上海)则是关内较早真实披露平顶山惨案的媒体之一,其于1932年11月15日、11月23日、11月27日分别以《抚顺村民被屠》《东边人民被屠三千余》《日军屠杀详情》等为题,报道、揭露日军在抚顺制造的屠杀血案:“抚顺千金堡,栗子沟,平顶山三村人民三千余,悉被日军屠杀。其屠法是先令人民齐集平顶山西南沟内,谎称演说,三百日兵即包围,架机枪扫射,逃出者百三十余,未死者四十余,村民尸体悉被焚毁。”(2)参见《抚顺村民被屠》《东边人民被屠三千余》等,《新闻报》1932年11月15日。其后,《时代公论》第三十六号(1932年12月2日)刊登的《抚顺大屠杀案》、1932年12月8日《申报》的《抚顺日军屠杀农民》等,也相继予以报道。1932年12月13日《北平晨报》发布题为《抚顺惨杀案 我国驳复照会 颜惠庆已通知国联》的消息,内称,国联中国代表颜惠庆致国联通知书,“申述中国外交部曾于十二月六日致一严重照会,抗议日本对于抚顺中国农民之屠杀,并答复日本之照会”。12月19日,《北平晨报》刊登长篇通讯《抚顺屠杀 美人汉特目击记 史上未有之惨酷 中国人生命不如狗! 呜呼何以救我关外同胞!》,随后《申报》等媒体对此通讯亦有转发。《北平晨报》对该文的说明是:“抚顺平顶山日军大屠杀事件,业由国际新闻社记者汉特前往视察后发表纪事,译载本报。”“九月十六日我国抚顺同胞近三千人为日本军队屠杀一节,已于十一月三十日由美国国际新闻社访员汉特氏Edward Hunter向纽约所发一电予以证实。”此通讯“乃国闻社根据中立之第三者所为报告而公布者”。(3)参见《浴血归来说抚顺惨案 栗子沟难民张荣久母妻弟子均被屠杀》,《北平晨报》1932年12月22日;《抚顺屠杀 美人汉特目击记 史上未有之惨酷 中国人生命不如狗! 呜呼何以救我关外同胞!》,《北平晨报》1932年12月19日。森岛守人指出,“当时只有国际新闻驻奉天特派记者汉特,发了有关这一事件的电讯稿”[2]86。其翔实性、唯一性和影响性可见一斑。汉特笔下遭难后的农庄,“血流成沟地为之红”,“新土隆起,均为新坟”,“男女妇孺,阒无一人。栋梁焚烧之灰烬,充满于为火焚成黑色墙壁所围之广场内”,无处不是“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景象,成为断无人烟的“死村”,“惟有乌鸦惨然隐于烟筒中”。民宅“无一屋顶得幸存者,所有车辆,均遭破碎或焚烧,鸡犬不留”。诸多个相,令人不忍卒睹。汉特写道:
当余入此等房屋遇及之人,彼必指余以彼等友朋之死处:“此处有一老太太,为焚余之栋梁所压,彼不能逃,以至化为灰烬。”“彼处为沈婶婶,因不欲远离,至在火坑(炕)上烤毙。”
作者不禁哀叹:“此种可怕之惨闻,笔难尽述。”汉特对大屠杀的关键情节“机关枪当作照像机”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日本兵复告彼等谓将举行照像。惟当时既无照像机,复无镜头,所有者,惟机关枪与枪弹而已。福姓称,彼之老母即系第一批被杀者。当彼倾跌时,其母之尸身即倒压彼身上。时忽有高丽人大呼:‘日本人已经退去,汝等可起立。’彼当时幸无力起立,凡起立者,即受第二次机枪扫射,应声而倒。凡被踢而有动作者,以及儿童,均受枪刺。”12月20日,《北平晨报》又发表一则报道《日本使馆对于抚顺屠杀更正之原函》,内言:“本报昨日译载美记者汉特目击抚顺屠杀记后,日本驻华公使馆于昨晚来一火急公函,声请更正。兹将原函照录于左。”公函诬称:“九月十五日晚间兵匪及不良民众约计二千余名攻击抚顺,放火于市内各处,且有对于我方独立守备队擅行袭击之事实。……于此我方守备队于十六日派遣一排队伍搜索千金堡时,偶(遇)该村内匪贼反击我方,因此我方军队万不得已自卫起见,用迫击炮应战后,约有半小时,扫灭匪贼矣。”一派谎言之后,又不得不承认“交战结果,焚烧该村庄大半房屋”,并假惺惺表示“实行十二分救济”,“复兴该村庄一切善后事宜”。 日本驻华公使馆的《更正》公函,使人不禁想起美籍犹太作家、纳粹集中营大屠杀的幸存者和“记忆者”,当年“一个无比笃信宗教、无比天真而无辜的小男孩儿”埃利·威赛尔此后的经历:“未能想到的是——没有人想象过——故事(按:指大屠杀)有一天会被完全地否定,有一天他不得不站在这里,站在你们面前,告诉你们:‘是的,他是真的。’”这可足见出学者中的某些人在“下流地说话”[4]。12月22日,《北平晨报》又刊长篇通讯《浴血归来说抚顺惨案 栗子沟难民张荣久母妻弟子均被屠杀》,全篇系平顶山屠杀幸存者、栗子沟难民张荣久的口述,日兵残忍杀害中国农民的证言。此文与同日《大公报》发表的《抚顺惨案又一证明 栗子沟难民张荣久逃来北平 昨对记者谈平顶山屠杀惨状》文字相同,当代学者已有述及,此不赘述。
言及平顶山惨案发生的原因,汉特说:“盖日方对村人之报复手段也。缘当九月中旬,进攻抚顺之义勇军,曾通过该区。是项攻击,使日方损失三十五万元,并杀日人数名。”[5]12月21日,《大公报》发表社评《呜呼抚顺惨杀案》,援引当时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的报告,细列了缘由和过程:“九月十六日,由东来大刀义勇军三人,至平顶山探路,被日人侦悉,同时日人疑邻村千金堡栗子沟有联络,乃由抚顺派遣军队二百余人,携机关枪十数挺,至平顶山,召集三村村长,追问大刀队下落,并言欲检查三村居民,乃迫令三村男女老幼三千余口,齐集平顶山西南沟内,先令一齐坐于地上,静候检查,同时将机关枪十余挺,安设于侧面约七八十步,布置完毕,令群众对枪跪起,其中机警者,知有意外,站起欲奔,而日人机枪齐发,迅烈扫射,煞那之间,男女老幼狂奔乱逃,号痛之声,达数里外,负轻伤逃出者仅一百三十余人,负重伤中途陨命者六七十人,其余男女老幼二千七百余口,皆死于非命,间有襁褓婴幼小儿女,或因身小未为弹中,或中弹而未毙命者,蠕动于血泊尸堆中,日人用刺刀一一杀之,事后日人将尸身堆起,用火油杂秫秸焚烧,然后将三村房屋亦尽付一炬。”[6]森岛守人也说:“经调查证实,原来是当地日本守备队的一个大尉,以当地村民有窝藏土匪的嫌疑,把村子里的妇女儿童集中在一起,用机关枪扫射屠杀而引起的。”森岛守人又写道:“一位留在日本内地的军官夫人在给出征到满洲的丈夫留下了‘希望不必有后顾之忧,要努力为天皇效忠’的遗书以后,身着素装而自杀”,“一时曾被传为战时妇女的典范”;而“在抚顺屠杀中国妇女儿童的这个大尉,就是这个夫人的丈夫”[2]86。此后有分析说,这个日本妇女的自杀直接导致了“平顶山惨案”。
平顶山惨案发生后,有关这一事件的文学叙事,是九一八国难文学的重要一环,也是中国现代创伤叙事的组成部分。它带给中国民众的创伤记忆,有着深远的历史性,更有着无法隐去的痛楚。以此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尽管还在不断挖掘和丰富中,但它与奥斯维辛大屠杀的文学叙事,显然具有重要的关联性和观照性。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德国哲学家特奥尔多·阿多诺的这句话经常为人引用,但歧义多出。据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的揣度,阿多诺此言意义有二:其一,“浸淫在‘私密、自负的凝思之中’的诗人找不到文字来表现奥斯维辛机械式、无灵魂和工业性的残忍”;其二,“诗歌是一种创造美和愉悦的过程,用来描述大屠杀不合适”。而且布鲁玛发现,似乎德国的艺术家“都将他的话铭记在心”,“鲜有直面大屠杀这一素材的小说、戏剧或电影”作品。保罗·策兰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关于死亡营题材的诗歌《死亡赋格》,因“具有一种舞曲般抑扬顿挫的节奏感,与诗里集中营长官玩的残忍游戏形成呼应”,而使人产生怀疑:“它是不是有点太抒情了?是不是太悦耳了?是不是没有表现出恐怖,反而将其美化了?”然而在布鲁玛看来,“策兰的诗依旧是有关大屠杀最感人肺腑的声明。诗的凄美并没有淡化字里行间的恐怖气息,相反,倒是加深了这种感觉。”尽管《死亡赋格》被作为经典收入西德的教科书,但保罗·策兰始终被拒于“战后德语主流文学圈”外[7]87-88。同样是诗歌,同样是讲述大屠杀,芝冈创作的《平顶山》与《死亡赋格》有着不一样的格调。
如果说,《死亡赋格》是一首充满隐喻和反讽意味的诗作,以一种沉冷、忧郁的格调,构建起威斯康辛大屠杀与赋格音乐之间的连接,意在展示德国纳粹残暴的反人类行径;那么,芝冈的叙事诗《平顶山》则凸显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融一的美学力量。诗作开篇是对平顶山农家景色的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当然含有相当的虚构成分。作者展现的是一幅陶渊明式的情境:平静的村庄,风吹的麦浪,栖水的牛羊,安流的小溪,高吟的雄鸡,傍晚的落日,飘荡在田野中的村歌;中秋时节,有升起的皓月,团圆的美酒,飘香的饼果,身着新衣的小儿;入夜,更有异样的明月挂在天际,草际间秋虫的低吟唤醒了篱前的睡犬,开放在篱边的桂花随风吹起阵阵芳馨,一派宁静、和乐、安详的景象。当然,在这样的叙述中,作者也暗加伏笔,以巫婆的预言、夜猫的长啼,预示灾祸的来临,但很快就被“宣统爷要放恩粮”的“好音”所掩盖。最终,诗作定格了大屠杀的场面:照相机发出机关枪的子弹,“一时间烟起弹飞,老幼哭喊”,三千条生命的鲜血染红了山坳,西下秋阳的“余光映射着山中的血槽”。其实,这种“照像”掩盖和欺骗下的枪杀还并不意味着结束,诗作的最后一节,是对日本军人屠杀手段达到极端的实写:
几十个日本兵笑骂交加,
夕阳中露出了血口獠牙,
用刺刀乱刺这满山的尸体,
向空山显它们惨酷的矜夸。
不难见出,作者正是在把鲜血淋漓的残酷现实与心目中理想生活的对照中,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血腥屠杀的愤怒与声讨。对这种创作方式,我们可以借用埃利·威赛尔的话进行诠释:“他们的目的不仅是描述大屠杀,而且是描绘大屠杀之前的事情。生活,家庭的宁馨,假日的欢乐,小丑的魔力和孩子们的智慧。”“这就是故事的讲述者为什么尽他所能地呈现它最美好的方面,让刽子手知道他们毁坏了什么。”[4]
诗歌《平顶山》的这种叙事方式,不期然地在近70年后当代作家迟子建创作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中,得到了复现。《伪满洲国》以编年体的方式书写了那个怪异的伪国。在第一章《一九三二年》中,以约8000字的篇幅,记述了平顶山大屠杀那个魔鬼疯狂的时日。其中第六节开端,作者以颇多的笔墨和细腻的情节,描述了美莲一家虽不富裕却也知足的静好岁月与祥和生活。中秋月圆之时,恩爱善良的美莲夫妻,慈祥爽直的公婆,为着孕育中的孩子而喜悦;10余口人的大家庭沉浸在节日的欢快中。不幸的是,翌日晨,日本守备队包围了村庄,一家人以“照像”之名被逼到东山坡的洼地里。俄顷,山坡上遮盖机关枪的布被扯开,一场惨烈的大屠杀开始了:
在一个日本军官挥手之间,机关枪的火舌像炽烈的岩浆一样喷涌而出,顷刻间,人群中血肉横飞,惨叫声惊天动地地响起。一个八岁的孩子当时正啃着月饼,子弹当胸穿透他的脊梁,他弹跳了一下,手中的半块月饼飞向空中。这月饼落下时滑着一个老人血肉模糊的脸,立刻就成了血饼子。
《伪满洲国》同诗歌《平顶山》一样,也是将一种特定的生活美彻底毁灭给世人看。这种对美的毁灭当然是历史真实的存在;以两个互为观照的叙事,肯定会引起人们更为深广的关注和超越凡响千百倍的回声,这也许就是文学家的智慧之处。
石光发表于1934年6月的短篇小说《火拼》[8],讲述了伪满军队官兵因不忍日本军官的肆意妄为而投奔义勇军的故事。为伪满洲国皇帝登基时的安全,日本指导官元郎来到东北某县衙内查看收缴民间枪械情况,只因翻译官的误译而枪杀了县长。在横行凶悍、恣意任性的元郎看来,“打死个县长,中国人还敢怎样他”。而黄队长则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虎狼的环境里,生命确悬在日本人的喜怒间”,带领队伍毅然反正。这其中,作者插入县衙卫兵老王和老江的一段对话,引进了平顶山大屠杀的情节:
卫兵老王很活跃,他端着枪,等号令。“老江,前年什么地方来着,两千多,老的幼的都有,说是照像,都用机关枪给毙了?”
“不是,三千多,不是在平顶山吗?可惜,咱们没有机关枪,不能给‘他在临死的时候,照个像。’” 老江说着,把枪实上了一粒弹。
老王举起了枪瞄瞄准,把枪星着指在元郎的鼻子尖;“嘿!这不也是照像吗,你看我给他对对光。”
《黑白半月刊》在其设置的“国难文学”栏目中推出的醒槐的短篇小说《照像》[9],直接引入了平顶山大屠杀的情节。作品中的背景虽然模糊,但与日本侵略者在平顶山肆意杀人的场面有着高度的一致:在义勇军刚刚离开王家村不久的一天清晨,王老伯接到村长王四爷的通知:“日本兵营来了命令:今天他们要来给我们照像,表示我们是好人。”这对祖辈以耕种为业的农人来说,是新鲜、兴奋和期待的。“照像”的地点黄土坑上此刻“早立满了一群人们。王老伯因为有了先前的经验,所以就挤在人群的前面站着候等。”“这时,在每个人底心里都是抱着一团高兴,翘着脚,仰着头地张望那照像者的降临。”然而,巨大的阴谋和悲惨的命运正在袭来:
“咇……咇……咇……” 大道上来了三辆汽车,开到黄土坑底近旁站住,从上面下来二十多个凶纠纠的日本兵,拿着三架用黑布蒙着的照像机,还有几个照像箱子。他们把照像机安放好了,又从箱子里拿出照板来装进照像机里去,一切都妥当了,就听着一位官长是在下着命令:
“不要动!”
这时数百的人们似高粱颗子般地无声无息地直立着不动。
“照!”
啊!黑幕揭开了!三架照像机原是机关枪直对着这伙人们!“嘟……嘟……嘟……”似雨点般地在扫射。
天崩地裂了!哭的,喊的,四下里狂奔的,卧地呻吟着的……声音,形景震动了与混乱了大地里底一切!
过了些时间,枪声停止;人声沉寂;二十多个日本兵狞笑地往城里开着汽车;王老伯同着他底同村的人们,是长眠着在那天然的为他们预备好的黄土坑里!
大地底一切是铁般的寂静,只有树枝上底鸟儿是在婉息着这血与肉而构成的惨迹!
全篇围绕日本侵略武装以“照像”为名进行残暴屠杀而展开。 “照像”既是小说题目,也是创作文本的主题词,并据此建构全篇。据考,执行屠杀任务的日军,主要是以川上岸为队长的日本抚顺守备队第二中队,配合守备队的是以小川一郎为队长的抚顺宪兵分遣队。临出发之前,小川一郎提出,应当想出一个办法“把平顶山居民顺利地哄骗出来”,时为宪兵队翻译王长春(通译)、成员牟文孝提议:昨晚大刀会袭击,平顶山居民了无伤害,“为纪念大家太平无事,来给大家照像”,“大家传一下,都到大庙前去集合”,被小川一郎采纳[10]49,54-55。九一八事变后,以“照像”为诱骗对平顶山民众进行屠杀,此属罕见甚至唯一,对那些善良淳朴的村民,有着极大的欺骗性和暴力特征。小说中的王老伯,在乍一听到“照像”的消息时,不禁想起多年前自己的第一次集体“照像”,当年还被挂在城里照相馆的玻璃窗里。 “现在是第二次照像了”,愉悦之情,溢于言表,王老伯特别换上一件平日不舍着身的新衣急忙上路了。血雨腥风之后,作者不仅感慨:“照像的惨幕演过了。王老伯底像片没有挂在照像馆底玻璃窗里;可是,在张村,李村,刘村……里底人们每个人底心里,却悬上了一幅血与肉而构成的惨图。”《照像》篇幅不长,仅2000余字,但题旨鲜明集中,在严格忠于事实、意在重返历史现场的基础上,又精心塑造了王老伯的形象,准确传达出那个时代人物的典型性格和特征,更真切地表现出高于人物的思想内涵,成为我们一睹现代国难生活场景的窗口,是将历史意识转化为艺术文本的有益尝试。作品并不以宏大叙事、史诗创写见长,旨在对历史事件进行文化再造,细节的虚构和想象显现出天然的合理性和崇真情怀;以“在从先曾在王家庄里住过的义勇军内,最近蓦然地又增添了许多新的同志”的结尾,显示了以唯物史观逻辑地审视和建构历史发展的艺术新面。
“照像”,无疑是平顶山惨案的日军实施的“花式”伎俩和欺骗手段。石光的随笔《照像的故事》,便是又一篇以此为中轴的揭露屠杀之作。作品文字较短,照录如下:
从西班牙战地中逃出的儿童,到英国上岸的时候,新闻记者拿镜箱向他们摄影。这些可怜的儿童,以为是用机关枪来扫射他们,一起哭了起来。这是一个有关照像的很悲惨的故事。
在我们国土的东北部,还有比这个故事更悲惨的一个。那是在照像的欺骗下,有三千多男女老幼的同胞,被害死了。
故事是这样发生的:义勇军攻打抚顺城之后,日军在阵亡的义勇军壮士身上,发现了一枚工人证章,于是这个住在平顶山小村中的三千多老百姓,就有了应该杀死的罪名,说是给他们照像,把这三千多人诱骗到一个山坳里去。准备照像了,黑布片揭开,机关枪,突突……无情的把他们扫射了!
三千多名同胞,在哭声震天中,不到三分钟,整个失掉了生命[11]!
石光的上述文字,发表于1937年3月,此距平顶山惨案爆发已四年有余。作者之所以如此长时间萦绕心头,而于此际坦露心声,一个不容回避的特殊缘由是,石光出生在抚顺县距平顶山百余公里的千金寨。家乡父老乡亲的罹难,无疑让他万念俱焚,愤懑悲怆之情挥之不去,致使一位流亡他乡的文学青年,唯缘笔为文,以倾吐胸襟。作者以“照像”为中心情节所展开的仅300余字的精短叙述,从西班牙战地儿童逃生英国的“照像”故事引发开去,营造了一个极为惨烈的场面,深刻揭露了日本法西斯的为所欲为和惨无人道,展现了苦难叙事的一种国际性视野,内含着无穷的意蕴。
继石光的《照像的故事》之后,受“西班牙难童登英国口岸时,因记者‘摄影’,疑为‘机枪扫射’的新闻”引发,鉴于平顶山惨案“这段惨史,当时曾很简略地刊于京沪各报,外部已有抗议,但因种种关系,不见下文,盖当时烽火遍地,此事亦渐为他事所掩,所以社会也没怎么注意”的社会情状,署名“民”的作者,同样以“照像”为主题词,又发表《“摄影机”扫射之惨剧》[12]一文,对平顶山惨案再度进行揭露。因其系转述作者同学的亲身经历,便显示了相当的真实性:“那时同学某君,客居在平顶山麓,经营他的牧场事业,不幸厄运的到来,他也遭了几乎亡身之痛。”遭到枪杀、“身负数伤”的某君,以假死得免日军的二度枪刺,“夜半匍匐逃至廿里外的义军医院所在地,从事治疗,愈后返里,述说间悲愤犹不可遏。”借同学之口得到的惨案信息是:“在冰天雪地的一个早晨,日本的多数武装士兵,就包围了这整个区域:于是逐户搜查,老幼靡遗,声称‘摄影’存据,俾有户籍保障;有的妇孺以为‘摄影’是它们常有的勾当,便欣然前往”。然而,日军“就在那钢丝网及武装警备下,开始动作:覆有遮光红布的两架一字号的‘摄影机’旁,已经有人在感光——瞄准,警号响处,排列前后四层的同胞,也就在那百分之一秒的感光下,前赴后倒了!”一句“我们的变色的锦绣国土——平顶山上,两千五百多个同胞的生命,就在那艺术国‘摄影’之下,化为乌有了!”展现了刺心切骨的讽刺力度。
与《照像》《照像的故事》《“摄影机”扫射之惨剧》有相似之处的,是骆驼生的诗歌《铁的纪律,铁的洪流》。已有学者指出,《铁的纪律,铁的洪流》“所记录的正是1935年到1936年3月实行的‘冬季肃正’期间,及紧随其后的1936年4月‘治安肃正计划’启动后,军警对东北民众所犯的历史暴行”。又说:“在该政策下,日伪先后开展了对东边地道区武力镇压、奉抚地区军事围剿和平顶山惨案,以及针对东北全境的‘一齐讨伐’。”[13]但也有学者指出:“日伪军在伪满洲国开展的‘治安肃正’工作共分为三个时期,即第一期(1932年3月至1933年10月)、第二期(1933年10月至1936年10月)、第三期(1936年10月以后)。”[14]如果这种分期得以成立,那么,发生于1932年9月16日的平顶山惨案,便可以囊入伪满当局实施“治安肃正”的第一时期。它当然不是孤立的存在。这一时期还包括了1933年7月开始的日军对抚顺县边境残暴的“集家归屯”。进入计划的有120多个部落,一时间“凶猛烟火,红遍天空。号哭声,真是震撼山谷”,村民“苦心经营血一滴汗一滴建立起来的房屋、家园,一眨眼间化为灰烬”[15]108-109。
《铁的纪律,铁的洪流》明显融入了平顶山惨案的真实细节,这在开篇便得到揭示:
“友邦底指导官,要和大家讲话;
你们都要集合在村西头儿的空地里!
快!快快地!”
这是一个翻译官来传的大令,
满村的老小,都慌了神,
都抱着一颗噗咚噗咚的心,你瞅瞅我,
我瞅瞅你,都怔着眼睛。
接着诗人述说道:
这儿便是村西头儿的一个空场,
雪地上的老小,谁个敢嚷!
太阳射到雪上,闪着耀眼的金光,
在周围的刺刀上,挑着人们底希望!
一丝丝的希望,一丝丝的渺茫!
为什么候了很久,不见什么队长?
当着现在,他又有什么话要讲?
哦!讲话又为什么抬来了机关枪?
各个小队长的眼里,燃烧着贪婪的贼光!
一颗颗的心灵,由战栗又变成了硬僵!
死神底黑翼,在头上拍开了翅膀!
突然爆仗似的枪笑,炸弹似地呼娘!
一群野兽,狂啸着奔下山岗,
黑龙江底洪流,卷起了巨浪!
啊!银色的雪地上,铺满了软条条的羔羊;
点点的殷仁,抱着雪,消失了人们底希望[16]!
这是一篇带有鲜明叙事特征的诗歌作品,日军如“一群野兽,狂啸着奔下山岗”,借口所谓“友邦底指导官”“要和大家讲话”,把村民骗集到“村西头儿的空地里”;但讲话却“抬来了机关枪”,进而是“爆仗似的枪笑,炸弹似地呼娘”,瞬间村民便成为“铺满了软条条的羔羊”,消失了生的希望。这一系列平顶山屠村的“花式”手段和罪恶画面,在诗中一一得到如实的再现,诗作无疑是对主要包括平顶山大屠杀的日伪实施“治安肃正”计划的深刻揭露和泣血控诉。
与醒槐的《照像》、石光的《照像的故事》等文本以“照像”为关键词不同,穆木天的《扫射》[17]则凸现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平民进行血腥屠杀的“扫射”手段并极尽抨击。这种声讨,无疑纳入了平顶山惨案的历史细节。《扫射》开头便写道:“这是一九三二年的夏天,∕那些天真的民众受了帝国主义的扫射,∕他们就了他们所预想不到的死,∕在那青青的山坡之傍,阳光辉耀之下。”他们“大多数是佃农和雇农”,只是因为此前义勇军来到他们的村庄,“使日本军队出了好多死伤”,致使日军在义勇军离开后来到这里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疯狂的报复。“他们全副武装,还带着大炮和机关枪”,将 “当地的民众”——“有的抽着黄烟,有的抱着孩子,有的光脚露胸,戴着草帽,有的穿着长衣”——召集在一起,虚伪高唱“同种同文”“日满是一家人”的调子,编织着“我们要给你们照像证明你们不通匪都是好人”的谎言,使善良、单纯的村民感到了“日本人还是讲理”“我们这样也算有福气”。然而,“照像”竟是一场血色屠杀的前奏,瞬间“机关枪就啪啪地响起来”,还处在“莫名其妙”和“鬼哭狼嚎”的“喊叫”间,便有“三五千的民众一起在地上扑倒”,如山的尸首随后又被“倒上了煤油,放了火给他一烧”。《扫射》虽是以大屠杀中的“扫射”为中心的书写,但还是比较完整的叙述了惨案的因果与过程,并且自然再现了民众倒毙瞬间内心的吐露:“为什么没当义勇军去!”“为什么没同日本人拼一下!”而且这血案“更增强了大众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因为每个农民每个工人都有同样被扫射的命运”。这显然是将“被扫射”上升为国族命运层面的思考。收入此作的穆木天的诗集《流亡者之歌》,作为“国防诗歌丛书”之一种出版,作者显然将《扫射》归为诗歌类,这当然无错,但文本融入较为浓重的散文笔调,也是不争的事实。
龙宝鋈的《平顶山》是平顶山惨案叙事中尚未被论及的一出独幕剧。剧末“作者按”写道:“全文事实是由张荣久逃往北平后述出来的,见北平晨报(日期忘记),或广州民国日报二十二年元旦第二张第三版。”作者所述《北平晨报》忘记的日期,即前述的“1932年12月22日”。《广州民国日报》的刊载比《北平晨报》晚了9天,内容大致相同,题目改为《抚顺惨案又一有力铁证 抚顺难民之口述 看日人如何狡辩》。从作者的说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得知,独幕剧《平顶山》更多显示了鲜明的纪实性与历史互文的特征,尽管同题的诗歌、小说也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这样的征象。
不消细说,一个文本必定会同其他文本发生各种关联,这都是在其前文本的遗迹或记忆基础上产生,或是在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中形成的;它包含了对于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回忆,以及对于文本作为素材所进行的改变与转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任一文本都是在重新组织和引用已有的言辞。剧作《平顶山》的互文性,与一般意义上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显性文本与隐性文本的互文不同,它是两种显性文本的互文,所依从的幸存者的口述证言,本身就具有了浓烈的悲剧色彩和骇人的血光情节。剧作全篇以平顶山上的一片草茵为背景,截取张荣久一家被日兵从山脚下驱赶至此、张荣久与远房亲戚佟二的相见与交流、日兵血洗平顶山等片段,再现了平顶山大屠杀的真实场面,具有纪实的完整性,几乎不见戏剧文学的虚构和想象。
剧作《平顶山》又与小说《平顶山》的环境截取具有相同性。小说《平顶山》同样是以村民被押解平顶山途中和平顶山屠杀现场为故事发生地,但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融进了形象的描绘、虚拟的想象和生动的意象。
令人慨叹的是,在小说的这种互文性表达中,充盈着浓重而鲜明的身体意识和身体话语色彩。如果说被誉为中国现代白话小说开山之作的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以人体的重要部分“眼睛”为主线构思全篇,那么,小说《平顶山》则是通过对人脚的塑造来钩织作品的。
作品开篇就从“大脚的,小脚的”女人进入故事的身体叙事维度。在被驱赶至平顶山的途中,作者接着述说道:“山是静着的,静得像洪荒时没有人,没有兽一样;树木也是死的,死得像披了缟素在白皑皑的雪光闪烁下,只有那一一只只乃至几千只的已经不能走动然而还勉强竭了力,提起了足踝子搬动着的脚算是动着,算是活着,算是在颤动着他们底生命的力似的,其实这些活着的脚还不如说死着的好,他们老早没有自己的主意,也没有使生在自己身上的两只脚情情愿愿打着勇气走。”“今天的脚不是他们自己的了,今天的脚只是颤抖着,颤抖着,老是索索索的打颤,老是脚踏不稳,就是雪积得很浅的地方,也很费力的走着,常常翻筋斗儿,常常把膝踝子弄破弄碎,血殷红的殷红的冒着溅着,滴在白雪里的确是很美丽,很触目,又是很平常很平常的。”恐惧之巅也许是茫然和麻木,农人在通往死亡的路上,“老早没有自己的主意”“像鬼推磨似的走着”的脚,便是这样在驱使中行进。而这种精神层面的脚,也融进生理性的煎熬。“本来已经很松”的泥土,又覆盖了“白棉絮似的雪,脚踏下去时便跟着泥土和雪块陷落下去,提起脚踝子时又带起了冰冷冰冷的雪块”“几乎每一个人都不能走动,冻得不能走动,麻木得不能走动,每个人的脚尖都生起了冻僵的泡,愈走路愈麻木,愈难搬动”。
小说《平顶山》意在以纪实和镜头叠加的方式,再现那场毫无人性的大屠杀,因此小说中的身体意象,不仅具有精神、环境和身体的多重建构,而且也深深浸染了野蛮、暴力的色彩。同样是脚,在作者的笔下,杀人的日本刽子手具有了“矮脚”的符号,化作了“矮脚的穿皮靴的人”,施展着非人道的淫威和暴虐:
一只穿皮靴的短矮的脚瞄准了眼风没命的向大肚子踢去,那女的站不住脚跌得又痛又昏的倒了。嘴里咕噜了一声,跟着那脑袋就冒着血,嘴里也冒着血,胸脯上也躺(淌)着血,又是几只皮靴的短矮的脚连续不断的踢像皮球似的踢着踏着……几只孩子的脚,女人的脚,残废者的脚,衰老的瘦削的脚,都索索的在颤了……
一个军官在屠杀前还在制造着恫吓与谎言:“好好儿听着话!饶你们!”“静静的站着……让咱们替你们拍照!动就要射杀,就要砍头!” 随即“是数千只脚的骚动”;“黑压压的数千只经过了极度的兴奋,极度的沮丧,极度的痛苦,极度的惶恐战栗的脚又在扰动了!”即便在难民忍无可忍的反抗中,同样闪现着脚的意象:他们“想脚底上给那些鬼子一些颜色看”,并开始了威武不屈的抗争与拼搏。然而,“那几十只几百只的穿长靴的摆动着的脚可有些忿恨了,很残酷的把那些无罪的灵魂割下了脑袋……”作品中脚的意象,几乎贯穿了小说的全篇,确立了一种独特的身体叙事方式,既揭示着身体的主旨意义和审美张力,又呈现着它的分裂与悖论,旨在高扬起身体的正义主体,呈现出蓬勃的生命精神和文化气质。
小说《平顶山》显然不是以传统小说的手法表达意旨,而独幕剧《平顶山》亦以非戏剧的形式展现特定的时空情境。独幕剧《平顶山》的非戏剧特征,可以用叙事性来概括。我们知道,传统话剧是以对话为主的创作和表演,多人物在规定情境中的对白和行动,剧作《平顶山》则突破了这种界域,细述那令人不堪回首的血腥屠杀。这与布莱希特把戏剧视为说讲故事、叙述事件有契合之处。在独幕剧《平顶山》中,作者严格依据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编排那段历史,包括张荣久一家、张荣久远房亲戚佟二等在内的人物设计,难民在山路上的被驱赶、遭受机枪扫射血流成河的场面和情节等,还多有小说体惯见的大段场面描写,无不具有鲜明的写实性。这也许更符合西方学者的某些主张:只有把种族屠杀的事实用写实的语言编成一个事件记录才保存其历史真实性;任何个人化表述,都显得既没有根据也缺少一致性[18]。而作为“第三者”的融入剧情及大篇幅情境叙事,开阔了读者的视域和戏剧的多角度体认:
从前给乌云遮闭的太阳,现在全伙跑出来,在殷红的鲜血里沐浴。呜呜的西风奏着凄苍的旋律的追悼底悲乐。鲜血禁不住日晒风吹,渐渐不似从前这般流得起劲了。太阳光线渐向东倾斜,太阳像重物断掉绳索般向西坠下。鲜血虽向未全干,但自有月亮来承其乏。跟着就要睡去的树林,满了森然的寂寞,俯伏在枯槁的梧桐下的落叶,反映着才烧完的晚红,坭土蒸发出来的又干又触鼻的腥气,经微慢波动的晚风吹来,充满一阵怪难受的血的香味。
这与长篇小说《伪满洲国》中的叙事,有同工之处,后者是如此表述日本兵制造平顶山大屠杀中那震撼人心场面的:美莲高高隆起的肚子被刺刀挑开了,那“一团紫红色血肉”的婴儿,被日本兵用刺刀“抛绣球般掷向远方”,美莲的肚腹“依然喷出一汪汪的血水,远远一看,就像艳极了的红牡丹的花瓣在临风舞动”。“日本兵纵火焚烧着那一座座还残留着炊烟的房屋。水缸在烈火中的崩裂声就像除夕夜燃放爆竹,挂在山墙上的农具的木柄被烧得赤红,远远看去就像鲜艳的冰糖葫芦一样一串串地挂着。”
独幕剧《平顶山》中悲凉格调和凄美景色的呈现,显然不是戏剧之用,但这种非戏剧因素融入戏剧的对话与动作中,展现出一种新的戏剧样态,我们称剧作《平顶山》为“叙事体戏剧”亦无不可。这种叙事,不仅体现了“以诗证史”“以史证诗”和“诗史互证”的传统阐释模式,又当是这种方法在戏剧创作领域的具体实践。它们,共同构成了平顶山惨案创伤叙事文本群,极大地增强了九一八事变创伤叙事的厚重感和悲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