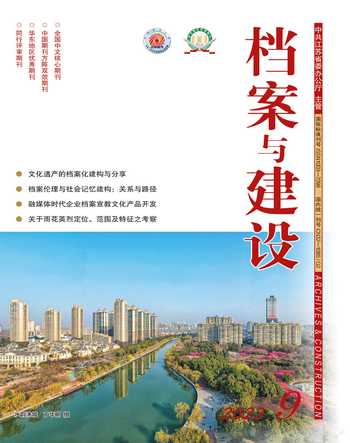唐代长江下游地区灾害述论
吕金伟
摘 要:唐代长江下游地区灾害多发,在时空分布上呈现出一定的不均衡特征。灾害出现以后,唐代政府采取了赈济、赈贷、减蠲赋役等措施进行应对,但成效难以判断。唐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灾害记载呈现出前期少、后期多的特征,与安史之乱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有关。
关键词:唐代;长江下游地区;社会应对;灾害记载
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以此解释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他认为:“(唐代)长江流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很快成了供应首都漕粮的主要生产地区,最后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1]冀氏所言“长江流域”,主要是指长江下游地区。20世纪末以来,郑学檬深入探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问题,指出唐代安史之乱以后至北宋后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南北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促成了这一时期经济重心的南移。[2]冀、郑两位学者的论断虽非不刊之论,但揭示出长江下游地区对唐王朝的重要性之所在。
在中国传统社会,农业作为最基本的经济生产部门,其良莠状况影响着整个社会系统运行的方方面面,而灾害的出现无疑会给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带去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基于上述两方面因素的考虑,本文拟探讨唐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灾害情况及政府应对措施,进而更为深刻地理解灾害与中国传统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当前社会治理提供镜鉴。
一、 灾害概况
长江下游地区行政区划在唐代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以元和十五年(820)的疆域政区为准,长江下游地区大致包括舒州、庐州、滁州、和州、扬州、江州、宣州、饶州、润州、常州、苏州、湖州、杭州、明州、越州等15个州,地跨淮南道、江南西道、江南东道。据《旧唐书》《新唐书》《通志》《文献通考》等统计,这一地区唐代有灾109次,其中水灾46次、旱灾28次、疫灾13次、风灾7次、虫灾5次、雪灾5次、地震4次、霜灾1次,是除两都所在的黄河中游地区以外灾害出现频繁的地区之一。
唐代长江下游地区灾害的时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特征。其一,以帝王在位时间为统计标准来看(见表1),在灾害次数上,唐文宗时最多,达28次;灾害频率上,唐文宗时最高,平均每年有灾2次。其二,以百年为统计标准来看,7世纪(618—700年)时有灾12次,8世纪(701—800年)时有灾28次,9世纪(801—900年)时有灾67次,10世纪(901—907年)时有灾2次,其中9世纪是唐代长江下游地区灾害的多发时段。其三,以安史之乱为界,安史之乱结束(763年)以前长江下游地区有灾27次,结束以后长江下游地区有灾82次,表明后一时段灾害的出现次数远多于前一时段。其四,在灾害的发生季节方面,春季10次,夏季28次,秋季29次,冬季21次,跨季5次,不详16次,反映出夏、秋是唐代长江下游地区灾害的多发季节。
唐代长江下游地区灾害的空间分布也呈现出一定的不均衡特征。其一,灾害仅出现在某一州的现象较少,有14次,而跨州的现象比较普遍,达95次,表明唐代长江下游地区灾害的波及范围一般较广,较少局限于一州之境。其二,以州为单位进行统计,各州出现灾害的次数存在着一些差异,其中舒州3次,庐州3次,滁州4次,和州3次,扬州15次,江州3次,宣州10次,饶州3次,润州10次,常州7次,苏州15次,湖州9次,杭州7次,越州2次;指代范围较广的各个区域出现灾害的次数也不相同,其中吴地2次,越地1次,江南5次,江左1次,江东2次,江淮10次,淮南20次,浙东、浙东西、两浙等17次。
从致灾因子方面来看,自然环境因素对长江下游地区灾害的影响较大。以水灾为例,其作为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发生次数最多、危害最为严重的灾害,首先与长江下游地区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降水量较之两都所在的黄河中游地区为多有关。比如,元和十一年(816)六月,“饶州浮梁、乐平二县暴雨,水,漂没四千余户”[3];长庆四年(824)夏季,“苏、湖二州大雨,水,太湖决溢”[4],“水入州郭,漂民庐舍”[5]。此外,唐代长江下游地区部分水灾的发生可能与这一地区夏秋两季时常发生的台风有关。开元十四年(726)七月,“润州大风从东北,海涛奔上,没瓜步洲,损居人”[6];天宝十年(751)八月,“广陵郡大风,潮水覆船数千艘”[7];大历十年(775)七月,“杭州大风,海水翻潮,飘荡州郭五千余家,船千余只,全家陷溺者百余户,死者四百余人;苏、湖、越等州亦然”[8];大和二年(828)夏,“越州大风,海溢”[9]。上述4次水灾系由大风引起,“海涛”“海水翻潮”“海溢”等记载表明致灾因子从海上而来,且发生季节分别为秋季、秋季、夏季,极有可能是台风;而广陵郡出现危害如此之大的“大风”则非台风莫属。
在旱灾方面,同样也能看到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比如,贞观十二年(638),“吴、楚、巴、蜀州二十六,旱;冬,不雨,至于明年五月”[10],此处的“吴”是包括长江下游地区在内的,但具体位置不详,而旱灾的发生则是由贞观十二年(638)冬季至贞观十三年(639)五月连续数月不雨所致。又如,咸通二年(861)秋,“淮南、河南不雨,至于明年六月”[11],咸通三年(862)夏季“淮南、河南蝗旱,民饥”[12],可见此次淮南、河南的旱灾、蝗灾是由咸通二年(861)秋季至咸通三年(862)六月持续数月不雨所致,且造成了民众饥荒的后果。
由于文献记载不详,难以一一判断唐代长江下游地区109次灾害出现的原因,以致无法详知每一次灾害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二、 应对措施
长江下游地区作为唐代尤其是唐代后期重要的经济区之一,受到唐代政府的关注与重视。这一地区出现灾害,给政府与民众带来了一定灾难,为缓解危害,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应对。现择其要者,分述如下:
(一)赈济
赈济是指无偿地给予灾民钱或物,救济他们。灾害出现以后,普通灾民最迫切需求的乃是维持生存的基本之物——食物、医药等。因此,赈济灾民是唐代荒政中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根据文献记载,长江下游地区灾后赈济灾民12次,居诸项救灾措施之首。其中,最早于災后赈济灾民者,是在唐太宗贞观八年(634),该年“江、淮大水”,唐太宗“遣使赈饥民,申挺狱讼,多所原赦”[13]。

当时赈济长江下游地区灾民的具体物资主要有二:其一为米,可使灾民食以果腹。元和四年(809)十一月,“浙西苏、润、常州旱俭,赈米二万石”[14];太和四年(830),“京畿、河南、江南、荆襄、鄂岳、湖南等道大水,害稼,出官米赈给”[15];太和六年(832)二月,“苏、湖二州水,赈米二十二万石,以本州常平义仓斛斗给”[16];等等。向灾民赈米是一种直接舒缓灾民困境的方法,有助于维持灾民的基本生存需求。其二为棺器,可以安葬死者。宝应元年(762)十月诏云:“浙江水旱,百姓重困,州县勿辄科率,民疫死不能葬者为瘗之”[17],所谓“瘗”有掩埋、埋葬之意,表明州县官吏将染疫而亡的民众予以安葬;太和六年(832)五月,杭州出现疫灾,“给民疫死者棺,十岁以下不能自存者二月粮”[18],表明此次杭州疫情出现以后,官府不仅赈济了米,而且为染疫而亡的民众配发棺器,以便安葬。
(二)赈贷
赈贷与赈济有别,并非一种无偿行为,一般是指以低价或者平价向灾民借贷粮食、种子、农具等,帮助他们度过灾年。比如,长庆二年(822)闰十月,唐穆宗下诏:“江淮诸州旱损颇多,所在米价不免踊贵,眷言疲困,须议优矜。宜委淮南、浙西东、宣歙、江西、福建等道观察使,各于当道有水旱处,取常平义仓斛斗,据时估减半价出粜,以惠贫民”[19];又如,太和四年(830)夏,长江水溢,“没舒州太湖、宿松、望江三县民田数百户”[20],九月,“诏以义仓赈贷”[21]。
(三)减蠲赋役
荒政举措中所减蠲之赋役,涉及长江下游地区民众向政府承担的部分基本经济义务,包括租庸调制中的租、庸以及两税法中的税、徭。其一,免除部分租庸调制中的租、庸。大历七年(772)十月,诏云:“以淮南旱,免租、庸三之二”[22],此处的“淮南”是指淮南道,包括长江下游地区的舒州、庐州、和州、滁州、扬州等地,由于当时唐廷实行租庸调制,所以“免租、庸三之二”是指免除舒州、庐州、和州、滁州、扬州等地三分之二的田租、力役。其二,蠲免两税法中的租税、徭役。太和五年(831),“淮南、浙江东西道、荆襄、鄂岳、剑南东川并水,害稼,请蠲秋租”[23];开成元年(836)十月,“扬州江都七县水旱,损田”[24],次年三月诏云:“诸州遭水旱处,并蠲租税”[25];开成五年(840)六月,“河北、河南、淮南、浙东、福建蝗疫州除其徭”[26];等等。
唐代长江下游地区灾害出现以后,也有采取多种措施应对某一次灾害的现象存在。比如,大中九年(855)七月,发生旱灾,“遣使巡抚淮南,减上供馈运,蠲逋租,发粟赈民……庚申,罢淮南宣歙浙西冬至、元日常贡,以代下户租税”[27],可知此次旱灾出现以后,政府采取了“减上供馈运”、蠲免租税、赈粟、罢常贡等数项措施进行应对。
三、 余论
经济重心南移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两汉时期,江南基本上处于“地广人希(稀)”[28]的状况。汉末至六朝时,江南得到逐步开发。唐代以来,江南经济开发的广度与深度均远超六朝。安史之乱以前,唐朝的政治中心、经济重心、文化中心都在以关中为中心的关陇、河东、河洛一带[29],安史之乱期间,这一带遭到战火涂炭,经济破坏严重,江淮及江淮以南地区则因张巡等人死守睢阳(今河南商丘)而基本得以保全。安史之乱以后,江南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唐廷赖以维持统治的赋税重地,时人认为“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30],经济重心逐渐南移。至北宋后期,江南经济总体上超过了黄河中游地区,这种经济格局一直延续到近代。[31]长江下游地区尤其是江南经济地位的上升对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政府对此地区重视程度也提高,这一地区的灾害记载、灾害应对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
考察历史上长江下游地区的灾害,应关注不同阶段这一地区的开发程度、经济状况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变化。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高,应对灾害能力就强;反之亦然。不过,经济发展水平高也可能折射出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程度加深,人与自然关系一旦难以协调,灾害便随之而来。历史经验表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是实现区域社会与灾害之间动态平衡的关键。
*本文系2020年度南京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六朝农业灾害研究”(项目编号:SKYC2020009)、2020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六朝农业灾害研究”(项目编号:2020SJA0056)、2021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大运河江苏段水利史典籍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1LSD003)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页。
[2][31]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与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4-21、19-20页。
[3][4][9][10][11][13][17][18][20][22][26][27](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33、933、934、915、918、3970、168、234、934、176、240、250页。
[5][6][7][8][12][14][15][16][19][21][23][24][25](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0、1358、225、1361-1362、652、429、540、544、500、538、543、566、568页。
[28](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70页。
[29]鲁西奇:《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0-186頁。
[30]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