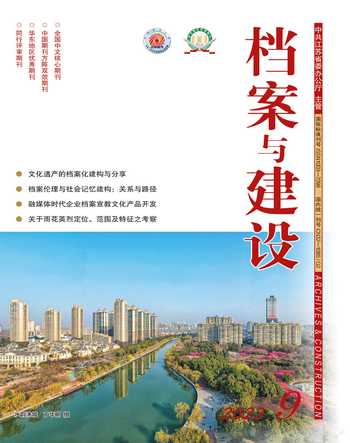如何保卫根据地之物资
耿殿龙
摘 要:经过与中国共产党长期的交手,侵华日军已深刻体会到游击战的威力,这不仅体现在军事作战方面,更体现在物资隐藏方面。中共军民通过有技巧地藏匿物资,为自己积蓄了力量,也让日军的战时补给陷入窘境。为此,日军制定了一套详细的搜索与剔抉要领,妄图开展全面“扫荡”,剔抉中共力量。在实践中,日军更多的是采用血腥暴力方式去实现所谓的“搜索剔抉”,使广大农村民众进一步认清其侵略面目,中共则借助人民力量,巧妙应对,使得日军的图谋难以奏效。
关键词:侵华日军;剔抉战术;《华北治安战》;华北抗战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收录有一份档案,名为《扫荡剔抉共军根据地之参考》。这份文件来自日军大本营陆军部,于1943年11月以《战训报第十三号》形式下达给各部队,用于战前教育,要求“贯彻到一兵一卒,并使之彻底掌握”[1]。这份文件涉及如何查找根据地物资的要领,将侵华日军的缜密、阴险及其行动计划性展露无遗,同时也从另一角度印证了中共作战之巧妙,物资隐藏技巧之高超。在以往的研究中,尚没有专文对该文件展开分析,因此本文着墨于此,在探讨日軍如何搜索根据地物资、“剔抉”共产党军队的同时,反观中共高超的斗争技巧和坚不可摧的军民鱼水关系。
一、 藏匿与搜索
1941年世界法西斯势力甚嚣尘上,侵略气焰正盛的日军为把华北变成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后勤基地,加大了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在当年冬天的“山西肃正作战”中,日军攻破了晋冀豫根据地黄烟洞兵工厂,初步总结出中共隐藏物资的方法——“(物资)多在离村庄50至200公尺的断崖、地缝、梯田隐藏……多在攀登困难的断崖绝壁之中,挖设横洞以‘悬吊法’隐藏人员或物资……在隐藏物资的洞穴上,往往放些煤灰、干草、马粪,或立有墓碑等进行伪装,或从房屋内挖地洞与之相连接。隐藏物品之处,往往埋设地雷”[2]。
隐藏物资的确是中共军队游击战术之一,此举一来为了积蓄力量,二来避免资敌。隐藏物资也确有技巧,如何在敌人“扫荡”时将重要物资妥善藏匿,需要慎重考虑且迅速决断。例如1942年夏,晋冀豫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紧张进行时,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晋冀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率领的人马在山西长治杨家山村与日军正面遭遇,李达“当机立断,要部队轻装,将笨重物资埋藏在山洞中,分成小股,互相掩护着突出了重围”[3]。当天傍晚,李达命令部分士兵星夜兼程赶到曾与日军遭遇的地带,收容失散的人员和物资。据当时参与收容工作的人员回忆,“第二天早上,我们赶到了那里……在石缝中找到了三部完整的和一部机件不全的电台,电话桌机和总机也都找到了”[4]。一二九师师直部队一连串的举动降低了物资的损失程度,展现了中共军队在隐藏物资方面的独特技巧。
为了应对日军疯狂地搜查物资、捕杀干部,冀中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地道战——用地道、地洞等来隐藏人员和物资。据日军记载,在1942年“冀中第三期扫荡剔抉作战”中,“共军煞费苦心地在平原地区修筑了多种地下设施,并以此作为抗击日军的据点。例如,在各家炕底修筑地下室,互相连通一气,甚至有的火炕地下室通过地道与村外秘密联络点相连接……地下室的规模不一,有大有小,一般能收容一百多名兵员,有的地下室仅能隐藏、储存部分军需品”[5]。而据中共方面证实,地道确为其隐藏重要军需品提供了保障,比如电台。电台需要马达转动发电,但转动时要发出沉重的响声,声音大且传得远,特别是晚上传得更远。若被特务发现,就会向日军报告,不但电台会遭到破坏,而且堡垒户甚至全村老百姓都会遭殃。经过多次试验后,冀中军民“干脆把马达放进地道里,再盖上洞口……收发报机也开设在洞口里边一侧的‘猫耳洞’里”[6]。将电台放入地洞,不仅掩盖了声音,躲开了特务侦察,保护了堡垒户,而且避免了资敌。电台持续运转,冀中地区的共产党就可以继续活动,巧妙打击日伪。
以上种种情形引起了日军强烈不安,《扫荡剔抉共军根据地之参考》由此“应运而生”。
二、 “以华制华”与暴力“剔抉”
受地域、语言、生活习惯、民心等诸多因素限制,日军单靠自身展开搜索与“剔抉”有一定难度,故除了上述提及的自行搜索途径外,还通过“以华制华”策略,“向居民、俘虏进行讯问,利用挑夫、翻译、工作队搜集情报……适当使用善于发现问题的士兵和富有经验的人员”[7],以抢夺根据地储备物资。具体说来,就是敌人派出若干间谍,“把我军驻地与军民潜藏的资材,尤其是兵工设施,绘成图表”[8]。在这些间谍向导的带领下,每至一地,日军先占领制高点、要点,构筑据点。继而“主力分犯要点,挖掘军民资材,抢走或摧毁之,同时以小部队向周围轮番搜剿”[9]。在搜剿时,日军经常利用汉奸、俘虏或胁迫民众“假装妇女叫喊,儿童啼哭,驴叫牛鸣”诱捕中共军民,“并压迫被捕者指出资材之所在”[10]。
在《扫荡剔抉共军根据地之参考》中,日军提出要强化利用俘虏、伪军和群众的力度,他们坚信中共军队“与附近居民串通一气,不论隐匿地点多么巧妙,居民是必定知道的”。为此,日军要求:“在攻击村庄时,首先应尽量搜捕俘虏或查找村内有影响力的人士,以引导、宣抚、怀柔等工作,获得人心,设法让村民自动前来报告隐藏地点。攻击村庄后,将残存的全体村民集合一处,首先进行服装检查,找出有影响的头面人物。然后根据他们所提供的情报进行扫荡、搜索……利用中国方面武装团体的协助,发挥其灵活性,效果极大,但不应令其单独行动。如无日军监视,往往会发生抢掠行为,这样会损害与扫荡有密切关系的宣抚、政治、经济工作。”[11]从文件不难看出,日军承认伪军和民众在搜索物资方面可能起到的协助作用,认同“以华制华”的效力。不过他们在搜索物资时,并不会严格地按照上述文件约束自身及伪军军纪来拉拢民众,更多是采用公开打家劫舍、刑讯逼供、烧杀淫掠来威胁民众尽快交代物资的下落。以例为证——
1943年6月,日军突袭冀中的一个村子,搜索到一口井并认定井里藏有八路军的物资,但因惧怕地雷不敢轻易下井,于是抓来附近三位老人,叫他们下井去取八路军藏匿的物资。井里确有枪、手榴弹,但三位老人矢口否认。于是敌人“弄绳子系上一位老头下了井,硬叫他捞,他在井里还说没有。敌人就把他拉出水面,再猛力摔下水去。这样几次摔,几次问,第一位老头就被灌死了。接着,后面两位也在同样折磨下牺牲了”[12]。11月,日军包围了阜平县罗峪村平阳河西边山场,开始“扫荡”。据幸存者回忆,当时不少乡亲被抓住,敌人将被抓的人“衣服脱光,绑在枣树上,开始进行审讯”。因为敌人事先已经知晓罗峪村保存有八路军的东西,所以被抓的人一旦不招供,敌人就放出狼狗咬,咬一阵,问一阵,但仍然没有人招供。“凶恶的狼狗在他们的腿上、屁股上、胸脯上乱咬,肉一条一缕地被撕下来,鲜血染红了枣树和脚下的土地。最后,鬼子又把他们从树上解下来,拖了老远,用刺刀刺死。”[13]
上述例子不胜枚举,日军妄图通过刑讯、烧杀等极端凶残的方式逼迫村民交代八路军的去处、泄露中共军队的物资下落,以此“以华制华”。然而这样的手段只会愈加激发百姓的抗日意识,加速日军图谋的破产。
三、 中共的应对之策
日军曾指出,在搜索共军物资的时候“有时需要使用重武器及炮兵部队。如有可能,应使用较大的兵力”[14]。“如有可能”一词,恰恰说明使用较大兵力的难度很大(兵力不足始终是侵华日军难以摆脱的难题)。正如刘伯承分析的那样,日军为捉拿中共首脑机关及搜刮重要物资,“必须轻装急行,才能奇袭。但轻装行动于空舍清野的根据地,就不能作持续的‘扫荡’”[15]。在《扫荡剔抉共军根据地之参考》中,日军提出建立“轻装搜索班”,正是为了“轻装急行”“奇袭”,更好地搜索物资、“剔抉”中共力量。但轻装部队力量有限,一旦补给不及时就得返回据点以作休整。尤其是随着日军南进,华北兵力持续削弱,加之国力锐减、补给普遍不足,对于驻扎在农村的日军来说,生活尤为窘迫。对此,中共抓住时机,持续深入群众、教育群众,提高其民族意识、抗战意识;同时加大了对日伪军据点的武力袭扰,各种巧妙战术轮番使用,令日军的搜索“剔抉”图谋难以实现。
以坚壁清野为例。在中共的领导下,饱受日军“扫荡”之苦的群众逐步掌握了坚壁清野的方法,他们把粮食、被服等物资分片埋藏,室内与室外结合埋藏,利用山洞、沙岭、树丛、墓地和河堤等进行埋藏,尽可能不被敌人搜到。这正应了晋察冀军区干部刘荣所言,由于日军不断地烧杀掳掠,“广大人民觉悟了,认识到唯有抗战才是生路,群众的组织力量加强了,如坚壁清野工作,在数十天内完成很好……鬼子真的在边区内实行所谓‘三光政策’,然而劫不光,烧不光,更是杀不光,因为人民把东西坚壁好了,找不到……至于杀光,人民根本不见面,人民到处可以转移”[16]。曾在河北景和镇参与过“扫荡”的日军联队长藤原彰证实了刘荣所言——“在日军扫荡所到之处的‘非治安区’……民众全都逃走了,留在家里的只有老人”[17]。另以地道战为例。1942年“五一大扫荡”之后,冀中根据地就广泛发动群众秘密挖地洞,利用地道隱藏物资。如冀中六分区,就在束鹿县的司马村地道里设了一个兵工厂,“有军工30名,专门制作手榴弹和地雷等”;而宁晋县建的藏粮洞,“可以存粮一千斤到一万斤”;同时各地区还在地道里“建了弹药库、牲畜洞等,减少了物资的损失”[18]。
在想方设法藏匿物资的同时,中共也强化了统战工作以及对敌伪的策反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抗日,以应对日军的“以华制华”。据吕正操记述,在安平县统战政策效果明显,羽林村地主佟老佐在极端残酷的环境里,腾出房屋,供抗日干部们隐蔽,并在家挖了地洞,“刻印蜡版,分发文件”;在实行了革命的两面政策后,不少伪军在每次出发“扫荡”前,“就事先送出信来”,为根据地军民赢得了隐藏物资和人员的时间;还有很多伪军“向敌人以有报无,掩护我隐蔽,或以多报少诱敌来袭,或以无报有、以少报多来威吓敌人不敢出动”。与此同时,有些伪组织、大地主还设法给冀中军队提供给养,解决物资紧缺难题。如在十分区高家场,通过当地有影响的高家兄弟,党组织“和四十八村的许多伪大乡长、联保主任、保长等建立了关系,逐步把伪大乡和保甲组织争取过来……高氏兄弟还以商人的身份,在天津为我军购买了许多药品、纸张、子弹等军需物资”。此外,十分区“赵村的大地主、联保主任宋雅斋,石岱的大地主、联保主任贾秀山,河西陶营的地主王汉池等都答应合作抗日,主动将了解到的日伪军情况提供给我们,并为我们供应给养和款项”[19]。
在1943年后日军颓势已显、中共力量正在恢复的时候,伪军、伪组织开始认清日本战败必不可免,有“很多政治小傀儡们试探和共党接近,请求他们证明其在政治上并无劣迹,这样可使他们在战后获得安全”[20],实际宣告日军的搜索“剔抉”计划破产。
四、 结语
日军所谓的“剔抉”战术虽强调“引导、宣抚、怀柔”,但实则是一种变相的烧杀掳掠战术,这只会让更多的中国人认清日军的侵略面目,加入抗战的队伍。相比之下,共产党方面在全力保护民众生产,一边藏粮藏物,并想方设法购进物资,抢耕抢收,积蓄力量;另一边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军民一起开荒种地,抗战抗灾,努力实现物资的自给自足。结果不言而喻,中共逐渐渡过了难关,且和民众建立起了深厚的鱼水关系,这种关系正是中共军民能够应对日军持续“扫荡”的力量之源。正如聂荣臻所言:“八路军英勇抗击侵略者,保护了人民,人民同样尽心尽力地保护我们,这就是经过发动群众,在军队和人民中间建立起来的鱼水关系……”[21]在这样的情形下日军想要顺利搜索物资、“剔抉”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必定走向失败。
注释与参考文献
[1][2][5][7][11][14][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M].樊友平,朱佳卿,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835,546,642,546,835,546.
[3][4][8][9][10][15]陈斐琴编.巍巍太行[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318,318,381,387,391,385.
[6]杜敬编.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99-200.
[12]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编.《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上)[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415.
[13]广濑龟松主编.燕赵悲歌:侵华日军在河北省的暴行[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356.
[16]梁山松,林建良,吕建伟编.烽火晋察冀:刘荣抗战日记选[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76.
[17]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M].林晓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38.
[18]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冀中平原抗日烽火[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375-377.
[19]吕正操.冀中回忆录[M].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271-274.
[20]G·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M].李凤鸣,译.上海:希望书店,1946:259.
[21]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327-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