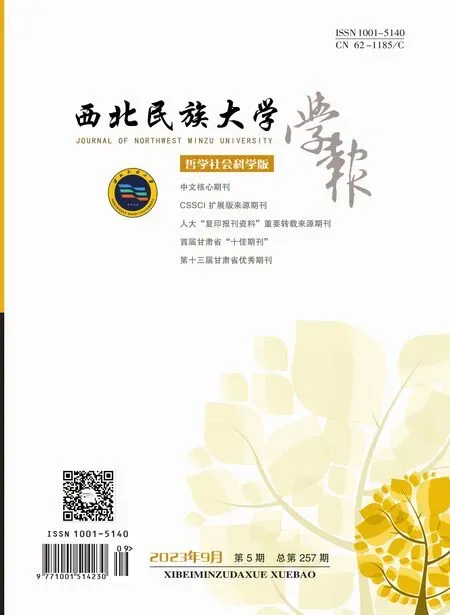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的文学精神认同
彭容丰,孙纪文
(西南民族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认同”这一术语伴随着全球化带来的冲击而逐渐被人们关注,作为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极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也一直被现当代文学与文学理论研究所重视。有学者在摸索了从精神分析到文化研究的认同理论后,总结出“认同的实践和建构始终与文学重要的表意实践密切相关”[1],同时,“认同”也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表现出一种和谐气象。如此看来,“认同”不仅仅是现当代文学与理论应当考虑的问题,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当注意的。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学交融是不应被忽视的历史事实,尤其是采用通用语言文字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群体(1)中国文学史是中华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清代文学作为中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多民族性和以秉承与发扬“诗骚精神”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的认同性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少数民族”是一个现代概念,但它的提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历史事实的总结。且文学研究应“回到文学生存的原本状态”(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而清代文学原本的发展状态便是多民族文人相互交流、交融产生的文学共同体,同时“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群体的存在的确是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奇异独特的文学现象,始终是充满活力的中华多民族文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多洛肯:《清代少数民族文学家族研究》)。故以“少数民族”概念介入清代文学是可行的,这也是当下诸如朝戈金、多洛肯、米彦青等学者着重关注的研究领域。,他们与主流作家群体之间存在着这种“认同”关系,并通过文学的实践呈现出来,其中,少数民族家族式作家群体的文学创作具有典型意义。如同多洛肯所言:“明清两代,少数民族文学家族得到充分发展,他们在郡牧儒雅的群贤文会之上积淀人文禀性,在家族亲姻的世系交融中修养家学,用诗酒酬唱汇聚独特才情,从一定意义上说,少数民族文学家族显现出明清文学家族的诗性存在意义。”[2]这是就少数民族文学家族的整体特征而言,若以空间维度来看,清代少数民族文学家族也存在明显的地域特征,如陈友康在论及古代少数民族家族文学这一现象时谈道:“少数民族家族文学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蕴含共同的生活情趣,表现出相似的艺术风格。”[3]具体而言,在清王朝的西南地区,因文学传统、地理风貌和民族混融的状态,造就了与西北、东北和东南民族地区相似的文学语境,又形成迥异的人文环境。有清一代,西南地区出现了彝族、土家族、白族、回族、布依族等三十余个少数民族文学家族,他们的文学创作体式集中表现为诗、词、文这三种中国传统文学类型,并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中,他们的文学创作所体现的文学精神有着不断与主流文学精神相融通的特征,呈现出对主流文学精神认同的现象。立足于这一背景,本文主要对毕节彝族余氏家族、姚安彝族高氏家族、酉阳土家族冉氏家族、弥渡白族师氏家族、昆明回族孙氏家族、遵义布依族莫氏家族等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2)关于家族文学的概念与研究范畴,本文采用张剑在《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宋代以降家族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及文献问题》中提出的观点:家族文学既包括家族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的文学实绩和特色,又包括家族成员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研究应该包括两个基本的范畴: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本文第二部分侧重于从文学的家族视角进行相关话题探讨。之文学精神认同进行分析,着重探讨文学精神认同产生和传承的深层原因以及这一现象与构建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话语之关联。
一、文学精神认同的主要体现
有学者指出,文学精神“是以文学为载体,从中抽绎出来的有关文学的观念、思想意蕴、审美理想、人文精神、价值取向、文体风范,以及创作主体所体现的人生态度、人生追求、人格力量和艺术创造力”[4]1-2。另有学者立足于文学史的演变事实,认为“文学精神作为一种理性智慧的结晶和形而上的哲理品格,始终存在于文学发展的进程之中……是一种动态的、历史的、内在涵义丰富而具有独立性的现象,是多元化和多种思想智慧的综合体,并历经不同时代的作家和批评家的共同创造和传承而趋于发展与成熟”[5]。综合起来看,文学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向度,存在于具体的文学实践当中,与作家和时代息息相关。一方面,文学精神在文学的发展演进中形成了具有超越个体、群体乃至时代的普遍性意义;另一方面,也因作家价值观念、生存理想等因素的不同而体现出不同的个性色彩。但不可忽略的是:因文学家族的存在,使个体文学精神得以汇聚,并在家族文士的代代传承中,构造出家族文学精神的共性特征。以清代文学而言,既有对历代共有文学精神的继承,又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文学精神,其中崇雅精神、诗史精神以及事功精神作为清代推行的重要文学精神,不仅贯穿于中原地区文学发展之始终,也在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的整体风貌中加以体现,得到认同,并浸染其中,成为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发展的精神力量。
“雅”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理念,因其呈现出儒家正统道德理想和文学审美精神相统一的特征,成为有清一代官方推行的意识形态之一,并深深嵌入到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的创作实践之中。清代帝王对文学领域的热衷与控制使“雅”作为一种精神指向风靡全国,所谓“文章归于醇雅,毋事浮华”[6]277“衡文一道,专以理明学正、典雅醇洁为主”[7]8“文艺以清真雅正为宗”[8]71等帝王们对“雅”的重视和阐发,就足以见出推行程度之盛。流风所致,明堂学校、坊间书肆等文化场所须以崇雅为宗旨。如顺治九年(1652年)《颁卧碑文于直省儒学明伦堂文》中对各地学校教学书目的明文规定:“直省学政将《四子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等书责成提调教官课令生儒诵习”,且勒令:“坊间书贾只许刊行理学政治有益文业诸书,其他琐语淫词通行严禁。”[9]646实际上,清代的崇雅精神是对具有教化人伦作用的儒家诗教理念的一种强化,也加深了这种精神在文学领域的流行。不仅北方地区的家族文士普遍崇雅,如山东新城王士禛家族中王士禄曾赞许清初著名回族诗人丁澎的诗风“典切婉和”[10]248,而且,崇“雅”的风潮也在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士群体中得到了积极响应,他们从思想观念到文学创作都表现出对崇雅精神的深刻认同。其中跨越明清两代的高氏家族文士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对“雅”的推崇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主要活动于清代的高奣映在《训子语》里特别强调对子孙的教育应以儒家经典为主,倡导学问也须从六经入手,明确说道:“入塾一二岁后,常课经书外,必讲明忠孝之大节,人情物理之曲折。”[11]471“然不贯该乎六经,是学问之无本,成渠之无源。”[11]472如此可以看出,崇雅精神已成为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士为人、为学之渊源所自。
同样,崇雅精神表现在文学领域的显著情形便是对中正和平、温柔敦厚诗学思想的提倡。如针对宗唐宗宋的诗学取向,尽管少数民族家族文士各有取舍,但是崇雅的志趣却是共通共融。如孙氏家族作为经历明清两代的文学家族,唐宋诗之争成为其家族文士面临的重要问题,但生活于清初的孙鹏以中和的眼光和视角对此进行了融合式的回答:“诗,声音之道,与文不同,以气味为高,以体格为贵,常有字句甚工,而卒不可语于诗者,气体卑也。太白之高,高在气味;少陵之贵,贵在体格……唐诗以情胜,宋诗以气胜……《十三经》尚矣,次亦必取诸子、史,他无可采。”[12]231在他看来,宗唐与学宋并不冲突,当在明源流、知法度和取材上下功夫。这些看法,既有对清代诗学发展方向的把握,也有对《十三经》、子、史典籍中汲取创作力量的推崇。又如当性情与格调之论充斥着乾嘉诗坛时,师氏家族作为乾嘉时期云南著名的文学家族,明确选择了以“雅致”为宗的诗学思想,代表人物师范一方面肯定诗歌的抒情性,他的《金华山樵诗外集》所收多温婉言情之作,但却不会因情胜而俚,诚如师范之外侄张元弨所言:“试教掩卷审音,何碍性情之正?”[13]692另一方面,他强调诗歌应当有温柔敦厚之旨,不应一味抒情,流于浮薄肤浅。在《止汀诗序》中,他对当时的诗坛风气进行揭示:“自一二浮薄者出,恃其纷杂之学,济以偏僻之才,紫色蛙声,流毒艺苑。即有斤斤自守,期无悖于温柔敦厚者,非目之为迂,则笑以为腐。呜呼,《三百篇》以及汉魏唐宋元明诸大家之所作,岂尽迂且腐哉?”[14]指出一些诗人对传统诗教的叛逆态度有害于艺林,而温柔敦厚之诗教传统才是诗道之本,他的文学主张对当地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从高氏家族、孙氏家族和师氏家族文士的身上,我们不难看出:文学崇雅精神已然化为一种自觉的文学认同感和一种文化归属感。
如果说文学崇雅精神多少带有一种意识形态味道的话,那么,对诗史精神的认同则成为清代少数民族家族文学创作的一种自觉追求。诗史精神主要源于儒家文化的熏陶,以杜甫的诗歌为榜样,把文学作为关切现实的一种艺术手段。具体而言,诸如忠君爱国的家国情怀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等,由此表现出文士们的历史使命感与忧患意识。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的创作与诗史精神的延展密切关联。诸多家族中的文士虽多居于深山密菁,却能心怀天下,将所见所感形诸笔端。他们或钟情于家国情怀与家国书写,以表心志,如余氏家族便是代表。土司家族的特殊身份并没有使家族文士忘却心系天下的责任感,文学创作表现出的诗史精神更具时代意义。自清中后期至民初,余氏家族出现了六位文士,其中以余家驹、余昭和余达父最为著名。他们对国家的认同和强烈的忠君意识在家族文学的流传中代代相承。如面对清朝地图时,余家驹写道:“观图应识我帝功,食土须尽草莽忠。”[15]81发出对国家疆域之辽阔、帝王功勋之卓越的赞美和对百姓应尽忠尽力的呐喊;余昭则写道:“图中多苍生,苍生属我意。他日展经纶,按图舒壮志。”[16]38激起为国家苍生谋福的万丈雄心;而生活于清末民初的余达父高呼“安得大手一一区划而整饬,巩固疆圉奠乾坤”[17]94,希望有能力的人涌现,整顿大好河山,重现强盛的家国。他们或以诗愤世,揭露黎民苦难,表现悲悯情怀,如冉氏家族便是一例。冉氏祖先为土司,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而成为士族,虽以诗文传家,但家族文士的仕宦不显,却使得他们能够接触到普通百姓,感受到百姓的真实生活状况,故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更加多样,思想更为深刻。尤其是生活于清朝末期的冉瑞岱、冉崇文叔侄,将诗史精神自觉地融于文学之中,成为创作的主要基调。道咸年间,天灾人祸频发,百姓的生活朝不保夕,以至于“人情恇惑,殆岌岌不可终日”[18]299,因而冉瑞岱有《苦雨谣》《大水行》《种菜行》等作品反映民生维艰的社会现实;冉崇文有《金筑张道生有金陵捷后闻客谈兵燹状感赋七绝十首次韵奉和》《洋烟赋》等作品,揭露战争的残暴与鸦片的危害,并指出“舞文纳货贿,此辈本常态。大体如斯持,我恐国体坏”[19]59,借以表明正是朝廷的腐败才致使国家罹难,民不聊生。从以上两个家族文士的创作主题可以发现,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士对诗史精神的认同不仅仅停留在对事实的描写与感怀方面,也能够发掘诗史精神所蕴含的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意识,既蕴含了作者人生理念中现实存在与理想世界的矛盾,又是积极入世的一种体现,正因如此,诗史精神所系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也愈发凸显,成为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士普遍认同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种文学精神得到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士的认可,它就是事功精神。换言之,崇雅精神、诗史精神和事功精神共同构成“‘士的文学’的脉络谱系”[20],对古代文士而言,所谓“得志得时,行其素蕴,上之正君治国,内清朝廷,下之泽物乂民,填安华夏”[21]283,即要有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儒者之志;做到自强不息,以天下为己任的儒者之行,前提便是事功精神。总的来说,事功精神是对儒家思想影响下经世致用信念的推崇,进可辅佐君王,退可严律己身,同时不废道义,区别于趋炎附势的功利主义。但在清代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文士“正君治国,内清朝廷”的志向于政治高压中日趋蜷缩,致使“经世先王之志衰”[22]473,逐渐转为对实现自身价值的关注,故而在文学创作中,事功精神多表现为对远大理想坚持不懈的追求。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对事功精神认同的表现以师氏家族和冉氏家族最具代表。其中师问忠有“非博一科第,不足以报吾亲于地下”[23]25255的志向,师范深受其父师问忠的影响,也高扬功名思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师范名落孙山,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参加“大挑”仍未成功,其在《金华山樵诗前集序》中言:“庚子仍落孙山外……辛丑遇大挑,送人作郡歌,郦者半天下,情所独注,意不容默也。”[13]378科场频频失利的冷峻现实并没有消磨掉师范的鸿鹄之志,他直言“一片雄心未肯灰”[13]388,更畅谈“松柏有本性,不作桃李姿。鸿鹄有远志,不求鷃雀知。士苟负独行,身心互相师。宁为愚者笑,无为智者嗤。即令智者嗤,所抱诚难移……仙人乔与松,浩邈非予期”[13]382,以诗言志,抒发对功名、对远大志向的坚守,不愿走向如王子乔、赤松子一样的仙隐之道,事功精神的影响可见一斑。与此情形相类似,事功精神在其他不得志的家族文学作品中常以怀才不遇和郁郁不得志的愤慨主题呈现,冉氏叔侄可谓代表。冉瑞岱有隽才,却“应本省乡试,屡荐皆不售”[18]428,冉崇文虽“屡逢名士犹青眼”,为当时著名文人何绍基看重,却科场不显,终致“十困名场已白头”[24]139,一生蹉跎,报国无门。冉氏叔侄秉持“不平则鸣”的诗歌传统,以惆怅悲慨的笔调抒发沉痛的内心,正如冉瑞岱感慨:“一万四千四百日,雄心消尽壮怀磨。”[19]33又如冉崇文叹息:“黄钟毁弃用瓦缶,白璧沉埋悲卞锅。”[19]67这些诗歌表现出的惆怅悲慨与苍郁古挺,正是事功精神影响下不遂心愿的无奈呐喊。
总之,崇雅精神呈现的美善理想、诗史精神体现的批判意识以及事功精神彰显的自强气息,因其裹挟着儒家文学思想的底蕴,成为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一以贯之的文学精神认同的三个层面,且这三种文学精神在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中的体现相互兼容,并行不悖。当然由于文学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不同,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对这三种文学精神认同的程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如李怀莲在《时园诗草序》中对余氏家族文学的评价:“先生西南世家,其胸襟之阔大,宜与寻常文士不类,又能特立风尘之外,以养其高标,故为诗沉雄浩荡,不名一家,当其上下千古,绝所依傍。”[15]245可见余氏家族文学对文学精神的认同是有所偏倚的,他们一方面有着对崇雅精神和诗史精神的认同,另一方面也不固执于对事功精神的盲目追求,反以诗酒唱和,游历名川大山为乐,故能“与寻常文士不类,又能特立风尘之外”,也因此造就了余氏家族独特的文学风格。然而就整体而言,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士偏好这三种文学精神的坐标是毋庸置疑的。这些认同现象显示出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与其他地域家族文学“异地而神交,旷世而相感”[25]445的特征,是中华文学共时性与历时性相通的情感共鸣的具体映现,也由此见出文学精神认同的巨大伟力。
二、滋生文学精神认同的文化土壤
上述三种文学精神认同的现象取决于文学内部发展规律的作用,也取决于历史文化这一广阔生存土壤的支撑。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诗文集的编纂与刊刻、秉承诗骚传统的文学理念、兼容并蓄的文学创作方法、吸收民间文学的养分润泽、保持各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优良传统、接受其他地域家族文学的成功经验等因素,构成了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精神认同的文学土壤,成为这一论题的基石和源流。而文化土壤又是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精神认同的倚靠和底蕴。钱穆曾说:“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26]41故而,从文化视角出发,探讨滋生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精神认同的文化土壤之情状,毋庸置疑是科学而有效的。
具体而言,在清代二百七十余年的历史变迁中,儒家文化始终贯穿其间,不仅成为清代文化的主体内容,更成为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发展演进的主要依据。是故,儒家文化自然成为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发展的宏大背景,也是滋生文学精神认同的支柱与底色。故要探寻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之文学精神认同诞生的文化因素,第一需要了解儒家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发生关联的起点,即文教政策在西南地区的实行成为儒家文化和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互动互构的基础,也成为文学精神认同产生的主要依据;第二要理解文学精神认同的形成当首先始于某一个体,经过家族传统与家风家脉等文化传承功能才可构成家族文学整体的文学精神认同。如此,我们才可进一步感受文教政策、科举制度、家族传统、家风家脉等因素所彰显出来的“土壤结构”力量。而在此基础上,也应回到家族文学本身,关注儒家话语体系下传统文学与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的关系。这样方能以整体的眼光,自外而内地将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之文学精神认同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清晰呈现出来。
文教政策作为清廷实现民族政治一体化,达到“华夷一家”和大一统目的的方式之一,为儒家文化在西南地区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中,作为儒家文化传播的载体,官学、书院、义学在西南地区大量兴起,以书院为例,据《中国书院史》统计,从顺治到宣统年间的新建书院,“四川(含重庆)383所、贵州141所、云南229所”[27]409,达到历代最多,这些承担教化作用的文教场所成为儒家文化与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互动互构和文学精神认同的诞生地。清初,程朱理学成为学术主流,在官方的推行下于西南地区的书院中兴盛。理学以阅读儒家经典、推行忠孝仁义、涵养性情为原旨,以提倡风雅传统和温柔敦厚之理念为目的,在这一学术思潮的影响下,儒家正统“雅”文化得以在西南民族地区流行。“雅”不仅在教化人伦和维护正统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也作为儒家传统文学精神贯穿于文学创作之中,如曾就读于昆明书院的孙鹏在谈及作诗之法时,认为经、史是创作的灵感来源,正如上文所引述的话语:“《十三经》尚矣,次亦必取诸子、史,他无可采。”表明孙鹏认识到经、史作为“雅”之精神的载体,应当渗入到文学创作主体的生命之中,形成个人性情与文学表现的统一,只有这样文学作品才能底蕴丰厚。至道光年间,以考据和学问为根底的汉学经莫氏文人传入西南,在汉学与文学的互动互构中,不仅掀起了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士文学思想的变革,也将汉学之精神旨归——以学问为根底和经世致用之思深深嵌入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士的文学创作中。如莫友芝在《郑子尹〈巢经巢诗钞〉序》中云:“圣门以诗教,而后儒者多不言,遂起严羽‘别材、别趣,非关书、理’之论,由之而弊,竟出于浮薄不根,而流僻邪散之音作,而诗道荒矣。夫儒者力有不暇,性有不近,则有矣!古今所称圣于诗、大家于诗,有不儒行绝特、破万卷、理万物而能者邪?”[28]577-578指出历来大家名家都是博览群书之士,学问是文学创作不朽的源泉。与此同时,在清末国家动荡,外国殖民者入侵之时莫友芝也表现出对国家命运和百姓生活的切实关怀并高喊“卧榻事殊南岳远,可容鳞介溷冠裳”[28]405。不仅表达了作者对殖民者的厌弃,更反映出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士的家国观念和中华民族整体意识,这是汉学与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互动结果的真实写照,更是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对诗史精神认同的有力表达。
儒家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除了通过学校、书院、义学等文教场所,更在于清廷对科举制度的推行。起初,朝廷采取分别苗汉、加额取进等优惠政策鼓励少数民族士人入学和参加科举,随着“儒教益兴,而悍俗渐变”[29]10030,四川学臣隋人鹏上奏曰:“川省苗民久经向化,嗣后苗童有读书向上者,准与汉民文武童生一体考试,于各学定额内凭文去取,卷面不必分汉苗字样。”[9]693表明儒家传统对西南民族地区的文化滋养已十分深厚,故而科举成为西南少数民族文士追求仕进的必然选择。如前文所述,在清代的政治高压下,士人往往希望通过科举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抑或通过个人的功成名就带动家族的声名远播,兼之渴望以一己之力,为所治之处带来安宁。但在艰难的科举之路中,能够成功者屈指可数,即便如此,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士依然以其自强不息和不断进取的精神迎难而上。如师问忠、师范父子,对仕进的追求已然成为其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师问忠将取得功名视作家族荣耀的根基,师范在其父的影响下“上下数十年,抱玉投珠,按剑刖足,困公车者七次,坐寒璮者六载,遍历豫、晋、秦、蜀、吴、越、齐、鲁、豫章、黔、楚、燕、赵,极涨海冰天,悬峰峻栈之险,始博一官,治一邑,功名之际,戛戛乎难哉”[13]338。师氏父子怀着对功名的炙热之情和不懈追求,正是科举制度蕴含着的事功精神在其生命中生根发芽的重要体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科举与家族紧密关联,“没有不断的科举入仕,就很难获得必要的政治资本、社会关系和经济基础”[30]5,这一针对宋代家族的论述也同样适用于清代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家族。以土家族文学家族为例,在改土归流后,作为土司家族的后裔,冉氏家族中“冉正维,其子冉瑞嵩、冉瑞华、冉瑞岱、冉瑞珉皆为增生或附生”[31],他们通过科举兴家、文学传家,最终成为名噪一方的文学家族。钱穆指出:“门第盛与学业之盛并举,惟因其门第之盛,故能有此学业之盛,亦因其学业盛,才始见其门第之盛。”[32]190是故,家族的组织形式与传承方式成为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之文学精神认同生生不息的物质保障。
自汉代以来,继统守业便是中国家族的显著特征,其中家族的传承依赖于家风与家学。清代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家族以家风作为家族的精神文化传统、以家学彰显家族的文化修养。如甘孟贤《高雪君先生家传》引道云言曰:“先生(高奣映)自幼承父训,嗜书成癖,无昼夜寒暑皆读书,倦则静坐默诵,诵已又读,博涉经史百家,凡宋元以来先儒论说,与夫诗古文词及近代制艺,皆窥其底蕴而各有心得。”[11]505可见高奣映之儒学思想与文学造诣皆有家学渊源。不仅如此,高奣映也十分注重家学传承和对后代子弟的培养,“携门人故友游结璘山馆,竟日酌酒高歌,将阑,召诸孙侍侧,为讲《孟子·养气章》”[11]506,即便是在与友人诗酒唱和之际仍不忘以儒家经典教育子孙。又著《迪孙》,旨在使子孙“顺而蹈善,进之则处仁,迁之则协义已焉”[33]140,以此来启迪后辈,不废教养。家族中学业有成的文士会自觉担任起传承家学的重担,除了亲自教导和著书立说以传于后世这两种有效的方式外,编修家谱,确立家规也是传承家学的主要途径。在冉氏家族中,将读书作为家规刻入族谱,教约子弟,《冉氏家规》曰:“顾教之之法,无过于读书,贫乏富贵,俱当留意。盖子弟贤,读书即显达之姿;子弟愚鲁,能多读书,多识字,亦必化其桀骜,开其颖悟。”[34]266指出读书问学是开启蒙昧的重要路径,更是使家族声名显赫的必由之路,家中子弟必须遵循。可以发现,家学对族中子弟的影响相较于官方儒学教化来说更直接、更有力。正是在家族的不断发展进程中,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之文学精神认同也在家族文士的文学思想与创作中以家学的形式代代相承。不仅如此,这一精神更影响着围绕在文学家族周围的文士。如在与师氏家族文士的往来中,钱沣(1740—1795)为人处世上曾受师问忠影响,以“铁面御史”之称垂范青史,在文学创作中多与师范交游唱和,切磋诗艺,在其去世后,师范搜辑其遗诗,刻为《南园诗存》。
此外,与家族紧密相连的便是家脉,即“文化家族构成系统及其延伸的姻娅脉络”[35]6,以姻亲关系联结而成的家族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生发机制,是世家大族实现家族文化源远流长和家族影响范围不断扩大的重要途径,且“文学家族的女性出嫁,会带出父母家的家教,此种家教与夫家的家教汇合,或互补或强化,形成家学传承的新推动力量”[36],这一文化特质,在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家族之间也多有体现。以余氏家族为例,自宋元以来,余氏先祖永宁宣抚使与其邻近的水西宣慰使、乌撒盐仓府便结成姻亲关系,形成牢固的姻亲网络,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这三个土司家族的联姻,不仅对巩固自身政治地位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家族文化与文学的发展上,更有利于家学与家风以及家族文化资源的不断积累。如奢辰(余保寿)六世孙余人瑞娶水西安氏女,育有二子:余家驹、余家骐。其中余家驹的诗画才能与高雅情趣的养成与他的母亲安氏有着莫大关联,也是自余家驹开始,余氏文学家族逐渐形成。且在余氏家族中,余昭之妻安履贞,便是乌撒盐仓府后裔。安履贞受家族文化影响,汉文功底深厚,诗文造诣颇高,有《圆灵阁遗稿》传世,其与余昭的诗文唱和一时被传为佳话,且其文泽亦惠及子孙,影响到了余氏家族最有成就的文人余达父。又如高氏家族在家训中明确规定:“宜择世职、名绅、贤商、文士之家。非此不宜轻构世缔。”[37]33这种以门当户对为基础条件缔结姻亲的家规,不仅使高氏家族自明至清绵延兴盛了数代之久,更使得家族之文脉不曾中断。可见,姻亲关联造就了庞大的家族体系,家族中文士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也在家学与家学的交织中确立与传递。区别于一个家族内部文学精神认同的历时性传承,以姻亲为基础构建的文学精神认同则具有传播范围宽广的优势。当然,不论是代际间的传承还是族际间的传播,均作为家族文化发展的主要内容,蕴含着文学精神认同在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中不断深化的内涵。
进而言之,文学精神认同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既是从外部、也是从内部被决定的,从内部——由文学本身所决定;从外部——由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所决定。”[38]38文教政策、家族文化等条件形成外部因素,决定了文学精神认同的发生与传承,而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与儒家话语体系下清代主流文学的互动互构则是文学精神认同形成的关键内核。在清代儒学传播的时代语境中,主流文学立场所包含的思维方式、文学观念以及文学理论形态等特征已经成为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吸纳其中精髓的同时又各有见解,从而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学的内容。如冉氏家族文人不仅主动接受了“性灵说”的文学主张,更有结合自身创作实践的自主发挥。冉正藻有《论诗十首》[19]142,其言:“思如泉涌笔如花,机杼天然自一家。”(其四)正是对提倡性情为本,以人的自然天性和个性表达为主要内涵的性灵说的认可。同时,冉正藻又有自己的思考,以诗歌创作而言主张不因袭,认为“应声虫是可怜虫”(其二);在诗歌取材方面主张万事皆可入诗,认为“庖厨渊海皆诗料”(其九);在文体选择上认为民间歌谣也是传达作者思想内涵的一种形式,所谓“歌谣中有禹皋谟”(其八)。可见与主流文学的互动互构造就了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的多样性特征,不唯如此,清代主流文学的风雅传统与民族特色的融合促成了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传统的塑造。如余氏家族的汉文诗歌创作中有不少篇章表现出对民族文化与历史的追忆,将对家族和族群历史兴亡的感怀融入其中,成为世代相传的创作主题,像《听读夷书》一诗,描写彝族毕摩传经的方式和内容,其中有言:“我本夷人解夷语,字虽未识义能通。命翁一读我试听,其义皆与经籍同。此书亦惟言仁义,与子言孝臣言忠。忆昔未曾入版图,圣教何有至荒区?始信人生性本善,华夷虽异理无殊。”[15]101“夷”虽是自古以来中原文明对边疆文明的蔑称,但在诗人眼中,用彝语传授的彝族经典,在内容上与儒家典籍和儒家思想相会通,所谓“华夷虽异理无殊”。可以看出,在与主流文学的碰撞中,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以其强大的接受和滋生能力,为文学精神认同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养料。
从一般意义上说,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是交互作用的。正如学者所说:“文学作为审美的精神文化方式,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千丝万缕的互相制衡和互相渗透的关系。一方面,文学存在于文化的巨大网络之中——我在你中;另一方面,文化的因子以文学为精微的载体——我中有你。二者在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交互作用,展示了文本内部深度阐释,以及文本外部对运行轨迹和历史动力的宏观考察的综合功能。”[39]96总而言之,在秉承各少数民族优秀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之文学精神认同因文教政策而生发,经家族传承和姻亲联结而源源不绝,并在主流文学与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的交织碰撞中彰显出别样风采。虽然清代西南地区所拥有的教育条件和文化资源与中原地区各家族文学相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些差异性,然而,鲜明的地域色彩、浓厚的生活情趣、多样的艺术风格、淡泊的气节心志等精神向度,弥补了地域偏远所带来的不利因素。是故,植根于此的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之文学精神认同更为凸显,以此生发的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更具活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力度。
三、文学精神认同与构建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话语之关系
针对“话语”这一概念,学术界有多种解释,本文以为:“文学话语的基本内涵是超出句子之后的语言组织规则,映射出外部文化政治语境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程度,即文学话语背后还存在着一些不易察觉的社会文化层面的规定性和制约性。”[40]换言之,文学话语首先以文学文本的形式存在,同时,其深层意蕴指向文本背后隐藏着的社会空间中结构化的关系网络,包括文学、文化、经济和政治等方面。具体到清代西南少数民族文学话语,可以发现它与文学精神认同息息相关。
文学精神认同与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话语的建构存在着促进与反哺的双向互动关系。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的创作是不断对传统文学吸收、学习并最终融入到其中的过程,通过文学文本之间的对话交流等形式,成为承载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话语的载体。同时儒家文化与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的互动与互构,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成为文学话语的外在支撑。可以说,文学精神认同及其生发之背景,为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话语提供了相应的文学话语资源和文学话语权力,反过来,文学话语资源和文学话语权力的掌握与运用,又深化了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之文学精神认同。纵观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的发展历程,会发现其话语的建构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也是在与清代文坛和文学思潮的关系链条中发生和呈现的。我们认为,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话语的构成既有对中华传统文学话语的吸收与借鉴,如“文以载道”“感物吟志”的创作话语,含蓄蕴藉的表达话语,“以意逆志”的批评话语等;也有融合家族、地方与民族等因素的创见,如强调直觉的思维话语,提出情景可分的审美话语,使用民族语言的表达话语等。本文则从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话语建构与文学精神认同之关系入手,结合福柯话语理论的原理,主要对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话语包含的“文学话语资源”和“文学话语权力”两个层面展开讨论。

其次,文学精神认同为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话语的建构带来一定的话语权力,而话语权力的掌握使文学精神认同的深度得以提升。按照福柯对话语与权力的解释,可以认为话语是某种言语行为在受到特定集团的认可后而具有合法性,以此形成规范相应集团内部行为的权力,这一“权力”可以指隐藏在话语背后的支配力量,“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以一种强大的话语权力来结构中国文学阐释思想理论的,是儒家‘经学中心主义’”[42]。结合清代文学而言,这一“权力”则多与政治相关联。当清代政治权力的掌握者进入文学领域之中,便通过行使文学话语权力的方式完成对文学的规训,如前文所述清代帝王们对文学崇雅精神的推行,即是在对儒家“经学主义”思想的秉持中显现出的文学话语权力,由此形成影响全国文学创作的时代风潮。故而,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士通过官学、科举走入仕途,通过文学交游和仕宦声名传播等方式积累人脉,并因为文学精神认同,促使其文学创作逐步向清代主流文学靠拢,从而在被主流文学认可的过程中拥有了一定的文学话语权力,成为家族乃至地方文坛的文学代表。如姚鼐评师问忠:“有文学、才识。”[43]371评师范:“天下才人也,工诗文,明吏事。”[43]255又如何绍基评冉崇文曰:“诗论甚有怀抱。”[44]383而莫友芝更被称为“西南巨儒”等,这些都是家族中个体文士被认可的表现。与此相应,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士文学话语权力的展现,使清代的文学思潮中出现了他们的声音。针对时人浅薄之弊,师范指出“温柔敦厚,诗教也,即闲涉讽刺,要使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方无戾于《三百篇》之旨”[23]24272,以温柔敦厚之诗教矫之,得性情之正。在格调与性灵相争的诗学背景下,冉正藻直言“鸾凤啸高空,坫坛推巨手。国朝二百年,吾服随园叟”[19]133,表明他对性灵派的推崇与支持。这些言说虽然无法在当时的文坛激起很大的波浪,但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清代文学思潮更加充实和丰富。
此外,个人文学话语权力的掌握也对提升家族文学话语权力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冉瑞嵩曾追述祖辈的赫赫功勋曰:“守忠公之平定酉阳也,仡佬獽蜑,革其獉狉而威以刑赏焉,然而文物犹未也。兴邦公请立学校,而九溪十八洞有呫哔之儒矣,然而功业未振也。海门公改官宣慰。而四司三千户,知忠义之效矣。”[45]174冉氏虽为一方英豪,早年却未有以文学著称者,故至改土归流后,冉氏文人致力举业与文学,冉广燏著有《寓庸堂文稿》《二酉山房杂著》,文学功底深厚。冉广鲤著有《信口笛吟草》,广鲤之子冉正维著有《老树山房集》等,在一代代文士的积累下,冉氏家族从以武功起家的土司家族一变而为文学世家。嘉庆辛未(1811年),黎永清序《老树山房集》云:“奉檄赴酉阳分州任。下车,询州人士之负才德敦品诣者,众口一词以地山先生(冉正维)对……先生(冉正维)设教于王姓之槐荫书塾,去镇八里,予因公赴蒲海,遂投刺谒之。先生不以俗吏为嫌,幅巾深衣,坦然相见。坐谈之欢,道气挹人,门下弟子数十,皆彬彬雅雅,有儒者气象。”[18]536从黎氏充满崇敬的口吻中不难看出,冉正维在酉阳的声名之盛和冉氏一门家学修养之深厚。如同冉崇文在《同治冉氏家谱序例》谈及冉氏家训所云:“文以载道,言以足志。词苑儒林,千秋一致。兴寄所托,汩汩其来。惟我宗人,伟抱英材。”[45]130正是在冉氏家族以文传家的家族传统中,每一位饱读之士施展出来的文学话语能力(亦可视为一种话语权力)对家族文化建构和家族声名传扬都起到支柱作用,从而构成一个家族的标志性符号,最终变为一种软实力维护家族的声誉。同时,文学话语权力不仅仅是个人声名彰显的关键,也能在家族文学的传承中强化文学精神认同的深度与广度,促进家族文学的发展,如此相辅相成,生生不息。
总之,文学话语资源的多样性是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发展的优势,文学话语权力是在拥有文学话语资源的前提下,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得以立身的关键,二者共同构成了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话语的核心内容。而这一文学话语的建构是以其在与儒家文化互动互构的基础上对文学精神认同为契机展开的,同时文学精神认同也贯穿于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话语建构过程中的各个方面,共同构成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发展演进的动力机制。立足于中华文学的整体发展脉络可以发现,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家族文学表现出的认同性使得它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与中华文学交流、交融,最终走向合流,成为清代文学乃至中华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