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的世界难题与实现路径
【关键词】流失文物追索 文物国际争端 法治建设
【中图分类号】D997 【文献标识码】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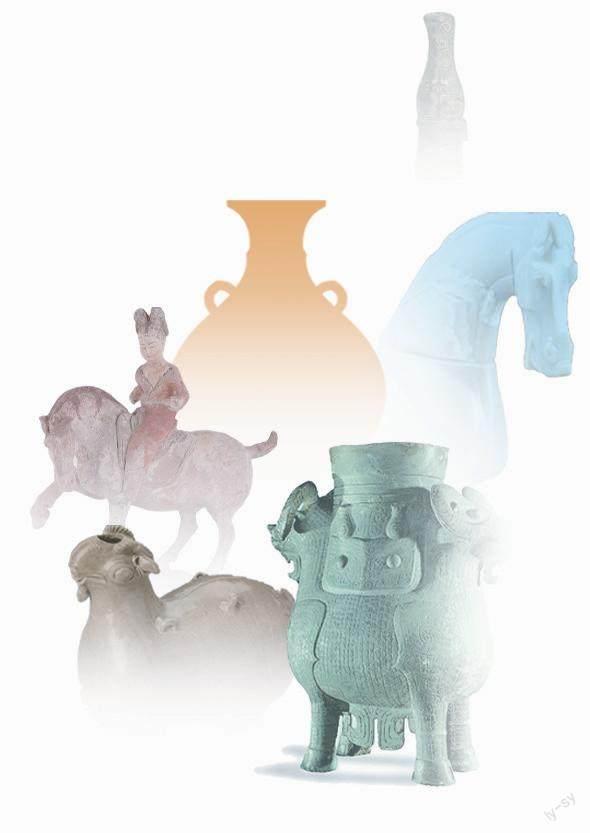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不可再生、无法复制,一旦流失损毁,其影响不可估量。近代以来,亚非拉等广大地区的大量财富,包括曾见证其古老灿烂文明的文物,因战争劫掠、殖民侵占、非法贩运等原因源源不断地流失到西方国家,①被摆放在富丽堂皇的博物馆或私人豪宅里,炫耀着其占有者的财富,也在诉说着原属国的苦难和掠夺者的罪行。
涉及文物归属的跨国纠纷,其牵涉的各方诉求、引发的国际关注、牵动的各国利益,是其他任何一种财产纠纷无法比拟的,其影响远超经济利益层面,更关乎民族情感和文化主权。譬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遭英法联军切割并掠走的圆明园青铜兽首,每次在国际拍卖会现身,就会激发亿万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再如,2019年“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成功追索流失文物带来的民族荣誉感和自信心由此可见一斑。近期,大英博物馆约2000件藏品被盗丑闻曝光后,曾受英国殖民统治的多国立即声明,被盗事件凸显了大英博物馆以文物能得到更好保护为由拒绝返还文物的荒谬性,要求其尽快将文物返还给原属国,由此引发文物追索返还的国际呼声空前高涨。尽管被劫掠和被盗文物应当返还,符合人类社会朴素的正义观和道义标准,但源于复杂的历史、法律、国际格局以及现实利益的羁绊,包括中国在内的文物原属国追索流失文物举步维艰,道阻且长。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构成一项世界性难题,亟待破解。
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的理念之争
文物是民族的文化印记与历史存证,各民族与国家对其创造的文物享有所有权,这是不容剥夺的天然权利。从历史根源看,世界范围的文物规模化流失是西方侵略、殖民统治与暴力掠夺的产物,见证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文物流失国的屈辱史。②从这个意义上说,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是对殖民、侵略与掠夺等历史罪行的矫正,是对国际秩序和公平正义的恢复。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西方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亚非拉地区的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文化主权意识不断提升,在此情形下,要求西方国家系统反思殖民罪行,将文物返还原属国的主张,已得到国际社会愈加广泛的认可。联合国大会已通过为数众多的决议,支持文物原属国追索殖民及战争期间被劫掠的文物,表达了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意志。③
然而,面对愈加有利于文物返还的国际环境,文物流入国加紧抱团和统一立场,并提出“文物国际主义”,作为拒绝返还的理念支撑。所谓“文物国际主义”,是指人类拥有共同的祖先,各民族的历史是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整体,无法彼此割裂;作为文明的载体,文物因而构成人类的共同财富,而不能由某个国家或民族独享。西方多家著名博物馆曾于2002年联手发布《环球博物馆价值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提出拒绝返还文物的理由,成为文物国际主义的代表性立场文件。
《宣言》首先构建了一个“环球博物馆”(universal museums)的概念,指出与一般意义上的博物馆不同,“环球博物馆”不是特定国家的博物馆,而是“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旨在向全球参观者提供一个参观、鉴赏、比较和研究全人类各种文明与文化成果的平台。因此,由“环球博物馆”继续持有、展览、收藏来自世界各国的文物,让各国文明在此交相辉映,更有利于文物发挥其历史、文化与艺术价值。其次,宣言指出,“环球博物馆”收藏、展览的外国文物绝大多数是历史上获得的,其合法性只能以彼时的法律予以衡量,而禁止劫掠文物和不得征集来源不明的文物是20世纪下半叶以后才逐渐确立的法律原则。换言之,那些数十年前甚至数百年前就被摆放在欧美博物馆的外国文物,它们被获取的条件与今日不具可比性,以当代法律为依据要求博物馆返还历史上获取的外国文物是不公平的。最后,“环球博物馆”拥有世界一流的文物馆藏与研究水平,文物继续由它们精心看护,更有利于保护。并且,经过多年的收藏、展出和保护,“环球博物馆”早期以各种方式获得的他国文物,已经构成这些博物馆的一部分,并由此构成其所在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因此,由“环球博物馆”继续持有这些文物符合包括博物馆所在国和文物原属国在内的各国人民的利益。
《宣言》对文物国际主义进行了系统性阐释。尽管某些主张看似合理,但只要对其行文加以仔细推敲,即可发现,这份以文物国际主义为基本理念、以“环球博物馆”为核心概念的宣言背负着一个其无法自辩的逻辑悖论:一方面,它高擎文物国际主义的旗帜,声称“环球博物馆不仅是为某国公民服务的机构,而是为世界所有国家公民服务的机构”;另一方面,它却强调这些源自他国的文物已构成所谓环球博物馆的一部分,并由此构成这些博物馆所在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如此一来,它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文物国家主义的窠臼。有学者指出,博物馆的“环球主义”(universalism)是虚伪的,它无异于披着文物国际主义的遮羞布,向世人宣布:环球博物馆拥有属于其自己的歷史、自己的政治,它们捍卫的是其自己的遗产,而非世界遗产。此外,环球博物馆获取的大多数外国文物虽发生在缺少法律规制的近代,但这本身并不能证明其合法性。更重要的是,这些摆放在西方博物馆的他国珍贵文物固然吸引着各国公众的来访和欣赏,但亦会助长不负责的征集和收购行为。对历史上劫掠、破坏文物的行为予以漠视甚至合法化,必然会助长各类文物犯罪,尤其是跨国文物贩运。
随着交通日益便利以及绝大多数文物原属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这些文物如果能被返还原属国,并置于原初历史文化环境中,它们不仅不会受到破坏,还有助于修复被割裂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增进公众对文物所承载的文明与历史的了解和对其本身的鉴赏,从而更好地认知和洞悉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身份。更何况,大英博物馆等西方博物馆近年来被盗事件频发,所谓“文物在这里保护得更好”的承诺已彻底丧失了吸引力和可信力。
由此可见,不论是借助“环球博物馆”的概念,还是“文物国际主义”的理念,《宣言》都無法掩盖文物与生俱来的民族性,亦无法为这些博物馆拒绝返还外国文物提供正当依据。
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的法律障碍
虽然战争劫掠在道德上一直受到鞭挞,但自亘古直到近代,该行径长期未得到法律上的禁止和惩罚。以史观之,不难发现,劫掠财富(包括珍贵文物)、摧毁设施(包括文化遗址)往往构成战争的主要目的。然而,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具有反思的能力与纠错的勇气。从另一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也是一部与战争暴行进行卓绝斗争的历史。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付出惨痛代价之后,人类社会终于在20世纪下半叶建立起禁止战争期间劫掠文物、禁止和平期间贩运文物和便利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的国际法体系。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法治建设水平的提高,世界各国逐渐建立了文物保护和禁止文物贩运的法律制度。尽管如此,文物原属国追索流失文物,依然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一是国际法障碍。二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在禁止战时劫掠文物与促进流失文物返还领域陆续制定了一系列国际条约,主要包括:1954年在海牙制定的《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以下简称“1954年海牙公约”)、1970年在巴黎制定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以下简称“1970年公约”)与1995年在罗马签订的《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以下简称“1995年公约”)。以上公约构成当代文物保护和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的三大国际法支柱。尽管这些国际公约的重要价值和积极意义不容置疑,但它们依然无法系统解决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的国际法问题。
首先,公约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对其生效以前的行为或事实不产生拘束力。尽管在上述三大公约的制定过程中,文物原属国普遍希望公约能明确规定其具有溯及力,以解决历史上被盗和劫掠文物的返还问题,但由于受到文物市场国的强烈反对,三大公约均未对其溯及力作出明确规定。《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除条约表示不同意思,或另经确定外,关于条约对一当事国生效之日以前所发生之任何行为或事实或已不存在之任何情势,条约之规定不对该当事国发生拘束力”,据此,上述三大公约均不具有溯及力。由此,文物原属国无法依据各公约追索其对相关国家生效前已流失的文物。公约溯及力的缺失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实际效用大为降低,亦构成文物返还的首要国际法障碍。
其次,作为文物原属国与文物市场国利益博弈和妥协的产物,上述公约大都存在核心条款措辞模糊、适用范围相对狭窄、监督机制孱弱等缺陷,致使其适用效果不彰。例如,“1954年海牙公约”将“军事必要”作为文物保护的例外,但由于公约并没有对军事必要例外进行明确定义,且限制其使用的措辞明显存在主观性过强、可操作性不足的缺陷。因而在公约的实施实践中,该例外被滥用成为一种常态。再如,“1970年公约”核心条款第7条的适用范围狭窄,事实上仅适用于馆藏被盗文物的返还,而对于原属国追索因盗墓而导致大量流失的地下考古类文物,则无法适用。④此外,上述三大公约均未能建立有效的履约监督机制,其具体实施事实上依赖于缔约国国内执法机关。由于各国执法能力、水平与态度的差异明显,公约的实际执行效果呈现出国际和地区之间的明显失衡状态。
最后,公约仅对其缔约国有拘束力,而不少文物市场国基于对其既得利益的维护,一直拒绝加入对其不利的公约,尤其是“1995年公约”。由于侧重保护文物原属国利益,强调一切被盗文物均应返还,并规定了对追索文物极其有利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创设了“文物所在地”这一新的管辖权基础,且不允许缔约国保留,“1995年公约”被视为对文物原属国最为有利的现行国际条约。然而,该公约迄今为止仅有54个缔约国,且基本为文物原属国,绝大多数文物流入国均拒绝加入。毋庸讳言,只要主要文物流入国不加入该公约,纵使其再有利于文物原属国,公约的宗旨和目的也无法真正实现。
综上可见,现行国际条约存在诸多制度和规则上的缺陷与障碍,它们尚不足以对原属国追索流失文物提供全面有力的国际法保障。
二是国内法障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当代世界各国逐渐建立了完善的文物保护和防止文物贩运的法律制度,但基于法律传统和自身利益考量等原因,各国法律在私法和公法层面依然存在对文物追索构成障碍的制度和规则。
从私法层面上看,各国国内法上广泛存在的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时效及消灭时效制度,构成文物追索返还的三项主要国内法障碍。“善意取得”是指动产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以转移动产所有权为目的,由让与人将动产交付于受让人,纵使让与人无转移所有权之权利,受让人以善意受让时,仍取得其所有权之法律行为。善意取得制度旨在保护交易安全,被世界各国民商事法律普遍采纳。在跨国文物交易实践中,买受人往往以“善意”购买人自居,并据此主张获得文物的所有权。由于“谁主张、谁举证”是各国民事诉讼法普遍采用的举证责任制度,在跨国文物追索诉讼中,文物原属国或原属人主张现持有人购买文物时为非善意,原则上需要承担举证责任。然而,由于来源存在瑕疵的文物交易大都为非公开交易,加之往往经过数次转手,文物原属国或原属人承担这一举证责任,显然是极其困难的。可见,善意取得制度及“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举证规则对于通过诉讼手段追索文物构成重大障碍。
“取得时效”是指无权利人以行使某权利之意思继续行使该权利,经过一定期间后取得其权利的制度,旨在保护长期占有的事实而产生的法律关系、防止占有与所有权长期分裂,以维持社会安定。⑤取得时效制度滥觞于罗马法,被大多数大陆法国家的法律所继受。⑥因此,即便文物持有人在购买文物时为非善意,甚至明知其为被盗文物,但经过一定时间的持续占有,依然可以基于取得时效而获得其所有权。⑦
除善意取得与取得时效之外,广泛存在于各国法律中的消灭时效制度也是文物追索的法律障碍。“消灭时效”是指“因一定期间权利之不行使,而使其请求权归于消灭之制度”。尽管各国法律关于消灭时效的性质、期间、起算、中断及中止等事项规定不一,但该制度对于通过诉讼手段追索流失超过20年以上的文物普遍构成难以逾越的法律障碍。例如,在引发各界关注的“肉身坐佛追索案”中,我国福建当地的村民委员会之所以赶在2015年12月前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地方法院提起跨国追索诉讼,主要原因在于这尊坐佛像系于1995年12月被盗,如不尽快起诉,《荷兰民法典》关于20年的诉讼时效就会届满,从而产生不利的法律效果。
从公法层面上看,不少国家的国内法规定,公共馆藏文物构成本国文化遗产,具有“不可转让性”(inalienability),从而禁止本国政府将其所有权转让给外国政府或外国人。这为西方公共博物馆返还外国文物制造了法律障碍。例如,2014年前后,中国启动对法国吉美博物馆的追索工作,要求其返还收藏的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被盗金饰片。尽管法国政府和吉美博物馆均持积极合作态度,但由于《法国文化遗产法典》关于国有博物馆藏文物不得转让的规定,双方的谈判一度遭遇困难。之后,经中法两国磋商,双方就文物返还问题达成共识,促成金饰片原捐赠人撤销对吉美博物馆的捐赠行为,使金饰片退出法国国家馆藏文物目录,再由原捐赠人将之返还给中国。大堡子山遗址流失金饰片的回归,是中法两国通过协商合作促成流失文物回归的成功案例,摸索出克服国内法障碍,实现文物返还的新途径。
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的实现路径
在流失文物追索返还问题上,国际社会历来分裂为利益对立、立场对峙的两大集团,即文物原属国(流出国)和文物市场国(流入国)。它们分别以文物国家主义和文物国际主义为理念,在国际法律、政治和舆论舞台进行长期斗争。尽管近年来国际法律和舆论环境整体上朝着有利于文物返还的趋势发展,但由于文物原属国的整体实力仍处于相对弱势,国际话语权和国际规则制定权仍主要由文物市场国掌握,原属国追索流失文物依然困难重重,文物追索返还构成一项有待系统性破解的世界性难题。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文物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自2015年起,中国(含港澳特区)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文物与艺术品交易市场国。作为文明古国、世界大国,又兼具文物原属国与市场国的双重地位,中国有能力和条件带领国际社会跳出两大集团胶着对立的利益格局与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弥合分歧,融合共识,为破解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的世界难题提供中国方案。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指引。如前所述,长期以来,文物原属国和文物市场国两大集团分别以文物国家主义和文物国际主义为理念支撑自己的利益诉求,并由此陷入零和博弈和理念困局与利益窠臼。与绝对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不同,从价值追求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审视问题的视角提升到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为解决文物原属国和文物市场国难以调和的矛盾提供了一种崭新理论,为文物追索返还领域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提供了基本理论指引。换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机调和了文物国家主义和文物国际主义,准确反映了当代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本质特征和辩证关系。
具体而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文物的要素可分解如下。首先,一国及其民族创造的文物构成该国文化主权内在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国家主权在文化领域的逻辑延伸,其中包含的民族文化发展的独立自主权构成国家文化主权的核心要素,蕴含着世界各民族文化不分高低、各文化主权平等共生的内在逻辑。因此,任何一种文化不应当成为他者的工具,成为被他者文化观察和把玩的对象;各国天然是其文物的最佳守护者,这不仅是因为一国对其本国文物最为关切,也是该国文化主权得以实现的本质要求。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诠释了各国文明多样性与人类文明统一性之间的逻辑辩证关系,是理解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钥匙。各国应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应积极展开文物交流,共同保护与共享文物发展红利。因此,流失文物应当返还原属国,但文物归属纠纷不应成为文物国际交流互鉴的障碍。同时,各国是其本国文物最合适和最便利的保护者、管理者、研究者,但在例外情况下,如一国因战争等特殊情形失去对返还文物予以有效保护的能力或意愿,国际社会应当共同承担文物的保护职责,将确保文物安全作为返还的前提,必要时施以国际援助。
至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文物民族主义和文物国际主义形成了辩证统一的关系:作为文物保护的现实路径,文物民族主义是维护文物安全、还原和展示文物真实完整价值以及实现各国文化主权的基础;而从推动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目标来看,文物国际主义则体现为民族主义的有益补充。只有在国家主义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国际主义的积极功能,才能为确保流失文物实现返还和安全的有机统一创造条件。
以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为实现路径。我国推进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一方面要在国内法治体系内加强制度建设,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手段追索流失文物的能力与水平;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本领域国际法朝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演进,做文物跨国争端解决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
从国内法治建设层面看,首先应加快修改完善法律,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流失文物追索法律制度和規则,为文物追索返还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一是充分利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历史契机,系统制定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法律条款,明确追索主体、负责机构等事项。考虑到中国流失文物的实际情况,应针对非法流失的国有文物和非国有文物,分别明确追索主体。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国家豁免法》于2023年9月颁布,我国在国家主权豁免问题上正式由绝对豁免原则转向国际通行的限制豁免原则。这为我国在外国法院提起国有流失文物的追索诉讼扫清了法理障碍。因此,我国《文物保护法》应明确,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负责国有流失文物的追索工作,并有权作为原告在相关国家法院提起流失国有文物的追索诉讼。
二是系统修改完善我国文物进出口管制法律制度,改变现行法律“管出不管进”的文物出入境单边管制状况。我国立法机关应对中国已兼具文物原属国与市场国的身份现实有准确认识,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对文物出入境制度作出实质性修改和完善,使中国法律既管住中国文物非法出境,也管住外国文物非法入境,形成双向防御屏障。
三是修改完善民商事法律制度,对被盗文物的善意取得、诉讼时效以及文物追索诉讼的举证责任制度作出特别规定,建立契合流失文物追索特点和相关国际条约要求的民商事法律制度与规则。从世界各国的立法经验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加入“1970年公约”和“1995年公约”后,为解决国内法与公约条款冲突的问题,修改其民商事法律及民事诉讼法等国内法,对涉及公约调整范围内的文物纠纷进行专门规定。例如,荷兰在加入“1970年公约”后修改其《民法典》,对公约调整范围内的文物交易作出多项专门规定,包括将举证责任倒置,即要求文物占有人而非原主承担善意购买举证责任;对涉及请求属于“1970年公约”调整范围内的文物返还诉讼适用比20年更长的特殊诉讼时效等。令人遗憾的是,我国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及2023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涉外编均未对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调整范围内的文物追索事项作出专门规定。目前,仅有司法实践通过解释“举轻以明重”的法理,在遗失物、埋藏物、隐藏物、漂流物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情况下,推定盗赃文物亦不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鉴此,为适应流失文物追索的特点,建立与国际条约兼容的民商事法律制度,我国应尽快修改民商事法律,明确对被盗国有文物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对于其他被盗文物,应建立起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对历史上的流失文物,保留国家对之提出追索的权利,有关请求不受法定时效限制等。
从涉外法治层面看,应不断加强运用国际法解决文物归属国际争端的能力,着力开创国际文物争端解决的新机制和新平台。首先,我国应积极发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合作论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合作平台,携手具有相同或相近诉求的国家,大力增强文物追索返还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权,打破西方国家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利用国际协商机制和先行制定国际软法规则等方式,推动现行国际条约制度和规则缺陷的弥合和完善。⑧
其次,充分利用我国正主导建立的世界上首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国际法律组织——国际调解院,将之打造成为国际文物争端解决的新机制和新平台。如前所述,流失文物追索返还通常涉及复杂的历史、法律、文化及民族情感因素,仅依据现行国际法与国内法,无论是诉讼还是仲裁,均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法律解决方案。与之不同,调解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往往能照顾不同涉案主体在文化、思维及法律等方面的差异,充分赋予涉案主体平等自由的选择权,更能营造一种公平公正的纠纷解决氛围,也更有利于达成令双方均滿意的调解结果。因此,作为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一项全球法治公共产品,国际调解院致力于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将超越司法和仲裁你输我赢的局限性,致力于以和平方式处理分歧,以对话协商解决争端,以互利互惠,摒弃零和博弈。这一新型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契合国际文物争端的特点,能为文物追索返还国际争端的解决提供新的选择和新的机制。为此,在国际调解院的机制构建过程中,我国和相关发起国应充分重视调解在解决文物国际争端中的独特作用,将此类纠纷纳入调解机制并制定相应的调解规则,从而为解决文物追索返还这一世界难题贡献中国智慧。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中国文物的流失和回归见证了中华民族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从屈辱危亡走向伟大复兴的国运变迁。而世界范围文物的规模化流失与追索返还则体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饱经殖民侵略之苦,在实现民族独立之后,致力于维护文化主权和国家利益的沧桑巨变。经过长期努力,中国国际地位大幅提高,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此背景下,作为文明古国和世界大国,中国追索流失海外文物,并携手广大文物流失国积极参与和引领文物追索返还领域法律规则的制定与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不仅旨在维护本国文化主权和利益,也是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的必然要求。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注: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22JZDZ003)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等著、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页。
②霍政欣、陈锐达:《文化主权视域下流失文物追索的法理思考——基于石窟寺流失文物的分析》,《学术月刊》,2022年第1期。
③霍政欣:《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法律问题》,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1—182页。
④霍政欣:《1970年UNESCO公约研究:文本、实施与改革》,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
⑤谢在全:《民法物权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6页。
⑥史尚宽:《物权法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0页。
⑦对于非善意占有获得所有权的时间,各国规定有所不同,从10年到30年间不等。
⑧何志鹏、申天娇:《国际软法在全球治理中的效力探究》,《学术月刊》,2021年第1期。
责编/银冰瑶 美编/陈媛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