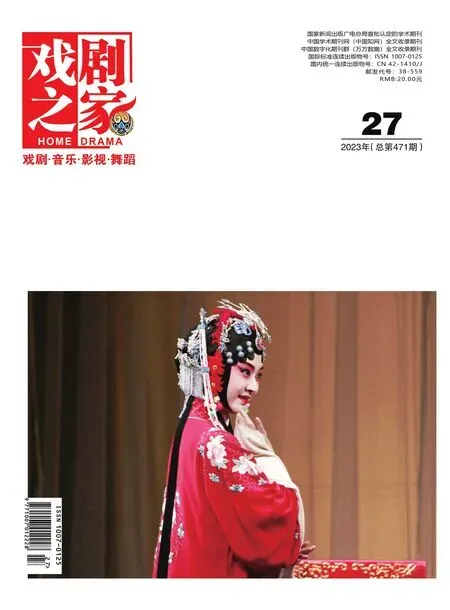想象的进化
——人工智能科幻电影中的后人类
李 琳,郭玉冰
(1.河北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11;2.洪相镇人民政府 山西 吕梁 030599)
1902 年,梅里爱拍摄的影片《月球旅行记》第一次将科幻电影带入了人们的视野,他用影像的方式呈现出人类对外太空的想象,伴随着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从20 世纪80 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科幻电影创作更多地转向了人工智能领域。
一、后人类的主体性实现
早期的科幻电影中机器人形象并不鲜明,在1927 年弗里茨·朗拍摄的影片《大都市》中,机器人玛利亚是科幻电影中首次出现的仿真(人)机器人形象,她在外形上与女主角玛丽娅相似,是策划动乱的“女巫”,虽然只是故事中的辅助叙事元素,但这种设想无论从艺术创作还是对现实科技的启示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一)机器人从绝对服从走向有“意识”
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在1950年提出了“人为主,机器为奴”的机器人三定律,这种规则展示了人类对机器人的绝对控制,成为机器人的安全标准,也预示了机器人可能到来的觉醒。在《2001 太空漫游》中,智能操作系统“HAL9000”拥有与人类如出一辙的意识和情感,它会乞求、恐惧,甚至反抗,但一旦当“理性”的研判遇到程序设计之外的情境时,则经常作出违背“情理”的错误;在《我,机器人》中,戴尔目睹了在溺水事故中,机器人凭借计算推断救下了存活机率更大的他,而放弃拯救存活机率小于他的女孩,所以戴尔始终不信任机器人。从形体的模仿到思维意识的赋予,甚至人类情感的获得,机器人在不断呈现着“人格化”的趋向,但这是以数据概率逻辑判断的结果,与“感情用事”的人类相比,它们缺失人类独有的善良、温暖等“人性”因素,戴维·多伊奇在《真实世界的脉络》中认为,人工智能是“具有人类心智属性的计算机程序,它具有智能、意识、自由意志、情感等,但它是运行在硬件上,而不是运行在人脑中的”①,机器人进化之路依然还很遥远。
(二)人——机嵌合的“赛博格”
因机器人越来越接近人类、效仿人类,人类对机器人绝对控制的“上帝”心理逐渐发生变化,凯文·沃里克根据控制论的发展过程,对“人机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类如果不与机器进行融合,那人类可能成为低等的生命。1960 年,曼菲德·E·克莱恩斯与内森·S·克莱恩在《药物、太空和控制论:赛博格的进化》报告中,首次将有机体与控制论的概念结合起来,提出“赛博格”一词,他们试图通过机械或药物等辅助方式能够让航天员更适应外太空的环境;唐娜·哈拉维将控制论与赛博格的含义相联系,在其1985 年的文章《赛博格的宣言:科学、技术与20 世纪80 年代的社会主义与女性主义》中,将赛博格定义为“一种受控的有机体,既是机械和有机体的混合体,也是社会现实和虚幻作品的产物”②,正式命名了赛博格,赛博格是有机体与机器的混合,它打破了有机体与无机体、物质与非物质的界限。
有机生命体与外在机器的结合在科幻电影中比比皆是,《机械战警》中的警察亚历克斯·墨菲有着金属盔甲的身体,《我,机器人》中的探警有着强大的机械右臂,《终结者》中格蕾丝的身体里也被植入微型钍反应锥,这些外在辅助设备的植入,超越了自然的身体,使人类增强了自身的速度与力量,甚至使用电子或生物科技脱离身体达到意识永生的人类成为赛博格形象的一种;而机器人通过不断进化,除了在外形上与真正的人类别无二致,甚至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思维与意识的超级智能机器人则是赛博格的另一种形象,“赛博格”成为跨界矛盾体的混同。在《机械姬》中,智能机器人伊娃的设计者纳森邀请程序员卡勒布帮助他完成对伊娃的图灵测试,评判伊娃与人类的真正差异,在测试过程中,伊娃诱导卡勒布讲述她想了解的知识,拉拢卡勒布并成功让其爱上自己,后又利用他杀死纳森后将其禁闭在实验室中,自己则走向了人类社会,虽然这只是电影中的想象,但人机合体的“赛博格”却提供了可替代的本体概念,它被解读为一种新型主体的哲学,打破了主体与客体、现实与虚拟、自然与技术等二元对立原则,发展成为后现代的多元性的主体概念,它的存在不仅模糊了人与人、人与机器、自然与人造等二元对立的界限,还借着界限的崩解,形成了断裂的非确定性别和身份的新主体。
二、赛博空间的虚拟化生存
“人类”是由肉体与意识构成的,意识依赖于肉身且因肉身的存在而存在,梅洛·庞帝认为,身体是人与世界接触的桥梁,人之所以存在于世界之中,正是因为我是身体的主体,因而人类意识具有唯一性,当大脑与互联网连接,意识被上传后其实处于极易被篡改的状态,黑客们可以像入侵计算机一样随时侵入人类的大脑,将别人的记忆“移植”到你的大脑中,这样的你到底又是谁呢?
(一)突破真实的物理时空
赛博空间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创造出的虚拟世界,我们可以在这里实现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功能,但它并不遵守时间、地点的限制,甚至可以没有这些参照。对虚拟空间的顶级呈现要属1999 年的影片《黑客帝国》,电影中的“矩阵”是通过连接器与人体大脑神经相连的虚假网络空间,主人公尼奥以救世主的身份被解放到脱离“矩阵”的世外桃花源“锡安”,然而“锡安”实际上是“矩阵”设计师设计的另外一个虚拟世界,虚拟世界之外还是虚拟,“矩阵”的绿色数字雨在视觉上成为技术系统控制“现实”的同义词,真实的世界根本不存在。柏拉图曾在《理想国》中以“洞”喻“世”,我们能看到墙壁上的影子,世界被分为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随后电影理论家让—路易·博德里又将“洞穴之喻”类比电影造梦的机制,电影的世界是人类梦境的实现,今天通过脑电波与电脑的连接,进入由电脑模拟的一个逼真的网络虚拟世界,当虚拟空间建立,平行现实与另类虚拟世界轻易获得自由穿梭时,它与现实的边界在哪里,它们能互相替代吗?现实和虚拟的概念还有意义吗?所谓的真实究竟在“多大范围”内存在?每当我们沉浸在感官世界中时,真实的消失和“超真实”的出现成为真实与意向的混合物,这些干扰在潜移默化之中成为我们生活的主基调。
人类一直追求意识永存、去身体化,渴望探索人类更高水平的发展,在电影《攻壳机动队》中,素子成为头脑存活身体被一体化的改造人,为了更好地实现对她的掌控,记忆移植时将素子之前的记忆篡改,带着依稀仅存的不断出现于脑海中屋子的形象,素子一直在追问“我是谁”?努力寻找着真正的自己;在《超验骇客》中,威尔尝试通过意识与计算机连接的方式抛弃物质身体,达到复活目的,由于以网络形态生活,威尔不再需要睡觉和进食,可以通过网络传播得知一切消息,但是当处于断电状态时,威尔便会受到限制,影片结尾处威尔的消失再次揭露了导演传递的人类脱离身体注定失败的观点。当科技介入了人体的改造,从机械物理的身体到和人类近似的“肉身”存在,再为不需要借助身体的虚拟化存在,但一味强调人类的“去身体化”,人的肉身被抛弃,我们都化身为社会中的信息有机体,只会让人类可能随时会面临被关闭的风险,在离身性的发展中丧失自我认同,受困于被废弃的物体形成的迷宫之中,哈拉维也曾提出“我的赛博格神话是有关边界的逾越、有力的融合和危险的可能性”④的警示,仅依赖离身性存在意味着人类的贬值。
(二)解构“乌托邦”
超越物理界限的空间拼贴和脱离肉身的虚拟存在摆脱了现实的束缚与局限,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人们的精神空间,虚拟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逃避现实的“乌托邦”。在《头号玩家》中,所有虚拟生命都可以“听命”于自己,体验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的情境,满足心灵精神的慰藉,其实看似平静祥和的游戏世界中也随处可见人性的冷淡与无情。玩家们会因贪心走进诺兰设定的金钱陷阱中,为还清债务,只能选择从事廉价且不合理的劳动;“IOI”科技巨头公司也会为了获取更多利益,一心想着独裁统治绿洲,一个没有等级制度、官僚体系、开明平等的乌托邦只是美好的想象,影片结尾,男主角获得“绿洲”的所有权后,决定每周有两天停用“绿洲”的服务器,使大家在享受“绿洲”乌托邦的同时,不要忽视现实生活。在现实世界和赛博空间可以自由游弋的网络时代,人们通过计算机连接可以摆脱身体的约束获得自由,展现了生存于信息时代的人类新景观,当打破线上和线下的界限,冲出现实与虚拟的划分,剖开种种节制时,也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需要被清醒认识并且被亟待解决的问题,凯文·罗宾斯就认为“新技术看似可以为人类创造一个新的乌托邦世界的可能、让人类以为赛博空间创造出来的仿真世界意味着对现实世界的某种解决方案,但现实却恰恰相反:视觉文化让人类变得更加厌倦旧事物和陈腐之物”⑤,最大的快乐终会带来最大的痛苦,人类可能在离身性的发展中更悄无声息地走向灭亡。
三、后人类生存的展望
人类文明长久以来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在依赖于科技却担心被科技反噬的矛盾中遭遇一次又一次的异化,罗伯特·佩普勒尔在《后人类状况:意识超越大脑》中写道:“后人类是技术世界延伸的一种存在形态”,朱迪思·哈伯斯塔姆和艾拉·利文斯顿在《后人类身体》中提到,“后人类身体是电子技术,也是屏幕图像的投影……人的身体不再是‘人类整体’的一部分,而是后人类属性的集合”⑥,恰恰是这种矛盾的存在使得我们不断反思人类主体,也许这正是想象的要义。
《霹雳五号》中的“霹雳五号”不是想要“统治”地球的“魔鬼”,也不是人类的机器“奴隶”,而是宣称“我也是一个生命”的机器人,他渴望被人类接受;《机器管家》中的安德鲁作为唯一具备独立学习与创新能力的家用型机器人,一生都在追求成为一名真正的“人类”,在陪伴了这个家庭4 代人之后,他甚至为了获得人类的身份,同意在自己的身体中注入血液,结束自己300 年的生命;《人工智能》中是莫妮卡的冷漠无情与人类伤害机器人的场面,最终导致影片中人类灭亡、新物种出现。人工智能科幻电影包含了如此多的焦虑、纠结、矛盾和不安,电影中呈现的危机深层次的原因是技术伦理失范后,人类价值异化导致的集权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后果,对人类而言,人类伦理观念的形成与自身意识、社会原则、文化规范等层面息息相关,人类行为受法律与自身道德观念的约束,同样,在面对机器人能进化为有意识个体可能中,应该给机器人学习并形成一套全新的伦理观念的设定,而不是单纯以人类的规则制约与惩罚。人工智能技术本身还远远没有达到我们想象的人类智能水平,在此发展过程中需要人工智能专家进一步发展研究人工智能伦理学,将人类最大的感性和文明优势如情感、人性、伦理道德等这些科学技术所不具备的要素加入机器与人、机器与社会环境的探寻关系中。可以预期,人类与机器人之间不再是相互竞争的对立关系,而是融合共生。
注释:
①[英]戴维·多伊奇著,粱焰,黄雄.真实世界的脉络[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84.
②Haraway,Donna,Simians,Cyborgs,a 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New York:Routledge Press,1991:149.
③[美]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M].陈静 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213.
④Kevin Robins,“Cyberspace and the World We Live In”,Mike Featherstone,Roger Burrows Ed.Cyberspace/Cyberbodies/Cyberpunk:Cultures of Technological Embodiment,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 Press,1996,P.135-154.
⑤Halberstam J,Livingston I,Posthuman bodie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