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小说的“零度写作”
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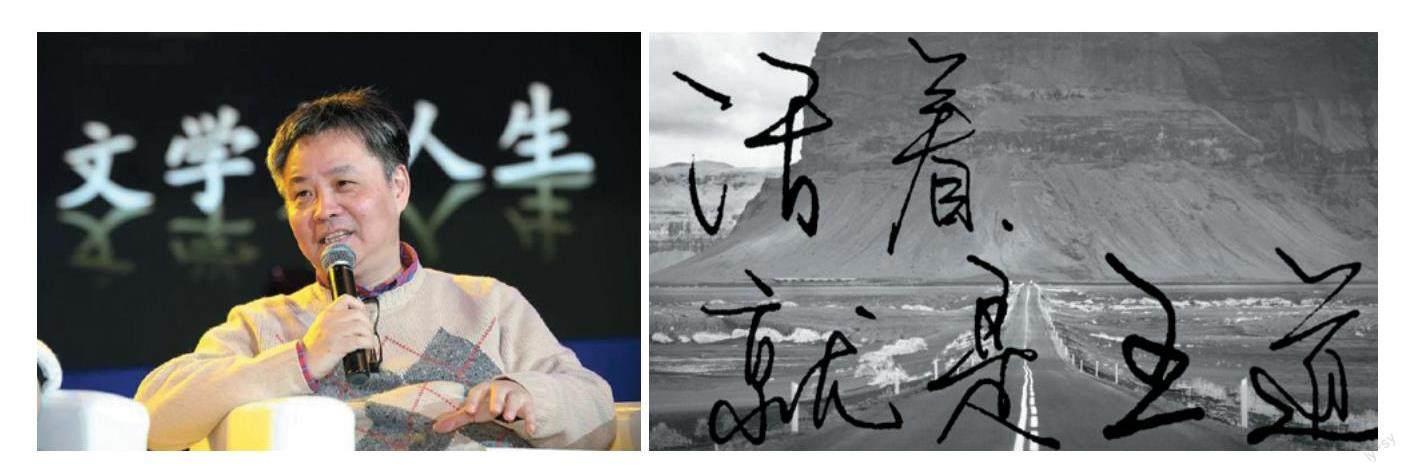

摘 要:20世纪50年代,法国文学家罗兰·巴尔特在其著作《写作的零度》中提出了“零度写作”的概念,这一概念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迅速发展,对中外现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及文学作品评论产生了深远影响。余华作为早期先锋派作家深受“零度写作”的影响,《活着》就运用“零度”的笔触,写出了福贵悲惨的一生。本文运用“零度写作”的理论,分析《活着》中所体现的“零度写作”式的叙述方式和语言,并以此来探究小说《活着》背后所体现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余华;零度写作;《活着》
一、“零度写作”理论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文学的内容及形式也会产生变化。在阶级出现以前,文学语言具有自由性和丰富性,整体写作风格呈现一种欢欣感。而17世纪阶级出现后,资产阶级为了追求权力集中,扼杀民众的话语权,自由的文学转变为古典写作,古典写作成为既具有工具性又有修饰性的写作。显然,巴尔特对古典写作的概括评价是具有批判意味的,因为在《写作的零度》一书中“工具性”被解释为“形式被假定为为内容服务,正像一种代数方程式为一种运算步骤服务一样”,修饰性则指“这种工具是以在其功能以外的外在事件来修饰的,此功能是它毫不犹豫地从传统中继承而来”。由此可见古典写作存在着某些问题,它不仅缺乏对写作的种类和意义以及语言结构的讨论,而且强调写作要有说服目的,过于政治化。因此,作家的意识形态经过不断分裂和发展,古典写作又转为现代写作,写作变得更加多样化,例如有中立客观的写作、口语化的写作、民众主义的写作等。
但是,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神圣被打破,思想写作的权利被怀疑,语言解体似乎成为一种必然。“纯文学威胁着一切不是纯然以社会性言语为基础的语言。一种混乱的句法不断向前展开,于是语言的解体只可能导致一种写作的沉默了。”这种沉默让语言的秩序逐渐被瓦解,文学语言被破坏,一些作家陷入失写症,开始逃避惯用语言,不再对作品中创造的语境负责,此时的文学进入了低谷期,马拉美、福楼拜等作家一直在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罗兰·巴尔特提出:“创造一种白色写作,它摆脱了特殊语言秩序中的一切束缚。”这里的“白色写作”就是“零度写作”,“零度写作”的概念由此诞生。
陈晓明先生在《表意的焦虑》中曾这样评价“零度写作”:“巴尔特设想有一种摆脱了意识形态、摆脱历史记忆的纯粹文学写作。”这说明“零度写作”具有丰富的内涵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零度写作”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直陈式写作、非语式写作,也是新闻式写作。这种“直陈”与古典写作所谓的“文字的现实的客观再现”有着本质区别。古典写作对现实世界的描写看似是真实和自然的,实则处处表现了客观的虚伪性,而“零度写作”力求揭开古典写作标榜的虚伪性,这就要求作家在创作时要保持客观的态度,不掺杂任何个人思想和感情,只需冷静、平淡、从容地表达出想要讲述的内容即可。其次,“零度写作”作为一种“白色写作”,其主体具有“不在”的特征。这表现在作家写作时没有任何隐瞒和隐秘,作品中不再出现作者的身影。文学语言的神圣性和社会性被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作家保持著一种中性和惰性的状态。蔡洞峰把这种“状态”解释为“零度写作的目的在于淡化写作主体的介入式价值取向和审美批判,在中性的自由写作中消解作者写作中的功利色彩,从而让文学表现生活的面更广,途径更多,内容更丰富”。最后,“零度写作”还具有工具性特征。这与古典写作的“工具性”截然不同,古典写作把写作看作代数方程式,为运算步骤服务,否定了形式的自由性;“零度写作”则以语言和社会问题为前提,使用全新的语言摆脱对古典或华丽风格的依赖。同时作家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意识的束缚,语言不再沉重,而是变成了一种可变形的中性状态。
巴尔特虽然在1953年就提出了“零度写作”,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零度写作”这一概念才在中国得到广泛发展。研究界借鉴西方文学理论所取得的成果,来分析中国文学界存在的问题,于是,“零度写作”成为评价新写实主义、先锋派等后现代写作的常用术语。随着“零度写作”在中国普及开来,对“零度写作”的批评声也接踵而至,“零度写作”开始与“不再承载某些主流意识形态”“标榜无意义或消解中心”相关联,此时作家及评论家们则需要更加辩证地看待“零度写作”。
二、“零度写作”式的叙事方式
20世纪80年代,先锋派作家们打破了旧时的文学规范,消解与反叛传统的文学模式,他们注重描写人的内心世界,放弃对历史真实和本质的追寻,强烈要求作家保持创作主体性,正如陈晓明所评价的“没有真实的历史与现实,没有意识形态的真实诉求,先锋小说似乎有些像罗兰·巴尔特所说的达到一种零度写作状态”。余华作为先锋派文学的重要作家,其前期是完全的先锋叙事风格,作品内容张扬暴力,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处于非常态、非理性;到了90年代,余华开始从极端的先锋写作,转向了平和的民间立场,但仍带有先锋姿态,限制作家对作品过多的情感投入,保持零度风格。《活着》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其“零度写作”的风格在小说中有着明显体现。
从叙事视角来看,《活着》采用的是双重叙事视角,消除了“主体感伤”形式的可能性。小说中构造了两个叙事者,一个是民谣采风者,一个是福贵,民谣采风者去乡下搜集民谣时遇到了老人福贵,并听福贵讲述他的悲惨人生。采风者在听故事时可以看作“当下”的时间,福贵回忆过去则属于“过去”的时间,这就形成了“当下”和“过去”两个叙事结构的组合和嵌套。但无论是“当下”叙述还是“过去”叙述,第一叙述人“我”都与作者无关,作者不介入、不评判。
《活着》中福贵以“我”的口吻平淡地讲述故事,这种第一人称的讲述方式让叙事者不再是全知视角,叙事者既处于故事情节中,又是一名旁观者,小说的主体性变得模糊,这也是“零度写作”理论中所说的保持“一种中性的和惰性的状态”。因为小说是第一人称,读者只能跟随福贵的视角来看待世界,通过福贵的讲述来了解小说中每个人的性格特点。但是福贵自身认知水平和感知兴趣存在局限性,对每个人的评价必然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主观性和不全面性,这又让福贵的叙述呈现出“不可靠叙述”的叙事特征,正是这种“不可靠”,拉近了读者与“我”的距离,读者和“我”在情感和心灵上产生共鸣,从而全身心沉浸在福贵讲述的故事中,作者则隐身于故事之外,任由故事自由发展,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完全感受不到作者的存在,成功实现了作者的“不在”,即“存在于各种呼声和判决的环境里而又毫不介入其中”。
从叙述语言来看,《活着》的语言平静淡漠,运用白描手法表现人物特征及内心情感,简短精练地进行非感性化叙述,与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截然不同。这在小说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活着》以短对话为主,辅以少量的心理描写来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例如,在描写福贵的爹(老爷)将要死去的时候,王喜说:“少奶奶,老爷像是熟了。”还有凤霞对福贵说:“爷爷掉下来了。”福贵点了点头,凤霞又问:“是风吹的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的死亡是既沉重又严肃的事情,但在《活着》中,只是通过几句简短的对话,就交代了死亡的经过和众人的反应。后期母亲、儿子等人死亡的时候,也是这样简单描写就一笔带过,言语之中没有过多渲染悲伤情绪,死亡的沉重与语言的淡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反而更能感受到一种压抑的悲伤。作者屏蔽了主观因素,真正做到了心無旁骛地陈述事实,这正与“零度写作”的艺术特点相吻合。
其二,《活着》用词朴素真实,毫不掩饰地表达内心真正的想法。小说中有些言语甚至是粗鲁的,例如“畜牲”“疼得嗷嗷直叫”“比几百头猪吃东西时还响”等词,但这正符合人物和环境本身的特点。小说还体现了“零度写作”揭露真实与自然,拒绝虚伪性的原则。例如出于战斗需要,解放军招人摇船,福贵本想报恩报名去摇船,但他又想到“可我实在是怕打仗,怕见不到家里人”。福贵作为底层的小人物有这样的想法无可厚非,他内心牵挂家庭而不敢去打仗,既善良又懦弱,作者塑造的并不是“高大全”的人,而是有血有肉的小人物。
其三,《活着》中客观冷静的语言下暗含着黑色幽默意味,福贵眼中的世界又带着浓厚的荒诞、绝望和残忍。小说中福贵的一生非常不幸,先后经历了父亲、母亲、儿子有庆、女儿凤霞、妻子家珍、女婿二喜、孙子苦根的死亡,而这些人的死亡方式又是非常规的,例如父亲掉下粪缸摔死,儿子抽血过多而死,女婿被石板夹死,孙子吃豆子撑死,种种离奇的死亡方式为小说增添了些许黑色幽默感,但这种幽默背后透出的荒诞让读者深深感受到世界的残酷。此外,他们死亡的时间点也很巧妙,每次都在温情的时候戛然中断,无论是故事中的主人公还是读者,都经历了情绪的大起大落,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能久久无法平静,难以从悲情中释怀,但是在小说中作者只是用客观的语言轻描淡写地结束了这件事情。例如凤霞死的时候,福贵“心里疼得蹲在了地上”,二喜“又哭又喊”,“心里疼”“哭”看似是富有感情的词,实则作者并没有投入过多感情色彩,只是进行冷静客观的零度叙述。
三、“零度写作”背后的人文关怀
提到文学作品,人文关怀是绕不开的话题。所谓人文关怀就是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崇尚和尊重人的自由发展,它与人的生存状况、尊严、情感及命运等息息相关。人文关怀不仅体现了作家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还体现了文学作品共同的价值追求以及文学追求中的真善美。余华在英文版自序中曾经谈过《活着》的创作灵感:“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历经磨难,却仍然保持对生活的初心,这也许就是余华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余华早期的作品充满了血腥暴力,对丑恶现象展开了激烈批判,但在小说《活着》中,余华以底层人民福贵的视角来描写,对福贵所经历的苦难及不公进行了巧妙化解,贯穿作品始终的是淡淡的温情,余华虽没有直接描写人文关怀,却在作品中处处体现着内心深处的悲悯情怀。
福贵和老黑奴一样,无论受过多少苦难,都怀着善意生活。例如福贵的儿子有庆为县长夫人献血,但医生抽血过多,有庆失去了年轻鲜活的生命。福贵得知这种情况后,原来心里非常仇恨愤怒,但发现县长夫人是老朋友春生的老婆后,就原谅了他,后来春生被判定为走资派,每天痛不欲生想要自杀,福贵还开导劝解他,这充分体现了福贵的宽容和善良。读者从中感受到的是人性的单纯美好、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这种真挚的感情能浸透人的心灵,于无声之中打动人心。从福贵身上可以感受到余华毫不吝啬地对生存苦难的人们给予关怀,善于发现生存中温暖人心的事,保持对生命真善美的敬畏,体现了余华对生命的人文关怀。
余华曾经说过:“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活着》这部小说中余华改变了以往的暴力叙事,他更多关注苦难中人的生存和发展,当福贵身边的亲人一个个死去,此时死亡对福贵来说已经不可怕,如何坚强地活下去才最考验人的意志。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任何时候,福贵从来没有放弃过生的希望,悲伤过后他总是能及时调整心态,继续微笑面对生活。余华的叙述方式和语言虽是“零度”的,但他的内心却充满着感情,透过冷漠的文字,可以感受到余华对福贵的怜悯之心以及浓浓的人文关怀。因此,余华的《活着》并不是要谴责社会的不公、生命的不幸、人生的苦难,而是要展现超脱常人的心态以及人性的高尚和美好。
四、结 语
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曾经对余华作过这样的评价:“余华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作家,他在每一次时代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上,都能够敏锐而且深刻地把握时代的变化,以艺术的形式表达出自己的感受、思想、情感,并且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阅读余华的多部作品可以发现,余华在文学创作上有着明显的转变,他的早期作品《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公认的先锋派的开山之作,而《在细雨中呼喊》则标志着余华的创作正在转向现实主义,《活着》虽是余华转型后的作品,但并不完全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叙述,作品中仍残留了其特有的荒诞幽默。此外,《活着》最特别的是运用了“零度写作”的手法,小说不过多渲染悲伤情绪,反对作者对作品过度干涉,运用平静淡漠的语言描述一个客观的世界,避免影响读者对作品的判断。而且余华笔下的“零度”不是虚无的,而是将个体置于历史的语境下,让小说既关注到个体的发展状况,又具有历史的思辨性。余华的作品从先锋时期的“冷漠”到现实主义的“温情”,真实是其作品永远的内核,值得读者反复阅读和揣摩。
(喀什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巴尔特.写作的零度[M].李幼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 陈晓明.表意的焦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3] 南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
[4] 陈玉洁.冷漠的局外人 炽热的零度情:《局外人》的零度写作解读[J].宿州学院学报,2014,29(7):60-62,69.
[5] 文玲.“零度写作”在中国的接受过程[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2):92-96.
[6] 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7] 萧惟丹.叙事视角延伸下的《局外人》叙事艺术分析[J].文学教育(上),2020(4):68-69.
[8] 陈思和,张新颖,王光东.余华:由“先锋”写作转向民间之后[J].文艺争鸣,2000(1):69-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