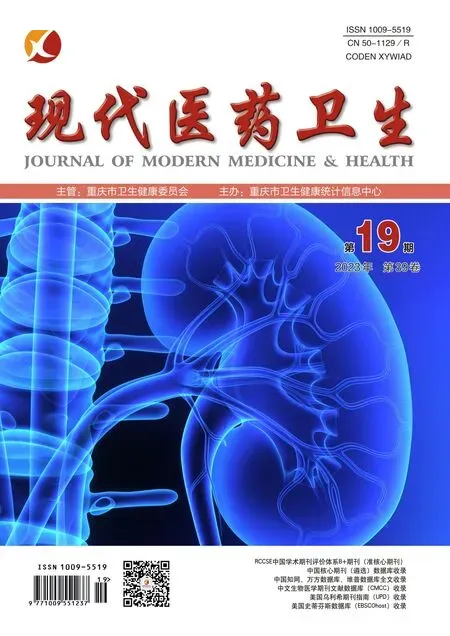肝切除术后肝功能衰竭影响因素及预测方法研究进展
苏琪植 综述,万赤丹 审校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肝胆外科,湖北 武汉 430022)
肝癌是全球第6大常见的高发病率癌症,也是导致癌症相关死亡的第3大原因,我国的肝癌患者数量约占全球肝癌患者数量的一半以上,是肝癌高发病率国家[1]。肝癌的主要风险因素包括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丙型肝炎病毒感染、脂肪肝、酒精性肝硬化、吸烟、肥胖、糖尿病和各种饮食暴露。目前,肝癌的治疗方案较多。随着肝切除手术安全性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患者可接受肝切除手术治疗,因此外科手术成了肝癌的首选治疗方式之一[2]。肝切除术后肝衰竭(PHLF)是一种较少见的术后并发症,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是导致患者术后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围手术期预测PHLF风险十分重要。
1 PHLF定义
PHLF是指由于肝切除术造成的肝脏形态结构破坏,导致肝脏合成、解毒、生物转化等功能产生障碍,其临床主要表现为高胆红素血症、凝血功能障碍、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由于纳入群体及术后诊疗方案的不同,PHLF的诊断尚缺乏统一标准。2005年,BALZAN等第1次系统地描述了与肝切除术相关的肝功能衰竭,提出了“50-50”标准,即术后第5天凝血酶原时间小于正常值的50%[即国际标准化比值(INR)>1.7]且血清胆红素大于50 mmol/L(2.9 mg/dL)是肝切除术后死亡率超过50%的简单、早期和准确预测指标。2007年,MULLEN等提出术后胆红素最高水平大于120 mmol/L(7.0 mg/dL)时可准确预测肝切除术后肝脏相关死亡风险[3]。这2个标准的主要缺点是仅将PHLF与非PHLF进行比较,缺乏分级诊断。为了克服这一问题,国际肝脏外科研究小组(ISGLS)在专家协商会议上将PHLF定义为术后肝脏维持其合成、排泄和解毒功能的后天获得性恶化,其特征是术后第5天或之后INR增加和伴随的高胆红素血症。同时,会议也制定了包含3个不同等级(A~C级)的PHLF标准。其中,A级为患者出现生化指标异常但无明显临床表现,无需干预;B级为出现较轻的临床表现,可通过非干预性措施控制;C级为出现严重的临床表现且需要进行侵入性干预[4]。上述定义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适用时间点在术后第5天或之后,对于早期预防和治疗PHLF的帮助有限。2021年,NIEDERWIESER等[5]研究认为,术后早期乳酸动力学是PHLF的重要标记物,可指导术后治疗方案。然而,这些尝试并没有产生新的和广泛使用的定义。因此,目前ISGLS制定的PHLF标准依然是文献中最常用的定义PHLF的标准,且被临床广泛接受。
2 危险因素
2.1患者因素 相关研究表明,性别、年龄、代谢水平及患有糖尿病、心肺基础病、肾功能不全、败血症均是PHLF的危险因素。男性发生PHLF的可能性几乎是女性的2倍,这可能与睾酮水平抑制免疫能力有关[6]。高龄患者的PHLF发病风险会显著增高,其原因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胆汁流量和急性期蛋白产量降低,并影响肝脏再生。另一种解释可能是与年龄相关的肝脏假性毛细血管形成,导致肝窦间隙消失,抑制了肝脏再生。体重指数(BMI)也与PHLF有关。高BMI的肥胖患者对于肝脏功能要求更高,因此导致PHLF发生率更高;而营养不良的低BMI患者对于肝脏手术的耐受性降低,也会导致PHLF发生风险增高[7]。糖尿病患者肝切除术后死亡率明显高于非糖尿病患者,其原因主要为胰岛素是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和肝细胞生长因子的重要诱导物,而胰岛素耗竭会抑制肝脏再生和细胞凋亡[8]。此外,败血症患者PHLF发生率更高,其原因主要是细菌内毒素与肝细胞相互作用,抑制了肝再生早期所需的细胞因子的产生[9]。
2.2肝脏因素 肝脏的脂肪变性和纤维化程度及胆汁淤积、门静脉高压也会影响PHLF的发生。肝脏脂肪变性导致肝窦血流动力学改变,从而导致缺血-再灌注损伤风险增加,并增加PHLF发生风险。高级别肝纤维化或肝硬化的存在也对预后有不利影响。患者死亡风险随着纤维化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在慢性肝病晚期,肝储备与术后肝再生功能均显著减弱,也会增加PHLF发生风险[3]。此外,胆管结扎后肝脏生长因子表达减少,这对肝脏再生有不利影响。胆管外引流可能导致胆盐丢失,影响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19生成,进而阻碍术后肝脏再生[10]。有研究表明,与门脉压力正常患者相比,伴有门静脉高压患者发生PHLF的风险增加[11]。术前使用化疗药物造成的肝损伤也有可能导致PHLF发生率增加。含有伊立替康或奥沙利铂的新辅助治疗方案已被证明可导致化疗相关性肝损伤[12]。
2.3术中因素 术后残肝体积(FLV)是肝功能恢复的重要因素。由于FLV不能满足机体需要,门静脉压力升高,肝脏微循环改变,从而造成肝细胞损伤,可导致PHLF的发生。因此,临床上一般采取FLV/总肝体积大于20%(肝硬化患者建议大于40%)作为肝切除标准[13]。术中失血与术后并发症直接相关,术中失血过多会导致血流改变,从而导致细菌和细菌内毒素进入肝脏微环境,增加脓毒症、凝血障碍和PHLF发生风险。在手术过程中,间歇性血流阻断或全血管阻断会在肝切除术中引起缺血-再灌注损伤,这可能会增加PHLF发生风险。此外,过长的手术时间(大于4 h)、广泛切除门静脉区域及十二指肠韧带和下腔静脉重建已被证明会对术后结果产生负面影响,并会导致PHLF。有研究表明,与开腹手术相比,腹腔镜手术治疗肝硬化合并肝细胞癌可降低PHLF发生风险[14-15]。
3 实验室检查及肝功能评分系统
3.1生化检测指标 传统肝功能生化检测指标如胆红素、白蛋白、碱性磷酸酶、转氨酶及INR等预测PHLF的能力已被广泛报道。新的研究发现,透明质酸(HA)是一种糖胺多糖,由结缔组织细胞和滑膜细胞产生,专门从血液中摄取,由肝窦内皮细胞代谢,是一种较新的生化参数。血液中HA水平可以被认为是对肝窦内皮细胞和整个肝脏的功能测试。HA与几乎所有常规肝脏参数呈显著正相关,其中许多指标被用于预测评分系统,如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Child-Pugh评分及白蛋白-胆红素(ALBI)评分[16]。
3.2Child-Pugh评分 Child-Pugh评分是根据患者腹水程度、肝性脑病、凝血酶原时间、白蛋白和胆红素将患者分为A、B、C 3个级别,其中A级代表良好的肝功能,可进行任何方式肝脏手术;B级代表肝功能失代偿,只能耐受小范围肝切除术;C级属于肝功能严重失代偿,为手术禁忌。然而,由于腹水及肝性脑病的评价主观性比较强,同时,也有研究发现Child-Pugh评分A级患者肝储备功能也存在很大差别[17]。因此,Child-Pugh评分不能作为准确预测肝切除手术的安全性指标,但可以作为手术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
3.3MELD评分 MELD是评价晚期肝病患者预后的模型,其计算公式为:9.6×ln(肌酐)+11.2×ln(INR)+6.4×病因(胆汁淤滞性或酒精性肝硬化为0,病毒等其他原因肝硬化为1)。目前普遍认为,MELD评分大于或等于11分,发生PHLF的概率较高;MELD评分小于9分,发生PHLF的概率较很低。有研究表明,MELD评分大于或等于10分与PHLF发生率和死亡率的早期预测相关[18]。但是,MELD评分系统未考虑到胆红素、凝血时间、门脉高压等因素,对肝切除手术的安全性评价有局限性。
3.4ALBI评分 ALBI评分是肝储备功能的一种可替代、可重复和客观的测量方法,可分为3个等级(Ⅰ~Ⅲ)定义肝功能损害,其计算公式为0.66×lg(总胆红素)-0.085×白蛋白(Ⅰ级小于或等于-2.60,Ⅱ级为大于-2.60~-1.39,Ⅲ级大于-1.39)。有报道表明,ALBI评分是PHLF发生率和死亡率的良好预测方式,较Child-Pugh评分具有更强预测PHLF的能力,并且ALBI评分是远期预后的独立预测因素,与肝细胞癌患者远期预后密切相关。但是,ALBI评分也存在不足,如对于梗阻性黄疸患者肝储备功能评估并不准确[4,19]。
4 核医学及影像学评估方法
4.1半乳糖基人血清白蛋白(GSA)与99mTc-甲溴芬宁核素显像 GSA核素显像是一种与核医学相关的肝储备功能检测方法,GSA仅在肝脏内快速摄取,因此可利用GSA对肝脏功能进行量化的动态评估。来自该核素扫描的几个定量指标如受体指数、血液清除指数、受体浓度和GSA最大清除率等已被证明与PHLF发生风险相关。此外,GSA核素显像也可以与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CT图像相结合,从而得到功能性肝体积、肝脏摄取率、预测残肝指数等诸多指标,对外科手术方案的制定有重大意义[20]。99mTc-甲溴芬宁试剂是利多卡因类似物,可被肝细胞摄取,直接排泄到胆小管中,而不需要进行任何生物转化,因此可以计算出肝脏对甲溴芬宁的摄取率。随后,在示踪剂在肝脏中积累的时间内获得三维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CT图像,这提供了有关功能的分段分布定量信息,可以进行残肝功能的准确评估。有研究表明,在接受部分肝切除患者中,术前测量99mTc-甲溴芬宁摄取比术前测量FLV可以更准确地预测术后肝功能衰竭及其相关死亡率。但是,核医学相关检查需要较为昂贵的设备及专业技术人员支持,而许多基层医疗中心未配备,并且核医学检查花费较高,大范围推广仍存在困难[21]。
4.2超声及磁共振评估 由于术后肝脏血供主要来自门静脉,因此门静脉血量是决定术后肝储备功能、肝再生的重要因素,可以通过测定门静脉血量流速来评估肝切除手术的安全性。而彩色多普勒超声是目前测量肝脏血流最简便、准确、无创伤的方法。国内外研究证实,术后残肝生长速度与术后门静脉流速呈正相关,术后门静脉血流量低于术前的70%,出现严重并发症的例数明显增多,患者预后较差。但是超声只能对整体肝功能进行评估,无法评估局部肝功能,且受血栓等因素影响,因此多用于术后肝脏状况评估[22]。核磁共振技术是目前评价肝功能的方法之一,其主要的优势在于可以在一次检查中提供肝脏结构诊断信息和肝脏功能信息。核磁共振最直接的肝功能评估方法是注射造影剂后测量肝脏相对于另一个器官的相对增强,如脾或肌肉。在临床实践中,该方法能够较好地预测PHLF,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如信号强度易受扫描技术影响,不同磁共振成像序列及接收线圈的选择会影响评估结果[23]。
4.3肝脏体积评估 由于FLV及其功能与PHLF发生风险相关,因此术前使用多层螺旋CT和3D重建软件对肝脏体积进行系统评估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患者术前存在肝功能衰竭或预期行大范围肝切除时。对于肝功能正常患者来说,FLV大于20%被认为是最低要求;对于接受术前化疗患者来说,FLV大于30%被认为是必要的;而对于肝硬化患者来说,FLV建议大于40%。对于那些达不到FLV最低阈值患者,可以使用门静脉栓塞术[24]。近年来,新的研究又提出了标准残肝体积、残肝分数、FLV/肝脏总体积(TLV)、FLV/体重(BW)等评价指标,其中标准残肝体积=FLV/体表面积,残肝分数=FLV/功能性肝体积×100%。有研究发现,术后死于PHLF的患者标准残肝体积小于250 mL/m2。由于不同个体间肝脏体积差异较大,因此使用体表面积标准化的FLV来评估PHLF可缩小不同个体所带来的差异。有研究提示,普通患者肝切除术后残肝分数大于26.5%是安全的,而术前已有肝功能损害患者残肝分数大于31%则较为安全[25]。有研究发现,FLV/TLV能够预测肝切除术后肝功能障碍,患者术后FLV/TLV≤20%时,发生肝功能障碍风险极大。有研究表明,FLV/BW更能准确地预测大范围肝切除术后肝功能衰竭发生概率,RLV/BW≤0.5%的患者术后发生肝功能损害的风险增加,若RLV/BWR<1.4%,则患者发生PHLF的风险极大[26]。三维可视化成像技术在以上诸多方面存在优势,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首先,由于肝脏模型的建立需要质量较好的薄层CT数据作为基础,如果CT扫描质量不佳,会严重影响肝脏的体积评估。其次,巨块型肝癌因瘤体较大常压迫第二肝门及肝内粗大静脉,可能导致肝静脉成像不全,致使肝静脉走行及流域分析出现误差,给术前评估带来影响[27]。
5 其他评估方法
5.1吲哚菁绿(ICG)清除试验 ICG是一种水溶性菁染料,与血浆蛋白紧密结合,仅由肝脏清除。血浆ICG清除率,ICG半衰期及ICG 15 min滞留率(ICG R-15)等均已被引入作为潜在的肝功能指标,并可能与PHLF相关。LE-ROY等[28]使用ICG R-15制作的决策树提示,胆红素正常且无腹水患者ICG R-15<10%时,可以安全地进行大范围肝切除。若ICG R-15轻度升高(15%~20%),且预估FLV足够,也可进行大范围肝切除术。最近,日本肝癌研究小组将ICG R-15纳入修改后的肝脏损伤分级系统,其主要指标包括血清胆红素、血浆白蛋白、凝血酶原延长时间、腹水程度、是否存在肝性脑病和ICG R-15水平。新的评分系统比单独使用Child-Pugh评分更能准确地评估肝储备功能,并影响手术决策。但是,ICG清除试验受到门脉癌栓、动静脉瘘、胆红素水平及胆汁排泄分泌障碍等影响。因此,临床上也不能单纯依靠ICG来决定是否手术及手术切除肝脏的范围[29]。
5.213C-美沙西丁呼气试验13C-美沙西丁呼气试验是一种新的肝功能评估方法,具有非侵入性且易于执行的特点,其在临床应用中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13C-美沙西丁呼气试验原理是基于CYP1A2酶系统分布在肝脏的整个功能单位,且不受药物或遗传变异影响。有研究显示,术后第1天13C-美沙西丁呼气试验值与PHLF和肝功能衰竭相关死亡率的预测有关[30]。但是,在肝细胞癌患者中,CYP1A家族成员的表达显著下调,这使得该检测在需要肝切除的整个患者群体中的使用并不普遍。
6 小 结
随着外科手术的发展,PHLF发生率逐步降低,但其对患者预后的影响仍应被重视。术前对肝储备功能进行科学评估,预测手术切除的安全性是肝切除术的基础和保证,也是肝脏外科的核心问题之一。开发一种准确、易用、能够测量局部肝功能的评估方法是预防PHLF的最重要环节。这不仅可以帮助肝胆外科医生评估目前被认为无法手术患者的残余肝脏功能,而且可以避免对残余肝脏功能有限的患者进行手术。目前,由于肝功能评价方法众多,术前需要结合患者个体特征与临床经验,对常规生化指标、影像学检查和肝脏体积分析等结果进行综合评估,以更好地避免PHLF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