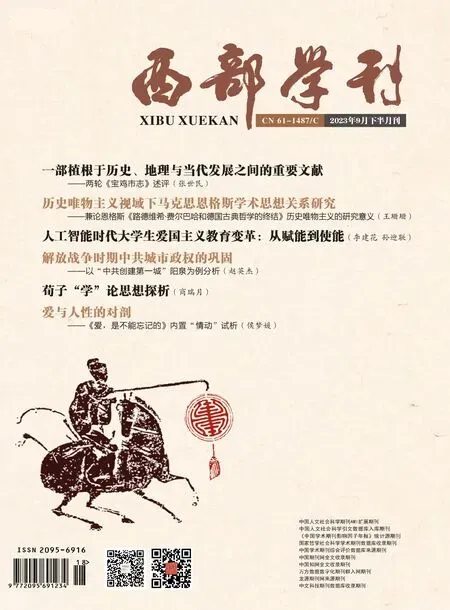爱与人性的对剖
——《爱,是不能忘记的》内置“情动”试析
侯梦媛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爱情彰显人性,两性关系的剖面夹杂着精神上的快感、痛感、绝望、奢望,以及世俗间所有的甜蜜、亏欠。人与人交往中形成的“情动”场景,既为当时所处的历史情境所规定,也取决于参与主体的个性与际遇。那些不经意间的暧昧与摩擦构成了现实伦理约制下的“羞耻”肇因,塞奇维克(1)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美国性和性别研究专家,早期致力于性别研究和对酷儿理论的开拓,代表作为《男人之间》(Between Men)和《密柜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将“羞耻”作为“情动”之一种,并赋予其独特的理论安置。主体为“羞耻”的召唤而联结,同时也因逃避“羞耻”建构出彼此的认同,“羞耻”反成为了情感内化与外显的交界,与斯宾诺莎、德勒兹(2)吉尔·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1925—1995):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到马苏米的本体论情动路径对观,或许可以开掘出中国当代文学文本内“情动”的多层向构。
一、“羞耻”还是禁地:非碰触的“情动”围城
细细品读张洁的文字可以省察到,《爱,是不能忘记的》(以下简称《爱》)有许多在时下看来“逆向”的“情动”呈露。例如,女儿珊珊产生的“不想嫁人”的理性冲动“绝不是因为害臊或是在忸怩作态”[1]105。面对乔林的求婚,珊珊的犹豫反倒仿佛“冒犯”了众人,招来了蜚短流长,“凭她那些条件,还想找个什么样的?”[1]102这与母亲钟雨的“反常”克制形成了鲜明对照。塞奇维克意义上的羞耻从酷儿(3)酷儿:是所有不符合主流性与性别规范的性少数群体所使用的身份、政治和学术用语。转借并拓展到性别层面,其社会性在于依恋和欲望的“中断回路”[2](broken circuit)对自我和他者的区隔、推拒和吸附。如果说珊珊的“羞耻”是被小说时代环境等外置视角观察定义的,即主体自身并没有这样的“情动”感知,那么母亲的“羞耻”则是小说内置“意识形态”规制的结果,即历史价值内化形成的“意志”压制与人本质性欲望的冲突。珊珊被外加“羞耻”是因为与“知性”常态偏离、对“爱”的不确定的想法。母亲的内生“羞耻”则是“情动”主体渴望获得“情感”接触对象的回应却因已知必然无法得到回应而对于“情动”回路的自我截断,如母亲与“他”相遇时,“牵我的手突然变得冰凉,而且轻轻地颤抖着”“虽面对面地站着,却是谁也不看着谁”[1]111,当“他”挨民警训斥时,母亲自然地发生了情感的联动,“就像小学校里一个一年级的小女孩,凄凄惶惶地站在那严厉的校长面前一样,好像那民警训斥的是她而不是他。”[1]112母亲的明明在意转化为同“他”极为悖反的“相约忘记”。张洁在小说中似未给出类似“拥抱”“爱抚”“呼吸急促”等更为明显的“情动”标记,但由“情动”而缔结的“窘迫”“惶惑”恰恰构成了生理结构性的自我局促,“冰凉”“颤抖”和目光的回避,何尝不是另一重意义上的“脸红”(blush)?Elspeth Probyn在Blush: Faces of Shame中将“羞耻”作为道德晴雨表的作用方式,它通过给人以不愉快的体验导致面部的胀红、“刺痛”[3],而这种“刺痛”进一步溢散便转换为人际关系或两性交往中的不稳定模态。母亲和高干“情动”关系的确认正是通过“非碰触”性的相吸与疏离的往复,以一种更隐微的方式搭架起了应激聚拢的网络。
那么,母亲和高干间的“羞耻”情动从何而来?现实“伦理道德”筑就的高墙多大程度上有被“震摇”的可能?张洁在《爱》里突出到一个特定的时间:1969年的冬天。在“文革”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他因为坚持真理、挑战红极一时的“理论权威”而受到迫害,死于非命,母亲为“他”在手臂上缠了黑纱并因此挨了好一顿批斗,当他人追逼乃至女儿询问时,母亲都闭口不言“他”的身份,此刻“羞耻”分裂出了二重性。一是历史时刻框定,母亲和“他”被动承受的污名、指责、痛苦;一是带有“自愿牺牲”意味的“羞耻”回避。在塞奇维克看来,羞耻通常具有延展性,其产生的原因多为个体在公共视线中的暴露,“羞耻”在承受的共同面上将母亲与高干隐秘地归聚一处,二人既被这种感觉所吞没,也因这种感觉实现了更深一层的相契。高干和他妻子的婚姻既是母亲和“他”爱的阻抑,也使“羞耻”情动被绑缚了时代的“情”和“理”的双重枷锁,母亲珍视心底涌泛的、隐匿珍藏的“恋慕”,却又从这“恋慕”中无法建构和“他”的爱情身份认同,“羞耻”早已超越了女性被传统预设规约的“矜持”造作,而成为了一种抑制性的情感存在,母亲在“羞耻”中愈加确认自我,同时,又因“羞耻”与“他”陷入了一个“情动”的双向围城和语境,想要靠近又无法靠近,想要宣称又无法宣称,想要动情却又耻于情动。如此,“羞耻”便兼有了情感施为和受予的双重意境。母亲和“他”只能“淡淡地、心不在焉地微笑着,像两个没有什么深交的人”,一生未曾告白、未曾碰触,甚至连手也没有握过一次,遑论其他。“羞耻”被抽衍出了深层“依恋”,“依恋”则在自我强制撤回的拉锯中加深了情动“禁忌”的历史确认。
二、从逃逸到收敛:情动链条的生成与变奏
格雷戈里·J·赛格沃斯的《从情状到灵魂》认为“情动”是“独异性(singularity)的瞬间”[4],情感在人与人之间分解消散并向各方逃逸,德勒兹和伽塔利更为强调“情动”逃避知性解释的一面,从情状(affectio)到情动(affectus)再到具有直接表现性的世界(灵魂),身体情感能力的区间不断拓宽,在有强度的变奏运动中,“知性”实际被逼遣到了“情动”的主观界域以外,张洁的《爱》里便带有时代症结凝绕的诸多“情”“理”冲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现代的性爱”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5]。但老干部的婚姻却起因于革命道德、阶级情谊,他的情动对象是在观念中被给予的,“想要”这个事实本身并不是一个观念,而是一个“情动”[6]。珊珊眼里的母亲“生得并不漂亮,可是优雅、淡泊,像一幅淡墨的山水画”[1]107,高干给人的观感则是白发“堂皇而又气派”,眼睛“十分冷峻地闪着寒光”[1]110,“情动”的观念借由肉体的直观得以具象化,同时进一步牵引着各自的行为:她为了他,煞费苦心地计算对方上下班可能经过那条马路的时间,只为了“看一眼他乘的那辆小车、以及从汽车的后窗里看一眼他的后脑勺”,当她在纷乱的台下隔着距离、烟雾、灯光、人头寻觅他在台上作报告的身影时,泪水会不自主地上涌眼眶,逢到他咳嗽得讲不下去,她就会揪心忧虑;同样地,他为了她,“天天,从小车的小窗里,眼巴巴地瞧着自行车道上流水一样的自行车辆”[1]114,担心她的车闸“灵不灵”“会不会出车祸”“逢到万一有个不开会的夜晚,他会不乘小车,自己费了许多周折来到我们家的附近”[1]114,在百忙中也不会忘记注意各种报刊查看母亲发表的作品。行动的双向回指无形地搭架起了二人的情动景观,个体行动与感觉的张力场就这样逐渐地联结并向外生长,无声的盟约在此建立,母亲和“他”的“情动”在纳入读者观察视角的一刻,自动生成了深沉而绵密的情感,这种外部目光对小说内置“情动”的审视加剧了身体触接在情节安排、关系集合构成中被压制的程度,即“情”自身的内蕴滋长逐渐与触接分离,“他”与“她”因礼法的限制只能生成各自理性范围内的情动,无法彼此抵达、接通,这就造成了“情感”与“行为”逻辑的失衡,对于斯宾诺莎或德勒兹而言,人的本质就是他的欲望,欲望是意识的冲动,但张洁的《爱》里,“欲”的部分被非常态地抛舍了,身、心在“情感”上极力合一,在“伦理”上极力离分,“爱”与“欲”成为犄角,压迫着“情动”下“他”与“她”的每一寸神经,情感的强度不断地收紧,却愈收紧愈贲张。高干本“不相信爱情”,但人至黄昏“才意识到他心里也有那种可以称为爱情的东西存在”,到了他已“没有权利去爱的时候,却发生了这足以使他献出全部生命的爱情”[1]118。母亲亦死死地挣扎过,她曾写道“有多少次我有意地滞留在远离北京的地方[……]可是等我出差回来,火车离北京越来越近的时候,我简直承受不了冲击得使我头晕眼花的心跳”[1]115。“爱”让母亲像“小孩子”一样紧张、痴心、忘情,她无可救药地悲苦着,同时也自甘着,缠卷进一种与自身关系不合的关系之中,没有什么力量能引领“他”和“她”走出这自伤损害的际遇,或曰,这决不是简单的“悲苦”,而是交杂着“愉悦”“忧惧”的复杂情动,行为能力摇摆于“削弱”与“增强”的心理之间,使情绪随着外界扰攘不间断地起伏耗散,主体“逃逸”解脱的愿求便生成于杂感线向稳定态的数次驱策回环。小说结尾处,女儿珊珊突然有些体会到了母亲行将就木才揭开的这份“爱”的恍惚悲凉、镂骨铭心:“我觉得那简直不是爱,而是一种疾痛,或是比死亡更强大的一种力量”,“爱”的不朽性得以彰显,是以“悲苦”在“情动”的容贯面上遭遇封堵,母亲内置的情感被强行中断,经由一次次地自我劝服终于瓦解,逃逸或清除了“情动”后撇弃了联结的可能性,走向了各自的通途,就像母亲“分明至死都感到幸福:她真正地爱过。她没有半点遗憾”[1]120,但从她对“天国”的希冀来看,怎么可能真无“半点遗憾”?“死”不过是“逃逸”的起点,“逃逸”的尽头不是“身”的毁朽,而是“心”的再生,“情动”的再度回敛。
三、去偏执化:情动主体的“抑郁”修复
1980年第1期的《文艺报》,同年第2期的《文汇增刊》,以及随后的《光明日报》《北京文艺》《新文学丛论》《鸭绿江》《读书》等刊物皆发表文章评论了张洁的《爱》,其中主要涉及的核心问题是“主人公的‘精神恋爱’是不是道德的?如何评价老干部的婚姻?”[7]既然性爱的本性是排他,老干部和原妻“无爱”的婚姻又在多大意义上可以出离“抑郁”?母亲和高干“就像一对恩爱夫妻”般精神上的日夜相契到底是对纯真之“爱”的持守还是三角情动主体相互的妥协、毁伤?道德的雷池究竟有无被反向成为人性中“懊悔”“软弱”“卑怯”的挡箭牌?在1980年代“人”的解放流向中,《爱》无疑承接了启蒙时代女性写作的总体氛围,世俗向度“情”的遏断转而接入了超时空性的男女平等、互悦之“情”的舒展,而转接的托举之力实为“压抑”切面爆裂后从人性固有的消极“情动”中提炼出的“治愈”幻象,“如今,他们的皱纹和白发早已从碳水化合物变成了其他的什么元素[……]哪怕千百年过去,只要有一朵白云追逐着另一朵白云;一棵青草傍依着另一棵青草;一层浪花拍打着另一层浪花;一阵轻风紧跟着另一阵轻风……相信我,那一定就是他们。”[1]120“抑郁”的质素全然化解,“情动”实现了自体的扭转,而这仅是宏观向度上的切号,“痛感”缠绕着“快感”,又反复寄身摇摆,母亲和“他”的两性之爱终于有了降落容处之地,尽管如此虚幻,不论是对肉身囿限的突破,还是“痛感”的消解抹煞,皆潜藏着对向的情感拉扯,“抑郁”以“爱”去修复伦理罪咎与历史创伤,结果可能仅限于“伤痕文学”潮流下的中度调和。
倘以母亲和老干部的原妻作为平行联结的视点,我们会发现情动主体的“抑郁”修复实际辗转于由爱衍生出的人性剖面“利他”和“自私”的中间地带。就张洁的叙述而言,“他”的原妻或许并不知晓母亲的存在,而母亲却避无可避地当上了旁观视角的知情者,面对老干部出于道义、责任选择的“殉道”性婚姻,母亲显然愿意表示理解并维护,但如此的淡漠真的不曾包含丝毫的嫉妒吗?为羡憎所起的“情动”真的可以避免走向彼此反对、互相畏惧的结果吗?“抑郁”在其中又起到了多大的作用?高干对掩护他被捕牺牲老工人的报恩究竟是利他还是自私?主观上的利他是否造成了客观上的自私?巴特勒举用了塞奇维克《男人之间》的问例表示,女性被欲求实际上暗含着两个男人之间的同性社会纽带[8],假令性别翻转,那么,母亲和“他”的原妻在“爱”之界河两侧的关系便陷入了微妙的共振。“妒嫉”被悄无声息地凝缩为了一种正向“偏执”,一种迷恋而不得的苦涩心情,情动主体罹受精神碎裂片刻的同时调用起了自我防御机制,母亲潜意识里拒绝接受丧失所欲、所爱的他者之痛,于是只能通过模仿行为“延续”这个他者的存在,把他者合并到自我本身的结构里,“经由逃避到自我里,爱免于毁灭”[9],老干部的情动逻辑同理,如“他”表露“情动”的言语符号就是依仗母亲的“抑郁”分衍:“您最近写的那部小说我读过了[……]其实,那男主人公对她也会有感情的,不过为了另一个人的快乐,他们不得不割舍自己的爱情。”[1]112“抑郁”情动的内化消解掉了老干部“崇高”选择背后对情动客体负面情感的激发,“他”和原妻并无“爱情”的许多烦恼,几十年风雨相伴,生活得和睦、融洽;“他”和“她”谨守礼法的红线,默默保持着精神上的共生固恋,道德的利他本与爱欲的自私势难调和,但“抑郁”则将二者的矛盾隐匿收束,使被搅动的“情动”流体重新提举到审美辨识的层面。
四、结束语
总体来看,张洁《爱》的内置“情动”实质上裹覆着绵密的社会学“毛刺”[10],而“羞耻”对于文本的渗透更像是“去主体化”的情动受到了过去时代精神“毛刺”拨弄的产物,因为“羞耻”,所以想要“逃逸”,“逃逸”的回敛又再次触发了“抑郁”的修复程序,快感为抑郁所支配,“爱”则冲破了麻木无情的表象,剖分出人性的异色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