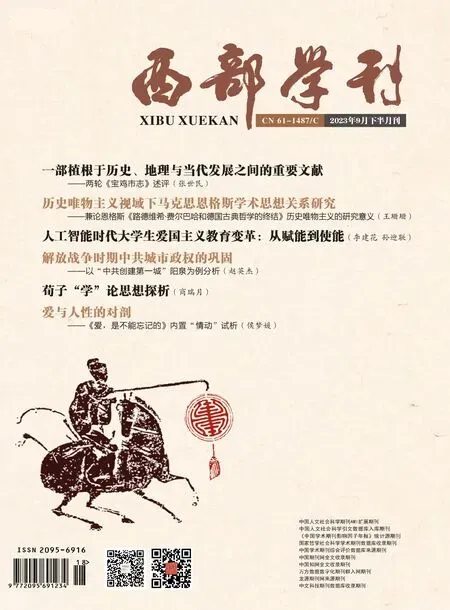价值论视域下柏拉图“诗哲之争”的矛盾调和
孙浩然 王 腾
(苏州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苏州 215000)
“诗哲之争”是西方哲学中一个古老的辩题,其主要讨论的是哲学与文学的关系。通常,文学不排斥哲学,甚至倾向于获得哲学的深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也不排斥文学。在柏拉图这里,作为文学的基础形式之一的诗,是受到贬斥的。这种贬斥实际上是柏拉图对诗的超越,其关键在于诗教思想。倘若我们从价值论的角度进入柏拉图的诗歌教育,考察其中的价值指向,将会对理解“诗哲之争”的矛盾调和大有助益。
一、柏拉图之诗论
柏拉图不惜以强辩的方式,发起“诗哲之争”,他用激烈的言辞批判诗人:
“诗人应该得到‘正确的’理解,并与画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因为他在两种意义上与画家一样。第一,他的作品从属于真理;但对真理没有多大价值。第二,他诉诸人性的低级部分……我们应该拒绝他进入一个有政治教育的国家,因为他培养了进化的人性的低级部分,破坏了理性部分。”[1]84
柏拉图将诗人与画家归为同一类人。诗人和画家首先应受到斥责的是“作品对真理没有多大价值”,这一点暗含着如果其作品对真理有价值,那诗人是应当受到爱戴的。
那么诗人的作品对于真理是否有价值呢?理念论中可以找到答案。在理念论中,理念的世界是作为真理而存在的,而现实世界则是第二性的,是真理的摹仿。在此基础上,柏拉图提出艺术模仿论:画家只是对摹仿的模仿。柏拉图以床为例阐释了对摹仿的模仿,他说:
“不是有三种类型的床吗?第一种是自然的,说是神做的并不过分,除他之外没人能做到;第二种是由木匠做的;第三种是由画家做的。”[2]
第一种床是神所造的,“是‘床之为床’的理念,被称作本有的床”,这个床是唯一的,神只会创造一个,再多创造则毫无意义;第二种是木匠制做出的“个别的床”,这个层次的床“不是实体,而是接近实体的东西”,是具体的体现,是对神创造的唯一的理念的床的模仿;第三类床是画家通过对个体的床的模仿而创造出的床的影像,柏拉图称之为摹仿的模仿,这种床的影像不是对理性的模仿,它只是一个影子的影子,“离实体有三层距离”[3]。由于模仿的对象“不是实体,而只是接近实体的东西”,所以模仿只能是“离自然三层”和“离现实三层”[3]。因此,模仿这种工作实际上与自然和真理隔着三层。因此,从柏拉图对画家的考虑中可以看出,理念是真实的,虽然他承认文艺是以模仿为其本质而存在的,但他否定了被文艺模仿对象的客观实在性,从而取消了文艺的真实性前提[3]。基于这一点,诗歌作为文艺的表现形式之一,自然也就被打入不具备真实性的境地,所以柏拉图说诗人的作品“对真理没有多大价值”。
然而,这一点也不足以使得柏拉图对诗歌如此痛斥,真正使柏拉图对诗歌反感的是第二点——“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4]。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写道:语言、音调和节奏。诗歌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也就是说诗歌的组成必然要以语言为基础,接着在该基础上增加音调和节奏,不存在没有语言的诗歌。柏拉图在论音调与节奏时提到:“节奏是运动的秩序,而音调是声音的秩序,它通过锐利与柔和的声音相协调而实现。节奏和音调的结合就叫做歌舞艺术。”[5]107紧接着又提到“美与丑对应着好与坏的节奏”[5]107。不利于引导城邦公民的生活向着节制、勇敢、正义等发展的都是坏节奏的典型。在柏拉图那里,道德是判断诗歌优劣的唯一标准。因此,柏拉图认为荷马史诗某些段落应该取消,原因在于“它们愈美,就愈不宜于讲给要自由、宁死不做奴隶的青年人和成年人听。”[5]406柏拉图从关心公民教育与道德的角度,抵制诗歌对“人性低劣部分的逢迎”[4],禁止不利于公民健康成长的诗歌。
以上两点原因互相影响,对真理的远离会导致诗歌在坏的层面越走越远,对人们低劣的爱好进行逢迎又会使得诗歌更加远离真理,进而形成恶性循环,也因此,柏拉图迁怒于写就诗作的诗人,认为应该将这群诗人逐出理想国。
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柏拉图贬斥诗歌并不是对所有存在的诗歌进行全盘的否定,而是对其中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靡靡之音”进行否定,从而从中筛离出“真”的诗歌。这也是柏拉图真正的目的所在,即构建自己的诗论,以确立“真”的诗歌,或者说,使诗歌能够通达“真”的层面。柏拉图指出:
“诗人应该用高尚精美的诗句来再现好人,用适当的节奏来再现好人的心怀,用优美的旋律来再现好人的节制,这些人是纯粹的,高尚的,简言之,是善的。”[6]“诗歌不仅具有娱乐性,而且对政治和一般生活也是有益的。”[7]631
而且,诗人和艺术家以其优良的天赋,可以沿着真、善、美的道路前进。
“我们的青年也可以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进入健康的环境中熏陶,从小不受坏的影响,并掺入良好的意识。”[7]368
可以发现,在柏拉图诗论中,诗歌首要要求便是对真、善、美的复刻,这也就意味着,在柏拉图的诗论中,一篇诗歌足以为“真”,其路径在于放弃对摹仿的模仿,而是越过摹仿,将其对象直接指向处于理念世界的真、善、美,从而达到对真理的摹仿。这也意味着诗歌创作在柏拉图这里已经对以往的诗歌创作进行了超越,诗歌中的理性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但柏拉图诗论中,诗歌又不是纯粹理性的,因为柏拉图本人是一个“迷狂说”的狂热的鼓吹[8]者。他认为,诗歌的创作源泉可以被看作是“诗神”。“缪斯依附于温柔贤淑的灵魂,激励它们表现出来,尤其是在各种赞美古人各种作为后世垂训的丰功伟绩的抒情诗中流露出来。”[8]如果没有缪斯的狂热,不管是谁想要打开诗歌之门,追求作为好的诗人所需的技艺都很难成功。狂迷的诗人以及他的诗歌作品总是比神志清醒时的更熠熠生辉的[7]158。显然,在柏拉图那里想要创作出优秀的诗歌,缺乏审美体验、创作的激情,或是缺乏灵感都是不行的。诗歌向“真”靠拢需要以理性为前提,但它本身无法以理性为基础,无论是否在柏拉图的诗论体系下,诗歌始终是诞生于灵感之中,灵感是一种迷狂状态。因此,他多次劝诫诗人,“不要害怕迷狂,神志清醒不一定比充满迷狂好”[7]158。
柏拉图的诗论是独具特色的,显示出了他本人的诗人的气质和他高度的诗歌艺术修养[8]。不难发现,柏拉图关于诗歌的非理性因素方面的论述,与他的理性主义的主张相悖,这也表现出柏拉图诗论的复杂性。
总而言之,柏拉图对诗是一种贬而不废的态度。在贬斥诗歌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诗论体系,而在这诗论中,又表现出诗的二重向度:指向理性却又源于感性。这也是柏拉图调和“诗哲之争”的重要基石。
二、诗与诗教的价值导向
柏拉图主要从两个方面批判通常所谓的“诗”和“诗人”。就主观方面而言,诗人缺乏对于真实存在的知识;就客观方面而言,诗人的作品在伦常、政治、教育等领域带来了恶劣的影响。可以看出,柏拉图对待诗具有非常明确的价值取向,即诗作一定要符合对理想国的建设——首先要“真”,其次要能将人民导向“真、善、美”的境界。正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下,柏拉图基于他的诗论体系,形成了柏拉图式的诗教思想。
古希腊在柏拉图之前早已有诗歌教育的存在。诗教作为古希腊的传统教育,为古希腊的辉煌文明的继承以及成就古希腊人的气质方面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荷马来说,诗歌实现了承担知识和教育的功能”。这就是古希腊的传统诗教[9]。古希腊的诗教传统虽然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但是在柏拉图这里,依然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诗教中承载教化作用的诗作,这些诗作大部分为柏拉图所排斥,认为它们会对公民造成不利的影响。
柏拉图的诗教产生缘由正是传统诗教中诗的缺陷。柏拉图将“真、善、美”的统一这一最高价值导向融入诗教中,以此重塑了传统诗教体系——厄洛斯神话(1)厄洛斯:最早称他是参与世界创造的一位原始神,是世界之初创造万物的基本动力,是一切爱欲和情欲和情感的象征,但在柏拉图之后,他被认为是爱神阿佛洛狄忒的儿子。其形象最初为一个手拿弓箭、光着小脚丫、长有一对小翅膀的淘气小男孩。而到了后来,厄洛斯的形象又转变为一个容貌英俊的男青年。是作为哲人的柏拉图进行诗教的明证,他在这则神话中教导人们要爱智慧,而不是盲目追随传统,更不能行不义。正义的人将会得到奖励,而不义的则受到惩罚。理性和爱智慧,以及行正义等教导成为了厄洛斯神话的主题和核心。
不过柏拉图并没有完全摒弃传统诗教,柏拉图的诗教里,仍然延续着传统诗教最大的功能:传达知识以及教育。他说它像一块巨大的磁石一样,并通过“这些有了灵感的人把灵感热情地传递出去,由此形成一条长链”[7]304。在这里,柏拉图将诗人、演员、歌舞队员、大小乐师、观众通过灵感这一非理性因素串联于一体,联结成一条艺术链。这艺术链条便是诗教发挥传达知识和教育功能的基础,通过这样的一条纽带,观众便能够得到作品中的知识与教育。柏拉图诗教在功能上能够对传统诗教的继承,其中重要原因在于,柏拉图诗论中的诗,仍包含非理性因素的。纯粹的理性是难以涵盖非理性的,柏拉图所承认的“真”的诗作为非理性与理性的统一体,是能够作用于非理性因素产生的“艺术链”的。所以说,柏拉图的诗教也是其诗论体系在实践层面的一种延续。
在诗论中,柏拉图表明,以真、善、美为价值指向的诗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在诗教中,柏拉图则意在将诗中的真、善、美推及众人。因此,柏拉图的诗教也是不废黜诗的体现。到这里,可以明确柏拉图对诗的态度——贬而不废。这也构成了调和“诗哲”矛盾的前提,否则便不是调和,而是直接将诗“清除”了。
三、诗哲的矛盾调和
柏拉图生活在雅典城邦的衰落时期,处在内忧外患之中的柏拉图对理性的作用和“理想国”的构建都进行了反思。想要建立理想国,就要使得教育的设计以道德品质为第一目标,也就是必须摒弃以“模仿”以及“迎合低劣人性的诗歌”,因此“诗哲论战”展开了[9]。
柏拉图认为,理想城邦的统治者应该由一位“哲人王”担任,只有通过哲学才能够使得公民接受好的教育,也只有哲学才可以作为建立城邦制度时的依据,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使哲学教育为普通人所接受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好逸恶劳可以说是人之天性。因此,哲学教育在某个层面上可以说是不符合自然本性的,而诗教则与人类的自然本性更为适应。然而,如果人想超越自己,达到更高的境界,过上更好的生活,克服不可预见的危机,就必须靠理性和智慧生活,也就是要摒弃诗歌,转向接受哲学的指导[10]。如果诗中没有哲学思想,它就会空洞。事实上,诗歌在理想国是为哲学服务的,它作为一种通向哲学的形式而存在。没有诗歌的哲学和没有哲学的诗歌一样不合理,二者之间不存在内部矛盾。自古以来,诗歌和哲学之间之所以有如此激烈的争论,其实是诗歌和哲学在某种外在层面的争论,但是事实上这些争论并不涉及核心,即争议是存在于表面的。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谴责并试图从城邦中驱逐的不是所有的诗歌和诗人,而是模仿性诗人、悲剧性诗人以及不利于公民成长的诗歌。
“这个奇妙的城邦制度通过教育灌输给我们的对这种诗歌的热爱,在我们看来肯定是最崇高和最真实的,然而,如果诗歌本身不能为自己辩护,我们仍然会在每次听到这句话时,重复的为诗歌进行辩护。”[11]
如果能发现一个诗人的作品对城邦是有用的和必要的,那么这样的诗或诗人就会获得被接纳的资格。根据张辉先生的说法“如果诗人能够表明自己说出的仅仅是有益的和高贵的谎言,那么诗就将获得公民地位。”[12]积极的诗歌,在城邦中还是有容身之处的。在治理城邦时,也不可能完全地割舍诗歌,因为,诗歌除却它本身的修辞、格式等特点,它还拥有着相当程度的政治影响[13]。柏拉图反复强调诗的价值何在,诗哲之争中最大的矛盾便是出现在价值层面——诗与哲学何者能够使得人们的德性得到提高,使人们获得真理?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明确何者能够接近真理。作为哲学家,柏拉图显然是支持哲学的,但是柏拉图早年也曾立志成为一名诗人。对诗,柏拉图也未轻易放弃。在柏拉图那里,真理应该通过哲学由理性去把握,而非感性,在诗论中,柏拉图指出了“真”诗的二重向度,即源于感性却指向理性。由此可以看出,柏拉图的“真”诗是一种“哲学诗”,是连接诗与哲学的桥梁,在这桥梁上,诗学与哲学获得初步的沟通。然而,仅仅是能够通达真理还是不够的,柏拉图还要求诗作能将其中的真理推及众人,有利于“理想城邦”的建设,这就是柏拉图的诗教。由真诗到诗教,柏拉图彻底完成了对传统诗作和诗教的超越,同时也为诗与诗教明确了最高的价值指向——真善美。到这里,哲学与诗学便具备了同样的价值指向、同样的教育作用。在柏拉图的诗论体系和诗教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已经是蕴藏在其中的哲学,在这里,哲学与诗学达到共通的境界,故诗哲之矛盾已然得到调和。
四、结束语
作为诗哲之争的发起者,柏拉图表现出对传统诗的贬抑,同时也在阐述自己的哲学诗论。于价值论视域下,诗哲之争可以视为诗哲二者价值指向的争论,实现“真善美”价值指向的哲学诗,即可一定程度上调和诗哲之争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