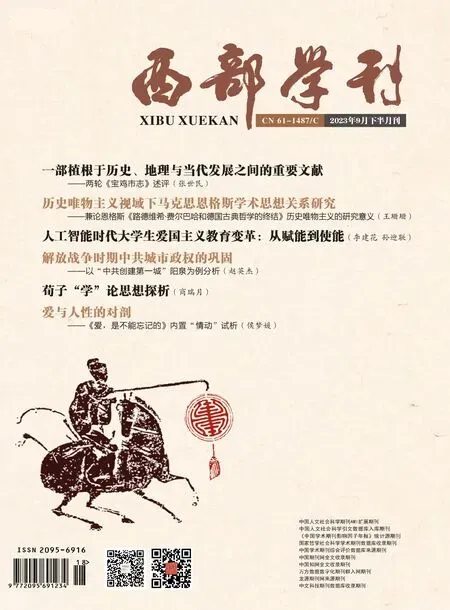族际文化的差异与共识
——从云南鹏鸟形象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罗 沛
(云南艺术学院,昆明 650000)
本文所研究的鹏鸟,是文化意义上的概念,特指跨地域出现于各民族艺术现象、文学描述、特殊空间建筑中的一系列名称身份、体貌特征与神话传说相似的神鸟母题,此类形象均奇大无比,与恶龙蟒蛇为敌,各地称谓有所差异,或唤作大鹏鸟、金翅鸟、鹏鸟、迦楼罗等,但异名同质,为求准确性并便于讨论,在此统称为鹏鸟。以往学界对于鹏鸟形象的研究,都是将其孤立地放到某一区域性的文化语境中,探讨其来源、流变与发展,虽然有相似形象进行比对,但皆旨在关注特征与差异,忽略了鹏鸟是一个全国范围内共通的文化符号,其共性代表着各民族文化在发展中的同步性。而本文也将从这一点出发,以云南鹏鸟形象为代表,分析云南各民族对鹏鸟创造性发展的同时,将其与中原鹏鸟形象联系起来,放到民族共同体语境中去进行解读,以呈现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内在文化基因。
一、云南鹏鸟形象出现的历史文化语境
文化来源于历史进程中人与特定生存环境的相互作用,云南的生态环境自古便有生物多样性的特征,鸟类资源尤为丰富。生态资源为文化思想奠定基础,自然崇拜意识便从此开始,在“万物有灵”的观念引导下,原始先民开始取媚于鸟。早期居于云南的百越、氐羌等民族将鸟类当作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族”,自古便有鸟图腾崇拜,而其后代,更化鸟为神,将天地与先祖从蛋中孵化而出的情景描述入创世神话中。
丽江纳西族《创世纪》记载,远古时期天地混沌,阴阳混杂,但“山上妙音与山下白气化成白露,露变海,海生海蛋,蛋里生出人祖恨矢恨忍。经过九代,传到崇仁利恩”[1]。红河地区哈尼族的《木地米地》讲到:“龙王寻天基地基、找天被地被、孵天蛋地蛋,孵出雏天雏地”官员、摩匹(巫)及工匠也皆是从蛋中孵出[2]。大理小部分地区的白族也认为其祖先是从金花鸡的蛋中孵出[3]。此类族源神话具体地说明了一个部族、民族的来历,也反映出该地区各民族与巨鸟崇拜早有渊源,这都为后期接纳印度传入的鹏鸟形象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中原汉族在早期也有一系列类似的卵生神话《史记·殷本纪》中记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4]91,173。秦人始祖神话提及“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脩织,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4]91,173。不同民族的族源神话都选择了卵生之鸟作为他们的祖先或使者,借此表明自己的氏族来历不凡。各族以鸟类崇拜为共同的精神依托,这显示出,尽管不同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生活存在差异,民族文化信仰丰富多样,但民族心理以及文化形态却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对于云南来说,现存的各类鹏鸟形象,源自本土的巨鸟崇拜对古印度“迦楼罗”的接纳与衍生[5]。迦楼罗又译作金翅鸟,意为羽毛美丽者,据《莲花往世书》与《摩诃婆罗多》介绍,迦楼罗体形极大,两翼伸展有三百三十六万里,破壳而出便为鸟禽之王,作为毗湿奴坐骑,被奉为古印度教的战神。5至6世纪,迦楼罗被吸收入佛教文化,成为居于须弥山北方,能日食巨蛇500条的大鹏鸟,并由佛家再创作出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等四种划分类别。作为佛家八部众之一,其造像要求反映出形象成熟时期的面貌:“……其身分自脐已上如天王形。唯鼻若鹰嘴而作绿色。自脐已下亦如于鹰蠡骆。宝冠发[影/目]披肩臂腕皆有宝冠。环钏天衣璎珞。通身金色。翅如鸟而两向舒。”[6]神明塑像都会有严格的仪轨与程式标准,按照各类经书与营造法式所述,鹏鸟形象当为人面鸟喙,大肚如蛙,两臂与双翅舒展而有力,双手持蛇,作威严的忿怒状以护持佛法。而后得益于两汉、两晋、隋唐等历代宗教传播,鹏鸟形象随佛教文化经东南亚、中国西藏等路线渐入云南,在地与各民族文化信仰结合后被不断重构而更具有本土特性。丽江纳西族、大理白族、西双版纳哈尼族与傣族等族群中,都可见到明显的鹏鸟形象,但这些距最初的迦楼罗以及大鹏鸟已有一定程度上的转变。
二、云南鹏鸟形象在地重构的多样性
“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民族文化再创造的动力和资源。”[7]云南自古便是多元民族互动的时空场域,民族迁移与融合是常事,频繁且持续的迁移,造就了诸多民族文化深处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外来文明提供的养分、本土各族族际间的互动,共同促进文化的转型与更新,构成了鹏鸟在云南多样殊异的文化面貌。
云南北部为横断山脉,垂直的河谷提供了天然的民族迁移路线与文化交流廊道。然而道路崎岖,也带来重重阻隔,令各族群分化出众多文化习俗。鹏鸟形象在国内经由西藏传入丽江地区时,已然携有藏密、苯教风格特征,头部增加了象征藏地牦牛崇拜的尖角。而后被东巴文化(1)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于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接受并改造,便唤作“都盘修曲”即白海螺大鹏鸟,其频繁出现于各类祭祀活动中,以东巴经书、东巴象形文字、东巴画、祭祀木雕等为艺术载体,一改“翅有种种庄严宝色”而简化为通身洁白,穿戴也不做过多装饰,展现出东巴文化质朴简约的艺术特点。东巴经《修曲苏埃》记载,居于“含依巴达”神树上的白海螺大鹏鸟,帮助东巴什罗调节了人类与巨蛇署神的矛盾,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8]。此处故事同大理金翅鸟的神话传说相似,皆保留了最初印度教与佛教传说中鹏蛇争斗的元素,而大理地区在情节上根据当地生态空间及文化传统有所删增,更多描述为治理水患等自然灾害。“……世传龙性敬塔而畏鹏,大理旧为龙泽,故以此压之。”[9]民间传说大理早期有恶龙作怪水灾频发,而龙只敬畏崇圣寺之塔和鹏鸟,所以塔顶立鹏鸟塑像以镇水患。崇圣寺塔顶端这尊最具有大理国文化代表性的银鎏金镶珠金翅鸟塑像,其头顶羽冠,后有火焰状背光,塑像优美、生动,线条曲旋流畅,但通体未见蛇元素,皆为鸟身而不具有任何人体特征。大理国地藏寺经幢上的迦楼罗石雕与其如出一辙,也是振翅欲飞的全鸟状。由于印度山琦遗迹与甘肃石窟中也出现过迦楼罗的单纯之鸟形,不论此处形象确实为鹏鸟,还是如方国瑜所言,此乃本土神话中的金鸡形象,讹传作鹏鸟迦楼罗“乃后世附会。”[10]都可见,鹏鸟形象传入大理时,由于同本土金鸡形象高度趋同吻合,而被内化吸收并大力宣扬,成为当地文化的补充与扩展。
三、鹏鸟形象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云南本土民族的巨鸟崇拜,受印度、东南亚、中国西藏等文化影响,在地形成多样殊异的鹏鸟形象,而在此期间与中原文化的互通有无,更使得鹏鸟跳脱云南地区与中华文化融汇一体。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大一统时期,期间频繁不断的民族迁移,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通畅繁荣等,极大程度上使中华各族互渗互补,逐渐产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艺术现象。各族对鹏鸟形象的交流与传承,强化了族际交往纽带与族际共同性感知,发挥族际接触作用并减少族际偏见,有效形成了较为稳固的中华文化认同和文化共同体意识[11]。
中原古籍《说文》中对“鹏”解释道:“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朋为朋党字。”[12]据此推测,中原鹏鸟最初应与凤凰同源,都来自原始鸟类崇拜。《神异经—中荒经》里描述的上古大鸟“希有”栖于昆仑山的参天铜柱,体型之大,从西昆仑到东海的距离,也不过是其两翅之间[13]。这与云南纳西东巴经中停在“含依巴达”神树上的白海螺罗大鹏鸟传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显示出相似的民族文化基础。除却巨鸟崇拜与前文所述卵生族源神话,更为具体的鹏鸟形象同样也在中原历代文化中频繁出现,《庄子·逍遥游》道“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14]这里的“鹏”由鱼化鸟,展翅可遮天蔽日,尚是华夏文明传说中的神兽,历代高才常以鹏鸟自居,抒发远大志向与豪放气概,希冀自己能同鹏鸟一般志存天地,不屑唐廷。而随着族际文化的交融,中原鹏鸟形象被充实与再创作,更为复杂,包含了更多元素。《西游记》中鹏鸟被塑造成为改恶从善的妖精形象,名号“云程万里鹏”,能抟风运海,振北图南。因作恶于狮驼岭,致使八百里尸横遍野而最终被收伏,皈依佛法成为佛祖座下的护法之一[15]。《说岳全传》又将鹏鸟传说与岳飞事迹结合,把岳飞神化成为如来佛祖座下嫉恶如仇的大鹏金翅鸟转世投胎所生,他凭借有勇有谋的意志品格,与赤须龙所化的金兀术大战,为平定中原之乱、保全宋室江山而尽诚竭节[16]。此时鹏鸟已与佛教文化联系,被纳入佛家诸神系统,如同云南鹏鸟形象一样,有着较为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在中原众多庙宇神祠中,鹏鸟或独立成像伫于莲花宝座上,或展翅盘旋于释迦牟尼周围,明眸如炬,审视人间,守护着一方百姓。
云南鹏鸟也受中原影响,逐渐褪去原始巫术中的凶禽猛兽气息与诡魅色彩,儒释道的互渗结合,使其将仁爱忠信、道法自然、止恶行善等文化观念兼收并蓄。纳西族的白海螺大鹏鸟,同佛家诸神与海螺、圣水瓶等法器并列于神路图中,不再咧嘴露齿作严肃恐吓像,更具有兼爱众生的亲和性。傣族与景颇族等,将鹏鸟形象体现于生活,各民俗节庆日中以载歌载舞的形式与自然对话,探索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展现老庄浪漫逍遥气息的同时也传递出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相比于中原严密精致的艺术塑形工艺,以及在各类文学中的各种象征与隐喻而言,云南少数民族对鹏鸟的呈现方式更为质朴直接、更为世俗化,但想象力更为丰富。渐同中原一般,云南鹏鸟追求着力量、形体、气势、神迹之美,追求着赏善罚恶、智慧勇敢等更为正面的人文精神价值。作为共享的文化视觉符号,各族的鹏鸟形象特征、故事题材、艺术表现技法各有特点,但最后指涉的文化层面之寓意却是殊途同归,不论如何变化,各式的鹏鸟内在蕴含着的价值取向始终具有一致性。
“文化的差异不是冲突的根源,而是互补的基础。”[17]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云南与中原渐进往复的族际文化交流过程,潜移默化地使两地间鹏鸟形象积淀了多层次象征意义。战神、守护神,抑或由恶改善的妖精,鹏鸟这一视觉形象是不同民族文化艺术融合的历史痕迹,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各族人民的深层心理依附,它成为了文化交流的见证,在族际文化之间力求兼容并蓄。在云南乃至全中国,鹏鸟代表着各族人民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对勇敢善良品质的追求、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考,这朴素的自然观和顽强拼搏的生命意识,实际上展现出了族际间精神文化与价值观念的趋同。共同的历史记忆原动力,产生情感的联结和内心的共鸣,历代流传下来的鹏鸟形象表明,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古已有之,诸如鹏鸟文化的共同认知,合力培养孕育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发展。
四、结束语
鹏鸟形象的发展演变,是各民族通过引入与借鉴其他文化中的形象母题,丰富自己,弥补缺憾,从而解决族源困惑、生存发展的一系列问题的重要途径。各民族皆依照自身审美情趣、文化传统对鹏鸟进行分解拼装,带有鲜明的民族个性和印记,又始终没有发生颠覆性变化。族际文化交往交融中,鹏鸟形象的相互接受与吸收,是对其所象征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的接受,共同的价值理念显示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基已经初步建立。鹏鸟代表着各民族、各地区在长期的文化互动、交流中形成同质化和一体化现象,是各族文化逐步整合成一个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模式的基础。作为视觉叙事载体和代表性文化符号,鹏鸟形象诉诸视觉而直映心灵,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文化记忆和精神标识。
进入新时代,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发展,在交往交流中,文化一体性现象不断增加,民族关系朝着更加包容和亲近的趋势发展,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交融程度不断加深,将出现更多如同“鹏鸟”的文化现象。以鹏鸟为鉴,在族际文化中保持个性与融通共性,差异与共识互生,体现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包容性与张力,以及中华文化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