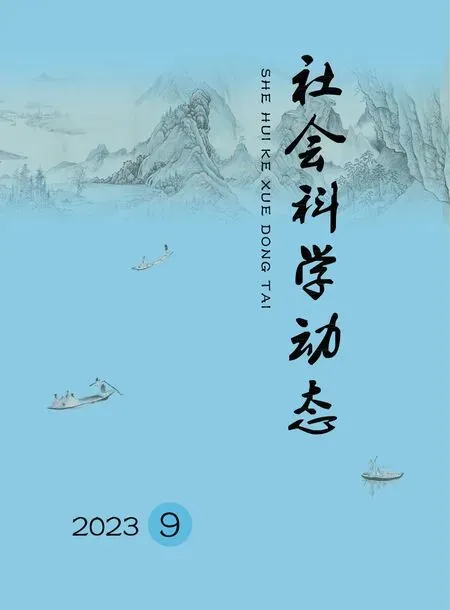论海德格尔对早期费希特哲学主体性格局的超越
——基于1794 年版《全部知识学基础》的分析
赵 瑜
德国古典哲学是海德格尔一生致思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他在1929 年的讲座稿《德国唯心论与当前哲学的困境》(以下简称《困境》)中的费希特阐释,可以被看作是《存在与时间》中此在生存论思想的进一步的延续和补充。①以批判费希特的“非我”(Nicht-Ich)概念为契机,海德格尔进一步展开了他的世界的形而上学(Metaphysik der Welt)②,在一种全新的视角下审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最终确立了以自我和世界作为双重本原的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以“问题格局”(Problematik)一词批评费希特哲学乃至整个德国唯心论哲学传统。在德语语境中,“Problematik”是“Problem”(问题、难题)更书面化的一种表达形式,特指困难与疑问本身所固有的更深层问题。也就是说,海德格尔认为以费希特为代表的整个唯心论在思考的一开始触碰到了核心的“存在问题”,但却没有以正确的方式对待这一核心问题。③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费希特将自我描述成一个不断生成的、活动着的主体,与费希特一致,海德格尔也将此在的存在看成是在生存活动中不断去赢获自身生存可能性;另一方面,费希特试图将非我作为经验性本原纳入到自我之中,仅仅从主体出发解释自我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何以可能。正是在后一点上,海德格尔批评费希特陷入了近代主体主义的桎梏。海德格尔指出:只有世界的形而上学中,自我和世界才能被关联着被设置下来,由此才能稳固地建立起存在的根基。就此而言,费希特未能以一种源初的方式思考此在这一存在者本身的存在方式。
本文的核心内容在于展示海德格尔的费希特批评中所体现出的自我与世界作为“双重本原”的学说。首先,展示费希特所刻画的作为自我与非我的统一体的绝对自我的动态结构,并指出这一结构的终极困难——非我最终没有获得独立的本原的地位。因此,费希特的哲学也就没能建立起外部世界的根基。其次,费希特的自我是一个通过设定活动实现了自身的主体,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海德格尔进一步将此在的生存描述为在活动中实现了“此在的存在”的“能在”(Seinkönnen)。然后,通过将此在的生存建构刻画为“在世界之中存在”(Inder-Welt-sein),海德格尔试图克服费希特哲学中难以彻底解决的“非我”难题。海德格尔从此在实际的生存状况出发,展示了此在与世界作为双重本原被同时关联着设置下来的生存图景。最后,海德格尔为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条与费希特哲学迥然不同的解决路径,在这条新路径上,人的存在的可能性与通达世界的可能性合二为一。这体现出海德格尔深刻的理论洞见——作为个体性的自我存在与作为整体性的世界存在之间有着必然的本质关联,而只有在这种关联之中存在之思才得以涌现。
一、《全部知识学基础》中的自我与非我
在这一节中,笔者将阐明费希特在《全部知识学基础》中(以下简称《知识学》)所刻画的自我内部动态结构,并试图展现:费希特通过设定活动将自我刻画为一个行动的主体;他的主体性理论试图将非我作为经验世界的“聚合”(Inbegriff)纳入自我的动态结构之内,但并不成功。
费希特从单纯的同一性命题“自我=自我”出发,展示了自我内部结构的复杂性:绝对自我同时设定了相互对立的自我和非我,但非我和自我又没有绝对地排斥对方,而是互相限制对方。但前三节中形式上的展示并没能够清楚地说明:经验中的自我和非我之间到底是如何既相互限制,又能够统一在绝对自我之中的。④在第四节中,费希特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自我和非我的关系问题。他将自我和非我之间的关系刻画为这样一个命题:“自我和非我两者都是经由自我,并且在自我之中被设定为互相对立限制的东西。”⑤
如果自我将自身设定为受非我限制且规定的,那么意味着,非我必须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去主动行规定的。⑥费希特把这种规定活动看作是去建构实在性(Realität)的过程,与之相应,被规定就是扬弃实在性的过程。⑦如果自我被规定了,那么自我之中的实在性就被扬弃了;而非我去规定自我,就意味它作为拥有着与自我中被扬弃的实在性等量的实在性,并且能够将这部分实在性重新设定给自我。进一步说,被扬弃了实在性的自我并非放弃了自己全部的实在性,而只是部分地放弃了实在性,这部分实在性通过转移活动(Übertragen)给了非我;而通过非我的转移活动,自我又重新获得了自己全部的实在性。实在性在费希特看来就是活动:“一切实在性都是活动着的(tätig);并且一切活动着的都是实在性。活动是积极的、绝对的(对立于单纯的相对)实在性。”⑧自我之中被扬弃的部分的实在性或者说活动被费希特称之为“受动”(Leiden),而当自我处于这种受动状态的时候,非我作为自我的对立面,就相应地拥有了实在性。“非我作为非我,本身没有实在性;但是只要自我是受动着的,它就拥有了实在性。”⑨也就是说,非我本身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实在性,它的实在性是在自我的设定活动中由自我赋予并最终被归还给自我的。但非我同时在设定活动中又必须以中介的方式承担一部分实在性,否则自我被削减的那部分实在性就无处可去。
于是,我们可以将自我设定活动刻画为这样一种交互规定(Wechselbestimmung):自我通过活动规定它的受动,或者通过受动规定它的活动。⑩在这样一种交互规定中,自我既是规定者又是被规定者;既是活动又是受动。自我的自身设定活动(Sich-Setzen)是“二重化的”(doppelt)⑪,作为绝对的规定者的自我是“绝对自我”(das absolute Ich),而被规定的自我则成为了所谓“理智自我”(das intelligente Ich),绝对自我的行规定的活动是彻底独立于经验自我和非我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因而是一种“独立活动”(die unabhängige Tätigkeit),或者说,是一种“绝对的自发性”(die absolute Spontanität):它同步规定了非我一侧的活动以及理智自我一侧的受动。此时两个自我不再是彼此对立的,绝对自我通过将非我设定为对立于自我的东西,把之前被扬弃掉的绝对自我的一半的实在性重新还给了理智自我,由此最终完成了自我的整个设定活动,也就是整个第四节想要演绎的原理:自我将自身设定为被非我限制的。
就其本质而言,具有二重属性的自我设定活动是一种无限性的绝对自我将自身固定为有限性的理智自我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之中,绝对自我将自身的一部分“排斥”(ausschließen)出去;而“被排斥出来的东西”(das Ausgeschloßne)就是非我,它同时构成了对剩下的那部分确定下来的也就是理智自我的领域的限制。费希特进而将非我称为“客体”(das Objekt)⑫,并认为客体被设定的活动本身也是具有二重属性的:
这里客体的被设定出现了两次;但是有谁看不出来它们是在不同的含义上的呢:一次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另一次是以被自我排斥出去为条件的。⑬
非我一方面构成了对理智自我的限制,另一方面非我又是在自我之中的,是绝对自我的产物。非我本身并不是作为客体而现成存在的,毋宁说,非我仅仅“是作为对自我的一种阻碍(Anstoß)而现成存在的”⑭,是为了使主体的领域不要无限制地扩张而被设置下来的。尽管非我构成了对自我的限制,但非我本身不是自我限制的原因,而仅仅只是在自我限制的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环节。没有自我的行动,就没有阻碍 。最终,自我的活动被界定为一种“回返自身的行动”(eine in-sich-selbstzurückgehende Tätigkeit)⑮,一种自我在向外投射的过程中碰到了由自己预先设定的阻碍后折返回来,从而构成对自身的限制的活动。
因此,在《知识学》中,非我并没有赢得一个独立于绝对自我的地位,而只能在和自我的关联中才能讨论,也只是在作为中介的意义上暂时获得了实在性。正如我们上文所说,引入非我本来的意义就在于为自我建构经验对象的活动奠定可能性基础;显然,非我并不具有存在论意义上的独立的本原地位,其内部缺少真正的经验对象的存在基础。正是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认为费希特“削减”(vermindern)了问题格局,使得自我和世界的关联从一开始就成了无法被解释的。
二、自我与此在
在本节中,笔者将横向对比费希特的“自我”与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概念,并发掘出两者的本质关联——自我和此在都是作为活动着的实践主体,试图去冲破自身的有限性,只不过费希特的绝对自我最终是要走向无限,而海德格尔所刻画的此在的生存境遇则是在有限和无限的张力之间来回飘荡。
在《困境》一书中,海德格尔对费希特的哲学的基本评价是,在费希特哲学中,“‘存在与时间’这个问题格局就像一道闪电在那里出现了”⑯。笔者认为,自我概念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一道闪电”——自我和此在都是一个活动着的实践主体。正如张柯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海德格尔“在费希特的知识学中看到了‘人与存在之关联’问题的一种预示”⑰。德国学者宾克尔曼(C. Binkelmann)也以类似的方式描述费希特和海德格尔的相似之处:
费希特和海德格尔在他们早期的创作阶段分析了人类此在生存的可能性条件。他们的重点主要放在实践关联上(Praxisbezug)。人通过他的行为与世界直接和源始地关联着。⑱
近代以来的笛卡尔主义哲学传统将“主体”理解为一个静态的、高高在上的、不可被继续追问的实体,主体与客体因而成为了两个互相独立并且都已经现成存在的实体——两者的对立也随之被固定下来。费希特所做的恰恰就是要破除这样一种静态的主体观,将自我刻画成一个不断地去进行规定与限制的行动主体。正如他自己在《知识学》中反复强调的,“自身设定和存在是一个并且是同一个东西”⑲。这表明自我不再是一种单纯事实性的存在,而是一种融合了事实与行动的“本原行动”(Tathandlung),即自我在自身设定的活动中去获得全部的实在性。也就是说,自我从来不是现成存在的已经具备了全部实在性根据的主体,而是恰恰要通过自己的行动才能去获得实在性的根据。进一步地,费希特把这种获得实在性根据的行动表述为一种保持着开放性的活动:
被规定的东西和能被规定的东西(das Bestimmbare)应该彼此互相规定,这显然是在说:被规定的东西的规定性(die Bestimmung des zu Bestimmenden)在于,它是一个能被规定的东西。它就是一个能被规定的东西,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这就是它全部本质之所在。⑳
自我之为自我,就在于它不断地进行规定活动;而这种规定活动的可能性恰恰在于,自我本身是能被规定性的集合。绝对自我本身如果不是这样一种能被规定性的集合,要么它就是静态的、已经被固定下来的现成存在,要么它就是一种不存在。作为一种现成存在,它存在的可能性将完全被描绘成一种现实性,一种不会再增长和削减的实在性,它的运动和发展将无从谈起。因此,只有当自我作为被规定的可能性的集合时,自我以自身为根基的行动才是可能的。
受费希特的影响,海德格尔没有把此在看成已经具备了全部存在规定性的现成存在者,而是将其看成是在生存中不断获得可能性的存在:此在本身是保持着开放性的“能在”(Seinkönnen)。
[自我]的存在的非封闭性构成了它对存在的一般把握的一个本质环节;这就使得生存总是意味着将自身维持在作为最本己的能在之可能性的那些可能性中。㉑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就将此在实际本质描述为:“此在在生存论上就是它在其能在中尚不是的东西。”㉒“尚不是”(noch nicht ist) 就意味着此在本身还没有被规定下来,还不是已经现成存在的存在者。作为“尚未”被固定下来的存在,此在才能在生存活动中始终保持自身的开放性,向着种种可能性去筹划自身的存在。换言之,海德格尔将此在的存在描述为一种能够不断去存在,不断去赢获存在的可能性的生存活动。因此,“此在”这种特殊的存在者的存在被描述为这样一种状态——此在在自己的生存活动中才真正地存在了;而这一观点正是受了费希特将自我表述为通过设定活动回返自身的这一结构的启发。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在费希特那里自我的行动最终应该是要冲破自身的有限性,再次将自身回溯到一个无限的绝对自我去的——这一行动“向着无限制的东西、无规定的东西、以及不能被规定的东西,也即是说,向着无限跃出。”㉓理智自我受到非我的限制,因而是有限的;行规定的绝对自我是无限的,作为有限自我与绝对自我的统一体的绝对自我最终还是要走向无限的。可以说,和非我一样,处于有限性的理智自我也只是一个中间的过渡环节,最终回到的绝对自我是一个无条件的活动本原。但是,海德格尔的此在是被抛的,始终处于有限和无限之间的张力中,并在这种张力中将自身落实为有限性的存在。正如德国学者舒尔茨(Walter Schulz)所说,“这里展现了海德格尔和费希特的不同之处——海德格尔的意图不是超人类的 - 无限的东西(das Übermenschlich-Unendliche)。海德格尔想要的是彻底的有限化(die radikale Verendlichung)。”㉔
总而言之,费希特的自我作为一种“本原行动”,一种将自身表达为一种动态结构的行设定、规定的行动;在费希特的影响下,海德格尔的此在同样在其自身存在的生存活动中不断地赢获自身。然而,自我的目标是摆脱由自己预先设定的非我所造成的有限性,重新返回到无限自我之中去;而此在的生存境遇则在有限性和无限性之间维持着自身的有限性。虽然两人的出发点原本是一致的,但是由于费希特没有在他的体系中给有限的非我保留位置,两人的哲学最终走向了两条不同的路径。当费希特把非我看成是回归绝对自我的无限性过程中的过渡环节时,他的体系反而未能建立起外部世界的根基。
三、非我与世界
在本节中笔者将指出,一方面海德格尔敏锐地觉察到“非我”是费希特主体性哲学中的终极难题——不具有独立地位的非我根本就不能在自我之中建立起对象性的根据,而自我的行动因此也就无法跃出自我的边界、向外拓展到外部世界;另一方面,笔者将论证,海德格尔试图将费希特的“非我”理解为他的“世界”概念,真实目的是为了表明——自我的活动一开始就是在世界之中展开的,世界和自我不可切割的关系本身就是存在的真实样态。可以说,费希特在非我概念上的自相矛盾恰好提醒了海德格尔,要在此在与世界的关联中描述此在在世的展开状态的生存论结构。
海德格尔指责费希特的问题格局不是源初(ursprünglich)的:“这是对问题格局的一种完全确定的削减,不是在相对的、量的意义上的削减,仿佛某些部分被遗忘了,就不具有充实性了,而是将归属于此在本身之真理的某种本质性事物削减了。”㉕这就使得费希特哲学最终“由此得到的只是一片鬼火(Irrlicht)”。㉖笔者认为,被削减的那部分问题格局就是被费希特仅仅作为中介的“非我”概念。
海德格尔指出,费希特《知识学》中的核心难点就是“非我”概念本身:
然而,这种唯心论并未澄清在表象问题上应当被澄清的一切,即触动(Affektion),“一种表象由之而产生”(卷一,第155 页),然而这却是从外部来侵袭自我者,而不是来自自我的恩典。㉗
表象的本质中成问题的因素乃是那种阻碍,亦即对自我“起作用的”非自我性事物的实在性。㉘
也就是说,在海德格尔看来,非我就是要为自我的设定活动引入外部对象的实在性;但正如我们上一部分所指出的,非我在费希特的哲学体系中并不是独立的,而仅仅在和理智自我的交互关系中才能被言说。换言之,试图在自我的活动中引入的对象性根据归根结底还是由自我所建构的,那么这样一来,非我便不能承担起在自我之中建立外部世界的对象性根据的任务。
海德格尔试图拯救费希特的体系,于是他有意将费希特的非我理解为一种“活动空间”(Spielraum)㉙:
非我:绝非这个或那个迎面而来者,而是在如其本来的自我中被维持的,迎面而来之物的活动空间。㉚
在海德格尔的语境下,“空间”的属性不是现成存在的,而是要通过此在的活动开启的㉛。“世界”作为此在的存在场域也就是此在的生存空间。作为空间的世界是此在与其他存在者打交道时才会慢慢展开的、使得形形色色的存在者能够作为存在者而存在的“视域”(Horizont)。“自我作为自我(Ich als Ich)进入这种视域,方能对待某物。”㉜也就是说,当海德格尔试图把非我解释为活动空间的时候,他的真实意图是将非我等同于他的世界概念,将非我和自我的关系等同于世界和此在的关系。如果非我可以被视作为“迎面而来之物”敞开着的活动空间的话,那么非我之中对象性因素何来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然而,费希特的非我是被自我所限制的,非我并没有和自我以同等方式被一起确定下来,而是在自我设定的过程中作为中间环节失去了独立性。正如德国学者施托尔岑贝格(Jürgen Stolzenberg)所说,“费希特式自我的有限性并不意味着人类存在是以原初世界关联为根本特征的,而是意味着从形式化的角度去理解就精神事实(der mentale Sachverhalt)‘关于某物的意识’而言的区分活动。”㉝
因此,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的一开始就已经将“世界”和“此在”作为两个具有同等独立地位的本原确定下来了。海德格尔将此在的基本建构描述为“在世界之中存在”㉞,也就是说,此在在一开始就是和世界关联着设置下来的,此在向来就已经熟悉着世界的结构。另一方面,世界作为“使上手的东西由之上到手头”㉟的条件,让此在与形形色色的“用具”(Zeug)打交道成为可能。世界作为使得“物”(Ding)能够涌上前来的场域,向来是对此在开放着的。自我和世界的关系并非是互相排斥、在一个中消化另一个,而是在源始的意义上就是彼此关联的。世界原本就是此在的建构要素。甚至可以说,自我和世界的这种亲缘关系是绝对的,乃至于任何对世界的反思活动都会破坏这种亲缘关系。吴增定教授指出:“一旦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反思世界,将世界当成一个对象来认识,那么对世界的这种亲切、熟悉和信任感就受到威胁,甚至遭到中断。世界开始与我们相分离、相对立,逐渐隐退,乃至最终完全隐匿。”㊱一旦自我将世界放在对立面,企图将世界作为一个对象来反思自身和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原本敞开的世界反而变成了自我不可通达的领域。
显然,费希特的非我概念并不具备这种本原意义上的地位。海德格尔意识到将非我等同于世界这种解释的非法性,于是在之后的行文中不再提起这种解释,而是反复地暗示费希特在问题格局上的狭隘性,并且认为整个德国唯心论传统在问题格局上都没能突破这种主体性哲学的桎梏,只有在世界的形而上学中这种此在和世界的关联才彻底被建立起来。更确切地说,只有将形而上学的任务规定为对此在的存在之追问,这样一种世界和此在的源始关联才能被发掘并确立下来。但是费希特恰恰没有去追问自我的存在,正如海德格尔所说:
形而上学的问题格局的这整个源初的维度对于康德和费希特而言还是相当隐晦的,因为对主体之存在,以及对如此这般的自我之存在的追问,并未在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的主导下被明确而极端地提出和树立起来。㊲
海德格尔看到了费希特哲学中无法解决的悖谬之处:非我作为一种阻碍,它的基底本来应该是异于自我的,否则便不能构成对自我行动的限制,但费希特的立场恰恰就是要在自我之中建立一切。这种追求在自我之中建立一个具有确定性的体系的做法“粉碎了现象,而没有使之在原初的饱满状态(ursprüngliche Fülle)中生效”㊳。最后,笔者将展示海德格尔对费希特的核心批评——自我本身不能独立地作为出发点来建构一套知识学体系,这种做法一开始就戕害了自我的生存体验。
四、自我和世界作为双重本原:世界的形而上学
在海德格尔看来,费希特的失败已经表明,仅仅从自我出发建立的知识学体系无法在真正意义上解决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只有在自我和世界的关联中才能揭示存在的真正面目。笔者在本节中将揭示海德格尔的真实意图,仅仅以自我作为唯一本原的哲学是无法将世界重新纳入到自身之内的,只有将彼此关联着的自我和世界作为双重本原的“世界的形而上学”才能在一种新的视野下审视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并能够在整体性的视野下妥善解决个体性的问题。
在《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第一部分的第三章,海德格尔将近代哲学的论题总结为自然与精神之对立的问题——“自笛卡儿以降,res cogitans 与 res extensa 之间的区别诚然得到了特别强调,并且成了哲学问题域之指导线索。”㊴也就是说,在海德格尔眼中,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史实际上是以精神和自然或者说主体和客体这一对立为主导线索的。海德格尔揭示了自笛卡尔以来的哲学的主体取向中所隐含的前提——主体和客体具有不同的存在方式。
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将目光转向了“自我”或“主体”,自我成了在一切怀疑中都绝对不可怀疑的基点。但自我本身和其他外部存在者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这种二元体系实质上并没有真正的发现“自我”,或者说只是在发现了自我之后就将其悬置下来,也因此始终难以摆脱怀疑论的诘难。费希特将以往的哲学称为“独断论”(Dogmatismus)。站在独断论的对立面,费希特将自己的“知识学”称之为“批判哲学”(Kritizismus):
在批判哲学的体系中,物是在自我之中被设定的东西;在独断论的体系中,物是自我在其中被设定的东西。因此,批判哲学是内在性的(immanent),因为它在自我之中设定一切;独断论则是超越性的(transzendent),因为它还要超出自我之外。㊵
这种将物纳入到自我之内的哲学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但反叛的过程是极其困难的。康德的批判哲学试图去一劳永逸地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自我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何以可能?他明确地划下了自我可以认识之物的界限——物自身,但这使得在自我之外始终有着一个不可认识且不可被规定的物。但是康德的这种做法受到了之后的德国唯心论哲学家们的一致批评。可以说,康德的后继者们都试图去重新刻画乃至扬弃掉这一界限,从而去恢复“自我”与“主体”的绝对地位。费希特的1794 年版《知识学》在康德的基础上试图进一步延展自我的“权能”(Macht),扬弃掉物自身中威胁到自我的本原地位的因素,转而在自我内部消化一切,使得自我本身成为了一个具有无限性的绝对主体。然而,这种做法实际上走向了另外一种极端:主体的绝对地位固然得到了保证,但客体乃至世界的来源问题却无法解决。也就是说,这样一种无限的自我并没有完全吞噬掉物自身,反而是物自身的存在使得费希特的体系面临无法挽回的危险。这种批判哲学最终是否是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变成了另外一种独断论呢?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当费希特把非我作为一个环节完全纳入到自我的活动中的时候,非我本身中“物”的因素就被弃之不顾了。㊶因此,费希特的批判哲学的问题格局不过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认为他走得比费希特的知识学更远。
在海德格尔看来,主体并不能成为一切存在的根基——费希特乃至整个德国唯心论从一开始便抓错了方向:试图将物自身消化在“自我”之中的努力必定是徒劳的,因为自我不可能是一切的根基;那么,由自我进行的划界活动已经排除了此在与世界之间的源始关联的可能性。“康德误认了世界现象(Phänomen der Welt),无论在他本人那儿,还是在其后继者那儿,世界概念(Weltbegriff)都没有得到澄清。”㊷海德格尔认为,世界作为预先被给定的场域和此在一起被关联着设置下来了,此在一开始就在被抛进世界的大背景下不断地投身各种生存活动。在海德格尔哲学中,始终存在着一个生存着的此在和作为场域的世界作为双重本原㊸。这种“世界的形而上学”从源头上把人与世界的关联确立下来了。
然而,尽管近代哲学发现了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却并没有正确对待这一对立。主体是具备着优先性的,但这一优先性并非是出于一种非基础存在论动机。由此,传统的主客二分的哲学实际上还是一种片面主体主义的哲学,因为单一的主体成为了一切的根基,而主体对客体的关系成了根据客体的偶然现成存在被附加到主体上去的东西。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是在反思中理解和领悟自身的,但这种反思就是对此在实际生存状态的描述——此在向来已经生活在世界之中,和形形色色的人与物打交道。此在正是在这种与他物之间的关涉中理解自身的。换言之,此在的原初存在方式并不是与世界相对的意识或认识,并不是一个孤零零的主体,而是一种具体的、事实性的存在,一种“在 - 世界 - 中- 存在”(In-der-Welt-sein),也就是操心(Sorge)。
那么,世界必定是与此在同样源始的、作为本原的存在。那么世界就不是主观性的,不是一种在极端的主观唯心论的视角下的世界,而是有着异质于主体的因素。尽管早期海德格尔还没有明确指出世界一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但是,他已经提醒了我们世界自身的独立性——“即使世界不存在,此在不生存,自然也能存在。”㊹
海德格尔与整个德国唯心论传统的最为本质的不同之处在于:在涉及到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时候,整个德国唯心论试图去彻底理解世界,海德格尔则保留了世界不可理解的一面。如庄振华教授所言,德国唯心论哲学家们甚至“认为自己是整个世界之存在的唯一审核者”㊺。费希特、谢林都希望建立一个确定性的体系,并在这一体系中恢复理性所应该具有的无限权能。而海德格尔“认为人的理性不可能达到对世界之整体的封闭而彻底的理解(并以此反过来证明理性的权能)”㊻,他所追求的从来不是建立一个具有确定性的体系,因为世界本身不可认识且不能把握的一面本身就是存在的真实样态。在前期的《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指出,世界作为此在生存的基本建构是和此在同样源始的,并且这一结构只能通过人的生存才能领悟,而无法通过反思活动通达。后期海德格尔更是提出了“天、地、人、神”(Himmel, Erde, Mensch und Gott)四方整体的存在建构,尽管天空是敞开的,但是大地是封锁和遮蔽的,在这种敞开与封锁的二元争执之中,存在的真正面貌才得以显现。也就是说,世界在海德格尔那里尽管是此在的建构要素,但世界有着此在不可理解的、神秘性的另一面,这种神秘性也是世界作为与此在同样源始的本原的体现。在这种神秘性中,海德格尔悄悄地恢复了康德的物自身的地位,使得人和世界始终处于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之中。㊼
诚然,海德格尔所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不再像德国古典哲学那样高举理性主义的大旗,试图彻底把握自然界。但这种在自然的神秘性面前的退缩,并非是要去无限后退直至沦入虚无主义的深渊,而如此这般的退缩本身恰恰是有限的人类存在和无限的自然之间的张力必然造就的结果。海德格尔的尝试并不是在提醒我们,有限性的人类存在无法彻底通达无限的自然;他真正深刻的理论洞见在于——作为个体性存在的自我只有在世界存在的整体性之中才能维持它的生命力。单凭纯粹的个体力量去倾覆整全的世界无异于以卵击石,因为世界作为大全一体的存在本身就是有限个体存在的条件。只有在无限的世界整体中寻找到安放有限自我的位置,个体的生命才不至于被存在的洪流淹没。
五、结论
在本文中,笔者从展示费希特所刻画的作为自我与非我的统一体的绝对自我的动态结构出发,揭示了费希特1794 年版《全部知识学基础》中无法解决的困难——一种仅仅以自我作为本原的哲学无法建立起外部世界的实在性。正是在非我问题上,海德格尔实现了对费希特哲学的超越。一方面,海德格尔吸收了费希特哲学中“自我”的因素,将此在描述为在生存活动中赢获自身可能性的能在;另一方面,海德格尔抓住了费希特理论的核心困难,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的阐释实现了对费希特单一主体性哲学的超越:世界不是外在于此在的生存活动,相反,世界本身就是此在的基本存在建构。同时,海德格尔这种把世界和此在作为双重本原的哲学可以看作是对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的回应。也就是说,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类要做的不是去彻底理解作为整体性存在的世界,而是要在整体性的洪流之中寻找安放自身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