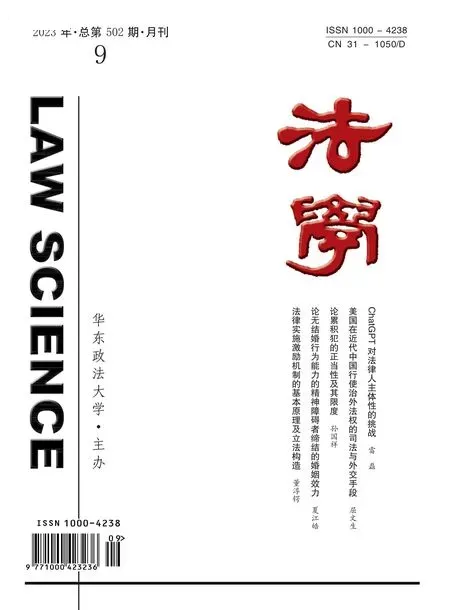我国民法诚信原则的类型化适用
●潘子怡
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诚信原则的适用范围极广,被誉为“帝王条款”。〔1〕参见梁慧星:《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填补》,载《法学研究》1994 年第2 期,第23 页。在比较法上,关于诚信原则的地位和规范设置存在两种不同的形态:一种是以瑞士民法为代表的“并列式”规范,将诚信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等置于同一条文的不同款项,诚信原则在此仅具有行为标准功能(即解释、补充功能);〔2〕参见[瑞]贝蒂娜·许莉蔓-高朴、耶尔格·施密特:《瑞士民法:基本原则与人法》,纪海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7 页。另一种则是以德国民法为典例的“大诚信”规范,诚信原则作为上位原则吸收了禁止权利滥用的内容和功能。〔3〕在德国民法中,禁止权利滥用理论的内容和功能更多地体现于《德国民法典》第242 条诚信原则、第826 条善良风俗等规定,尤其是被称为“帝王条款”的第242 条,它被从原先仅适用于债务履行内容的狭窄文义中解放出来,扩张为作为一切权利行使限制的基本原则。Vgl.Brox/Walker,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34.Aufl., 2010, Rn.684.我国民法由于特殊的教义学构造和源自德国法的学理继受,实质上也是遵循一个“大诚信”规范模式,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被视为诚信原则的具体化表现之一,在此基础上我国民法的诚信原则不仅具有行为标准功能,还具有限制权利功能和法律修正功能。〔4〕关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和诚信原则的关系,学界存在不同观点。本文采通说,即诚信原则是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上位原则,我国民法上的限制权利的诚信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同义。下文一般以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指代限制权利的诚信原则。
在我国《民法典》中,诚信原则体现为“基本原则—概括条款”的特色构造,《民法典》第7 条规定了诚实信用基本原则,其后存在诸多概括条款。〔5〕参见于飞:《基本原则与概括条款的区分:我国诚实信用与公序良俗的解释论构造》,载《中国法学》2021 年第4 期,第25 页。既有研究多致力于诚信原则的学理及其与其他原则的关系等内容,汇聚了相当多的智识。〔6〕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以诚实信用原则的法理分析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59-160 页;徐国栋:《诚实信用原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1-161 页;[日]营野耕毅:《诚实信用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法理的功能》,傅静坤译,载《外国法译评》1995 年第2 期,第39-45 页;王泽鉴:《诚实信用与权利滥用》,载《北方法学》2013 年第6 期,第5-17 页;于飞:《公序良俗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区分》,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11 期,第146-162 页。诚信原则具有“白纸委任状”的特性,为法官寻找裁判依据提供了便利,司法实践中诚信原则的适用十分普遍。但如何适用诚信原则缺乏妥适的理论指导,因此在该原则的具体适用上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相关司法案例的梳理与剖析,揭示我国民法诚信原则适用的诸多问题,探寻诚信原则类型化适用的方法和规则。
一、诚信原则司法适用乱象及其问题
作为民法基本原则,诚信原则应当遵循“先具体规则、后基本原则”的适用顺序,不加区分地适用诚信原则既无视各类型之间的差异,又有向一般条款逃逸的危险。
(一)统一适用诚信原则的司法乱象
通说认为,我国民法的诚信原则包含一个极大的范畴,适用范围包括一切法律行为,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仅为其中的一个具体化原则。〔7〕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38 页;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 年版,第268 页;徐国栋:《〈民法总则〉后我国民法基本原则理论研究述评》,载《法治研究》2022 年第1 期,第3 页;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40 页;尹田:《民法教程》,法律出版社2006 年版,第13 页;李双元、温世扬:《比较民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60 页。因而在我国民法上的诚信原则根据其具体功能,可以类型化为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限制权利的诚信原则以及具有法律修正功能的诚信原则,其中,限制权利的诚信原则即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不同类型的诚信原则存在不同的适用前提和评价标准,在仅能适用一种类型诚信原则的案件中倘若错误地适用另一种类型的诚信原则,即采用错误的评价标准,就可能出现案件裁判结果错误,个案不公正由此产生。
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以及作为法律修正工具的诚信原则在适用前提、适用标准上均存在实质差异,应当基于不同的类型区分适用。一方面,在适用标准层面,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的适用标准低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而作为法律修正工具的诚信原则之适用标准也较高,只有可能出现在特定“极端不正义”的情形下。另一方面,在适用领域层面,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仅能适用于存在“特别结合关系”(Sonderbeziehung)的场域,〔8〕比如在合同或者双方或多方的具体法律关系中存在更高程度的注意义务,亦可理解为“广义债之关系”。Vgl.Wolfgang Fikentscher/Andreas Heinemann, Schuldrecht, 10.Aufl., 2006, S.115.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和作为法律修正工具的诚信原则并无此种限制。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通常一并援引诚信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或是在部分案型中仅统一援引诚信原则,〔9〕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02 民终4123 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川07 民终3170 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豫民申4259 号民事裁定书;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云01 民终102 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21)渝05 民终140 号民事判决书。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区别被模糊化。这样的原则援引方式倘若不影响最终结果,那么仅是裁判论证规范的问题,不会产生实质的错误裁判。但问题是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和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具有不同的适用前提和适用标准,不加以区分会导致个案不正义。
譬如,在不存在“特别结合关系”的领域,在此一般应当适用的是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而此时若以“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之评价标准适用于具体个案,因“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之评价标准更容易被违反,对当事人而言负担过重,会造成个案不公正的结果。在“樊哲学、王安平排除妨害纠纷案”中,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认定该案为相邻关系纠纷作出纠正,认为该案应为排除妨害纠纷。但二审法院认为在被告王安平加高护坎时,“原告方樊哲学同意移走原护坎上所堆放砖块的行为,应视为原告方同意被告加高护坎,现又要求被告进行拆除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此对樊哲学要求王安平拆除护坎及栏杆的请求不予支持,并判决由原告承担案件受理费。〔10〕参见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湘08 民终432 号民事判决书。二审法院所认定原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不属于特别结合关系场域,在此不能适用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评判当事人的行为。而如果在此适用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评判原告的行为,尚须满足更高要求的适用标准,因此驳回原告诉求的判决有待商榷。
同样地,在存在“特别结合关系”的领域,亦应对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区分适用,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适用须以权利外观的存在为前提,不加区分只会造成司法实践的混乱。但此种情况比起前述非特别结合关系领域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之区分适用,对个案实际结果的影响较小,更多地涉及学理上的区分以及法律适用规范的问题。而在非特别结合关系领域,尤其是不存在合同关系时,适用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抑或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评价标准评判当事人的行为,对个案结果的影响更大。此时倘若当事人的行为未达到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评价标准,但违反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之评价标准,不能据此认定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进而作出裁判,这是因为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在此并不能适用,否则将造成个案不公正的结果。裁判文书同时援引诚信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现象不仅存在于民法领域,在知识产权法、公司法等特别私法领域也存在。〔11〕参见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1 民终998 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06 民终5830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 民终12890 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7 民终3633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1 民终10617 号民事判决书。
(二)诚信原则适用的不规范与空洞化
除前述未区分不同类型诚信原则可能导致的适用问题以外,还存在不加论证径直适用诚信原则等问题。诚信原则作为基本原则不能直接作为裁判依据,应当具体化为个案规则才能适用。在存在具体规则时应当适用具体规则,否则将构成向一般条款逃逸。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无实质意义式或向一般条款逃逸式等诚信原则适用现象。无实质意义式的适用主要表现为宣示性适用,在“本院认为”部分使用“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的套话,缺乏实际意义,〔12〕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01 民二(民)终字第62 号民事判决书;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甘民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而向一般条款逃逸式则是指在存在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仍然径直援引诚信原则,逃避论证义务。〔13〕参见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2011)淅民商初字第47 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1)黄01(民)初字第2106号民事判决书。例如,在“某某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与周某某电信服务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民事活动应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原、被告签订的入网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14〕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2011)闸民一(民)初字第5069 号民事判决书。类似案件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二终字第249 号民事判决书。但原《合同法》第60 条(《民法典》第509 条)已经规定合同履行的具体规则,即“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该案未援引合同履行具体规则,而是仅以“民事活动应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作为裁判论证表述,既不符合法律适用的基本原理,又无实际意义,在援引具体规则后该套话式表述即使去除也无任何影响。又如,在“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与海南伊斯兰有限公司等合作开发合同、土地使用权抵押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新宏基公司的行为违背了原《民法通则》第4 条之诚信原则和第58 条第1 款第3 项“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行为无效之规定,该《资产抵押协议书》应认定为无效,然而援引后者即可,同时援引诚信原则并无实质意义。〔1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1999)民终字第126 号民事判决书。
职是之故,在司法实践中区分不同类型诚信原则的适用方法及评价标准等,尤其是区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与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其一,在体系关系上,如果不具体区分各种类型的诚信原则,尤其是不明确禁止权利滥用原则适用的特殊性,那么与直接规定一个笼统的“公平正义”原则效果无异。其二,不区分各种类型诚信原则的适用,亦不正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其他具体规则与诚信原则的规范援引问题,只会导致法官先定结论再以空洞的诚信原则作为论证依据,有向一般条款逃逸的风险。其三,同类事物应作相同处理,不同事物应作差异化处理,此亦是类型化方法的法理基础之一。区分不同类型诚信原则的具体适用规则,符合公平正义和平等的价值要求。
二、我国民法诚信原则的“三分法”构造
依据诚信原则所发挥的功能、适用场域、评价标准的不同,可以将诚信原则类型化为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以及作为法律修正工具的诚信原则三种。其中,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仅可适用于“特别结合关系”场域,要求当事人能够保护相对人的合理信赖,照顾相对方的利益,“诚实信用”和“交易习惯”是其主要的行为标准要求。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作为限制权利的诚信原则,则可适用于一切法律行为领域,但其适用须以存在权利行使外观为前提,且须结合权利人的主观意思、客观行为、权利的客观目的以及各方利益衡量等要素加以识别。而作为法律修正工具的诚信原则之适用虽亦不存在“特别结合关系”的前提要求,但须非常谨慎,其实质标准是维护个案“公平正义”,应当经过充分的论证程序方可适用。
(一)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
德国法上诚信原则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行使审查”(Ausübungskontrolle),这一观点亦为我国学界部分学者所持。〔16〕参见于飞:《公序良俗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区分》,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11 期,第151 页。但《德国民法典》并未有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实定法一般规定,《德国民法典》第242 条所规定的诚信原则的行使审查功能是“大诚信”原则所具有的功能,包含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限制权利功能在内,对此应当作出区分。〔17〕《德国民法典》第226 条规定的“禁止恶意刁难”(Schrankenverbot)不过是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下的一个极罕见的子类型。
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要求当事人能够保护相对人的合理信赖,照顾相对方的利益,在交易中尽到一般之善意。〔18〕Vgl.Dirk Looschelders, Schuldrecht Allgemeiner Teil, 18.Aufl., 2020, Rn.29;王洪亮:《债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84 页。瑞士民法中的诚信原则发挥的即是此种功能,《瑞士民法典》第2 条第1 款要求每个人在“行使权利”和“履行其义务”时必须遵守诚信,这一行为要求在法国法律文本中亦被称为“行为准则”(règles de la bonne foi)。〔19〕Vgl.BK-Berner Kommentar, 2012, Art.2, Rn.20.这一功能是对权利和义务的实质性具体化,包括对合同以及法律的解释。在解释合同时,必须将措辞作为起点,还应当考虑当事人的语言技能和行业词汇。此外,诚信原则还可以用于解释原则(如模糊性规则与一般条款和条件解释中更严格的规则)、补充不完整的合同、根据重大变化调整合同,以及在必要时要求立即终止合同等。
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旨在提供一个一般的行为标准,要求根据对方的具体期望和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般规范,采取忠诚和正确的行为,表现出相互尊重和体谅。〔20〕Vgl.ZK-Orell Füssli Kommentar, 2021, Art.2-B, Rn.3.交易习惯也是一个衡量是否满足“诚实信用”要求的重要行为标准,尤其是作为商法这一诚信原则之起源领域中该原则具体化的依据之一。〔21〕参见徐学鹿、梁鹏:《商法中之诚实信用原则研究》,载《法学评论》2002 年第3 期,第33-35 页。具体而言,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之适用包括解释、补充合同和法律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可以补充解释合同规则、补充附随义务以及确立从给付义务和保护义务等内容。
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之适用须以“特别结合关系”(Sonderbeziehung)如质押关系、相邻共同体关系等存在为前提。这一“特别结合关系”并不局限于债之关系,但在如竞争的多个参与者之间等不属于特别结合关系的场域则没有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适用的余地。〔22〕Vgl.Karl Larenz,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and I, Allgemeiner Teil, 14.Aufl., 1987, S.127 f.诚信原则作为一种行为标准时所要求的一种较高注意义务需要以“特别结合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否则会造成不必要的负担甚至影响当事人的行为自由。〔23〕参见于飞:《公序良俗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区分》,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11 期,第153 页。此后“特别结合关系”的含义已经从广义债之关系演变为“与私人之间的一般社会关系相比存在有条件的社会接触”,一般权利和义务如注意义务、因侵犯一般人格权而提出的损害赔偿要求的衍生不在诚信原则范畴之内。〔24〕Vgl.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 8.Aufl., 2019, § 242 Rn.123.但考虑到《德国民法典》诚信原则的内容和适用范畴与我国民法中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并不一致,本文认为仍采“广义债之关系”为“特别结合关系”的含义较为合理,不至于加重当事人的行为负担。此外,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注重的是保护“特别结合关系”中相对方的利益,原则上其所涉利益权衡大多是相对方之间的,并且更多地针对相对权尤其是债权的行使。
(二)限制权利的诚信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限制权利功能包括限制权利的范围及行使方式。一项被法律赋予个体的权利,首先存在实定法规定或当事人约定内容的“外部”界限,即该项权利根据其性质或目的被授予,而“内部”界限则体现于法的一般性原则、法律制度的精神等限制。〔25〕参见[法]雅克·盖斯丹、吉勒·古博:《法国民法总论》,陈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705 页。一旦这种限制被转变为具体性的法律规范,即会构成权利的外部界限。如果某人出于损害他人的目的行使自己的一项权利,那么就有可能超越了权利的“内部界限”,尽管其并没有逾越该项权利的外部界限。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同实定法规范以及当事人间的约定一样,具有为权利划定更明确范围、限制权利的范围及行使方式的功能,只不过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划定的是权利的内部界限,而实定法规范和当事人约定则是作为权利的外部界限存在。作为诚信原则的具体化,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旨在为权利行使的行为划定一道界限,超越这一界限权利的行使便不被允许,从而使权利范围明确化并受到限制。〔26〕参见[日]营野耕毅:《诚实信用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法理的功能》,傅静坤译,载《外国法译评》1995 年第2 期,第43-44 页。
原则上,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可以适用于权利的行使并适用于一切法律行为领域,而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仅能适用于“特别结合关系”场域。作为诚信原则的具体化原则,在应当援引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时不应重复援引或不规范地直接援引作为其上位原则的诚信原则。但裁判文书通常同时援引诚信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无疑进一步模糊了两者的区别,不利于区分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适用边界。〔27〕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02 民终4123 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川07 民终3170 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豫民申4259 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民终755 号民事判决书;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云01 民终102 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21)渝05 民终140 号民事判决书。
在“限制权利”和“行为标准”的功能分野下,以及是否以“特别结合关系”存在作为适用前提的区分基础上,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和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在保护对象上也显现出明显的差异。原则上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保护的是相对人利益,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本旨不限于此,还包括对第三人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但这并非意指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等同于要求个人利益绝对让位于第三人以及社会公共利益,而是需要在具体个案中结合权利人的目的、各方利益权衡以及权利本身的客观目的予以判断。例如,房东将房屋出租给一群求租者中的一位可能造成其他求租者利益受损,但不能认为在此存在权利滥用。又如,以“产权商铺案”为例,原告所购商铺与商厦其他商铺之间存在物理上和经济价值上的不可分性,原告利用该商铺获取利益的理想方式应当是出租商铺收取租金。然而原告却无视其他92%业主同意将商铺集体出租给被告的意愿,要求被告搬离商铺、赔偿损失并赔礼道歉。衡量原告、被告以及商铺其他业主的利益,原告的权利行使可能使其获得不正当的高额补偿,但极大地损害被告以及其他业主的利益,存在客观利益失衡的情形。原告在此行使排除妨害请求权的行为不能证明具有正当用途,取回商铺也无法实现收取租金的经济利益,并非为实现本人正当利益,既违背权利的客观目的,亦存在利益失衡的客观情况,构成权利滥用。〔28〕参见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甬民一终字第123 号民事判决书。再如,权利人行使权利的行为可能造成环境损害,但认定存在权利滥用仍需结合权利人获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受损之间的比例大小、是否违背权利的客观目的等要素判断。对于权利人有其他可替代方式仍选择此种可能致环境受损的方式、该项权利行使违背权利本身的正当目的或社会公共利益受损与权利人获益相比较大等情形,可认定存在权利滥用。
基于两者保护对象和适用场域的区分衍生出另一条一般性规律,即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一般适用于相对权,而绝对权一般属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规制范畴。譬如,在“杨宏林与王腾明排除妨害纠纷案”〔29〕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1 民终8486 号民事裁定书。中,当事人之间是对案涉墙垛所在的宅基地使用权存有争议的邻居关系,不属于“特别结合关系”,且宅基地使用权系绝对权,此种排除妨害纠纷一般由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处理,因此该案的裁判依据应当是作为具体化原则的禁止权利滥用,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在此并不适用。在“限制权利”和“行为标准”的差异功能框架之下,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与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在适用场域、保护对象上均有所不同,这些层面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矫正司法实践中对两者引用失当以及重复援引所造成的混乱,应在我国民法大的“诚信原则”概念下予以类型化适用。
(三)作为法律修正工具的诚信原则
法律修正功能适用的前提要件是“存在明显的制度滥用”,只有当某项规则的适用会造成明显不公正的结果时,法官才可以使用基本原则对法律进行修正。〔30〕Vgl.Staudinger/Looschelders/Olzen Kommentar BGB, 2015, § 242 Rn.221.此种法律修正功能类似于起源于罗马法的一般恶意抗辩(exceptio doli generalis),又称为恶意抗辩(Einrede der Arglist),其作为一种法官矫正不公平的手段,自19 世纪初起扮演重要的角色。〔31〕一般恶意抗辩要求一般性的公平,主要是针对一些过于僵硬的规则适用特殊情况,给法官提供一种介入其中的依据并避免不公平现象的发生,是一种针对一切不公正的一般性预防措施。Vgl.Philipp Eichenhofer, Rechtsmissbrauch-Zu Geschichte und Theorie einer Figur des Europäischen Privatrechts, 2019, S.101; See R.Zimmermann, Roman Law, Contemporary Law, European Law, Oxford Press, 2001, p.83.在这一点上,一般恶意抗辩实际上起到的即类似于诚信原则这种法律原则的作用,具有运用特定的原则、指导性法律思想或一般价值标准以支配整个或绝大部分法秩序的作用。〔32〕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第355 页。而究竟是诚信原则抑或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发挥法律修正作用,应当考量该部门法的内在体系以及教义学构造。
在解释论上,德国民法以《德国民法典》第242 条为规范据点作出超出文义范围的解释,赋予其“公平正义”的内涵,在诚信原则的功能上发展出法律修正的功能,作为法官进行法律续造的依据,诚信原则作为一个灵活的工具,为法官在个案中判断具体规则适用是否公正提供助力。在此意义上,重要的不是个案的适用是否符合诚实信用字面意思上的要求,而是具体规则的适用实质上是否达到一个公正的结果,公平正义才是其背后的理论基础。而《瑞士民法典》则将这一功能赋予第2 条第2 款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瑞士民法中,发挥法律修正功能的并非《瑞士民法典》第2 条第1 款规定的诚信原则,毋宁是第2 条第2 款规定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而诚信原则在此仅具有法律解释、补充的功能。〔33〕参见[瑞]贝蒂娜·许莉蔓-高朴、耶尔格·施密特:《瑞士民法:基本原则与人法》,纪海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7 页。而由于我国《民法典》第132 条的适用范围比较狭窄且规定于“民事权利”一章,法律修正功能应当置于《民法典》第7 条诚信原则的教义学框架内。〔34〕参见李夏旭:《诚信原则法律修正功能的适用及限度》,载《法学》2021 年第2 期,第61 页。但是其他部门法应当选择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或者诚信原则实现法律修正功能,且视该部门法的内部教义学体系构造和特征等需求而定。
在法律修正功能下,诚信原则的适用标准不同于行为标准功能,而是须认定个案中是否存在“极端不正义”,并且这种不正义足以对抗实定法的效力。具体的论证方法应当是,法官在支持具体规则的实质理由和形式理由与诚信原则之间进行权衡,只有当后者的分量大于前者之和时,方可适用诚信原则对具体规则进行个案的法律修正,在此基础上设置例外规则。〔35〕参见雷磊:《论依据一般法律原则的法律修正》,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 年第6 期,第17 页。在具体规则与诚信原则的适用顺序上,通常的顺位应当是具体规则优先于诚信原则适用。但是,在具体的规则导致严重的不公正后果的情形下,可以基于原则产生限制性规定,从而排斥具体规则对个案的适用。〔36〕关于诚实信用原则这一法律修正功能的适用,参见于飞:《基本原则与概括条款的区分——我国诚实信用与公序良俗的解释论构造》,载《中国法学》2021 年第4 期,第41 页;李夏旭:《诚信原则法律修正功能的适用及限度》,载《法学》2021 年第2 期,第56 页。
此外,作为法律修正功能的诚信原则应当后于目的性限缩方法适用。因目的性限缩的正当性基础在于立法者的主观目的,而诚信原则的法律修正功能则是突破了立法者的主观目的,是寻求个案公平正义的工具,因此在目的性限缩足以解决个案问题时,不应直接适用作为法律修正工具的诚信原则。
如此,在我国民法认可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作为诚信原则具体化原则的基础上,诚信原则不再局限于行为标准功能,同时也具备限制权利之功能,其适用不必再以“特别结合关系”为前提,而是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民事法律行为,如在相邻关系中对物权的限制也可以适用诚信原则。此外,诚信原则作为一般行为标准之功能与法律修正功能的具体适用标准也存在差异,法律修正功能本身已经超脱了“诚实信用”的文义表述,替代以“公平正义”的核心内涵。
三、诚信原则“三分法”构造的法理基础
对我国民法诚信原则进行“三分法”适用具有充分的理据与必要性。一方面,在我国民法语境下诚信原则的三重内涵与三种诚信原则相对应,此种分类较为周延,亦便利同类事物作相同处理,契合类型化方法的要义。另一方面,基于不同的内涵,三种诚信原则具有互相区分的必要性,对精确化和规范化适用诚信原则有所裨益。
(一)诚信原则“三分法”适用的实质缘由:基于不同内涵
诚信原则在不同法域乃至不同部门法中都可能存在不同的内涵。实定法具体规范的形态影响了诚信原则的内涵和功能范畴,“诚信原则作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上位原则”并非是一条铁律,诚信原则的限制权利功能在如我国民法般的特定语境下方才成立。在具有完整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规范的大陆法系国家如瑞士、日本,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与诚信原则之间是一种同位阶关系,两者各自发挥不同的功能,此时诚信原则一般只具备行为标准功能,其内涵即为字面意义上的“诚实信用”。〔37〕在1947 年修订的《日本民法典》中,这一内容明确地规定于第1 条第3 款。See Kazuaki Sono &Yasuhiro Fujioka, The Role of the Abuse of Right Doctrine in Japan, 35 La.L.Rev.1039 (1975).而在不具有完整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规范的法域,例如德国民法和我国民法,禁止权利滥用的诸多内容和限制权利等功能被诚信原则吸收,此时的诚信原则之内涵不仅包括“诚实信用”,还扩张至“禁止权利滥用”以及“公平正义”。〔38〕Vgl.Brox/Walker,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34.Aufl., 2010, Rn.684.
在我国一些部门法中,当不存在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实定法规范时,立法和司法实践即以诚信原则代替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发挥功用,此时诚信原则的内涵亦包括“禁止权利滥用”。如《商标法》第7条明文规定:“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此处所谓“诚实信用原则”实则禁止权利滥用。一方面,就其义理而言,商标权纠纷当事人之间并无“特别结合关系”,法律课以诚实信用,以促其对他人妥为照顾,实无基础。另一方面,我国民事立法向来多用“诚实信用”,怯于使用“禁止权利滥用”或类似表述,则属立法语言选择之路径依赖,不足为训。因此,在已有明文规定之部门法中,可暂以统一的诚信原则之用语代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之功能,其余之处仍应予以区分。譬如在“王碎永诉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泰世纪百货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3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24 号民事判决书。中,双方当事人不属于“特别结合关系”,原告恶意取得并行使商标权的行为应当诉诸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而非诚信原则。在此由于欠缺实定法规范而暂以诚信原则之名行禁止权利滥用之实仅为一种权宜之计,尤其是须注意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仍需按照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适用标准,倘若在应当适用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案例中采用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之评价标准,将会导致本不违反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行为被错误地认定为违反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进而遭受不利判决。
(二)诚信原则三种功能区分的必要性:基于不同的适用前提及标准
三种诚信原则内涵的不同决定了彼此的适用领域和适用标准亦有所不同,在此基础上对诚信原则进行“三分法”适用有其必要性。
1.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区分
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无论是在功能、适用场域、保护对象上还是在评价标准上均有所不同。首先,当诚信原则作为一种对当事人行为的标准时,其本旨在于要求当事人在从事法律行为时恪守诚信,具体的表现应当是照顾相对方的利益,而禁止权利滥用则是规制行为人权利的行使,保护的不仅是相对人的利益,还包括第三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并基于此对行为人“滥用”权利的行为予以负面评价。其次,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为当事人设置“对相对人利益予以照顾”的行为负担,此种较高行为负担的正当性前提是当事人之间存在“特别结合关系”,在不具备“特别结合关系”的场域不应当课以诚信原则所设置的行为负担,而禁止权利滥用则不受此限制。因此,在我国民法诚信原则的实质裁判标准上,应当在不具备“特别结合关系”的场域适用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即“限制权利”功能的评价标准),诚信原则的“行为标准”功能在此并不适用,在裁判规范援引层面应尽可能援引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有助于区分两者的实质内容和功能。最后,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是一种易于被违背的道德性要求,而禁止权利滥用则要求客观上达到“滥用”的程度。权利滥用中的权利在实定法或当事人约定的“外部界限”内存在初显的正当性,其不法性来源是有违权利的“内部界限”,于此权利滥用不法性的强度须足以对抗权利初显的正当性。〔40〕参见彭诚信:《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法律适用》,载《中国法学》2018 年第3 期,第261 页。
有关权利滥用的具体识别标准,无论是大陆法系其他国家还是我国均存在多种学说,主要有“主观标准说”“客观标准说”“违背权利目的说”“违背权利目的与社会公益说”等。而我国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也并未就何为权利滥用的具体识别标准抑或如何识别达成一致意见。有学者将权利滥用分为行使权利所得利益微小而使他人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行为以及行使权利具有损害他人的目的的情形。〔41〕参见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总则编》,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21 页。还有学者则列举权利滥用的三项构成要件,即行为人具有权利、以损害他人为目的或者权利行使所得获益与他人所受损失之间严重失衡、权利行使的边界不清。〔42〕参见李敏:《我国民法上的禁止权利滥用规范——兼评〈民法总则〉第132 条》,载《法律科学》2018 年第5 期,第129 页。但是这些观点显然无法穷尽权利滥用的具体类型,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我国民法语境下虽属于诚信原则的具体化表现之一,但仍具有一般条款的特性,无法仅以封闭的构成要件加以适用,而是需要在个案中结合各项要素进行认定。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适用应当包括三项必备前提:一是存在一项权利行使外观,即行为人具备一定的权利基础并基于此提出主张;二是该项权利行使的行为可以被评价为“滥用”;三是损害他人或社会合法权益或具有此种可能性。首先,行使权利的行为仅可推断为具备初显的正当性,当权利行使行为超越行使权利的内部限度(基于权利本质或客观目的之约束)因而产生足够强度的权利滥用之不法性时,权利初始的正当性自此瓦解。其次,“滥用”的评价无法被直接定性或定量化,应当结合权利人的主观意思、权利滥用的客观行为、权利人和他人之间的利益衡量以及行使权利是否违背客观目的等要素加以判断。〔43〕关于鉴别要素的具体判断以及禁止权利滥用原则适用于个案的程序方法,参见彭诚信:《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法律适用》,载《中国法学》2018 年第3 期,第253-258、264 页。最后,权利滥用的行为鉴别中存在双方的利益衡量,客观层面上双方利益失衡(权利行使人所获利益与相对方相比而言较小)可能构成权利滥用,仅具有损害他人或社会合法利益之可能性也可能构成权利滥用,如于己无利而以专门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之权利行使。在实际判断中,损害他人或社会合法利益不应作为权利滥用的必备要件。一是因为实际利益损害的证明存在一定的难度,比如股东滥用诉权而使公司名誉受损或造成公司应付诉讼过程中的时间、精力损失。二是因为可能存在权利人的行为构成权利滥用但他人未遭受实质损害的情形。例如,在“滥用解除权案”中,法院认定原告行使解除权的行为构成权利滥用,但该案被告并未遭受实际损失。〔44〕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青民二商终字第562 号民事判决书。又如,在“产权商铺案”中,被告及其他业主的利益并未发生实质损害,只是存在潜在的受损可能性。〔45〕参见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甬民一终字第123 号民事判决书。
就限制权利和作为行为标准功能的区分角度而言,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标准无疑高于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它要求一种较高的不法性强度,而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要求的是一种忠诚、为相对方考虑的道德性行为标准,后者显然更容易被违反。
2.作为行为标准和作为法律修正工具的诚信原则之区分
关于诚信原则作为行为标准和法律修正工具亦存在不同的评价标准,应对两者区分适用。譬如,在“为获益而主张违法合同无效”的案型中,〔46〕参见李夏旭:《诚信原则法律修正功能的适用及限度》,载《法学》2021 年第2 期,第57 页。仅以诚信原则的行为标准功能评价个案中“主张合同无效”之行为因违反诚信原则并产生相应后果可能并不妥当,尤其是以此直接认定合同有效更为不妥。一方面,倘若允许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在该类案件中直接适用,所产生的后果应当是驳回当事人的无效主张,但禁止违反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一方主张合同无效,合同无效的结果并不会因此发生改变。〔47〕当事人的无效主张与合同本身的效力认定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通过适用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而禁止主张合同无效并不能改变实际的后果。参见于飞:《诚信原则修正功能的个案运用——以最高人民法院“华诚案”判决为分析对象》,载《法学研究》2022 年第2 期,第59 页。另一方面,在一般情形下,双方的此种违法合同不值得受到诚信原则的保护,要求一方当事人不得主张违法合同无效并不妥适,在此应当考虑诚信原则法律修正功能的适用。表面上,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似乎违反的是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但究其实质当事人滥用的是“合同无效”的法律制度,构成制度滥用(institutioneller Rechtsmissbrauch)。〔48〕Vgl.Staudinger/Looschelders/Olzen Kommentar BGB, 2015, § 242 Rn.217.在具体个案中,严格适用合同无效制度具体规则会产生严重不公正的后果,在经过原则实质理由、规则实质理由以及形式理由的权衡和充分论证等程序后,诚信原则的法律修正功能在此得以适用并对具体规则予以限制与修正。
与限制权利功能以及法律修正功能相比,行为标准功能是诚信原则最初所具备的功能,这种“一般之善意”和“照顾相对方利益”的标准比起公序良俗和禁止权利滥用都更为严格,其适用前提是存在特别结合关系。因此,在以行为标准功能的具体要求判断该案当事人是否构成对诚信原则的违反反时,首先须明确于此存在特别结合关系。在非特别结合关系的场域,以行为标准功能所要求的“一般之善意”以及“照顾相对方利益”对当事人的行为作出较高的要求是不适宜的,会增加当事人的行为负担,诚信原则所发挥的只能是限制权利功能和法律修正功能。
四、我国民法诚信原则类型化的具体适用
(一)类型化适用的方法论
在法律修正功能以外,禁止权利滥用和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具有各自独特的功能和适用场域,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两者会发生重合,但仍有更接近案情的一项可以适用,不必重复援引两者。即便是在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实定法中仅存在诚信原则的实定法规范,以“诚信原则”作为统一的裁判依据,也应当重视两者的功能差异而予以区分适用。首先,在不具备特别结合关系时,行为标准功能所要求的更高评价标准在此不应适用,以免将不违反我国民法诚信原则的行为错误地纳入规制范畴。针对非特别结合关系场域以及法律修正功能的适用,因为并不存在诚信原则行为标准功能适用的可能性,仅需分别贯彻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和法律修正功能的适用标准及判断方法即可。其次,在存在特别结合关系的场域,由于诚信原则行为标准功能之评价标准更容易被违反,因此应当首先判断案涉当事人是否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标准,以及案涉利益是否涉及第三人利益或公共利益。在案涉行为不违背行为标准功能之评价标准时,再进一步考量是否违反限制权利功能的评价标准。在规范援引上,应当在条件符合的情况下援引诚信原则而不必重复援引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不构成违背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的情况下应当援引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最后,诚信原则的法律修正功能不同于行为标准功能和限制权利功能,只有在具体规范的个案适用会导致难以忍受的不公正时,才能依据前文所述的适用标准和严格的论证程序决定是否适用诚信原则对个案结果进行矫正。
在司法实践中,首先判断案涉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特别结合关系,诚信原则的行为标准功能在此能否适用,但仍需要进一步考虑在特别结合关系的场域内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和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的保护对象、规制权利种类等因素,最终确认援引何种原则。例如,在“唐羽、刘国江共有物分割纠纷案”〔49〕参见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21)川0105 民初9901 号民事判决书。中,双方当事人对涉案房屋存在共有关系,且原告在受赠案涉第三人的部分不动产权份额时视为对其上设定的负担已经接受,原告主张对案涉房屋进行拍卖分割的行为违背受赠部分不动产权份额上的负担内容。虽然该案判决援引的是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但不代表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在此没有适用的余地,因为双方当事人对案涉房屋的共有关系实质上也是特别结合关系的一种。在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和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均可适用的此种场域下,则需要明确如何进一步区分两者的适用。
此外,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适用标准相较于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要求更高,因此在“特别结合关系”场域,首先审查是否构成对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之违反在逻辑上较为妥适。在前述“唐羽、刘国江共有物分割纠纷案”〔50〕同上注。中,原告在受赠案涉第三人的部分不动产权份额时视为接受对其上设定的负担,再主张对案涉房屋进行拍卖分割的行为违背受赠部分不动产权份额上的负担内容,此种不信守承诺的行为是对相对方信赖的破坏,乃对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之违背,在此不必援引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而在“上海联兴公司诉泰国森富公司和上海龙富公司以及工行上海市分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信用证付款纠纷案”〔51〕参见https://www.pkulaw.com/pfnl/a25051f3312b07f30f86fcce1872eb1b3aca12dd8ac0e2f5bdfb.html?keyword=禁止权利滥用原则%20, 2023 年3 月15 日访问。中,开证人银行在支付信用证时应当有一个注意义务,即如果已知基础交易中存在实质性欺诈,那么为了维护相对方申请人的利益应当终止支付,否则即违背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因此,在该案中不必重复援引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和诚信原则,仅援引诚信原则即可。另在“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青岛虹厦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52〕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02 民终4123 号民事判决书。中,以中建八局提供的混凝土标定用量推算减水剂数量作为双方结算依据违背的是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损害了相对方利益,不必重复援引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倘若案涉纠纷不涉及对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的违背,特别是在涉及第三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情形下,违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对权利范围的内部限制,则应当直接援引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例如,在“席海军、陈静等合同纠纷案”〔53〕原告即使有其他合理方式可弥补遭受的损失,却仍要采取行使合同解除权这一会致使他人利益受损的方式,构成对权利本旨的违反。参见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川07 民终3170 号民事判决书。中,虽然鑫驰梅西管理公司未按照约定向席海军、陈静等人支付租金收益已构成违约,但出于对商场整体利益以及其他业主利益的考量,案涉委托经营管理模式的特殊性质和购房人所有的商铺位置特点等因素决定了业主的缔约、续约、解约等合同权利均会不同程度地受限。此外,原告还可以通过请求被告支付违约金的方式弥补损失,因此倘若原告等人此时仍要行使合同解除权即构成对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违反,仅须援引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限制权利功能在此为这一合同解除权划定了内部界限,即不得损害第三人利益或公共利益以及以必要的方式弥补遭受的损失。
在前述“樊哲学、王安平排除妨害纠纷案”〔54〕参见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湘08 民终432 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曾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原告屋后护坎以上20 厘米归原告所有,该协议合法、有效,被告基于合同关系应当依诚信原则履行。因此,该案中违反诚信原则的是被告的不履约行为,其适用的是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而原告并未违反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在此也不适用于对原告行为的评判。一方面,此案将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错误地适用于“非特别结合关系”领域,且未有证据显示原告同意挪走所堆放砖块,亦无法从同意挪走砖块的行为推导出原告同意被告加高护坎。另一方面,原告的这一行为仅能作为判断其是否违反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依据,但结合该案事实无法认定原告的行为违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均认为被告加高护坎和加装护栏的目的是为保障原告的生活安全,属于合理行使相邻权的行为,但其实被告在本来建筑的晒台边缘加装护栏亦可达到同样的目的,且不侵犯原告的合理空间。该案原告诉请被告按约定拆除加高的护坎并无不当,法院在此未合理区分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适用,导致个案结果于原告而言不公平。
(二)诚信原则的三种具体适用情形
(1)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之权利滥用
民法上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主要适用情形之一即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不正当行使权利,在比较法上也多见类似实定法规定。例如,《德国民法典》第226 条“行使权利不得专以损害他人为目的”之禁止恶意刁难的规定,但这一规定的适用条件过于苛刻,因此符合其规定的情形较为罕见。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48 条第1 项“不得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之规定则比上述德国法规定略显宽松。
是否构成“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不能仅凭当事人的主观意思,而是要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得失进行衡量。〔55〕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523 页。在法国的“气球案”中,土地所有权人的邻屋是一间气球厂棚,而该土地所有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构建了一间极大的木棚并装有锐利的铁尖,有一个气球在试航(为提交给陆军部)时被木棚上的铁尖触破。于是气球厂棚的所有人起诉要求该土地所有人进行赔偿,并要求拆除这一可怕的木棚。法院认为被告在这一案件中损害他人的意思表现得十分明显,主要判断依据在于双方当事人的恶劣关系、被告购买土地的日期和付出的成本,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种特殊的建筑对其所购得的土地无利益且可能有害,比如造成土地荒芜的结果。因此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构成权利滥用,原告可以据此得到损害赔偿并要求拆除该建筑的一部分。〔56〕参见[法]路易·若斯兰:《权利相对论》,王伯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 年版,第12 页。而在“吴风顺与杨秀章、张明英排除妨害纠纷案”〔57〕但该案原告本身负有主要过错,因此承担主要责任。参见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28 民终412 号民事判决书。中,在一审审理期间,被告杨秀章、张明英在吴风顺的车辆尚未驶出争议地时即封堵该道路,客观上限制了该车的正常营运权,显然会给吴风顺一方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被告应以正当方式行使土地使用权,而其封堵道路主要是为了限制原告的车辆通行,给原告利益造成损失而于己无利,应当被认定为“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违反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2)客观利益显著失衡的权利滥用
客观利益显著失衡的权利滥用是指经由客观利益衡量,发现权利人行使权利的行为于己无利且对他人有损害或者所得利益与他人受损相比极小的情形。此种类型与“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的类型有重合之处,在司法实践中也更容易识别与操作。客观利益显著失衡的判断方法为纯粹以主观标准判断是否存在权利滥用提供了修正方案。譬如在“信鸽案”中,被告在自己阁楼饲养信鸽的行为并不能被认定为主观上“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的权利滥用。倘若以此案为例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扩张至“违反行使权利应尽的注意义务进而存在过失”,又存在要求过高之嫌,而学界关于权利滥用的主观标准亦存在诸多分歧。〔58〕参见彭诚信:《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法律适用》,载《中国法学》2018 年第3 期,第250 页。但在该案中如果对双方利益进行衡量,则可认定被告饲养信鸽的行为虽于己有利,但其严重侵扰原告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构成客观利益显著失衡的权利滥用。〔59〕参见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浙甬民一终字第152 号民事判决书。
这一客观利益衡量不仅涉及当事人之间,还需考量对其他多数人利益以及公共利益的影响,对他人或公共利益损害的认定不仅包括实质的损害结果,还应包括可能发生的利益受损。如在“产权商铺案”〔60〕参见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甬民一终字第123 号民事判决书。中,案涉商铺并非独立商铺,不具有可分性,在利益衡量时须考虑对大厦的整体规划和运营以及其他大多数业主利益的影响。原告基于商铺所有权诉请被告搬离商铺等要求损害绝大多数业主的利益,于己基本无利益且影响大厦的整体经营从而构成客观利益显著失衡的权利滥用。
(3)违背权利客观目的之权利滥用
作为农村的一所独立高级中学,学校除了坚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之外,还努力发展校园文化建设。校园社团是学生课余时间施展才华、展示风采的大舞台,是提高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重要载体,是学校课堂的有益补充和延伸。学校社团在丰富学生学习生活的同时,也推动了学校的文化建设的发展,也成为了校园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每项权利的设置均有其客观的制度目的,行使权利违背该项权利本身的客观目的即有可能构成权利滥用。例如,在股东滥用撤销之诉的情形下,股东行使诉权违背权利本身的客观目的,即股东提起撤销之诉的诉讼目的不在于实现撤销之诉的正当诉讼目的。例如股东向公司提交辞职报告后,又诉请撤销董事会关于同意该股东辞去职务的决议的行为。
此外,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虽是诚信原则的下位原则,仍需遵循“具体规则—一般条款”的原则适用方法,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民法典》中主要体现为滥用代理权、滥用地役权等规定。《民法典》第164、168 条规定了广义的代理权滥用行为,包括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实施代理行为、自我代理以及双方代理(经特定人同意或追认的除外),第384 条则规定了滥用地役权的内容。在不具备现行具体规则时,方可经由充分论证适用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一般条款进行裁判,以避免向一般条款逃逸。
2.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之具体适用情形
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要求当事人以“诚实信用”或交易习惯作为行为标准,在此基础上对合同内容、当事人义务等加以补充、解释。在司法实践和学理上,作为合同解释规则、确立附随义务、作为订立合同中的行为标准、后合同义务、合同禁反言等情形可以被划分至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之下,在遇到类似情形时,可以现有类型作为参考确定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之适用前提和标准。
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包括合同解释规则。《民法典》第510、466 条以及第142 条第1 款分别就合同内容、合同条款含义以及意思表示如何解释作出规定,均属于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的具体体现。在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可以按照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的标准之一即“交易习惯”予以确定。而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的另一标准即诚实信用也可用于解释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或合同条款的含义。例如,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花园路证券营业部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市办事处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关于花园路证券营业部出具的承诺鉴证书性质的争议源于对承诺鉴证书第2 条的理解。承诺鉴证书第2 条约定:“花园路证券营业部对申请人或出质人的国债交易负责监控,保证申请人或出质人国债账户市值与资金账户余额之和在质押期间不低于1900 万元。”法院在此援引原《合同法》第125 条(《民法典》第466 条),结合承诺鉴证书中所使用的词句、签约目的以及证券市场交易习惯等进行论证,认为不宜将承诺鉴证书定性为担保性质,也不宜将承诺鉴证书第2 条解释为花园路证券营业部负有保证责任。〔6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二终字第44 号民事判决书。又如,“福州休曼电脑有限公司及福建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福建省体育局合作合同纠纷案”判决在解释案涉《会议纪要》第2 条关于投资返还是依照休曼公司投资的原值返还,还是按照该投资在合同终止时的价值返还的规定,以及第4 条关于“以发行总额的5%作为投资成本返还先锋集团进行结算,为明年买断关系作准备”的规定时,依据的实际上也是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关于合同解释的规范。〔6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160 号民事判决书。类似案件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938 号民事判决书。
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还可以适用于确立义务,包括附随义务和后合同义务等。例如,在“中商华联科贸有限公司与昌邑琨福纺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根据原《合同法》第60条(《民法典》第509 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而琨福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未尽相应的通知、协助等义务,具有一定过错,应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确定责任承担。〔6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38号民事判决书。类似案件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458号民事判决书。又如,在委托合同终止后,受托人应当履行协助委托人处置股权和领取分红款的义务。〔6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二终字第63 号民事判决书。
可以从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中解释出附随义务,并不意味着相对方未履行附随义务即应当负主要责任,而是应分析哪一方先具有过错或过失行为。例如,在“北京康正恒信担保有限公司与河北天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夏建龙矿业科技有限公司、河北省矾山磷矿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虽然原《合同法》第60 条是合同附随义务的法律依据,但在案涉《协议书》对拟收购方如何知晓矾山磷矿新公司注册成立时间从而作出约定的选择权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首先构成拟收购方及时跟进并了解的注意义务,而非构成拟转让方对相对方主动通知的附随法律义务。拟收购方中油公司漠视、怠于既是权利又是义务的注意的行为导致康正公司无法按照《协议书》约定选择收购、参股投资新公司,只能被视为自动弃权的行为。在此情况下错过了选择权,过错责任首先在于拟收购方自己,而不在于拟转让方是否存在通知的附随义务。以拟转让方没有主动履行告知拟收购方关于新公司成立时间否认拟收购方漠视自己应尽的主动注意义务、怠于行使权利的行为,不仅有违事实,也不符合诚信原则。〔6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二终字第44 号民事判决书。
此外,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还可作为订立合同中的行为标准。《民法典》第500 条第2 项规定的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属于民事欺诈行为,造成对方损失的,行为人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例如,在“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宝安路证券营业部与中国工商银行郑州市经三路支行、河南省龙浩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龙浩世纪实业有限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深圳龙浩公司分别与河南龙浩公司、宝安路营业部签订约定有融资和担保内容的协议,深圳龙浩公司为该案所融资金的约定用资人,因此对其证券账户中没有国债是明知的,其为达到融资目的,向经三路工行实施了民事欺诈行为。深圳龙浩公司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违背了诚信原则,故意提供虚假情况,致使经三路工行的质押权利落空,应当对其因此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6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二终字第75 号民事判决书。类似案件参见最高人民法院(1997)经终字第11 号民事判决书。
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还可规制特别结合关系领域中的自相矛盾行为。〔67〕自相矛盾行为和权利失效(Verwirkung)属于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重叠之处,为规范两者的区分适用,仍应以是否存在特别结合关系作为界分标准。当事人在合同纠纷中就某项合同条款的内容或是否适用问题,以其表示或行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创设一种事实或权利状况,相对人因此产生合理信赖,行为人事后作出与先前行为相反的表示或行为,构成自相矛盾的行为。〔68〕Vgl.Medicus/Larenz, Schuldrecht Allgemeiner Teil , 20.Aufl., 2012, Rn.149.例如,在“长沙金霞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长沙市先锋支行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金霞公司在合同中承诺为金帆公司“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并未对金帆公司的借款用途加以限制,但在诉讼中又提出不同意借款人将借款用于偿还债务有违诚信原则。〔6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二终字第33 号民事判决书。
权利失效(Verwirkung)是一种特殊的自相矛盾行为,权利人长时间不行使权利,相对人因此产生合理信赖并认为权利人不会再行使权利,嗣后权利人再行行使权利对相对人而言是过分的,即构成权利失效。〔70〕参见王洪亮:《债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86 页。例如,在“王秀群、武汉天九工贸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在交易过程中,王秀群、天九公司未主张《11.56 亿股权转让协议》失效以及收取了农产品公司支付的可换股票据、现金和承付票据等行为说明双方并无适用所约定之合同解除条款解除协议的意向。此后,王秀群、天九公司又以该合同解除条款主张协议失效,有违诚信原则,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7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677 号民事判决书。
3.作为法律修正工具的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在“新疆华诚安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案”〔7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347 号民事判决书。中以诚信原则修正合同无效规则,为作为法律修正工具的诚信原则之适用作了典型展示。作为招标人的华诚公司试图从自己先前的错误行为中获利,明知合同违法无效仍签订、嗣后又主张合同无效的行为应受背信评价,否则将鼓励此种行为。若严格适用具体规则会产生无效的结果,将极大损害诚信原则,造成个案极端的不公平。〔73〕参见于飞:《诚信原则修正功能的个案运用——以最高人民法院“华诚案”判决为分析对象》,载《法学研究》2022 年第2 期,第66-67 页。在具体适用时,应当遵循“查明严格适用具体规则是否会产生极端不正义的结果→查明规则的立法目的并确认目的性限缩在此无法适用→引入诚信原则的要素进行重新论证权衡→经由诚信原则修正具体规则而产生个案限制性规范”的步骤谨慎地适用作为法律修正工具的诚信原则,以矫正严格适用具体规则所产生的个案不公正之后果。
此外,诚信原则对合同的修正也可以纳入作为法律修正工具的诚信原则适用之特殊情形,因两者均是以“公平正义”作为背后实质的考量标准。如《民法典》第533 条情势变更规则以及《民法典》第585 条、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9 条关于合同违约金调整的规定均属此例。据此,在合同交易基础出现障碍时,直接援引情势变更规则即可。此后出现与合同有关的新问题时,立法者倘若不能及时从现有规定中觅得妥切的实定法规范,便可以诚信原则作为法律修正工具,经充分论证制定出新的具体规则以适应司法实践的变化,维护公平正义。
针对合同违约金的调整问题,根据《民法典》第584、585 条以及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9 条,违约金制度系以赔偿非违约方的损失为主要功能,而不是旨在严厉惩罚违约方。如果任由当事人约定过高的违约金且以意思自治为由予以支持,在有些情况下无异于鼓励当事人通过不正当的方式取得暴利,也可能促使一方为取得高额违约金而故意引诱对方违约。据此,法院可以对不合理的违约金数额进行调整,以维护民法的公平和诚信原则,并使违约方从高额且不合理的违约金责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7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二终字第125 号民事判决书。例如,在“宁波兴合货柜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依据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9 条第1 款、第2 款,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所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原《合同法》第114 条第2 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兴合公司擅自转租构成违约,东港公司有权依约行使解除权,兴合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而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明显高于实际损失,法院判决依法酌情予以调整。〔7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202 号民事判决书。类似案件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59 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261 号、民终446 号、民终686 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839 号民事判决书。又如,在“上海同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远东电缆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亦从实际损失及可得利益两方面审查,经充分论证后适用前述条文进行裁判。〔7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二终字第55 号民事判决书。
五、结语
我国民法诚信原则作为禁止权利滥用的上位原则,其内涵不仅有“诚实信用”,还包括“禁止权利滥用”以及“公平正义”,分别对应于具有不同内涵和功能的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以及作为法律修正工具的诚信原则。三种诚信原则在适用场域、适用标准上均有所不同,对不同功能诚信原则的适用标准进行区分适用极为必要。在实质适用标准上,即便仅以“诚信原则”作为统一的裁判依据,仍应结合不同情形对诚信原则的适用标准作出区分。应当注意避免在应适用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时错误地适用要求更高的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以免增加当事人不必要的行为负担。
此外,在法律修正功能的适用上,应当结合不同部门法的教义学体系选择适用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抑或诚信原则以发挥这一功能。在民法的一些特别私法领域,如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仅规定诚信原则的实定法中,为确保法官有据可依,可暂以诚信原则之名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之实。这一类型化适用标准的区分对于其他部门法的实践也颇为重要。例如,在判断“知假买假”是否有违诚信原则时,应当明确“知假买假”并不属于特别结合关系场域,在此诚信原则仅有禁止权利滥用或法律修正功能的评价标准。只有类型化区分适用诚信原则方可确保个案的公平正义,对不同类型诚信原则的适用要求不同的论证理由,如此亦可避免向一般条款逃逸的司法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