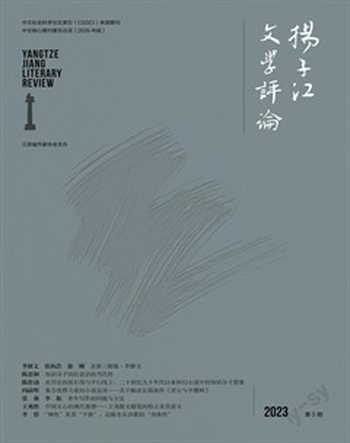拨开历史的褶皱
田振华
历史散文具有“宏大与磅礴的生命力,历史的融入某种程度上挽救了散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散文不再局限于过于狭小的格局,走向一种恢弘与大气”a。历史散文的写作需要作家具备更为开阔的胸怀和包容的心态。夏坚勇就是一位能够持续深耕于历史散文创作并取得卓越成就的作家。从20世纪90年代凭借《湮没的辉煌》走红,到新世纪初《旷世风华——大运河传》问世,再到近年来“宋史三部曲”之《绍兴十二年》 《庆历四年秋》的出现,夏坚勇用自己独有的方式诠释着长篇历史散文写作的诸多可能性。近期,他又完成了“宋史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东京梦寻录》b,继续在历史细节的褶皱里展开丰富的想象和深度的思考,在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的巧妙融合中彰显了他驾驭长篇历史散文的高超能力。
“宋史三部曲”以近百万字的洋洋巨著,徜徉于宋代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伦理、风俗和信仰等诸多层面,给读者呈现了一个立体的、饱满的、真实的而又颇具诗性的宋代社会历史画卷。作品融可读性、丰富性、文化性和批判性于一体。面对丰富驳杂的历史素材,作者夏坚勇并没有面面俱到,而是采用截取历史横断面的方式,透过宋史中重要年份重要历史事件的书写,辅以适当的延伸,巧妙地将宋代的历史文化和内在肌理呈现出来。《绍兴十二年》围绕着读者耳熟能详的民族英雄岳飞被杀事件写起,展现了民族英雄被迫害的来龙去脉,表达了作者的惋惜之情及其对皇帝不识真才、昏庸无度的批判和反思。《庆历四年秋》重点书写的是庆历新政期间文人官员命运起伏的点点滴滴,以及他们面对历史的无奈和惆怅。到了《东京梦寻录》,作者在时间上继续向前追溯,讲述了宋真宗从登基到登基之后,多次举行“天书”封祀运动与大兴土木的故事。作者对每一次封祀的过程都进行了充分展现:从人为制造“天降天书”到封祀前群臣虚假的请愿,从封祀过程中的各类仪式和细节到封祀后的大兴土木和供奉天书,最后到真宗去世后天书灰飞烟灭,作者都如穿针引线般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因果缘由。作品通过一次次封祀的细节呈现,展现了官家和群臣极度虚伪造作的一面和历史人物真实的人性。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每一部作品中,并不是对历史事件和素材的简单陈述或梳理,而是用历史的眼光捕捉那些饱含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元素,同时面对千余年前的历史,作者站在当下性的视角,以冷静和客观的态度予以审视,呈现出作者对历史的追问、反思和批判,追求“思想和言说的快感”c。作者试图拨开历史的褶皱,呈现历史中被遮蔽和被遗忘的一面。作品在历史理性、审美诗性和反思智性的呈现中,彰显了作者试图拨开历史褶皱的努力以及弥补历史结构完整性的决心。
一、历史理性:素材的甄别及其与历史学家的对话
长篇历史散文创作如何面对历史,也许是作家创作首先要思考的问题之一。历史纷繁复杂、林林总总,作家们既无法做到对自己所关注的历史面面俱到,也不能对那些没有文学价值意义的历史喋喋不休。这就对作家选取和甄别历史素材的能力提出了考验。这看似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实则需要作家具备较好的专业知识和敏锐的判断能力。作家们需要以理性的眼光,甄别出那些反映历史真现实、真问题的素材,同时对这样的素材加之文学上的处理和思想上的提升。这首先需要作家具备历史理性。所谓历史理性,“就是探究历史过程的所以然或道理和探究历史研究过程的所以然或道理”d。作家既不能对自我推崇的历史和人物进行肆意拔高,又不能对自我厌恶的历史或人物过度贬低。特别是在历史散文这一文体中,虽然作家可以进行适度想象性的创作,但是这种创作依然要在遵循历史基本真实的基础之上来进行。在《东京梦寻录》中,作者敏锐地发现了真宗“天书”封祀运动这一既真实而又荒诞无比的故事。之所以说真实,是因为这些事件确实是历史中真实发生过的;之所以说荒诞,是因为在今天看来,整个事件充满了戏谑和讽刺元素。历史的真实性让作品具有了充足的说服力,这一真实所带有的荒诞又成为文学最好的素材。在此基础上,作者既避免了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娱乐主义,又做到了历史与文学的适度调和,以此增强了作品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那么,作者是如何做到以历史理性的方式架构长篇历史散文的呢?一方面,作者在素材选取上,选择的是自我擅长和熟知的历史细节来展开书写;另一方面,作者做到了以理性的方式与历史学家对话。
夏坚勇在创作谈中说道:“在历史写作中,即使面对着同样的题材,分道扬镳的想象力也会使每个作家的作品因其独特的禀赋而具有鲜明的‘私人写作的质地,这就是所谓的辨识度……关于《承天门之灾》,当初其实就是《宋史·真宗本纪》结语中的一句话触动了我。”e也就是说,正是宋史中的真实事件,触动了夏坚勇的心弦,让他选择这样一段历史来展开书写。这说明作者对宋史的精准把握和选取,是建立在自我对宋史熟知的基础之上的。在《东京梦寻录》中,作者对宋史中上到王公贵族、君臣关系,下到饮食起居、日常礼仪等都可谓是信手拈来、掌控自如,这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达成历史理性的重要基础。作家对历史真实的书写,不仅体现在对历史大事件的呈现上,更体现在对历史细节真实的展现上。在《东京梦寻录》中,作者除了对封祀前的准备、封祀中的活动进行了细节的呈现,还在事件背后穿插书写了宋代的日常饮食起居和繁琐的礼仪文化。如作者在“解语杯”这一小节中,就对朝廷中的宴会进行了详尽的书写。作者对宴会中使用的器皿、呈上的酒类和菜系及其使用过程中的礼仪规范等的书写,都可以看出宋代日常文化礼仪的丰富和繁琐。作者将官家举行宴会的真正目的揭示出来,特别是在赐给宰相王旦的“解语杯”中加一壇珠宝这一细节上,明显可以看出官家对王旦的信任和依赖,群臣关系和交往的细节就在这宴饮期间揭示出来。此外,封禅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期间发生了诸多历史书中不曾或少有记载的细节:真宗登基后不久和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为宋朝争取了一段时间的和平,太平盛世滋生了真宗封祀的私心。但是真宗知道,“封禅这样的大典,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需要得到天瑞”f。于是,封禅过程就在群臣不断逢迎而真宗不断拒绝间展开了虚伪的博弈,最后营造的表象是真宗在群臣不断逢迎中不得已才同意了封禅。真宗要将这种封禅先制造成天意,再编造为民意。作者就通过对封禅过程中的细节呈现,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书中看不到的元素。这些都可以看出,作者甄别历史素材和驾驭历史细节的能力,只有那些真实的细节才是最感人的、最能令人信服的。
与历史学家的对话,是夏坚勇长篇历史散文彰显历史理性的重要特征,从作品每一章最后的诸多引用文献就可见一斑。文学与历史有着重要的区别:历史学家重点呈现的是历史的结果,文学家則侧重呈现历史的过程;历史学家侧重从历史必然性的规律中总结结果,文学家则试图从诸多方面推断历史的可能性。当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也有共性:历史学家对历史结果的判定,需要他们通过对史料的考据和挖掘不断地修正和调整;文学家在长篇历史散文的书写中,在对历史细节和过程的把握中,透过文化、情感和人性的视角,有时候就自觉不自觉地承担了修正和调整历史结果的任务。在《东京梦寻录》中,作者就多次通过商榷的方式实现了与历史学家的对话。如宋代史学家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六十八卷中曾记载,宋真宗北上亲征时,留守东京的王旦问如有不测该当如何,真宗的回答是“立皇太子”。作者夏坚勇就通过时间上的推算指出了其中的问题:“因为官家当时尚无子嗣,所谓立皇太子根本无从说起。”g夏坚勇认为这“是史家在这里做了手脚”h。再如作者还对史书中记载四月一日大内皇宫再次发现天书事件的遮遮掩掩进行揭示。作者认为这种遮掩很不正常,虽然这一事件至今仍旧没有定论,但作者根据蛛丝马迹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这无疑增加了读者认识历史真实的可能性。在这里,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作者在书写作品前所作的精心准备,没有前期大量的阅读和积累是无法与历史学家进行商榷和对话的;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作者眼光的独到和判断能力的突出;还可以看出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充分利用历史素材而又不拘泥于历史素材的高明之处。
二、审美诗性:长篇历史散文的重要标识
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i长篇历史散文的写作需要遵循历史理性,但更要强调其文学性或者诗性。长篇历史散文对历史事件和素材的选取固然重要,但是如何处理这些事件和素材,则是长篇历史散文创作的重中之重。可以说,能否处理好长篇历史散文“史”与“诗”的关系,是判断一部作品质量高低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长篇历史散文首先是散文,是一种侧重精神传达和情感抒发的文体。长篇历史散文有着自我独特的文体特征和要求。因篇幅长、信息量大等特点,长篇历史散文同样需要在结构、人物塑造和语言上下功夫。在《东京梦寻录》中,历史素材成为夏坚勇建构文学想象的翅膀,他“合情合理地再造逻辑使历史有了想象与虚构的成分,历史真实被阐释为意义的真实”j。具体而言,首先,虽然作者是有意识地截取宋史横断面进行创作,但在这一横断面上,作者并不是平铺直叙地将故事讲述出来,而是着力呈现长篇历史散文的内在结构;其次,作者对宋代人物的塑造着力颇多,特别是在塑造宋真宗这一历史人物时,作者力图把历史人物当作“人”来写,写出了历史人物的丰富和立体;再次,作者的语言特色明显,呈现出长篇历史散文语言所具有的历史感和文化感。这些都彰显了夏坚勇长篇历史散文创作的审美诗性,这些审美诗性也成为长篇历史散文的重要标识。
如何处理散文之散与结构之整之间的关系,是长篇历史散文创作的一大难题。如果过于强调散文的结构之整,很容易将散文小说化,如果不注重结构的呈现,长篇历史散文就容易流于芜杂。相较于中短篇散文而言,长篇散文还是要在结构上下一定的功夫。在《东京梦寻录》中,作者就在尊重散文文体特点的基础上,内嵌了多层次的结构。一是从时间上来看,总体上是以顺序的方式呈现了事件发展的进程,中间也零星夹杂着闪回、跳跃来弥补事件的可靠性;二是从空间上来看,基本上是围绕着东京至三次封祀活动所在地“泰山”“汾阴”“亳州”及其之间的往返来进行;三是从人物命运轨迹来看,作品围绕着宋真宗赵恒命运发展的轨迹“因缘巧合登基——被迫北征——三次封祀活动——国运衰败——因病死亡”来运行。三种结构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相互交织,共同融汇成一个多元立体的宋朝历史政治文化景观。此外,作者在结构编排的过程中,有序而合理地穿插着宋朝的朝纲纪要、君臣交往、礼仪规范乃至生活日常。在保持大的结构规整性的同时,将宋代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伦理等融入其中,构成了一个宋代官场版的“清明上河图”。这就恰到好处地处理了散文之散和结构之整之间的内在关联,写出了长篇历史散文的整体性和饱满度,增强了长篇历史散文的系统性和可读性。
把历史人物当作真正的“人”来写,是夏坚勇长篇历史散文的重要表现。传统的历史书写中,那些帝王将相、王公贵族往往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存在,历史人物的内在性格往往被历史的宏大事件所遮蔽,其内在的、细微的属于自我个体的人性往往不容易表现出来,这就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性。实际上,在“宋史三部曲”中,夏坚勇始终坚守着将历史人物当作“人”来写这一信条。在《绍兴十二年》中,作者在岳飞被杀事件的前后,重点书写了包括岳飞、秦桧及多位皇帝性格生成和发展的历程,写出了岳飞被害的来龙去脉及其不屈不挠精神的具体表现。在《庆历四年秋》中,庆历新政背后的富弼、韩琦、欧阳修、苏舜钦、蔡襄、王洙、王益柔、晏殊等人物形象饱满而立体,他们的命运走向和最终归处,既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现实状况有关,又与他们的内在性格相连。在《东京梦寻录》中,作者借助具体事件,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交织叙述中,塑造了“万人之上”的宋真宗内在性格中阴险、自卑、虚伪的一面。本质上来讲,历史一定是必然性与偶然性共存的。但史书往往更为注重历史的必然性,而忽略历史的偶然性。作者夏坚勇说道:“国事家事天下事,这一系列变故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赵恒,陈桥兵变,一夜之间让赵氏取代柴氏成了国姓;烛影斧声,一桩谜案让老爸赵光义成了大宋王朝的第二代君主;煮豆燃萁,对德昭兄弟和廷美的迫害则保证了皇位将由太宗的子孙世代传承。”k宋真宗就是在这种偶然与必然的交织中走上了高位。作者用颇多笔墨写出了真宗阴险的一面,如关于真宗上位就写道:他“采用的是钝刀子割肉的方法,慢条斯理,不慌不忙,一边又有足够的机会表演自己的假仁假义”l。此外,作者还写出了真宗性格上的弱点,指出了真宗生性自卑,迫不得已之下甚至还会讨好宰相臣民等。在几次封祀活动中,作者写出了真宗极度虚伪的一面:真宗向往封禅,却在臣民的多次蓄意恭逢中欲拒还迎,等等。作者将真宗皇帝作为“人”的七情六欲挖掘出来,而这都体现了真宗性格中的复杂性和真实性。在作者笔下,真宗有着历史人物的共性,更有着人之为人的个性。
夏坚勇长篇历史散文审美诗性传达的第三个表现,就是在作品中对艺术性的坚守和文学语言的用功。作品的开篇,作者从雪景写起,表面上营造了一个诗意的氛围,但紧接着说到景德四年冬的第一場雪并没有“兆丰年”的意思。作者有意将第一章命名为“瑞雪兆‘疯年”m,给作品接下来的讲述奠定了基调。在作品的结尾,作者写到官家为供奉天书建造的昭应宫连同三封天书毁于天火,这同样达成了一种讽刺效果。此外,作者用第一人称展开叙事,作品中时不时出现“我”的身影,这种叙事方式,在拉近读者与作者关系的同时,也增强了作品讲述内容的通俗性和可靠性。在语言方面,作者做到了口语与书面语的巧妙融合。从口语来看,作者化用了传统说书的方式,巧妙地穿插讲述了宋代历史中的故事。虽然作者摒弃了“请听下回分解”等传统说书形式,但在具体的讲述中,说书具有的通俗性、亲和力的语言随处可见。读者阅读这部作品,就像作者站在舞台中间将作品说了一遍一样。从书面语来看,作者在尊重现代语言规范的同时,大量引用了古籍文献,保证了历史叙事的真实性。作者在这种口语与书面语的混合使用中,就恰到好处地达成了历史书写的通俗性与严谨性的统一。此外,在具体的行文过程中,语言也颇具意味。如整部作品明显表达了作家对真宗及群臣行为的批判,在具体的语言上,作者就有意识的使用了带有讽刺性、隐喻性的语言。这种有意味的语言,恰到好处地传递出作者的创作初衷,同时契合了作品主旨表达的需要。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写到君臣交往、宫廷礼仪、风俗文化时,有意无意将那些具有宋代标识的语言运用到作品中,这是作者精通宋代历史文化的直接表现。“语言(language)区分了不同的民族;人只要一开口,就会显示出他来自何处。”n作者对具有宋代标识的语言的使用,让我们真正看到了宋代上层文化和市井文化的独特。这成为作者对宋代历史文化书写的一种重要手段。正如作家张炜所言:“语言在许多时候简直可以看作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语言差不多就是一切,一切都包含在语言中。”o
三、反思智性:传统文化反思与“大历史观”的呈现
长篇历史散文除对历史的理性思考及其文学表达外,还应该具备一种思想的力量,即呈现散文的精神高度,书写散文的“力”与“重”。“散文如果没有了纵深和厚度,那么阔大和厚重也就不可能实现。”p作家面对历史,总会有意无意间渗入自我精神价值和个体观念。“这种从事实到思想的转换,需要的也许正是‘历史理解,以及如何‘给予历史一种意义。”q实际上,作家对历史的书写,其最终目的就是借助历史这一媒介,传递自我现实的思想与精神。甚至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对历史的追溯主旨其实在于建构现实合理性”r。长篇历史散文的书写更是如此。夏坚勇能够耗费十余载,用近百万字对宋史持续深耕,必定有着对宋代历史和文化的深度省思。宋代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个重文轻武、市井发达的社会,何以会出现“宋史三部曲”中书写的那些问题,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反思。此外,一个朝代人物性格的生成与这个朝代的文化氛围有着直接的关联。“宋史三部曲”中,宋代文化背景下的皇帝、宰相、群臣等各色人物的命运,都与宋代文化乃至中华文化有着直接的关联。实际上,作者对宋代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的批判性书写,是借此实现对以宋代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下性反思,在这种反思的背后又呈现了作者通过长篇历史散文传递“大历史观”的尝试。
传统中国是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层级明确的伦理关系支撑了中国自古以来、自上而下的稳定性,但这种伦理关系也滋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在《东京梦寻录》中,作者对宋真宗时期政治和文化伦理的批判尖锐而直接。这种批判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对真宗皇帝个人上位过程中的不择手段、机关算尽的批判。作者不无尖锐地说道:“这个从皇侄到皇子再到皇帝的幸运儿是如何丧心病狂地折腾满朝文武和天下苍生的,他导演的那一幕幕荒唐的闹剧,即使不能说后无来者,也肯定是前无古人的。”s重要的是,真宗在经历了“澶渊之盟”后十年短暂的繁荣,很快就滋生了虚荣心。这既是人性的一种表现,也是我们所俗称的“富不过三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现实变体。二是对这一时期君臣之间的政治伦理关系的批判,君与臣之间的相互利用、尔虞我诈,臣与臣之间的相互倾轧、斗争等,在宋真宗时期可谓比比皆是。他们往往为了升官、上位、得利等采用一些阴险狡诈之手段,有些甚至是以牺牲他者生命为代价。还有诸多的细节书写,如官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奢靡之风、封建迷信等,也都体现了作者的批判性眼光。实际上,以上的诸多问题,或许在各个朝代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展现,只是在真宗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这或多或少与中华传统君臣伦理有着直接关联。中华传统文化伦理中有着很多优良元素,但同样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中华传统文化存在着两面性,需要我们正确辩证地看待。作者以勾陈的方式拨开历史的褶皱,给了我们重新发现和再审视中华传统文化伦理的可能。作家对历史的回顾,特别是对历史褶皱的细节呈现,更能够发现历史和传统中真正的中华文化精神。作家对中华传统文化伦理的书写和反思,同样有着极为重要的当下现实意义。作家对历史的回顾不仅仅指向过去,更是面向未来的别样途径。历史书写为当下和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经验的和精神的参照。
作者借由历史和传统伦理文化的书写,向我们传递了一种具有当下视野的新的“大历史观”。这种“大历史观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来分析和把握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过程,从横向的空间视野来审视和把握该历史事件和与之相联系的不同地区和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总体史的视角来研究和把握历史事件在其所处的综合网络中的历史坐标,从而得出客观、科学的结论”t。在《东京梦寻录》中,作者在大历史书写的过程中,借助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对历史细节的打捞,同时借助散文抒情的方式呈现了文学意义上的新的“大历史观”。这种大历史观实现了“史”与“传”、感性与理性、宏观与微观、官方与民间等的巧妙结合,“实现了中国古典王朝的恢弘气象与鲜活肌理在历史散文中的融会与统一”u。这为我们重新认识历史提供了文学上的参照。
作为“宋史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东京梦寻录》既做到了对《绍兴十二年》 《庆历四年秋》所具有的创作观念、方法和技巧上的延续,同时又有了一定的突破。除了更为扎实的史学功底和更为精妙的历史细节的呈现外,《东京梦寻录》明显写得更加从容和得心应手。归根结底来看,这是作者的散文创作愈发成熟、站位愈高的体现。“文化散文作家的站位,决定了他的视野,决定了他审视的维度,也决定了他精神的自由向度。”v夏坚勇巧妙达成了长篇历史散文所具有的“长度”“历史理性”和“散文诗性”“反思智性”之间的内在调和。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东京梦寻录》中,无论是作品体现出的长篇历史散文的历史理性、审美诗性还是反思智性,背后都有一个或隐或现的主体“我”的存在。正如谢有顺所言:“历史必须是无论如何和‘我有关的历史,生命也必须是‘我所体验到的生命——写作就是不断地把客观化的历史和现实,变成个体的历史和现实,只有这样的写作,才有望成为‘生命的学问。历史和现实往往就衔接在个体的生命节点上,写作就是要不断地捕捉这个生命的节点,并书写出在这个节点上的心事和感受。”w“我”与历史的关系实际上就构成了当下与历史的关系。“历史的肌理常常在那些散落的、被忽略的细节中”x,以史为鉴才能更好地面对现实,面向未来。“历史是个人对过往事件情感态度的一种表达策略,是现代人精神状态的一种载体。”y也就是说,夏坚勇总是能够拨开历史的褶皱,以文学的方式完成自我的审美表达和价值判断。在今天这样一个思想相对匮乏的时代,夏坚勇对历史辩证地、批判性地书写显得尤为珍贵,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文化调和”的作用。可以说,他的《东京梦寻录》是当下不可多得的优秀长篇历史散文力作。
【注释】
ajy马小敏:《从史实到哲思:历史散文中的真实祛魅》,《当代文坛》2013年第4期。
b发表时题为《承天门之灾》,《钟山》2021年第6期,出版时更名为《东京梦寻录》,译林出版社2023年版。
c蔡翔:《文体爱好者》,《小说评论》2023年第4期。
d刘家和:《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
e夏坚勇:《关于历史写作中的想象》,《钟山》微信公众号,2021年12月8日。
fghklms夏坚勇:《东京梦寻录》,译林出版社2023年版,第46页、31页、31页、18页、14页、1页、11页。
i[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詩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1页。
n[法]让·雅克·卢梭:《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摹仿》,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o张炜:《小说坊八讲》,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p赵普光:《历史文化散文:如何“历史”,怎样“文化”——从夏坚勇〈庆历四年秋〉谈起》,《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3期。
qw谢有顺:《散文中的心事》,海峡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94页、200页。
r罗小凤:《“历史”的另一种言说方式——论李敬泽散文对历史的“修补”》,《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1期。
t路宽:《大历史观的理论内涵与思想价值》,《科学社会主义》2021年第1期。
u汪雨萌:《气象与肌理——浅论夏坚勇的历史散文》,《当代文坛》2023年第3期。
v王志清:《灵魂之舞的自由维度——王充闾的历史散文与散文观研究》,《南方文坛》2008年第5期。
x王尧:《我只想做一个写作者》,《小说评论》2022年第3期。